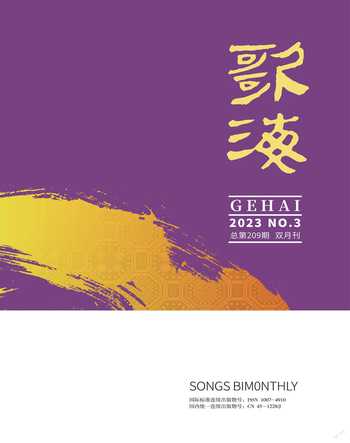集體記憶視角下的村落廟會研究
何茜
[摘 要]廟會是村落社會生活中最大的一場集體狂歡性節日,廟會的周期性正是村落生活“日常”與“非常”兩種交替節律的體現。依附在廟會走親儀式中的神親關系是山西鄉土社會一種常見的存在,神親關系的維系不僅依賴于村落間存在的地理位置、商貿往來,還要靠村際間的廟會交往、村落廟會傳說。神親關系對維護地方社會穩定、地域民眾文化認同有重要意義。年復一年的廟會活動通過群體聚集的場景間接地激發民眾的共同回憶,不斷建構著村落間的集體記憶,同時,地域認同在集體記憶的作用下被進一步強化。村落間聯合舉辦的廟會作為地方社會不同村落間共同的文化象征,對構建地方社會關系有著重要意義。
版本一、二主要在兩地民眾中廣泛流傳,這兩個版本中主要故事情節都是“女子因不滿意自己的婚姻而痛苦流淚”、因“流淚”感化了“上天”而導致下雨。在民眾的傳說中沒有時間,沒有人物姓氏,只有兩個簡單的地名,就好像發生在不久前。版本三是地方文化愛好者通過搜集民間流傳的各個版本編修而成,通過村史村志的方式傳播,故事情節更加完善,人物有了具體姓氏,通過這個版本我們可以得知西王、苗峪兩村落在幾百年前就有商貿往來。同時,隨著地方村史村志的修編,版本三在民眾中逐漸樹立起自己的權威地位,在訪談中,村民們多次提出“去問王某某,因為他講得清楚”。在過去靠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通過地方文化精英的書寫被文本化并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地位,這本質上說明“權力話語”在集體記憶的塑造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同時,“三仙姑”有求必應,祈雨靈驗的傳說在方圓百里廣為流傳。近年來,有村民祈求兒子考上大學,如愿后前來還愿的,也有西王村全體36歲的男女青年捐款給姑姑唱戲的活動。對“三仙姑”的信仰從祈雨到升學求官再到祈求保佑平安,幾百年來,在不斷演變中豐富和發展著,她的信眾也從以苗峪、西王為中心的村落擴展到灣里、朝峰、東坡、通化、七郎廟、光華、東王、常村、東關、鄧村、賈朱等周圍十多個村落,從而形成一個圍繞西王村和苗峪村的信仰圈。在民間,通過“三仙姑”傳說的口耳相傳,反復講述,其信仰和禁忌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不斷穩固著村民的信仰和禁忌。作為村落記憶的傳說,是村落的口述史,以口耳相傳、文字記錄的方式為村落成員的自我認同提供了基礎,對“三仙姑”的記憶代代相傳成為村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仙姑”愛憎分明、扶弱濟貧、懲惡揚善形象的塑造是民眾對歷史記憶的再加工,是民眾樸素價值觀的體現,有求必應、對抗干旱的超能力更是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渴望。關于“三姑姑”祈雨靈驗、求學升官靈驗、保平安靈驗等傳說在幾百年的流傳中被不斷地建構與重建,在不斷的重現過程中或被增添、或被修改,不斷改變著其存在的外在形式并建構起新的意義。
二、為農祈雨:村際神親關系傳承發展的內在動力
苗峪村位于豁都峪深處,據《道光太平縣志》《光緒太平縣志》記載,自明嘉靖十一年(1532)至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近三百年間該區域共發生大旱十九次,平均每一百年發生六次大旱(統計如下表)。
干旱在西王、苗峪一帶頻發,在傳統農耕社會,農業生產方式落后,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有限,旱災對于依靠農業生存的村落來說是致命的威脅。西王、苗峪兩村落物產貧乏,過去主要靠發展農業為生,這就使得靠天吃飯、共同對抗自然災害(干旱),向神靈“祈雨”,春祈秋報,祈求風調雨順、農業豐收成為兩個村落共同的需求,也是兩個村落間村際神親關系傳承發展的內在動力。在當地,“三仙姑”又被稱為“水母娘娘”,“兩村都成立了民間民俗會,只要遇到旱情,兩村民眾都打著龍旗,舞者用柳枝編的大龍一條,小龍多條,人們頭戴柳條帽,身著柳條衣,腳穿柳條鞋,敲鑼打鼓,鐵炮齊鳴,接送‘三姑姑”。“三仙姑”往往有求必應,在方圓數百里廣為流傳,聽長者說,“多次把‘三姑姑從苗峪抬到西王村口或從西王村抬到苗峪村口,當時是晴空萬里,頓時烏云滾滾,電閃雷鳴,傾盆大雨,嘩嘩而下,峪里的洪水一流多天,實在是太靈了”。村際聯合共同對抗自然災害、排解對旱災的恐慌,有效地釋放了面對旱災的焦慮情緒,是民眾面對苦難的一種生存策略、一種心理寄托,同時通過祈雨儀式增強了村際成員間的內部凝聚力,形成社會群體的共同記憶,這種記憶通過祈雨儀式又得到進一步加強與鞏固。
三、走親習俗:村落集體記憶形成的重要形式
農歷正月初八,是西王村三仙姑廟會正日子,一大早,西王村100多人,十幾輛汽車,組成一個“接親”的隊伍,每輛汽車都披紅戴彩,每個人都身著紅裝或佩戴紅圍巾,在會首的組織下有秩序地前往苗峪村接上整裝待發的新娘子“姑姑”(三姑姑娘家為西王村,所以西王村稱呼“姑姑”;苗峪村是婆家,稱呼“娘娘”,兩村平常以“親家”相稱),之后回到西王村,在西王村舉行隆重的儀式。參加這一儀式的不僅有老人、小孩,還有中年男女,他們全部都是36歲同齡人,這一天在西王村舞臺舉行慶典大會,有歌舞團進行文藝演出,“三仙姑”將被邀同村民們一同“觀看演出”。演出完畢,“姑姑”塑像被安置在舞臺旁邊的圣母殿內,直到農歷七月初十前幾天(有時是六月農閑時),苗峪村村民到西王村迎回“娘娘”。苗峪村村民去迎“娘娘”時,西王村將會以“親戚”款待,并陪同苗峪村村民將“姑姑”塑像送到苗峪村,回到苗峪村,苗峪村村民同樣也會以“親戚”款待之,之后會唱三天共計七場大戲。據民眾回憶,每逢唱戲必下大雨,唱戲完畢,“姑姑”塑像被安置在苗峪村九江圣母殿內,之所以選擇在七月初十這天,是因為七月初十是“三姑姑”的生日,直至第二年正月初八再被接走,周而復始。其中每年八月十五前幾天,西王村村民都要去苗峪村接回“姑姑”,并在八月十五給“姑姑”唱戲七場,之后在西王圣母殿作短暫駐留,每年過年之前,因為當地有女子不能在娘家過年的說法,苗峪村村民都要前來再次迎回“娘娘”。
中國古代社會,女子出嫁后成為夫家成員,不能隨便離開夫家。女子回娘家須由娘家人去接,住一段時間后,再由婆家人迎回來,這種古老的歸寧習俗正是西王、苗峪兩村落間走親習俗產生的生活基礎。這種“走親”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民眾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是民眾日常生活中以血緣和姻緣為紐帶的交往模式的一種投射,是民間結婚儀式的真實反映。記憶是實踐的積累,走親活動有助于喚起村落群體的集體記憶,同時通過參與這一儀式,村落成員增強了彼此間的凝聚力,新的記憶又被塑造,走親儀式中人們身著紅色衣裳,抬著披紅掛彩的神像繞村,像是參加一場“神”與“神”之間的婚禮,世俗與神圣、“人”與“神”共處一個時空,給這一活動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參與儀式的表演者與觀眾共同置身于一個由走親儀式形塑的新的意義世界里,從人到神全部身著紅色衣裳,制造出一種不同于日常的強烈的喜慶感,男女老少在民間信仰的外衣下得以暫時突破日常的倫理約束,精神得以放松,這是“一種心理的解脫,一種心靈的松弛,一種壓迫被移除的快感”,通過這樣的走親活動,被壓抑的人性得到釋放。
四、廟會:村落集體記憶的強化
廟會是以神誕日或神忌日為依托,圍繞在廟周圍而發生的全民性具有固定時間的周期性的祭祀行為。長久以來,廟會活動作為人們一種周期性生活形式一直處于延續狀態,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生產生活方式單一,活動范圍有限,村際間的聯合廟會成為民眾突破地域藩籬、調節生活、休閑娛樂的有效手段之一。歷史上西王、苗峪兩村落每年都有正月初八、七月初十、八月十五三次廟會活動,其中七月初十的廟會最為熱鬧,這一活動持續幾百年不間斷。農歷七月初十是“三仙姑”的誕日,為給“三仙姑”祝壽,每年從這一天開始,苗峪村都要進行為期三至五天的廟會活動,在此期間有七場大戲,屆時,廟東側的大廣場上各路商販云集,人山人海,上至地方官員,下至平民百姓都來參加,鑼鼓喧天,戲聲悠遠,小孩、老人、年輕人,前來看戲的人絡繹不絕,苗峪坤元神宮殿的香火更是不斷。“鳴炮的、燒香的、磕頭的、獻花的、敬果的、捐款的成群結隊,香火十分旺盛。”
近些年,兩個村落間的廟會活動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以苗峪古廟為核心,不斷輻射到附近苗峪、東坡、灣里、通化、朝峰、七郎廟、光華等十多個村落,更有不少民眾開車從西王、古城、襄汾、臨汾前來觀看,廟會活動使得村落間得以打破地域的局限,體現出極強的全民參與性與空間開放性。這一活動不斷擴大的趨勢不僅僅體現在廟會的規模上,在重修廟宇的碑刻上也得到印證,且對這一現象做了合理“合法”的表述。在西王村1995年《重修圣母廟碑記》中這樣表述重修圣母廟的緣由:“原圣母殿毀于‘文革,為了繼承傳統文化遺產,進一步發展我村與苗峪人民的傳統友誼關系。”在這里關于圣母廟的供奉者(信眾)只提到西王、苗峪兩個村落,在修廟捐款名單中也只有兩個村落的信眾。而在2001年苗峪村《重修舞臺新建圣母殿碑記》中則這樣表述:“苗峪橋古廟位于鄂邑之東,豁都峪之內,歷史悠久,國之瑰寶,古系前后苗峪東坡灣里通化五村共有。”修復捐款名單中出現了除西王、苗峪兩個村落外的其他村落的民眾。傳統的廟會活動打破了村落間的地域限制與生活隔離,為地方民眾提供了一個廣闊的交往空間,從而滿足了人們對自身生活圈以外“他者”生活的好奇與交往需求。“三仙姑”信仰及廟會使西王、苗峪及附近村落得以凝聚在一起,通過共同捐款重修廟宇、協調組織舉辦廟會活動,密切村落間的聯系,加強了村落間的互動,有利于區域地方的和諧穩定,同時也推動了對地方文化的保護。
與過去單純的祈雨酬神唱戲不同,時下的廟會活動更多是為了娛人,不再是宗教集會,而是一場集市貿易活動。每年開廟之時,各路商販云集,各類物資無所不有。過去物資緊缺、交通不便,傳統的廟會在很長一段時期是村落民眾進行日常生活物資交流、實現貨品流通和購物消費的重要場所。廟會活動一方面是平日單調生活和辛苦勞作的調節器,另一方面“也是平日傳統禮教束縛下人們被壓抑心理的調節器”,生活在困頓中的人們內心的苦悶情緒借由廟會得以排解,廟會使得人們得以“打碎日常生活中各種身份地位的人為界限,使不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共同歡慶”,實現精神上的愉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不僅是底層社會民眾的一場精神盛宴,更是一場民眾得以脫離日常生活的集體狂歡。西王、苗峪兩村落每年通過正月初八、七月初十、八月十五這三個固定的時間節點,利用神靈間的姻緣關系建構兩個村落間的“親屬”關系,使得兩村落間保持日常生活的溝通與交流,“使個體聚集起來,加深個體之間的關系,使彼此更加親密”,將地方傳說與走親儀式結合,“能夠喚醒與強化民眾共同的歷史記憶,從而推動民眾認同的形成與地方文化的建構”。兩個村落間通過這種年復一年的模式重復和內容重復強化著人們的共同記憶,并在這樣的記憶強化下完成對村落地域文化的認同。
結語
西王、苗峪兩村落間年復一年的“走親”儀式和一年三次周期性的廟會活動不斷強化著苗峪、西王等村落間的地域認同和文化建構,傳達著地方民眾的生存智慧與文化邏輯,使隸屬于兩個不同行政區劃的村落能利用“走親”形式締結的村際神親關系和以“三姑姑”傳說、信仰為核心所形成的信仰圈來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訴求。同時,以“三姑姑”傳說和信仰為核心所形成的信仰圈進一步強化了地方文化認同。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傳統農耕社會血緣關系、宗族勢力日漸式微,這對構建地方社會和諧穩定和實現社會治理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在灌溉、人工降雨技術日趨成熟的今天,對抗自然災害(干旱)已然不再是兩個村落間的核心訴求,傳統的祭獻儀式性質被人民群眾新的心理訴求所取代,使得“走親”儀式得以幾百年如一日不斷地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