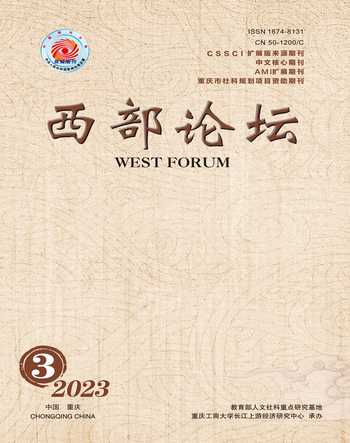數字經濟、個體能力與農民工工資差異
楊德利 周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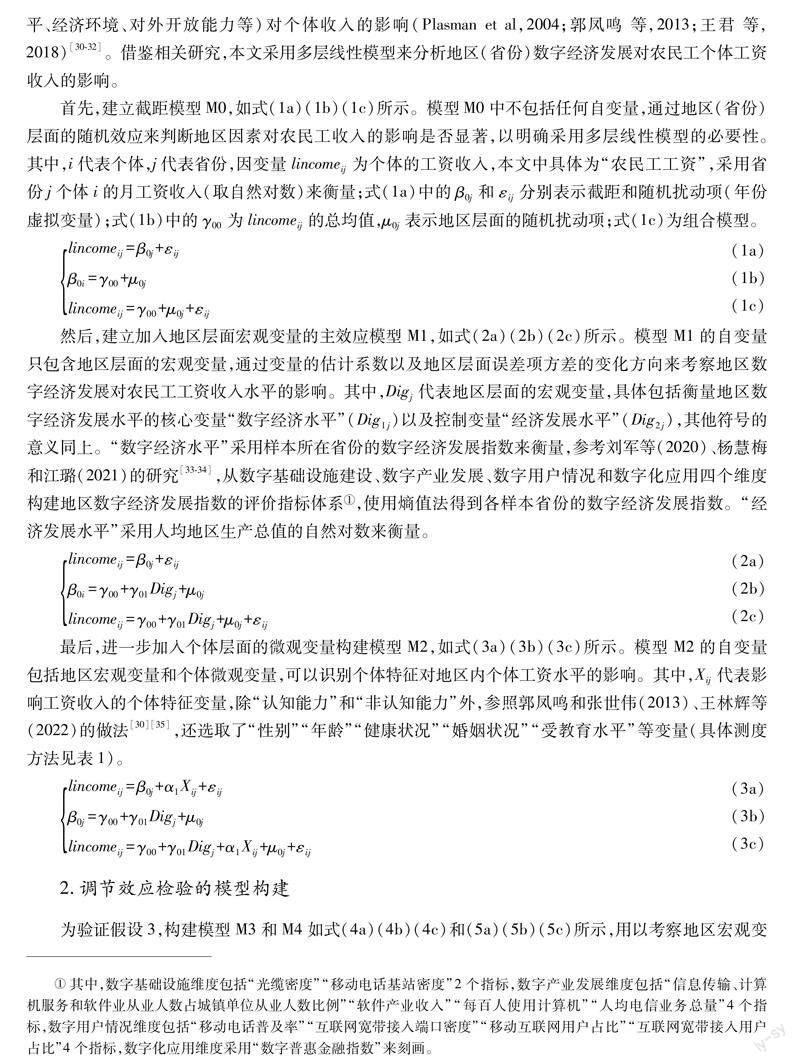


摘 要:數字經濟的技術偏向使其紅利產生群體偏向,從而通過個體能力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差異化影響形成并作用于群體的工資差異。從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視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以農民工為樣本,運用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發現:正規就業農民工比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及個體能力(認知和非認知能力),加上勞動力市場存在分割及就業歧視,導致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較高;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的增強不僅能促進農民工工資增長,而且能強化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數字經濟發展對正規就業農民工具有更強的工資增長效應,進而會擴大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差異,其中存在“數字經濟發展—非認知能力差異擴大—工資差異擴大”的傳導路徑,但認知能力差異的中介效應不顯著。Oaxaca-Blinder分解結果也顯示,地區數字經濟和個體能力差異都是兩類農民工工資差異的來源。因此,在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要更加關注數字紅利邊緣群體的發展,積極幫助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高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并加快構建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斷弱化和消除就業歧視。
關鍵詞:數字經濟;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多層線性模型
中圖分類號:F244;F30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0-0015-17
引用格式:楊德利,周琪.數字經濟、個體能力與農民工工資差異——基于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多層模型分析[J].西部論壇,2023,33(3):15-31.
YANG De-li,ZHOU Qi. Digital economy, individual abilities, and the wage difference of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HLM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employment[J]. West Forum, 2023, 33(3):15-31.
一、引言
當前,經濟運行方式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而不斷變化,數字經濟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許憲春 等,2020)[1]。數字經濟推動了新的產業格局和商業模式發展,平臺經濟、共享經濟迅速崛起,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消費和就業模式(劉皓琰 等,2017)[2],實現了對傳統要素質量的升級改造,提升了要素生產效率(叢屹 等,2020)[3]。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產生的數字紅利逐漸滲透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和領域,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也帶來了收入增長。盡管從整體趨勢上看,數字經濟的收入增長效應顯著存在,但是數字經濟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卻未形成一致結論。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促進所有社會群體的收入增長,但其對不同群體的影響程度可能存在顯著差異,進而在不同的地區,對于不同的群體分類,可能縮小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張勛 等,2019)[4],也可能拉大收入差距(蔡躍洲 等,2019)[5]。因此,在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不同群體收入增長差異化影響及其機制,進而尋求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徑。
關于數字經濟影響收入差距的實證研究,國內文獻集中于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經驗分析,僅有個別文獻涉及區域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及性別收入差距等(文淑惠 等,2022;賈甫,2023;喬小樂 等,2023)[6-8],顯然,相對于現實經濟中勞動者復雜的群體結構,這是遠遠不夠的。同時,在關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近年來針對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收入差距的探究較為欠缺。當前,非正規就業形式極大地緩解了我國的就業壓力,是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的重要路徑之一。但是,傳統觀點認為非正規就業是正規就業市場擠出的、效率低下的,在同等工作職能下正規就業者將獲得更高的收入(Farber,1999)[9]。在傳統就業市場中,教育背景、個人能力和社會資本等方面較差的勞動者易被市場擠出變為非正規就業者;而數字經濟創新了商業模式,帶來了新崗位,尤其是創造了大量的非正規就業崗位,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結構。那么,數字經濟發展對正規就業勞動者和非正規就業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會縮小還是擴大兩者的收入差距?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助于深入認識數字經濟的收入增長紅利產生機制與分配格局,進而更有效地以數字經濟發展驅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鑒于以上,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分析數字經濟對正規就業群體和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工資收入及其工資差異的影響;同時基于新人力資本理論,進一步探討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對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的調節作用;并采用多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HLM),以農民工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在于:第一,從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角度分析數字經濟的增收紅利在不同就業群體中的作用偏差,不僅深化了對數字經濟功效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入認識數字經濟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第二,針對農民工的實證研究為數字經濟對該特殊群體工資收入的影響提供了經驗證據,對其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分類分析則豐富了對農民工群體內部收入差距的研究視角;第三,探討了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在數字經濟影響農民工工資收入中的調節效應以及能力差異在數字經濟影響工資差異中的中介效應,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借鑒,也為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有效提高農民工工資收入、縮小群體收入差距等提供了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數字經濟、個體能力與勞動者工資增長
(1)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
從理論上講,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勞動者工資由邊際生產率決定,依托互聯網、大數據技術及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的數字經濟發展,可推動生產效率上升、促進經濟增長,進而提高勞動者的工作報酬(Autor et al,2015)[10]。但是,在現實經濟中,市場通常處于信息不對稱的不完全競爭狀態,此時勞動者的工資受到勞企雙方議價能力的影響(Cahuc et al,2006)[11],而勞動者議價能力的大小取決于其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特質(謝申祥 等,2019)[12],即當勞動者所處的就業市場機會較多且勞動者個人能力較強時,勞動者會擁有較強的工資議價能力,并獲得更高較高的勞動報酬。數字經濟的發展則擴大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崗位規模(韓鑫,2023)[13]。數字經濟不僅可以通過對整體經濟增長的促進帶來就業的增加(Bessen,2019)[14],而且創造了如網約車、外賣和直播帶貨等新的商業模式(李曉華,2019)[15],產生了新的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而且此類新增就業崗位對技能要求較低、進入門檻寬松(田鴿 等,2022)[16]。同時,數字技術進步會導致技能偏向,使高技能勞動者通過技能溢價獲得更多勞動報酬,并形成一種正向激勵,帶動低技能勞動者的學習和培訓,從而實現更高的就業水平和就業回報(曹靜 等,2018)[17]。因此,發展數字經濟將有助于增加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提升勞動者的技術能力,從而增強勞動者的工資議價能力,并產生普遍的工資增長效應。
(2)個體能力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
毋庸置疑,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與其個體能力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個體能力的提高通常會帶來勞動者就業水平和勞動報酬的提升。本文基于新人力資本理論,將勞動者的個體能力分為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二者均會顯著影響個體的經濟社會表現(Heckman et al,2006)[18]。認知能力是個體的計算、讀寫和分析復雜問題的能力,會顯著地影響個體的工資收入。非認知能力包括個體的生活工作態度、性格和價值觀等,會影響個體的受教育水平、職業選擇偏好和技能形成等。勞動者非認知能力的提高,會提高其教育回報率、經驗回報率和生產效率(Almlund et al,2011)[19],實現勞動收入的增長;同時,非認知能力強的勞動者更可能取得企業信任,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出更大競爭優勢,獲得優質和高薪工作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樂君杰 等,2017)[20]。因此,勞動者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提高都有利于其工資收入的增長。
(3)個體能力對數字經濟工資增長效應的調節作用
個體能力不僅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產生直接影響,而且會通過影響其他因素對勞動者工資的影響來發揮作用。從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來看,雖然數字經濟的發展整體上具有普惠性,但由于數字經濟本質上是基于數字技術進步發展起來的,勞動者個體能力(尤其是數字素養及數字技術水平)的差異會導致其獲取和享受數字紅利的差異,進而表現為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對于不同的勞動者存在差異。具體來看,數字經濟對勞動者的數字素養具有較高要求(陳南旭 等,2022)[21],具有較高認知能力的勞動者更容易掌握數字技術,更可能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獲得技能溢價,實現更多的工資增長。同時,非認知能力越強,越可能察覺到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的社會經濟變化,通過改變就業方向等方式跟上數字經濟發展的腳步(王國敏 等,2020)[22];具有較高非認知能力的勞動者可以發揮其應變能力強、外向開放等優勢,快速接受和適應數字化社會,接受新職業、新就業模式,尋求新創業機會,從而更容易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獲得更多更高報酬的就業機會。因此,相比而言,數字經濟發展會對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較強的勞動者產生較大的工資增長效應。
綜上所述,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會受到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自身能力(包括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影響。一方面,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個體能力的提高均會促進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另一方面,個體能力的提高可以強化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上述主要是從勞動者個體角度進行的分析,而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情形下,眾多的勞動者會在經濟實踐中形成不同類型的群體。同一群體的勞動者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而不同群體的勞動者之間具有顯著不同的特征,因而個體差異決定了群體差異,群體差異則反映了個體差異。比如,農民工群體的工資收入整體上低于城鎮居民,同時其個體能力在整體上也低于城鎮居民。因此,針對群體差異的研究可以更為深刻地揭示發展規律及影響機制,并具有更強的現實意義和政策價值。基于此,本文從正規就業群體與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差異角度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2.正規就業群體與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工資差異
(1)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
對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分類,通常是依據勞動關系的穩定程度,正規就業者的勞動關系穩定、有勞動合同約束,而非正規就業是指沒有勞動合同約束的就業形式(胡鞍鋼 等,2001)[23]。相關研究發現,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存在明顯的工資差異,正規就業者的工資水平高于非正規就業者。正規就業者的小時工資收入約為非正規就業者的1.65倍(薛進軍 等,2012)[24],并且該差異呈現出擴大的趨勢(王慶芳 等,2017)[25]。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工資差異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勞動力市場和人力資本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場分割和就業歧視,企業更愿意付出更多成本來聘用有正規就業經驗的勞動者;二是由于正規就業者的人力本往往高于非正規就業者,人力資本配置的正規就業偏向導致成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工資差異逐步擴大(屈小博,2012)[26]。常進雄和王丹楓(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非正規就業者與正規就業者的工資差異有81.01%是由人力資本因素、有18.99%是由市場因素造成的[27]。
(2)數字經濟對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工資差異的影響
從勞動力市場因素來看,在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成為勞動者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就業信息獲取及企業招聘方式的變革使得勞動者的正規就業經歷在招聘過程中更為顯性,放大了正規就業市場對非正規就業者的歧視,從而可能促使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擴大。從人力資本因素來看,正規就業者的人力資本要普遍優于非正規就業者,數字技術能力和數字素養也較強,更能適應數字經濟帶來的各種變化,并獲取更多的數字經濟紅利,實現更快的勞動報酬增長,從而導致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擴大。此外,數字經濟帶來的信息獲取便利還可能會加速高人力資本勞動力向正規市場流動,優質勞動力在正規就業市場的聚集則會進一步促使其工資收入上升。因此,數字經濟極大地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結構和就業方式,促進了整體就業及就業回報的增加,但該紅利更多地被正規就業者獲取,并進一步擴大正規就業群體與非正規就業群體之間的工資差異。
(3)數字經濟影響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工資差異的能力路徑
前文分析表明,個體能力(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差異是勞動者工資差異形成的重要原因,從群體的角度看則表現為正規就業者與非正規就業者之間的能力差異導致了其工資差異,因而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影響兩者的能力差異來對其工資差異產生作用。在傳統經濟形態下,正規就業者的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整體上強于非正規就業者,而且認知和非認知能力具有職業篩選作用,高能力勞動者獲取正規就業崗位的概率更高(王春超 等,2019)[28]。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信息便利使高能力勞動者更容易與正規就業崗位相匹配,加速高能力人員向正規市場流動;同時,數字經濟也會強化個體能力的自我增強和持續積累作用,能力較強的正規就業者更容易獲取更新、更高階的能力(李陽 等,2023)[29],從而擴大正規就業者與非正規就業者之間的能力差異。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會促使高能力勞動者聚集于正規就業市場,并擴大正規就業者與非正規就業者之間的能力差異,而數字紅利偏向于高能力勞動者聚集的正規就業市場,從而導致正規就業者與非正規就業者之間工資差異的擴大,即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擴大正規就業群體與非正規就業群體之間的認知和非認知能力差異來產生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工資差異的擴大效應。
3.研究假說的提出
根據前文分析,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個體能力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差異化影響會形成群體差異,從正規就業群體與非正規就業群體來看,具體表現為以下態勢:總體上看,正規就業群體比非正規就業群體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及認知和非認知能力,加上勞動力市場存在分割及就業歧視等問題,導致正規就業群體的工資收入高于非正規就業群體;無論是對于正規就業群體還是對于非正規就業群體,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個體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的增強均能促進勞動者工資增長,且個體能力提高能夠強化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正規就業群體的工資增長促進作用更大,會導致正規就業群體與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工資差異擴大,其中存在“數字經濟發展—能力差異擴大—工資差異擴大”的傳導路徑。
為對上述理論進行實證檢驗,本文采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數據以農民工為樣本進行經驗分析。選擇CFPS是因為該數據庫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能夠較好地滿足本文分析的數據要求;以農民工為研究樣本是出于以下考慮:一是作為一個特殊的就業群體,無論是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還是正規就業的農民工,都是數字經濟背景下需要被關注的數字紅利邊緣群體,而目前對數字經濟影響農民工工資收入的研究十分欠缺,尤其缺乏經驗證據;二是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研究農民工的就業形態(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三是農民工大多經歷了就業形態的轉變,在就業形態轉變過程中個體能力的作用往往會得到充分體現,而個體能力是本文分析的關鍵變量之一,因而采用農民工樣本的實證分析可能可能會得到相對顯著的結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1: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均具有促進作用,但對正規就業農民工工資增長的促進更大,從而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工資差異。
假說2:個體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提高會促進正規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增長。
假說3:無論是對于正規就業農民工,還是對于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對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都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農民工的認知和非認知能力越強,數字經濟發展對其工資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大。
假說4:認知和非認知能力差異在數字經濟發展擴大農民工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工資差異中發揮中介作用,即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可以通過擴大正規就業農民工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之間的能力差異來拉大兩者之間的工資差異。
三、實證研究設計
1.基于多層工資方程的模型構建
本文實證檢驗的核心內容是數字經濟發展對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影響,其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為地區層面的宏觀經濟變量,而農民工工資收入為個體層面的微觀變量,數據存在自然的嵌套結構,即個體嵌套于各地區之中,這種分層數據結構不符合傳統的線性回歸方法所要求的方差齊次、獨立分布等前提假設。多層模型則可綜合分析宏觀與微觀因素的影響,其將個體因素的影響從群體因素中分離出來,從而調節數據的聚類性質,使得研究的參數估計更為準確、更能反映數據的實際特征(郭鳳鳴 等,2013)[30]。因此,多層模型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中,其中就包括地區宏觀因素(如交易水平、經濟環境、對外開放能力等)對個體收入的影響(Plasman et al,2004;郭鳳鳴 等,2013;王君 等,2018)[30-32]。借鑒相關研究,本文采用多層線性模型來分析地區(省份)數字經濟發展對農民工個體工資收入的影響。
首先,建立截距模型M0,如式(1a)(1b)(1c)所示。模型M0中不包括任何自變量,通過地區(省份)層面的隨機效應來判斷地區因素對農民工收入的影響是否顯著,以明確采用多層線性模型的必要性。其中,i代表個體,j代表省份,因變量lincomeij為個體的工資收入,本文中具體為“農民工工資”,采用省份j個體i的月工資收入(取自然對數)來衡量;式(1a)中的β0j和εij分別表示截距和隨機擾動項(年份虛擬變量);式(1b)中的γ00為lincomeij的總均值,μ0j表示地區層面的隨機擾動項;式(1c)為組合模型。
然后,建立加入地區層面宏觀變量的主效應模型M1,如式(2a)(2b)(2c)所示。模型M1的自變量只包含地區層面的宏觀變量,通過變量的估計系數以及地區層面誤差項方差的變化方向來考察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農民工工資收入水平的影響。其中,Digj代表地區層面的宏觀變量,具體包括衡量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核心變量“數字經濟水平”(Dig1j)以及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Dig2j),其他符號的意義同上。“數字經濟水平”采用樣本所在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來衡量,參考劉軍等(2020)、楊慧梅和江璐(2021)的研究[33-34],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產業發展、數字用戶情況和數字化應用四個維度構建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的評價指標體系( 其中,數字基礎設施維度包括“光纜密度”“移動電話基站密度”2個指標,數字產業發展維度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數占城鎮單位從業人數比例”“軟件產業收入”“每百人使用計算機”“人均電信業務總量”4個指標,數字用戶情況維度包括“移動電話普及率”“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密度”“移動互聯網用戶占比”“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占比”4個指標,數字化應用維度采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刻畫。),使用熵值法得到各樣本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來衡量。
最后,進一步加入個體層面的微觀變量構建模型M2,如式(3a)(3b)(3c)所示。模型M2的自變量包括地區宏觀變量和個體微觀變量,可以識別個體特征對地區內個體工資水平的影響。其中,Xij代表影響工資收入的個體特征變量,除“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外,參照郭鳳鳴和張世偉(2013)、王林輝等(2022)的做法[30][35],還選取了“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婚姻狀況”“受教育水平”等變量(具體測度方法見表1)。
2.調節效應檢驗的模型構建
為驗證假設3,構建模型M3和M4如式(4a)(4b)(4c)和(5a)(5b)(5c)所示,用以考察地區宏觀變量與個體微觀變量的跨層交互作用。其中,調節變量X1和X2分別為個體的“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參考楊虹和張柯(2021)的方法[36],并根據CFPS的數據特征,從聽說讀寫和記憶能力等角度選取指標測度樣本的“認知能力”,包括是否讀書、總閱讀量、記憶主要事情、使用普通話和智力水平等;借鑒程虹和李唐(2017)、王春超和張承莎(2019)的研究[37][28],從嚴謹性(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順從性(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急于結束調查的程度)、外向性(人緣有多好、有多幸福)、開放性(互聯網作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情緒穩定性(我感到悲傷難過、我覺得生活無法繼續)等維度對樣本的“非認知能力”進行測量。對上述指標進行方向調整和標準化處理后平均,得到個體的綜合“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指標。
3.中介效應檢驗的模型構建
為驗證假設4,基于地區層面的數據,采用逐步回歸法構建中介效應模型M5如式(6a)(6b)(6c)所示。其中,被解釋變量(gincome)“工資差異”為樣本省份兩類農民工的工資差異,參考鄧翔和黃志(2019)測算行業收入差距的方法[38],采用樣本省份“正規就業農民工平均月工資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平均月工資之差除以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平均月工資”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Dig1j)為“數字經濟水平”。中介變量(gapatj)有兩個,一是“認知能力差異”,二是“非認知能力差異”,具體計算方法為:將全部樣本按“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進行排序并分組,前25%劃為高認知能力(高非認知能力)人員;分別計算樣本省份正規就業樣本中和非正規就業樣本中的高認知能力(高非認知能力)人員占比,用正規就業的高認知能力(高非認知能力)人員占比減去非正規就業的高認知能力(高非認知能力)人員占比,得到各省份的“認知能力差異”(“非認知能力差異”)。控制變量(Xj)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差異”(各省份正規就業農民工平均學歷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平均學歷之差)。
4.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所用數據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地區(省份)層面的數據來自相應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據庫,二是農民工個體層面的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最新發布的兩期(2018和2020年)( 只選取了最新兩期數據,一方面是由于調查問卷內容的調整導致本文所需一些變量在前幾期的數據中缺失,另一方面是考慮到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在2017年后更受重視。),選擇其中農業戶籍、18~60歲、從事非農工作的被調查者為研究樣本,刪除有缺失值等無效樣本,最終獲得有效樣本11 724份,其中2018年的樣本6 233份,2020年的樣本5 491份。對于農民工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分類,參考王慶芳和郭金興(2017)、胡翠等(2019)、席艷樂等(2021)的研究[25][39-40],將在問題“你的這份工作單位或雇主的性質屬于?”中選擇“政府部門/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外商/港澳臺企業、民辦非企業組織/協會/行會/基金會/村居委會”或在私企工作且簽訂了就業合同的樣本劃分為正規就業,其他的劃分為非正規就業(如個體工商戶、在私企工作且未簽訂就業合同等),由此,得到正規就業樣本6 582份,非正規就業樣本5 142份。
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認知和非認知能力以及受教育水平均高于非正規就業農民工。
表2展示了2018年部分省份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小時工資及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可以發現:東部地區農民工的小時工資明顯高于西部地區,這也符合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以正規就業的農民工為例,上海的小時工資是山西的2.21倍,地區間確實存在明顯的工資差異。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在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最高的上海,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小時工資均最高,符合預期;但是在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最低的甘肅,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小時工資處于中游水平,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小時工資最低,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對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再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差異來看,工資差異最大的是浙江,而浙江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位于全國前列;甘肅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最低,而工資差異卻位于中游。因此,簡單的統計分析無法直觀地判斷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工資差異與數字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多層模型估計
運用模型M0、M1和M1分別對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3。模型M0的估計結果顯示,農民工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工資的總體組內相關系數(ICC)分別為0.103 7和0.035 3,且組間方差在 1%水平下顯著。當ICC>0.059時,需要考慮組間效應(Cohen,1988)[41],即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存在明顯的省際差異(具有明顯的分層結構)。就業地區的差異確實會影響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因而建立多層模型是可行且必要的。
模型M1的分析結果顯示,加入了地區層面的變量“數字經濟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后,組間方差大幅下降,表明這兩個變量對地區間農民工工資差異有較強的解釋作用,應加入模型中。其中,無論是在正規就業子樣本中還是在非正規就業子樣本中,“數字經濟水平”對“農民工工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顯著提升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對比而言,“數字經濟水平”的回歸系數在正規就業子樣本中是非正規就業子樣本的兩倍多,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見表4),這意味著,相比正規就業農民工,數字經濟發展對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工資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小,而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本來就較高,因而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拉大了正規就業農民工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之間的工資差異。由此,假說1得到驗證
模型M2的回歸中進一步加入了個體層面的變量,與M1模型相比,組內方差降低,說明個體特征對地區內農民工個體的工資差異具有一定解釋作用。“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其中“認知能力”的系數較大),表明農民工的能力提升有利于其工資增長,且認知能力提升的工資回報大于非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的組間系數差異顯著,即非正規就業農民工非認知能力提升的工資增長效應大于正規就業農民工。其原因可能在于,非認知能力決定了勞動者的社會融入、社會接觸狀態,非正規就業者不穩定的就業狀態使其更需要通過社會接觸來拓展就業渠道,因而非認知能力提升對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資增長的促進作用比對正規就業農民工的更大。由此,假說2得到驗證。
其他個體特征變量對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影響大多顯著且正向。“性別”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非正規就業子樣本中更大,表明勞動力市場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別歧視,男性農民工有顯著的工資優勢,且在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群體中這一現象更為嚴重;從“年齡”和“年齡平方”的估計系數來看,年齡對農民工工資收入的影響呈現倒“U”型趨勢,這與職業的生命周期理論相符;“婚姻狀況”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已婚的農民工比未婚的農民工有更高的工資收入;“健康狀況”的估計系數在非正規就業子樣本中顯著為正,在正規就業子樣本中為正但不顯著,表明身體健康對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工資的增進作用更大;“受教育水平”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正規就業子樣本中更大,表明人力資本是影響農民工工資收入的重要因素,由于正規就業的學歷門檻相對明確且嚴格,正規就業農民工的教育回報也相對更高;“家庭規模”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家庭人口越多,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水平越低。上述分析結論基本與理論預期及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一致,表明本文的模型分析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為進一步驗證上述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本文也采用OLS估計方法進行了模型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的“OLS估計”部分。可以發現,“數字經濟水平”的估計系數同樣顯著為正且在正規就業子樣本中較大,“認知能力”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非認知能力”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非正規就業子樣本中的顯著性和絕對值更大。總的來說,OLS估計結果與模型M2的分析結果一致,但是系數有所差異,OLS估計中地區層面變量的回歸系數普遍偏大,而個體層面變量的回歸系數普遍偏小。
此外,本文還通過更換核心解釋變量的計算方法來進行穩健性檢驗。前文中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是采用熵值法計算的,參考劉軍等(2020)的研究[33],采用線性加權法(對一級指標賦予均等權重再分配給二級指標)計算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重新進行模型檢驗,回歸結果結見表5,與前述分析結果基本一致,進一步表明本文的分析結果是穩健的。
2.工資差異的Oaxaca-Blinder分解
上文分析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農民工工資的影響具有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組間差異,即可能會拉大正規就業農民工和非正規就業農民工之間的工資差異。進一步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來探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及個體能力在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工資差異產生中起到的作用。Oaxaca-Blinder分解可得到工資差異中的可解釋部分和不可解釋部分:可解釋部分是能被變量的數量差異所解釋的部分,為特征差異;不可解釋部分為是由就業特征、市場歧視等所導致的工資差異,為系數差異。表6的分解結果顯示,農民工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總差異顯著為正(0.213),說明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收入總體上顯著高于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大約高23.7%),其中,特征差異(0.133,p=0.000)占62.4%,系數差異(0.053,p=0.000)占37.6%。可見,特征差異是導致工資差異的主要因素,但系數差異同樣不可忽視。系數差異是個人特征和地區特征無法解釋的部分,反映出可能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和歧視等問題(比如“同工不同酬”現象),使得各種因素對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兩類農民工工資的影響存在差異,進而導致兩類農民工的工資差異擴大。
根據表6各變量的具體分解項,可以發現:(1)數字經濟發展是造成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資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數字經濟水平”的特征差異為0.025,說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工資增長效應在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兩類農民工之間存在差異,即對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增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從而會加劇兩類農民的工資差異;系數差異為0.082,說明數字經濟發展還可能通過加劇勞動力市場對非正規就業的歧視來加大兩類農民工的工資差異,這是由于數字經濟下企業招工方式變化(如互聯網招聘興起)使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較難獲取高薪資的工作,從而擴大了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2)從農民工的個體能力來看,“認知能力”的特征差異顯著為正,而系數差異則不顯著,說明個體認知能力是造成農民工工資差異的重要因素,但其對勞動力市場歧視的影響不大;“非認知能力”的系數差異顯著為負,表明非正規就業農民工非認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帶來的工資差異。
3.個體能力對數字經濟工資增長效應的調節效應
模型M3和M4的回歸結果見表7。“認知能力×數字經濟”和“非認知能力×數字經濟”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個體能力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促進農民工工資增長中發揮了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即農民工的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越強,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其工資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強。由此,假說3得到驗證。同時,交互項組間系數的差異均不顯著(見表4),說明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調節作用在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兩類農民工群體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4.地區層面的中介效應檢驗
中介效應模型M5的回歸結果(OLS估計)見表8,可以發現:(1)“數字經濟水平”對“工資差異”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擴大正規就業農民工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之間的工資差異,進一步驗證了假說1。(2)“數字經濟水平”對“認知能力差異”和“認知能力差異”對“工資差異”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表明認知能力差異的中介作用不顯著。可能的解釋是,數字經濟對兩類農民工的認知能力差異存在雙向作用:一方面數字經濟的技能偏向將幫助擁有較高認知能力的非正規就業者進入正規就業市場,進而拉大兩群體間的認知能力差異;另一方面數字經濟以遠程教育、在線教育等多元化學習方式彌補了農村地區的教育基礎資源弱勢(趙云,2023)[42],從而可以縮小兩類農民工的整體認知能力差異;在此情形下,認知能力差異也不再是工資差異產生的原因。(3)“數字經濟水平”對“非認知能力差異”和“非認知能力差異”對“工資差異”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非認知能力差異具有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即數字經濟發展會通過加大正規就業農民工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的非認知能力差異來擴大兩者之間的工資差異,假說4得到部分驗證。
五、結論與啟示
數字經濟對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提高了生產效率,推動了經濟發展,也改變著勞動者的就業形態和勞動報酬。當前,不同勞動者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還顯著存在,在加快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不僅要重視數字經濟普惠性的收入增長效應,也不能忽視不同群體獲取和享受數字紅利的差異,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非正規就業形式的蓬勃發展,非正規就業市場的擴大吸納了大量勞動力,為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提供了有效路徑。然而,在現階段,由于非正規就業者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個體能力(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整體上還低于正規就業者,加上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就業歧視的存在,導致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存在工資差異,而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個體能力又使正規就業者可以獲取較多的數字紅利,這可能進一步擴大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本文以CFPS2018和CFPS2020中的農民工為樣本,綜合地區(省份)層面的宏觀變量和個體層面的微觀變量,進行多層線性模型分析以及Oaxaca-Blinder分解,結果發現:正規就業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整體上明顯高于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民工工資增長,但該工資增長效應在正規就業農民工群體中更強;無論是正規就業農民工,還是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個體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的提高都顯著正向影響其工資收入,且會強化數字經濟的工資增長效應;非認知能力差異在數字經濟影響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工資差異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即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擴大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農民工之間的非認知能力差異來拉大兩者的工資差異。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啟示:第一,要逐步完善各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良好條件;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尤其要加快落后地區的數字經濟建設,縮小地區間的數字鴻溝。第二,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要更加關注數字紅利邊緣群體的發展,如非正規就業群體、農民工群體等。要深化改革勞動收入分配制度,完善非正規就業崗位的福利保障制度;要加快構建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斷弱化和消除就業歧視。第三,要積極幫助非正規就業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高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正規就業者與非正規就業者的工資差異以及數字經濟帶來的差異擴大效應,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兩者在人力資本水平以及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上存在差異,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普適化、數字化的培訓體系以不斷提高農民工和非正規就業者的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能,尤其應重視勞動者非認知能力的提高。地方政府應該擔起大任,通過積極的職業教育、政企合作和公益性學習平臺建設等,幫助農民工群體和非正規就業群體快速適應數字經濟帶來的經濟社會變化,促進其數字技能獲取和更新,提高其工作獲取機會和勞動報酬,進而不斷縮小正規就業者與非正規就業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參考文獻:
[1]許憲春,張美慧.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研究——基于國際比較的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20(5):23-41.
[2] 劉皓琰,李明.網絡生產力下經濟模式的勞動關系變化探析[J].經濟學家,2017(12):33-41.
[3] 叢屹,俞伯陽.數字經濟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J].財經理論與實踐,2020,41(2):108-114.
[4] 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J].經濟研究,2019,54(8):71-86.
[5] 蔡躍洲,陳楠.新技術革命下人工智能與高質量增長、高質量就業[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36(5):3-22.
[6] 文淑惠,程莉莉.數字經濟對泛珠區域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J].科技與經濟,2022,35(5):66-70.
[7] 賈甫.數字經濟、資本收益率與行業收入差距[J].當代經濟管理,2023,45(1):57-66.
[8] 喬小樂,何洋,李峰.工作轉換視角下數字經濟對性別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3(1):74-83.
[9] FARBER H S. Alternative and part-time employment arrangements as a response to job los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9:122-148.
[10]AUTOR D H,DORN D,HANSON G H. 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ur market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5,125:621-646.
[11]CAHUC P,POSTEL-VINAY F,ROBIN J M. Wage bargaining with on-the-job search:theory and evidence[J]. Econometrica,2006,74(2):323-364.
[12]謝申祥,陸毅,蔡熙乾.開放經濟體系中勞動者的工資議價能力[J].中國社會科學,2019(5):40-59+205-206.
[13]韓鑫.當前數字經濟領域的就業規模不斷增長——數字職業提供就業新空間[N].人民日報,2023-05-26(019).
[14]BESSEN J. Automation and jobs:when technology boosts employment[J]. Economic Policy,2019,34:589-626.
[15]李曉華.數字經濟新特征與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機制[J].改革,2019(11):40-51.
[16]田鴿,張勛.數字經濟、非農就業與社會分工[J].管理世界,2022,38(05):72-84.
[17]曹靜,周亞林.人工智能對經濟的影響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2018(1):103-115.
[18]HECKMAN J J,STIXRUD J,URZUA S,et al.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2006,24(3):411-482.
[19]ALMLUND M,DUCKWORTH A L,HECKMAN J J,et al.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M].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2011.
[20]樂君杰,胡博文.非認知能力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17(4):66-76+127.
[21]陳南旭,李益.數字經濟對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影響研究[J].西北人口,2022,43(6):65-76.
[22]王國敏,唐虹,費翔.數字經濟時代的人力資本差異與收入不平等——基于PIAAC微觀數據[J].社會科學研究,2020(5):97-107.
[23]胡鞍鋼,楊韻新.就業模式轉變:從正規化到非正規化──我國城鎮非正規就業狀況分析[J].管理世界,2001(2):69-78.
[24]薛進軍,高文書.中國城鎮非正規就業:規模、特征和收入差距[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6):59-69.
[25]王慶芳,郭金興.非正規就業者的境況得到改善了么?——來自1997—2011年CHNS數據的證據[J].人口與經濟,2017(2):116-126.
[26]屈小博.中國城市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基于非正規就業異質性的收入差距分解[J].南方經濟,2012,No.271(04):32-42.
[27]常進雄,王丹楓.我國城鎮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的工資差異[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27(9):94-106.
[28]王春超,張承莎.非認知能力與工資性收入[J].世界經濟,2019,42(3):143-167.
[29]李陽,張文宏.從自驅力到勝任力:非認知能力對新業態靈活就業人員作用機制研究[J].學習與探索,2023(2):31-38.
[30]郭鳳鳴,張世偉.區域經濟環境對工資性別差異的影響——基于多層模型的分析途徑[J].人口學刊,2013,35(4):42-56.
[31]PLASMAN R,RUSINEK M,RYCX F. Union wage gaps in multilevel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pplied Econometrics Association Mons(B),2004.
[32]王君,董長瑞.對外開放能力與收入代際流動性——基于CHNS調研數據的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8(5):53-62.
[33]劉軍,楊淵鋆,張三峰.中國數字經濟測度與驅動因素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20(6):81-96.
[34]楊慧梅,江璐.數字經濟、空間效應與全要素生產率[J].統計研究,2021,38(4):3-15.
[35]王林輝,錢圓圓,趙賀.人工智能技術、個體能力與勞動工資:來自認知和非認知能力視角的經驗證據[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24(4):58-69+149+147.
[36]楊虹,張柯.認知能力、社會互動方式與家庭金融資產選擇[J].金融論壇,2021,26(2):70-80.
[37]程虹,李唐.人格特征對于勞動力工資的影響效應——基于中國企業—員工匹配調查(CEES)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17,52(2):171-186.
[38]鄧翔,黃志.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對行業收入差距的效應分析——來自中國行業層面的經驗證據[J].軟科學,2019,33(11):1-5+10.
[39]胡翠,紀珽,陳勇兵.貿易自由化與非正規就業——基于CHNS數據的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19(2):3-24.
[40]席艷樂,張一諾,曹亮.外資進入擴大了正規與非正規就業者的工資收入差距嗎——來自微觀個體的經驗證據[J].國際貿易問題,2021(10):139-156.
[41]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M]. 2nd ed.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8.
[42]趙云.數字經濟賦能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3,44(1):9+23.
Digital Economy, Individual Abilities, and the Wage Difference of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HLM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YANG De-li, ZHOU Q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is in the ascenda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industrial patterns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upward trend of the economy and the growth of labor income, as well as brought abou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employment forms. The expansion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market has absorbed a large amount of rural labor, providing new exports for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lso affects the wage incom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is mostly based on formal employment.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s, as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have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the 2018 and 202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Firstly, a multi-layer model of the wage equ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abilities in it. Secondly, use Oaxaca Blinder decomposition to clarify the sources of wa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and pa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ir wage differenc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higher the salary incom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ncome increas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higher for formal employment migrant workers than for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s. Among them, individual abilities have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wage growth brought about by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ge ga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com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ividual ability differences. The digital economy expands the wage gap in terms of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and reward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pands the wage income gap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ds the wag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by promoting the regularization of employment for highly non-cognitive migrant workers.
Compared to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mainly expand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focuses on individual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ocuses on migrant workers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secondly, it focuses on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group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wage gap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migrant workers; thirdly, it explor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ffecting the wage income of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ability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in it, and also explores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ffecting the wage inc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analyz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gnitive ability differenc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difference in i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bias of the income increas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explor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wage gap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better employment guidance measur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provide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for migrant workers of different job type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formal employment; informal employment; cognitive abilitie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CLC number:F244;F304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0-0015-17
(編輯:黃依潔)
收稿日期:2023-03-29;修回日期:2023-05-02
基金項目:作者簡介:楊德利(1963),男,黑龍江賓縣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農業經濟學研究,Email:dlyang@shou.edu.cn。
周琪(1996),女,江蘇鎮江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農林經濟管理研究,Email:m200501264@sho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