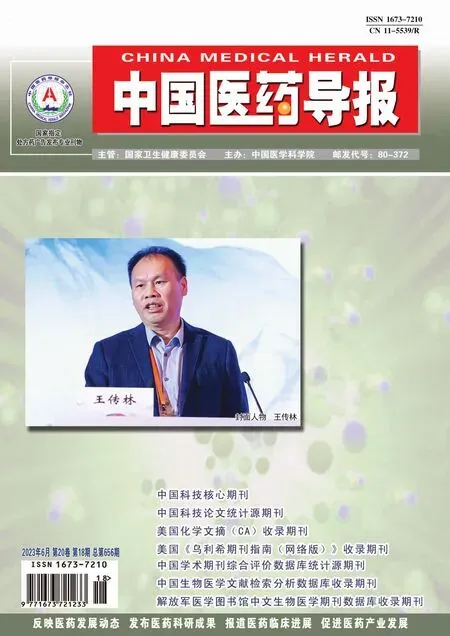基于政策工具視角的我國藥品監管政策文本分析
賈 倩 莊 倩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江蘇南京 211100
藥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關系到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還關系到經濟的增長和國家的長治久安[1-3]。從20 世紀30 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開始采取由政府專業執法機構依法對藥品安全實施監管的模式,并獲得其他國家的廣泛認同[4]。借鑒國外發達國家成熟的監管模式,我國制訂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以下簡稱“《藥品管理法》”)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從而建立科學、高效、權威的藥品安全監管體系[5]。對研究內容進行系統、定量及事實性描述的內容分析法[6]被廣泛用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中,如政府服務購買政策分析[7]、5G 發展政策[8];同時在醫藥政策也有涉及,醫保門診政策分析[9]、公共應急政策[10]、護理實踐[11]。故本研究以1984 年實施《藥品管理法》[12-14]為起始點,對1984—2021 年中央部委頒布的藥品監管政策進行分析,探究我國藥品政策監管方式變化特點,為優化我國藥品監管政策提供思路。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通過國務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相關官方網站并結合“北大法寶”,以“藥品”“藥品監管”“監管政策”“藥品監督管理”“藥品管理”“藥品安全”“質量”作為關鍵詞進行手動檢索。納入標準:①政策文本必須涉及藥品監管的具體內容;②文本必須是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正式文件;③文本的發布部門為國家層面機構。排除標準:①地方部門文件;②便函和通報文書;③同一階段內失效政策。最終共獲得從1984 年9 月至2020 年4月的119份樣本。政策文本的時間跨度較大,本研究以《藥品管理法》為界,考察藥品監管政策及監管方式的變化。作為藥品監管政策中最重要的法律,《藥品管理法》自1984 年9 月正式公布,經歷了2001 年和2019 年2 次變革性修訂[15-17]。故本文根據《藥品管理法》的發布時間作為重要時間節點將藥品監管政策分為以下階段:藥品監管探索期(1984—2000 年)、藥品監管發展期(2001—2018 年)和藥品監管深化期(2019 年至今)。
1.2 研究方法
政策工具是指為實現政策目標所使用的各種戰略和方法,科學地選擇和應用政策工具是實現政策目標的前提[18]。本研究將韓悅等[19]分類方式和霍龍霞等[20]分類方式相結合,并結合藥品監管政策特點,將監管政策工具劃分為強制型、激勵型、能力建設型和象征勸說型監管(表1);利用ROSTCM6 軟件篩選關鍵詞并分類;依托關鍵詞運用NVivo12 軟件編碼。

表1 監管工具類型與形式及其內容描述
2 結果
2.1 藥品監管政策關鍵詞
利用ROSTCM6 對各政策文本內容進行分詞處理,并提取其中高頻關鍵詞。見表2。

表2 藥品監管政策關鍵詞
2.2 文本編碼結果
本文采用NVivo12 自由節點樹編碼功能對原始政策文本進行編碼。結果顯示,監管政策文本整體平均編碼率達到分別達到60.25%、70.07%、85.87%,提示本文所采用的分析維度對于政策文本的契合度呈上升趨勢,能夠反映政策文本。見表3。

表3 藥品監管政策文本編碼率(%)
2.3 政策發布數量
本研究將政策按如下分類。1984—2000 年出臺20 項政策,最高發文3 份,年均1.2 份;該階段是我國藥品監管政策的初步探索與興起階段,藥品的法治化監管的正式拉開帷幕。2001—2018 年出臺86 項政策,年度最高發文8 份,年均4.8 份;該階段迎來了藥品監管政策的快速增長期,國家注重藥品審批和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維護了公眾安全用藥的合法權益。2019—2021 年出臺13 份政策,年度最高發文7 份,年均5.2 份;該階段迎來了藥品監管政策的戰略深化期,注重科學監管;同時政府的監管形式開始走向多樣化。
2.4 政策工具
2.4.1 總體情況
政策工具使用概況而言,四類監管方式均有所涉及,但差異較大:強制型監管的使用最多,占85.33%;象征勸說型監管次之,占比為6.93%;激勵型監管與能力建設型監管最少,占比分別僅為3.13%、4.61%。強制型監管方式的占比呈逐步衰減的趨勢;象征勸導型監管在2001—2018 年有飛速的增長,雖然后續期間回落至8.49%,但就整體而言,逐漸成為關鍵監管措施;能力建設型監管從2.19%一度躍遷至9.47%,提示政府越來越注重企業自身能力的提高;激勵型監管占比雖有所增長,但占比較小,整體仍處于較低水平。見表4。

圖2 藥品監管政策數量

表4 1984—2021 年各類藥品安全監管方式占比(%)
2.4.2 內部構成情況
選取占比最高的強制型監管和占比逐漸增長的象征勸導型監管來探究監管方式二級分類差別。
2.4.2.1 強制型監管 藥品監管政策對于執法方面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而重心在朝著檢查方向轉移。近年來,我國藥品安全檢查工作逐漸增多,而藥品監管部門將采取“雙隨機、一公開”進行安全檢查,并將檢查結果及時向社會公開。對于2019 年后制定標準規范與制度大量增加,可能由于新的《藥品管理法》剛頒布的同時會有大量的新的藥品監管細化的政策隨之更新。見圖3。

圖3 強制型監管
2.4.2.2 象征勸導型監管 藥品監管政策的側重點始終在信息公開、社會監督方面,同時越來越重視示范創建和自律。輿論監督作為社會監督方面最為典型的一種方式,雖然不是強制型,但是在道德方面能夠約束企業的自身行為;社會輿論監督是代表公眾意志的監督,其能夠修補政府強制性監督檢查的漏洞。而行業自律是一個行業內部的義務和責任,其能夠有效彌補政府執法的不足。對于2019 年后政策宣傳大量增加情況,可能由于新的《藥品管理法》和大量的新藥品監管細化的政策的頒布,政府將會增加對于新政策宣傳。見圖4。

圖4 象征勸導型監管
3 討論
本研究以1984 年9 月至2021 年4 月發布的119份政策作為原始文本,梳理了從1984 年《藥品管理法》發布以來我國藥品安全監管政策的變化情況。結果顯示,我國采取了強制型、激勵型、能力建設型與象征勸說型等多種監管方式相結合,但是使用比例失衡:熱衷于強制型監管,探究其原因:一方面,受改革開放前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強制型監管仍舊是最優的監管方式[21];另一方面,高危害性的藥品安全事件頻發,使得政府對企業信任度日益衰減,從而將不斷使用強制性手段約束企業的自身行為。而同時發現我國在引導性監管方式(激勵型、能力建設型與象征勸說型)嚴重不足,究其原因可能是稅收減免、幫扶政策和從業人員培訓等措施均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員。因此,應著力改善以上局面,可從以下方面入手。其一,重視監管人才隊伍建設。通過提供資金、開展增加專業技能人員與專職人員等教育培訓等措施提高藥品安全監管能力。可以通過國家牽頭高校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醫藥企業,實現產學研有機融合。其二,部分企業尤其是行業領軍企業主動推進行業自律[22-23]。相關行業協會應指定該行業協會內部標準,同時可以提出行業發展規劃供政府和企業參考,定期開展行業自律的監督檢查活動,受理糾紛投訴并開展調查和協調處理,建立誠信褒獎和懲戒機制。其三,藥品監管部門應借鑒“共治”理念,整合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共同合作,形成一個多元主體共同協作的藥品安全監管新氛圍,最終實現藥品安全治理的“善治”狀態[24-27]。針對監管部門的監管政策、措施以及成效積極向全社會公開;大力向社會公眾宣傳藥品安全用藥教育,鼓勵公眾積極向監管部門反饋有關藥品安全問題及對藥品監管工作意見與建議。加強新媒體平臺的建設,通過權威的渠道為社會大眾傳遞有用的信息,密切關注重大、熱點、敏感信息,第一時間澄清虛假信息,發布正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