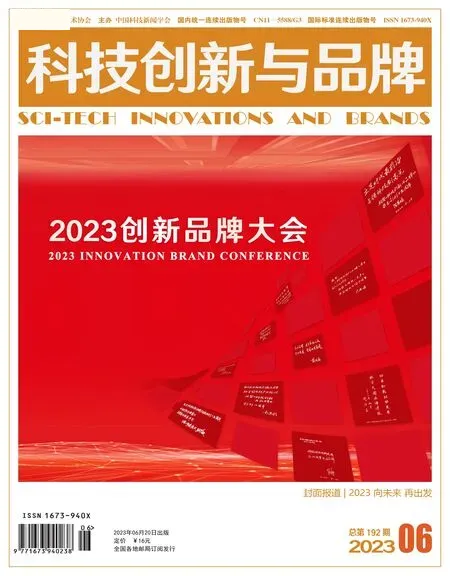黃國勤:以科研碩果報家鄉魚米之恩
文/本刊記者 馬思遙

“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用這兩個詞來形容江西省,最恰當不過了。江西自古以來就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擁有五千年以上的水稻栽培史。江西能成為我國重要的“糧倉”,除了在“前面”辛勤勞作的農民之外,同樣離不開以科技之力,提升農業技術含量、提高農產品產量和質量的幕后科技工作者。
夏日的田間,總會有這樣一個身影行走在稻田里。他挽著褲腿,擼起衣袖,頂著烈日,冒著酷暑,艱難地在水田中挪步。他時而低頭考察土壤肥力,時而拿起水稻監測生長情況。他身形不高,有時還戴著無框“老花眼鏡”,看上去斯斯文文的,而黝黑的皮膚是他奔走在田間地頭最好的佐證。他就是江西農業大學教授、生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從事農學、生態學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已40年的黃國勤。
1962年10月,黃國勤出生在江西省余江縣(現鷹潭市余江區)偏遠山區的農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勤勞樸實的農民。從小就乖巧懂事的黃國勤經常會跟著父母下地勞作,父母低頭種稻、抬手除草、汗流浹背的樣子,在幼小的黃國勤的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他想讓父母不那么辛苦。黃國勤意識到,只有以科學的手段提升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才能讓農民辛勤耕種的每一粒種子落地生花,結出豐碩的果實。
1980年,黃國勤以優異的成績從當時余江縣最好的中學——余江二中考到了江西共大總校(現江西農業大學)農學專業。江西農業大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是一所歷史悠久、農業教學底蘊濃厚的重點高等院校,曾經走出過周拾祿、楊惟義等農業“大家”,為我國農業,乃至世界農業的發展作出過重要的貢獻。在這里,黃國勤猶如麥穗汲取雨水一般“貪婪”地吸收著知識。在完成了4年的本科教育后,黃國勤再次因成績優秀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6年任教的兩年,為他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讓他更注重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解答學生各種困惑的過程中,他對于我國農業的發展有了更深刻的認知。
1986年,黃國勤深刻感受到想要更好地奉獻農業科研事業,現有的知識儲備是不夠的,為此他考取了本校作物栽培學與耕作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間,由于黃國勤出色的成績,敏而好學的品質,被導師鐘樹福選中參與他主持的“鄱陽湖區耕作制度調查與試驗”科研課題。也是這一次,正式開啟了黃國勤科研事業的大門,在與導師共事的過程中,他在導師一言一行與言傳身教里厘清了自己的科研脈絡和科研理想。
1990年,為了更進一步深化自己的科研事業,他又報考了南京農業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兩年的博士學業后,原本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在等著他,他還是毅然回到了江西農業大學任教。黃國勤說:“是江西這片熱土養育了我、培育了我,所以我要用我學到的知識,發展家鄉,建設家鄉。”
回校后,黃國勤將自己的青春與熱愛全部奉獻到科研工作中。為進一步發展,1994年9月他又進入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農學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這里,他結識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趙其國以及中國農學會會長張桃林等對我國農業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在他們的指導下,黃國勤艱苦鉆研、勤勉研究,他對中國南方耕作制度的改革和發展進行了實地調查和試驗研究,并在多種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自己的科研論文,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可。1995年,因學術研究成績突出,江西農業大學將黃國勤從講師破格晉升為教授(是當時江西省唯一一位從講師破格為教授的青年學者)。
在此間,他完成了15萬字的專輯《江西省冬季農業研究》,受到著名農業專家、教授郭文韜的肯定,“這是一部研究多熟種植不可多得的杰作”。緊接著,他又完成了第一本系統全面論述江西耕作制度的科學專著——《江西省耕作制度理論與實踐》。當博士后出站時,他在導師趙其國、張桃林的指導下,完成了《中國南方耕作制度》一書,該書為南方耕作制度的改革和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和重要參考。
在科研領域的累累碩果并沒有讓黃國勤感到“知足”,反而激勵他更加精進研究。至今他主持和參加完成國家級、省級及其他各級各類科研課題、專題項目90余項,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他共講授“農業生態學”“農業生態學專題”“農業現代化專題”“生態學研究方法”“生態學研究進展”“生態經濟學”等20余門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課程。他出版教材、專著、專輯或論文集等著作共計80余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及國際、國內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600余篇,獲得教學成果獎、科技成果獎和個人榮譽獎等共計100余項,如1990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996年江西省社會科學青年優秀成果一等獎、2015年第五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2017年江西省科技進步獎三等獎。就人才培養而言,截至2023年6月,黃國勤已指導培養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含在職生)共計124人,在“為黨育人、為國育材”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很多人曾經疑惑,以黃國勤的科研能力和他現在的身份,沒必要親自進入田間地頭考察調研,甚至有人勸他換個“更有錢途”的領域。他都只是笑著擺擺手說:“是農民養育了我,現在換我‘贍養’農民,沉下心來做研究很不容易,但是一想到農民站在土地里流汗,我覺得就沒有什么困難是無法克服的,我要用科學研究,滋養這片養育我的‘魚米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