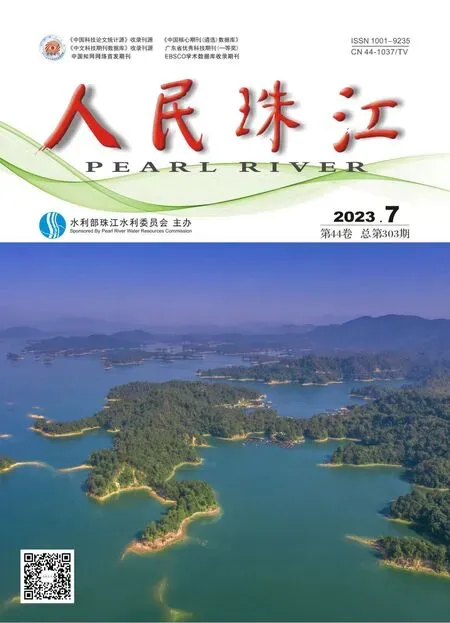贛江流域土地利用遷移變化分析
何 昊,劉衛林,李 香,張景嶸,楊 晴,涂序柯,劉建武,劉麗娜
(南昌工程學院江西省退化生態系統修復與流域生態水文重點實驗室,江西 南昌 330099)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進展,人類在開發和利用土地的同時,也改變著區域土地利用的類型,直接導致地表覆被改變[1]。而土地利用和地表覆被的改變會對環境產生較大的影響,繼而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生產生活。1995年,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 和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 IHDP) 聯合提出了“土地利用/覆被變化(land use/cover change 簡稱LUCC)”,使得土地利用/覆被變化成為全球變化影響研究關注的重要內容[2]。LUCC通過影響氣候條件、水文、土壤狀況等基本自然要素對生態環境產生相應的影響,引發了諸多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3]。通過對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可以合理規劃土地利用資源,根據各類土地特性,合理有效地使用土地資源,使其充分發揮自身功能。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土地利用變化特征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對于土地利用變化研究,已由最初的定性描述發展到運用遙感、GIS空間分析技術與數學模型相結合的定量表征[4-5]。典型的研究方法是采用動態度、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土地利用綜合程度等土地利用空間分析指標,從土地利用數量變化、類型轉換、變化速度等方面分析土地利用變化[6-8]。少數學者采用重心遷移法[9]和地學信息圖譜[10]分析了土地利用空間變化特征,使信息的表達更加多維化,彌補了基于非空間屬性數據庫的數據挖掘方法在形象思維和空間位置方面的不足,豐富了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11]。
贛江作為長江主要支流之一,鄱陽湖流域最大河流,是鄱陽湖流域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環境生態整治的重點區域,其土地利用格局對鄱陽湖流域生態安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影響重大。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經濟的快速增長驅使土地利用格局發生明顯變化,引發了一系列的資源、環境問題。近期干旱事件頻頻發生,其部分原因是由土地利用遷移變化造成的。在王暢[12]的研究中表明,隨著土地利用改變,流域重旱頻率上升約 23%,達到 36.1%,土地利用變化會加重干旱頻率以及干旱程度。同時陳昌春[13]在研究變化環境對江西省干旱特征的研究中,利用土地利用等數據建立SWAT模型,隨著土地利用改變,徑流下滑,干旱程度加劇。因此,深入研究贛江流域土地利用遷移變化,避免再次出現一系列問題,是極其重要的。近年來,雖然已有少量學者在贛江流域開展了土地利用變化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態效應與空間響應研究,例如郭強等[14]研究贛江流域土地利用變化對水文過程的影響;徐啟渝等[15]研究了贛江流域土地利用結構對水質的影響。缺乏長時間序列以及多指標對贛江流域土地利用時空變化特征的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以贛江整個流域為研究區,以土地利用動態度、土地利用轉移矩陣、重心遷移等多維度來分析1980—2018年長時間序列下的贛江流域土地利用時間和空間上的具體變化,為地方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和諧發展、流域生態建設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和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贛江是長江主要支流之一,為鄱陽湖流域最大河流,位于長江中下游南岸,源出贛閩邊界武夷山西麓,自南向北縱貫全省。有13條主要支流匯入,長766 km,流域面積83 500 km2,自然落差937 m。從河源至贛州為上游,稱貢水,在贛州市城西納章水后始稱贛江。貢水長255 km,穿行于山丘、峽谷之中。贛州至新干為中游,長303 km,穿行于丘陵之間。新干至吳城為下游,長208 km,江闊多沙洲,兩岸筑有江堤。贛江流域呈現山地丘陵為主體的地貌格局,山地丘陵占流域面積的64.7%(其中山地占43.9%,丘陵20.8%),低丘崗地占31.5%,平原、水域等僅占3.9%。贛江流域處于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氣候溫和,雨量充足,以春夏之交梅雨多,秋冬季節降雨少,多年平均降水量約為1 600 mm,多年平均氣溫約為17.8℃。
1.2 數據來源
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所提供的1980—2018年7個時段江西省土地利用現狀遙感監測數據,主要通過目視解譯遙感數據獲得,分辨率為30 m[16]。根據土地利用分類標準,利用ArcGIS重分類工具得到6類土地利用類型,分別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6類用地,再通過影像裁剪最終得到贛江流域1980—2018年土地利用數據。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動態度
為表達區域單一類型土地利用的變化速率以及土地利用的綜合變化速率,引入2個指標:K(單一土地利用動態)、LC(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
a)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
(1)
式中Ula、Ulb——初始時單一土地利用面積、結束時單一土地利用面積,km2;T——研究時段。
b)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
(2)
式中 LC——綜合土地利用動態度;ΔLU(ij)——第i類土地轉變為非i類土地的絕對值;ΔLUi——第i類土地在初期時的面積;T——研究時段。
2.2 土地利用轉移矩陣
為了表達各土地利用類型在空間上的分布和在各時期的轉移方向及比例,計算土地利用轉移矩陣[17],再通過轉移矩陣繪制土地利用轉移和弦圖,轉移矩陣見式(3):
(3)
式中Sij——i類轉化成j類的面積;n——土地利用類型的數量;i、j——轉移前后的土地利用類型(i,j=1,2,3,…,n)。
2.3 重心遷移
重心的確定方法,首先假設某一個區域由n個次一級區域i構成,那么該區域某種屬性的“重心”通常采用式(4)、(5)計算方法來表示:
(4)
(5)
式中X、Y——某一個區域某種屬性的“重心”經度值、緯度值;xi、yi——第i個次一級區域中心的經度值、緯度值;Mi——第i個次一級區域的某種屬性的量值。
3 結果與分析
3.1 土地利用空間分布
1980—2018年贛江流域土地利用分布見圖1。由圖可知:流域內主要以林地、耕地分布為主,草地、水域、建設用地、未利用地為輔的分布格局。流域內林地面積最大分布范圍最廣,集中分布于流域的中南部地區,以東部的武夷山區、南部的南嶺山區和西部的羅霄山區為主。耕地主要分布于贛江中下游子流域位置以及河流沿岸平坦區域,其他區域面積較少,分布具有一定集中性。草地分布較散,呈鑲嵌式分布,主要分布于低丘緩崗及各個子流域中。水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河流流經區域,一部分于湖泊及水庫,例如萬安水庫、峽江水庫等,水域分布具有較高的集中性。建設用地分布較散,但具有一定集中性,主要分布在城市及周邊區域。未利用土地面積最少,分布稀疏,處于流域偏僻位置。

圖1 1980—2018年贛江流域土地利用
3.2 土地利用變化分析
1980—2018年贛江流域各時期土地利用類型占有率見圖2。

圖2 土地利用類型占有率
由圖2可知,贛江流域土地類型占有率變化幅度較小。耕地面積占有率不斷下降,僅2000—2005年有所增加,增幅為0.02%,面積增加了19.2 km2,耕地面積共減少622.9 km2,占有率下降幅度為0.78%。林地面積在1980—2018年同樣呈減少趨勢,僅在1990—2000年面積增加了170.8 m2,占有率提升0.22%,之后一直減少,占有率下降幅度為1.15%。草地面積在1980—1990年有所增加,面積增加了222.8 km2,占有率增幅為0.28%,2000—2010年持續減少且趨于平緩,面積共減少了261 km2,占有率下降幅度為0.33%,之后草地面積少量增長,共增加310 km2,占有率增幅為0.39%。水域面積變化平穩,變化幅度較小,面積共增加95.1 km2,占有率增幅為0.12%。建設用地面積變化最大,且變化速度不斷增加,到2018年面積共增長1 208.6 km2,占有率增幅為1.52%。未利用地面積變化較少,共減少39.5 km2,占有率下降幅度為0.05%。
3.3 土地利用動態度變化分析
1980—2018年贛江流域各時期土地利用動態度見表1。

表1 土地利用動態度
由表1可知,從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來看,耕地動態度僅在2000—2005年為正,增速為0.019 %/a,其余時期均為負值,在1990—2000年減少的速度最快,速度達到-0.053 %/a。與其他時期的減少速度比,增長速度絕對值較小,說明該時段的耕地面積短暫增加對耕地面積的整體減少趨勢影響微小。林地動態度僅在1990—2000年處于增加階段,增速為0.033 %/a;其余階段林地面積均呈減少趨勢,且在2015—2018年林地減少的最快,動態度為-0.098 %/a。草地面積在1990—2010年基本以相同的速度減少,大致為-0.3 %/a。2010年之后年動態度轉為正值,且2010—2015年增速達到最大值1.423 %/a。水域面積在1980—2000年減速增加,1980—1990年動態度最大為0.419 %/a,之后2000—2018年水域面積整體呈現振蕩式變化,面積總體變化不大。建設用地面積在1980—2018年持續增加,且動態度不斷增大,在2015—2018年增速最大,為5.896 %/a。建設用地面積加速增加,反映了城市化的加速發展。未利用地面積整體呈減少趨勢,且在1980—1990年動態度絕對值最大,為-7.502 %/a。從整體土地利用動態度來看,1980—2018年贛江流域綜合動態度逐漸增加,并在2015—2018年綜合動態度達到最大0.329 %/a,說明贛江流域土地變化在逐漸加快。各類土地利用變化幅度具有差異,耕地和林地動態度變化趨勢大致保持一致,不斷減少。草地和水域動態度呈震蕩變化,總體為增加趨勢。建設用地動態度不斷增加,處于一個較高水平。
3.4 土地利用轉移分析
由于贛江流域研究區未利用地占地面積較少,僅在1980—1990年存在一個較明顯變化,主要為未利用地轉為耕地面積,其余時期面積變化較少,因此本文不對未利用地展開具體分析。圖3表達了贛江流域土地利用在各時期的轉化比例。

a)1980—1990年
由圖3可知:1980—1990年,土地利用變化主要以林地、草地相互轉化。草地面積共增加222.78 km2,主要由林地轉入,轉入面積為195.85 km2,占草地增加面積88%。1990—2000年,土地利用變化主要以耕地、林地、草地之間轉化。其中林地面積變化最大,共增加170.82 km2,主要來自草地轉入面積127.89 km2,其次來自耕地轉入面積57.58 km2。該階段林地面積增加,主要來自退耕還林的影響。同時這兩時期水域面積均為轉入,轉移面積主要來自耕地,受退田還湖政策影響。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土地利用轉移類型比較一致。主要為林地和草地輸出,建設用地不斷輸入,耕地面積既有輸出也有輸入,整體變化不大,其他類型土地變化較少。建設用地輸入主要來自耕地和林地,2000—2005年118.1 km2耕地面積以及19.2 km2林地面積轉為建設用地,2005—2010年134.2 km2耕地面積以及112.7 km2林地面積轉為建設用地,導致此期間建設用地面積增加。同時兩時期分別有99.7、84.8 km2林地面積轉至耕地面積,導致耕地面積大致不變。此外有少量草地轉向林地。此時期城市化進展開始表現。2010—2015年和2015—2018年以林地和耕地的輸出型轉移為主導。2010—2015年299.1 km2林地轉為草地;169.3 km2耕地轉為建設用地;同時林地也有147.5 km2轉向建設用地,反映該時期建設用地向林地的擴張。僅少部分的草地移向建設用地。2015—2018年建設用地輸入來源主要為耕地和林地,分別為228.3、102.6 km2。同時部分林地轉向草地,且少量的林地由耕地轉入。這2個時期的土地利用變化反映了建設用地在不斷擴張,城市化進展較快。
3.5 重心遷移分析
贛江流域1980—2018年各類土地類型的區域重心,見圖4。

圖4 土地重心遷移軌跡
通過圖4可知,在此期間贛江流域各類土地利用重心均發生了一定變化,重心變化較明顯的為草地、水域和建設用地重心,其中建設用地重心遷移最為明顯,這與社會發展及人類活動有很大的影響。耕地和林地由于面積占比較大,導致重心遷移不明顯,僅存在微小變化。重心遷移變化與土地利用實際情況較為吻合。因此本研究對重心變化較明顯的草地、水域和建設用地展開具體分析,結果見圖5—7。

圖5 草地重心遷移軌跡
贛江流域草地重心在1980—2018年大致表現為向西北方向遷移(圖5)。重心遷移軌跡在緯度上遷移0.012°,在經度上遷移0.022°。其中1980—1990在緯度上發生驟變遷移0.021°,2010—2015年在經度上遷移較大為0.015°。造成草地重心遷移的原因是1990—2010年期間贛江流域上游草地面積一直縮減,直到2010年之后動態度提高,草地斑塊逐漸增加導致重心呈以上遷移變化。
贛江流域水域重心在1980—2018年大致表現為向西南方向遷移(圖6)。重心遷移軌跡在緯度和經度上均遷移0.021°。遷移軌跡主要分為兩部分,在1980—1990年重心向東北方向移動,其中在緯度上遷移0.025°,經度上遷移0.007°;第二部分為1990—2018年向西南方向移動,在緯度上遷移為0.046°,經度上遷移為0.028°。造成水域重心遷移的主要因素是在此期間贛江流域13座大型水庫面積均有增加,很大原因歸因于政府對贛江流域新建堤防等治水工作導致重心遷移變化。

圖6 水域重心遷移軌跡
贛江流域建設用地重心在1980—2018年大致表現為向東南方向遷移(圖7)。重心遷移軌跡在緯度上遷移0.055°,在經度上遷移0.042°。遷移軌跡變化最明顯的在2005—2018年重心一直向東南方向移動,其中2015—2018年變化最快,在緯度上遷移0.096°,經度上遷移0.019°,其中該時期緯度變化在所有變化中最大,造成如此巨大的重心變化與高度城市化發展離不開關系,其重心變化軌跡與城市發展方向大致吻合,以南昌、新余、撫州三市構成核心區域,發展格局顯示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

圖7 建設用地重心遷移軌跡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通過本文研究可知,贛江流域土地利用存在較明顯差異。在研究期間,贛江流域建設用地面積變化最大,耕地林地次之。但由于耕地、林地占流域絕大部分面積,導致在重心研究中其遷移不明顯。土地類型中耕地和林地變化趨勢大致相同,不斷向建設用地轉移,總體呈減少趨勢。主要因為中國經歷了工業化發展,森林面積遭到砍伐,林地面積減少,直到后續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重視,為保護生態環境,人工造林和退耕還林等措施逐步實施和完善,從而面積有所控制[18]。2004年在實施了“中部崛起”戰略后,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直接使城市建設用地激增,江西省積極推進加快南昌、贛州和九江都市區等建設,因此贛江流域建設用地在不斷擴張,部分耕地被擠占為建設用地,建設面積不斷增加[19]。水域面積變化主要表現在圍湖造田上[20]。贛江流域對應的各類用地重心均發生一定遷移。因此結合本流域土地利用遷移研究,提出以下區域發展策略:贛江下游城鎮化較高,城市建設導致用地矛盾,應進行城鎮、工業、農村整合。更加聚集高效、節約集約,加大生態建設保護。以“三屏筑底”圍繞贛東-贛東北、贛西-贛西北、贛南的山地丘陵地區,筑牢3個森林生態安全屏障。水域依托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河五大河,構建區域生態廊道。同時嚴守耕地紅線確保糧食安全,遏制農業向建設用地轉化。在城市化的發展同時保證土地資源有效利用,加強生態建設和生態保護。
4.2 結論
a)贛江流域主要以林地、耕地分布為主,草地、水域、建設用地、未利用地為輔的分布格局。隨著城市化進展,林地、耕地面積不斷減少,草地先減后增,水域整體呈緩慢增長趨勢,建設用地不斷增加,到2018年建設用地面積是1980年的1.9倍。
b)贛江流域整體動態度逐漸增加,土地變化在逐漸加快。各類土地利用變化幅度具有差異,耕地和林地動態度變化趨勢大致保持一致,不斷減少。草地和水域動態度呈震蕩變化,總體為增加趨勢。建設用地動態度不斷增加。
c)1980—2018年贛江流域各類用地均發生一定轉移。其中建設用地面積不斷增加,主要來源耕地和林地的轉入;同時部分林地、草地向耕地補充;水域變化不大,主要受退田還湖的影響,導致部分耕地的轉入。總體來看贛江流域主要以耕地、林地輸出,建設用地不斷輸入,且隨著城市化進展,建設用地輸入不斷增加。
d)隨著贛江流域土地利用的變化,各類土地重心對應均發生一定遷移,其中變化較明顯的是草地、水域、建設用地重心。其中建設用地重心在2015—2018年變化顯著,充分表明城市化的高度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