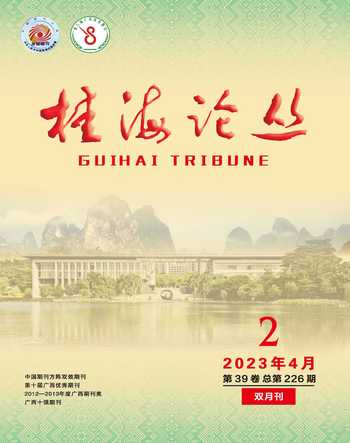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及其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意義
曾俊
摘要:馬克思對勞動問題的研究揭示了勞動形態發展與文明形態演進之間的內在聯系。而文明形態與勞動形態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哲學、社會學等學科關注的焦點問題。借助馬克思的對象化勞動理論透視勞動形態對于文明形態的建構作用,可以發現當代數字化勞動不僅印證了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所構想的社會發展趨勢,更為未來新形態“聯合勞動”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故而,對象化勞動理論不僅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更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提供了方向性的啟示。
關鍵詞:對象化勞動;數字化勞動;聯合勞動;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圖分類號:C97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494(2023)02-0046-11
基金項目: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資本論》元倫理思想研究”(YB2022001);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馬克思倫理思想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徑研究”(2022J0546);西南林業大學人文社科校級科研項目“元倫理學視野下的唯物史觀倫理邏輯研究”(WKQN109)。
“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1],恩格斯在為《資本論》所作書評中提出的這一論斷,闡明了勞動關系在社會形態建構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勞動問題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生所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的探索過程中,始終關注勞動形態的演變與發展。從對雇傭勞動關系的批判,到對象化勞動現象辯證運動的剖析,再到對聯合勞動制度的構想,馬克思對于勞動形態的研究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指明了方向。
將勞動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科學概念加以研究是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擴張而展開的。英國早期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提出“所有物品都是由兩種自然單位——即土地和勞動——來評定價值”[2],從而將勞動置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位置。配第認為國家政策特別是賦稅政策應該向創造財富的人口傾斜,從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國家的勞動人口。在配第的理論中,“勞動”作為經濟學概念開始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論域中“出場”,其后斯密、穆勒、李嘉圖等人也繼承了配第對于勞動概念的基本經濟學立場,以勞動為出發點展開政治經濟學研究。同時,在哲學領域,黑格爾也對勞動概念展開了哲學反思,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以勞動為中介,通過主奴關系的辯證運動,在個體層面上確證了人的自我意識形成機制。他認為,“奴隸據以陶冶事物的形式由于是客觀地被建立起來的,因而對他并不是一個外在的東西,而即是他自身;因為這形式正是他的純粹的自為存在”[3]。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更進一步指出,市民社會以個人與他人之間的勞動交換作為建構基礎,即“通過個人的勞動以及通過其他一切人的勞動與需要的滿足,使需要得到中介,個人得到滿足——即需要的體系”[4]。黑格爾通過在人的交往關系中理解勞動,首次將勞動對于社會關系的建構過程納入哲學研究的視野當中。可以說,配第等人以對勞動概念的經驗性理解重塑了政治經濟學;黑格爾以對勞動概念的超驗性闡釋重構了哲學視域下的社會發展理論。
與前人相比,馬克思既不是單純從經濟學角度對勞動進行經驗性的分析,同樣也不單純從哲學角度對勞動概念進行思辨理解,而是從哲學、經濟學乃至社會學等各個層面對勞動概念進行綜合性的闡釋。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起關鍵作用的雇傭勞動關系作為切入點,揭示了基于特定物質生產活動的雇傭勞動關系對于生產關系的重塑。在此過程中馬克思對于雇傭勞動關系內涵的認識產生了兩個方面的“跨越”。
馬克思將對勞動的理解從“主體性”層面跨越到了“主體間性”層面。無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是黑格爾哲學,都傾向于突出勞動的“主體性”,也就是將勞動視為個人的獨立性事務。如洛克認為“盡管原來人人所共同享有權利的東西,在有人對它施加勞動以后,就成為他的財物了”[5]。黑格爾哲學認為,勞動一方面是人通過自我限制欲望而將自身意識之內的各種精神形式賦予自然物,另一方面是將自己精神“對象化”的活動。換言之,是將勞動者視為魯濱遜式的人物,獨自面對物。從中可以發現,無論是政治經濟學還是黑格爾哲學,都是停留在人與自然物之間關系層面上看待勞動,只看到單個的人與自然物之間發生的改造關系。而馬克思則通過雇傭勞動關系透視人的社會關系,換言之,在人與物改造關系背后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塑造的關系。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得以建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各種現實勞動組成的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6]704。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最基礎的層面上表現為人與其他勞動者的勞動關系,故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人的勞動“只有被下一步勞動使用,它才是使用價值”[7]329。列寧對此總結道:“凡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交換商品)的地方,馬克思都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8]正是現代勞動這種環環相扣的聯系性,構成了現代人處于高度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之中,只有在與他人的協作中,勞動的價值才能得到體現。因而雇傭勞動關系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征,同時也體現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關系的特征。
馬克思將對勞動活動的理解從“辯證抽象活動”跨越到了“現實歷史性活動”。馬克思始終從歷史角度看待勞動,將雇傭勞動視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歷史性勞動形態,并不是如黑格爾那樣對勞動活動的歷史性進行諸如“主奴關系”那樣的抽象思辨闡釋,而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角度看待勞動,探尋勞動組織形式與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關系模式之間的內在關聯。馬克思強調勞動中的經驗性內容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機械唯物主義闡釋,而是將勞動的經驗性內容作為前提,凸顯出人類勞動對于人類社會的基礎性建構作用。如在評論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模式時,馬克思指出:“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9]95
基于對雇傭勞動關系在“主體間性”與“歷史性”兩個維度的理解,馬克思建構了對資本主義勞動形式的闡釋框架,并從中揭示了雇傭勞動關系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構作用。但馬克思并未止步于對雇傭勞動關系建構作用的經濟學分析,而是將其進一步拓展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領域。馬克思勞動觀的創新點就在于從雇傭勞動這一經濟學現象背后,發現了對象化勞動對于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基礎性建構作用。馬克思認為,“對象化勞動,即在空間上存在的勞動,也可以作為過去的勞動而同在時間上存在的勞動相對立”[7]230。在資本家所擁有的對象化勞動與勞動者自身活勞動的對立關系中,產生了建構新勞動模式的巨大張力,驅動著勞動形態不斷向前發展。這一驅動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象化勞動在勞動形態發展中所發揮的驅動作用,表現為對象化勞動對活勞動的抽象統治。對象化勞動不僅意味著過去的勞動以空間形式呈現出來,而且意味著過去的勞動對于現實活勞動的宰治。在簡單再生產過程中,對象化勞動以勞動資料、勞動工具的形式出現,也是資本家得以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前提,馬克思指出:“對他人勞動的過去的占有,現在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新占有的簡單條件。”[10]106但是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與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資本家對于高效率占有剩余價值的追求,對象化勞動作為勞動資料投入生產過程中,更多地被作為固定資本而吸納。“勞動資料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即機器體系;自動的機器體系不過是最完善、最適當的機器體系,只有它才使機器成為體系),它是由自動機,由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推動的。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當做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6]773,由此導致的問題是人的活勞動從兩個維度受到對象化勞動的擠壓。從共時態層面來說,人的活勞動要依賴對象化勞動所提供的生產資料而展開勞動活動;從歷時態角度而言,對象化勞動所形成的機器這一固定資產,正越來越多替代在商品制造過程中所需要的人的必要勞動。也就是說在勞動的過程中,人的活勞動所占據的比重越來越小,而機器本身所發揮的力量越來越大,因此在勞動過程中,原本居于主導地位勞動被機器所排斥,“對工人來說,知識表現為外在的異己的東西,而活勞動則從屬于獨立發生作用的對象化勞動。只要工人的活動不是[資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為多余的了”[6]776。這一現象背后所體現出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原本作為勞動過程主體的活勞動被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不斷替代,勞動創造價值的力量被過去的勞動所占用。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
第二,對象化勞動在勞動形態發展中的驅動作用,還表現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過程的“同一性”。馬克思認為,提高勞動生產力必須在最大限度上否定工人的必要勞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提高勞動生產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勞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資本的必然趨勢。勞動轉變為機器體系,就是這一趨勢的實現。”[6]775那么,為何資本主義社會提高生產力必須以否定必要勞動作為根本追求?眾所周知,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力向前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渴求,生產剩余價值的方式主要包括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在商品價值一定的情況下,工人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所占比例成反比,因此為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必須壓縮必要勞動或延長勞動時間以實現這一目標。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就是在必要勞動不變情況下,盡可能延長工作日時間以獲得更多剩余勞動。但每天所能延長的勞動時間受物理時間長度的限制,使得資本無法無限制地通過延長勞動時間而獲取剩余價值,因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對提高剩余價值量的有限性而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放棄。在馬克思看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是“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9]366。通過這種方式提高剩余價值量不存在任何物理和時空界限,因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我們在這里一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9]366。由于通過不斷縮短工人在勞動中必要勞動時間以獲得在單位勞動時間內更大的剩余價值比例,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因而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獲取剩余價值的最主要手段。在此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之間的張力,成為機器生產技術不斷發展的最主要動力。而實現機器的不斷發展依靠的是技術的不斷進步,固定資本的發展依賴的是科學的不斷進步,即“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6]777。馬克思在此揭示了現代社會科技飛速發展的驅動力在于資本對剩余價值的不斷追求。也就是說,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被異化為追求更多剩余價值的工具與手段。因為“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的時候,機器體系才開始在這條道路上發展”,而且“發明就將成為一種職業,而科學在直接生產上的應用本身就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性的和推動作用的著眼點”[6]782。因而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本質上是圍繞如何降低必要勞動在勞動過程中的比例這一主題而展開。
第三,對象化勞動在勞動形態發展過程中的驅動作用,表現為從客觀上為勞動者創造了更多的自由時間,為勞動的解放創造了物質條件。正是出于對相對剩余價值的不斷追求,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才通過不斷提升固定資產的技術水平,以更大程度上壓縮生產過程中必要勞動的消耗量。這一趨勢不僅意味著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高度對立,而且意味著新的社會形式與勞動形態呼之欲出。資本在不斷通過固定資產提升勞動生產力、降低勞動過程中工人必要勞動的同時,也在不自覺地為新的社會形態開辟發展空間。馬克思認為,“資本在這里——完全是無意地——使人的勞動,使力量的支出縮減到最低限度。這將有利于解放了的勞動,也是使勞動獲得解放的條件”[6]779。但需要注意的是,資本對于勞動時間的縮短不能簡單理解為工人閑暇時間增多。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必要勞動量的減少,一方面意味著工作崗位的減少,生產過剩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意味著簡單直接勞動減少,而勞動的復雜程度在不斷增加。這是因為,一方面,簡單勞動越來越多被固定資產的生產活動所取代;另一方面,操作不斷更新的固定資產,需要越來越復雜的勞動。資本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6]786。資本所創造的工人的自由支配的時間不是閑暇時間,而是有待于被進一步轉變為剩余勞動的時間。因此,馬克思認為,“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6]787。為了進一步占有更多剩余勞動時間,資本必須占有勞動者新產生的自由支配時間,而其依賴的方式是提高固定資產的自動化水平,進一步壓縮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必要勞動時間。勞動者自由支配的時間是活勞動的源泉,而固定資產乃是對象化勞動不斷凝結的產物。二者之間的對立產生了巨大的張力,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向前發展,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容納二者之間產生的巨大張力時,勞動者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余勞動,剩余勞動在生產關系中不再作為必要勞動(活勞動)的對立物而存在,這也意味著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之間對立的最終消解。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從雇傭勞動關系研究轉向對象化勞動分析,不僅代表著馬克思勞動思想研究的理論轉向,更意味著勞動理論從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理論,轉變為文明形態的建構理論。馬克思不但從資本社會勞動形式中發現了對象化勞動與活勞動之間的矛盾,更通過對這種矛盾的分析,發現了以雇傭勞動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以自由勞動為主體的人類新形式文明形態所取代的歷史發展趨勢。這對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具有重要啟示作用。
當代勞動形式發生的最重要變革,莫過于勞動的數字化。數字化勞動自21世紀以來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產業變革、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革,在短短幾十年間幾乎徹底改變了社會基本面貌與勞動一般模式。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數字化勞動所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是否顛覆或改寫了馬克思的對象化勞動理論?對此問題需要認識到,雖然數字化勞動從產業、技術與經濟等領域來說,對勞動模式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但從對象化勞動理論的視角而言,數字化勞動不但沒有超越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的范疇,反而是對象化勞動辯證發展過程具有時代性的“印證”。對此,我們可以從數字化勞動的“變”與“不變”兩個方面進行闡釋。
(一)數字化勞動“變”的特征
數字化勞動的變革特征突出表現于對于勞動活動的“壓縮”。這種“壓縮”分別存在于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之上。
第一,數字化勞動在時間層面上的“壓縮”直觀地體現為對人的重復性活勞動時間投入的壓縮。人工智能技術極大減少了人的活勞動消耗,意味著機器不僅從體力上實現了對人的替代,而且從智能上也實現著對人的部分替代。然而與數字化勞動一樣,人工智能技術也沒有徹底超越馬克思的勞動理論,馬克思通過固定資產分析預測了這一現象,“它們是人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6]785。人工智能本質上是對人之感性層面、知性層面上的概念、邏輯以及其相互之間關系進行判斷行為的模擬,目前為止人工智能技術仍未超越知性層面,也無法自行產生概念,但其進行判斷與處理概念的活動卻能以遠高于人腦的速度進行。人工智能雖然不能替代人的理性思維,卻能以更好的效率完成人的知性反思活動,由此導致機器能夠以一種類似于人的思維方式介入勞動過程,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效率,在時間層面上壓縮人的活勞動。因此,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模擬人思維的技術,其本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機器自動化水平。人工智能以更快的反應速度替代了人的相關勞動,從而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大幅壓縮了人的勞動時間。
第二,數字化勞動在空間層面上的“壓縮”作用具體體現為對生產所需物質性的勞動資料的壓縮。數字勞動是“在數字生產方式下產生,并能夠形成一定的生產后果的活動”[11]。當前學術界對于數字化勞動的類型爭議較大,有各種類型的區分方法。按照余斌的觀點,對數字化勞動的類型的界定雖然很多,但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化勞動是指以下兩類勞動:一“是指運用數字技術開發軟件、設計制造硬件、收集和加工數字信息產品,以及進行其他生產的勞動”[12]79;二“是指生產信息通信設備和開發相關軟件、提供數字內容以及鋪設信息通信網絡等方面的勞動”[12]79。
第一種類型的數字化勞動是運用數字技術開發、生產有形產品(如計算機、通信設備硬件,或是經過數字技術加工過的產品等),第二種類型的數字化勞動是運用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生產無形的數字化產品(如軟件、數據信息服務、網絡傳媒文化產品等)。二者的顯著區別在于其最終產品,前者為傳統經驗性有形產品,能夠在時空中存在;后者為無形數據產品,既能夠在數據存儲設備中存在,也能通過打印機、數控機床等設備加工轉化為現實產品。在數字化勞動中,人的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產品不再必須是占據一定空間的物質性的產品,而可以體現為數據資料、數字資產、數字服務等無形的勞動成果。這種空間性的“壓縮”作用,對于生產過程而言無疑可以將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存儲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本壓縮到最低程度,也能將數字化勞動資料的循環速度提升至最高水平。總之,數字化勞動對勞動資料在空間維度的“壓縮”,大幅度地提高了生產效率,甚至改變了生產模式、勞動形式乃至社會面貌。
(二)數字化勞動“不變”的特征
數字化勞動對于現代化生產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的基本形態。在勞動關系(雇傭勞動)、勞動價值歸屬(剩余價值)與勞動發展趨勢(自由勞動時間增加)層面上,均沒有突破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所劃下的界限。
第一,從關系層面來說,數字化勞動本質上仍然是以雇傭勞動為主要形式的勞動模式,并未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數字化勞動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而言,帶來的最大改變是勞動資料的虛擬化、非物質化,并在此基礎上導致了人的勞動形式發生了巨大改變。但這種改變主要發生于具體的生產形式領域,沒有對作為資本主義勞動本質屬性的雇傭勞動關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由于數字化勞動在時間與空間層面上對于生產過程物質性要素的“壓縮”,使得傳統工業生產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數字化生產對于時間、空間條件的要求越來越少,“碎片化”的分工體系、靈活的工作時間分配制度,使得勞資雙方的雇傭關系隨意性更強,大量臨時性崗位、外包工作等新型勞動組織形式快速興起。但勞動時間空間因素的改變并不意味著雇傭關系的改變。無論數字化勞動中勞動者以何種形式展開勞動,都是在一定的雇傭關系中產生,都需要以貨幣來計量數字化勞動的價值。而在雇傭勞動關系中,以貨幣計量的勞動價格,仍然存在著資本家對于數字化勞動者所創造的產品中剩余價值的占有。因此,只要數字化勞動還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存在,還以貨幣來衡量勞動價值,剝削現象就仍然存在,因為“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代價勞動”[9]619。
第二,從價值歸屬層面來說,數字化勞動本身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者受剝削的境遇。如前所述,數字化勞動仍然是一種雇傭勞動,其中存在著剝削現象。因此,數字化勞動仍然會產生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勞動。但數字化勞動中由于運用了大量高新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使得人們產生這樣的錯誤認識:即新技術的大量使用使得人的勞動強度大大減輕,從而使得科學技術替代人成為剩余價值的創造者。如哈貝馬斯在20世紀就曾經斷言:“當科學技術的進步變成一種獨立的剩余價值來源時,在非熟練的(簡單的)勞動力的價值基礎上來計算研究和發展方面的資產投資總額,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而同這種獨立的剩余價值來源相比較,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價值來源,即直接生產者的勞動力,就愈來愈不重要了。”[13]哈貝馬斯對于科學技術對生產的促進作用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并認為科學技術替代勞動者成為剩余價值的來源。但哈貝馬斯顯然是從單純體力勞動耗費層面上理解剩余價值的產生,在他看來,技術進步帶來的體力勞動耗損的減輕就代表著剩余價值剝削的減輕。但馬克思并不是單純以體力耗損來衡量剩余價值的剝削程度,而是從對勞動者本身奴役程度、損害程度來衡量剝削。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14]53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則進一步指出:“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的手段、剝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貧窮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壓制。”[9]579馬克思甚至認為,資本主義工業與農業的任何進步,都是對勞動者與土地掠奪技巧的進步。由此可見,馬克思從不認為生產效率的提高能夠減輕勞動者受剝削的程度,也不認為科學技術本身能夠創造剩余價值。相反,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科技的進步將加深勞動者受奴役、剝削的程度。這是因為勞動者受剝削的程度并不完全取決于體力勞動的耗費,生產技術的進步的確會大大減輕勞動者體力勞動強度。但是技術的進步也意味著掠奪勞動者剩余價值能力的進步,勞動者在高技術勞動資料所創造的勞動環境下,需要付出更多的智力、腦力。因此,從受奴役的角度來看,生產效率的提高不代表奴役程度的減輕,反而可能意味著奴役程度的加深。數字化勞動一方面將人的體力勞動降低到了極低水平,另一方面卻對勞動者的智力、創造力、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勞動者在數字化勞動中的腦力勞動強度也沒有明顯減輕,甚至與馬克思時代的體力勞動者相比,其勞動時間沒有變化甚至有所增加。因而,數字化勞動不僅仍然存在著剝削現象,而且剝削程度相比于馬克思時代的勞動者沒有明顯地降低。
第三,從發展趨勢上看,數字化勞動本身仍然體現著對象化勞動的特征,是對象化勞動在當代具有時代特征的表現形式,表征著對象化勞動的發展趨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工人所創造的對象化勞動,不僅被資本家所占有,而且在資本家追求相對剩余價值的過程中,代表對象化勞動的“不變資本”,不斷壓縮代表工人活勞動的“可變資本”的生產空間,使得勞動者日益被貶低為機器的附屬物。而對于數字化勞動所依賴的高技術軟件與硬件設備而言,它們同樣是對象化勞動的產物。以數字化勞動中的人工智能技術為例,現今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技術所依賴的程序與算法都來源于人的勞動實踐,是將人的行為方式、思維模式以程序的形式記錄下來,再以這種程序作為機器語言而使機器能夠模擬人的行為方式與思維模式,從而替代人的各種重復勞動。從本質上說,數字化勞動所依賴的機器,與馬克思時代的工業機器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更為精密、效率更高、用途更為廣泛。數字化勞動并不是對對象化勞動的揚棄,恰恰相反,數字化勞動的發展趨勢與對象化勞動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對象化勞動的發展趨勢是在勞動過程中,不斷壓縮人的活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按馬克思的話說,是“單個勞動能力創造價值的力量作為無限小的量而趨于消失”[10]186。大量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的數字化勞動,將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人力壓縮到最小,同時產品與生產者的直接需要也近乎消失。在數字化勞動中,勞動者所消耗的活勞動被壓縮到了最小,以致于在數字化勞動中所創造的價值被誤認為是數字化勞動資料自身所創造的價值,如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個性化數字內容閱讀推送、計算機輔助設計,甚至某些工業仿真軟件的計算能力,已經超越人力所能達到的極限,成為工業設計不可或缺的關鍵工具。可以說,在數字化勞動中,人的活勞動或者說體力勞動越來越被壓縮到幾乎忽略不計的狀況。對象化勞動的發展趨勢是將人納入機器固定資產體系中,這一趨勢也在數字化勞動中得到印證。馬克思曾指出:“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10]185人的勞動不僅與作為固定資本的對象化勞動對立,而且日益被固定資本所束縛,成為機器體系的一個部分,甚至成為生產體系的從屬性要素。數字化勞動同樣反映了這一趨勢,數字化勞動中的硬件與軟件,例如,計算機、網絡、應用程序等等,都是作為人的知識與技能的積累在生產過程中存在。同時人在數字化勞動中又高度依賴數字化的勞動工具,甚至以數字化勞動工具作為中介與他人協作勞動。在此過程中,計算機、網絡不是作為人肢體、器官的延伸,而是人的勞動活動“從一切方面來說都是由機器的運轉來決定和調節的”[10]185。在此意義上,人的勞動活動被進一步納入數字化勞動體系中,作為整個社會生產過程中從屬性要素而存在。因而,數字化勞動不但沒有超越對象化勞動活動,反而是對象化勞動活動在當代的具體體現。
綜上,數字化勞動雖然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大幅度壓縮了勞動資料物質形態,并加速了資本的循環速度,在此基礎上改變了社會生產面貌,乃至于人的勞動方式。但數字化勞動本身并未超越雇傭勞動關系的范疇,也沒有消滅剝削,消滅剩余價值。不僅如此,數字化勞動本身就是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具有時代性的表征,代表著對象化勞動發展的高級形態,預示著自在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向自為形式的自由勞動轉化重要轉折點的到來。而數字化的勞動作為一種自在形式的勞動,必須在“聯合勞動”的勞動形式下才能真正展現。而“聯合勞動”作為揚棄私有制的勞動形式,正是通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建構過程得以展現。
在馬克思的對象化勞動理論中,正是在勞動的不斷對象化過程中,雇傭勞動關系乃至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被揚棄。高度自動化機器的大規模使用,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壓縮工人的勞動時間同時,也在客觀上增加了工人自己掌握的時間。這一趨勢的產生源于資本內在的矛盾性,一方面不斷將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卻將勞動施加作為財富的源泉。資本在喚起科學和自然的力量使財富創造越來越少依賴于勞動時間的同時,卻又用勞動時間來衡量科技創造出的巨大社會力量,資本將科學技術的發展成果作為自我增殖的手段,但馬克思認為,“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6]784。也就是說,數字化勞動作為高級形態的對象化勞動形式,在自為地充當資本不斷增殖手段的同時,也在自在地成為資本關系自我消解的“催化劑”。
對象化勞動在其發展過程中,無意識地為“自由自覺”的勞動創造了物質條件。數字化勞動的出現正反映了這一趨勢,雖然從本質上說數字化勞動仍然是一種具有剝削性質的雇傭勞動形式,但數字化勞動創造的對象化勞動成果卻在客觀上為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形式(即“聯合勞動”)創造了客觀的物質基礎。這一過程不是一廂情愿的理想,而是具有歷史科學依據的必然規律。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偉大歷史方面”就是創造剩余勞動,而占有剩余勞動的“致富欲”,驅使資本不斷通過對象化勞動,使勞動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最終會使整個社會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要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更為科學對待再生產過程。實現這兩個方面之后,“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10]69。這從理論層面上描繪了通過對象化勞動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退場”的歷史科學原理。而在現實層面上,馬克思認為對象化勞動過程所導致的固定資本的不斷膨脹與集聚,最終將會導致資本的“社會化”,從而揚棄生產資料私有制。但是這一揚棄過程恰恰也是從作為資本關系高級形式的信用制度建立而開始。
馬克思在論證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作用時指出,信用發揮著雙重作用,其一是將剝削行為發展為一種巨大“欺詐”制度,減少剝削階級人數;其二是造成資本主義制度轉向“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后者發揮作用的主要形式便是股份公司的成立,在馬克思看來“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同時,以前曾經是政府企業的那些企業,變成了社會的企業”[15]494。生產規模的驚人擴大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在以“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為主要形式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擴大生產規模的主要方式就是固定資產數量和質量的不斷增大。這就要求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投入更多的資本,而單個資本家所具有的資本已經不能滿足固定資產的規模擴大,資本家被迫采用聯合的方式擴大投入生產過程中的資本規模,由此導致的是私人資本具有了“社會化特征”,多個投資者聯合出資所形成的“社會資本”與單個資本家所擁有的“私人資本”產生了對立,并且由于前者擁有更大規模的固定資產,具有更強的攫取剩余價值的能力,導致后者不斷被前者所轉化。由此產生的后果是有眾多投資人的“社會資本”無法由某一個資本家所掌控,真正擁有資本控制權、執行資本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職業經理人,而其他資本家則退出了直接生產領域,成為單純的食利者。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對于對象化勞動的分析,不難看出,勞動的不斷對象化,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驅動力已經超出單個資本家的控制,成為凌駕于資本家與勞動者之上主導社會生產的力量。因此對象化勞動的不斷集聚,在將工人必要勞動時間壓縮到最短的同時,也將資本家逐出了直接的生產管理過程。股份公司這種企業形式的出現,是單個資本家被動退出生產管理過程,這為工人成立“合作工廠”奠定了基礎。二者都“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15]499。“合作工廠”是“股份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在“合作工廠”中進一步揚棄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與之配套的雇傭勞動。馬克思進而指出,“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勞動工具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16]。從中馬克思向我們展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中的勞動特征,即在揚棄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雇傭勞動的基礎上,實現在自由人聯合占有生產資料前提下,勞動者自覺自愿的“聯合勞動”。
可以說,正是由于數字化勞動的出現,印證了對象化勞動在其發展過程中不自覺為勞動的解放創造條件的論斷。當代數字化勞動一方面是對象化勞動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另一方面由于高度的自動化、智能化,又為人自由自覺的“聯合勞動”創造了條件。因此,探索“聯合勞動”如何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過程中發揮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此,我們可以從人類文明新形態建構所涉及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等五個層面上,透視“聯合勞動”所具有的文明形態建構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建構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在當代具有現實性、時代性的表征。這種表征又具體體現在“聯合勞動”形態對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與生態文明發展所具有的“建構性”上。
第一,在物質文明層面上,“聯合勞動”形態的“建構性”體現為揚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制度性切入點。馬克思認為,“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14]160。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和發展首先是以物質文明作為基礎的。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以創造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作為勞動的終極目的,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勞動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目標,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以獲取剩余價值為勞動的最終目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可避免會導致勞動的不斷對象化,并且對象化后的勞動將會有很大一部分作為生產資料再次投入生產過程中。但與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不同在于,對象化之后的勞動并不是歸資本家個人所有,并異化成為資產階級奴役工人階級的工具,而是被自由人聯合占有,運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聯合勞動”,而不是雇傭勞動。個人勞動再不是為他人謀利而被迫出賣的商品,再不是生產“異己”的對象化勞動的商品,而是屬于為了自我實現的勞動活動。因而馬克思主義論域內的勞動是人自我實現的手段,而這種自我實現必須在超越了雇傭勞動形式的“聯合勞動”中才能得到體現。唯物史觀為我們指明了未來勞動形式發展的方向就是超越雇傭勞動形式,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聯合勞動”,這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物質文明發展指明了實踐方向。
第二,在政治文明層面上,“聯合勞動”形態的“建構性”體現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的堅實物質基礎。政治文明以建構追求公平正義的良序社會為主要目標。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治文明,其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價值目標,在雇傭勞動現實制度的異化與侵蝕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9]226。資本社會的“公平”建構于其生產方式之上,在雇傭勞動制度下資本家通過支付工資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其“公正性”并不在于資本家是否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而在于其符合雇傭勞動制度,而雇傭勞動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又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只有生產方式或者更具體而言勞動方式的變革,才會導致政治模式的形態的變革。如前所述,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試圖以形式性的“民主”來調和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但這種利益沖突的根源在于剩余勞動被無償占有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因而不可能通過形式主義的“民主”加以解決。這也是當代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虛偽性”與“形式性”的根源所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本質屬性,其特征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之所以能夠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了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揚棄了勞動剝削制度。因此,社會再無因社會總產品分配的不公,而導致的利益集團對立。因而,全社會勞動者的共同利益能夠通過民主政治而得到最大化的體現。以“聯合勞動”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為全過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性”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第二個特征就是其全過程性。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將全體人民均納入民主進程中,而且還將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公共事務納入人民民主的過程之中,并且構建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民主治理體系。這既建立在全國人民追求民主、團結一心、共同治理國家的強大意愿基礎之上,也建立在揚棄了私有制之后勞動者的自由聯合的強大經濟基礎之上。
第三,在精神文明層面上,“聯合勞動”形態的“建構性”體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資本主義文化以“資本”為核心。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4]178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資本作為決定性的物質力量,以資本對勞動者活勞動的無償占有為根本推動力。因此,勞動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承擔的勞動,是一種在分工條件下不自由、不自愿的勞動。文化意識形態創造活動作為一種人尋求自我超越的勞動形式,在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生產體制下也同樣出現“異化”特征。馬克斯·舍勒指出藝術家與學者們之所以屈從于所謂“市民趣味”,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他們認識到,獨立思考的精神與超越功利的良心并沒有那么強大,他們于是選擇屈從于“資本主義精神”。對于藝術家與學者的這種轉變,舍勒所給出的原因在于:“公理一:作為精神文化的某一作品的生產者,我欠經濟社會的若少,則經濟社會欠我所創作出的東西也少。公理二:由于我不以我的創作生產為生,而我是這一經濟社會的成員,所以,我有義務以一種與我的文化活動并行的方式名正言順地養活自己。”[18]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異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精神文化活動的“異化”。
以“聯合勞動”為核心的生產模式,突破了資本社會以“資本”為軸心的生產模式,在精神產品的生產領域,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只有揚棄了資本關系的影響,文學藝術創作才能真正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立足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19]人民既是精神文明的創造者,也是精神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精神文化成果是在人民的歷史實踐中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從人民的立場出發,以人民的生活作為創作導向,以人民的滿意度作為文化創造成敗的根本標準,在精神文化創作的全過程堅持人民主體性。因此,人類文明新形態中以“聯合勞動”為軸心建構起來的精神文明,擺脫了資本關系對于文藝創作的影響,恢復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創作活動之本真形態。只有以“聯合勞動”作為文藝創作活動的主要勞動形態,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精神文化產品的人民性的價值立場,才能建構表征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第四,在社會文明層面上,“聯合勞動”形態的“建構性”體現為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協調發展的關鍵要素。協調性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特征,社會協調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方向。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還要多的生產力。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確實建立在不協調、不正常的勞動關系之上,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勞動“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別人的;勞動不屬于他;他在勞動中也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別人”[14]54。同時,資本家的資本卻“一開始就沒有一個價值原子不是由無酬的他人勞動產生的”[9]672。勞動形式的內在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不可能引領人類社會走向和諧發展的“康莊大道”。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能夠建構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其實現了勞動內在和諧形式有著密切的聯系。
人類文明新形態中的勞動活動,既要在社會共同體層面上實現先進物質文明的發展,又要在主體性層面上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個性的自由解放。內在與外在、個體與共體的協調發展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實現協調發展的前提。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協調發展的前提與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本指引,并不簡單否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在消化和汲取資本文明成果的過程中揚棄資本文明”[20]。在利用一切要素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實現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協調發展。以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消解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異化、物化現象,通過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實現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模式,確保勞動關系的正常化、協調化。在生產與分配過程中,力求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第五,在生態文明層面上,“聯合勞動”形態的“建構性”體現為人與自然關系和解的重要中介。自然是人類勞動得以展開的前提,勞動的形態不僅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表征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其重要特征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獲得了空前的提高。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勞動形式,不僅表現為與人自身的對立,還表現為與自然的對立。人的勞動能力在飛速進步的同時,也造成了人與自然的高度對立。一方面,人類社會勞動形式的發展使得人類在控制自然、開發自然方面擁有無可比擬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無論人的勞動能力發展到何種程度,都無法改變自然作為人勞動活動前提的事實。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的勞動活動,一方面不斷使自然臣服于人的勞動之下,但另一方面,對自然改造能力的提升卻沒有給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以“自由”,反而隨著人類社會改造自然勞動能力的提升,使人更深入地陷入被資本奴役的進程中。馬克思對此進行了批判,“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21]故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形式,從外在方面而言,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從內在方面而言,則導致人與自身關系的對立。
“聯合勞動”超越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緊張狀態,人的勞動活動致力于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與穩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主張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理念的積極體現。這既源于中華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底蘊,又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政治經濟學基礎,正是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實現的“聯合勞動”的形式轉變。馬克思主義主張將以生產資料聯合占有的勞動模式,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體現的雇傭勞動模式。人的勞動不僅成為謀生手段,更從逐利手段的框架中被解放出來,成為人自我實現的重要手段,人的自我實現的重要特征不僅包括內在的、人與自身本質的和解,也包括外在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在揚棄私有制的“聯合勞動”形式下,自然不再作為人奴役的對象,也不會如前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成為“神圣”的存在,而是作為人的自我實現、自由實現的中介,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動中,實現了自身與自然的全面和解。因而,人類文明新形態以“聯合勞動”的形式,展現出生態文明辯證發展的歷史脈絡。從前資本主義社會敬畏自然、為自然所限制的勞動,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奴役自然的勞動,最終在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轉變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勞動,這一進程表征了生態文明在人類文明新形態中所實現的歷史性飛躍。
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文中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14]340這一論斷表明社會文明的發展與勞動形態的變化密切相關。馬克思發現了存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對象化勞動現象,并以此為切入點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全面的批判。對象化勞動既反映了資本取得對勞動抽象統治的歷史發展過程,又為勞動的解放創造了物質條件。當代數字化勞動的發展印證了馬克思對于對象化勞動趨勢的判斷。作為一種高級形式的對象化勞動,數字化勞動為馬克思所設想的“聯合勞動”提供了前提。在此意義上,通過對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的深入研究,不僅能夠揭示勞動形態變化對于社會形態變遷的巨大影響,更能夠對完善文明形態的建構理論起到積極作用。因而馬克思對象化勞動理論在當代所具有的時代價值,將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設實踐中得到充分展現。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
[2]威廉·配第.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貨幣略論[M].陳冬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45.
[3]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賀麟,王玖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90.
[4]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203.
[5]洛克.政府論:下卷[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0.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寧.列寧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4.
[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藍江.數字勞動、數字生產方式與流眾無產階級:對當代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蠡探[J].理論與改革,2022(2):60-72.
[12]余斌.“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5).
[13]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62.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17]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07-02(1).
[18]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M].羅悌倫,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79.
[19]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1-12-15(1).
[20]白剛.真理·道義·文明:中國式現代化的三大制高點[J].吉林大學學報,2022(11):18-28,231.
[2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責任編輯陸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