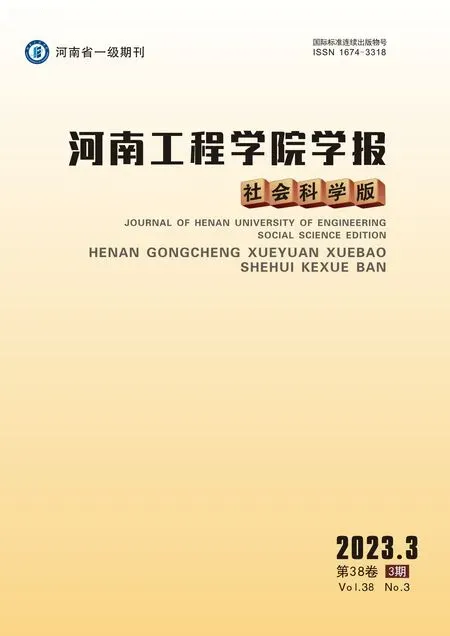草原上的精神家園
——懷舊認知圖式下薇拉·凱瑟的懷舊認知建構
許慶紅,沈 潔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薇拉·凱瑟(Willa Cather, 1873—1947)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評論家視為西部草原的“文化偶像”[1]10,Frus和Corkin也稱贊其“堪與文學行業中的詹姆斯、沃頓、福克納相媲美”[2]206。縱觀凱瑟的作品,其寫作思路于20世紀初發生明顯變化,“隨著20世紀20年代的推進,凱瑟對美國的發展方向逐漸產生疏離感”[3],她的作品也以這個時期為分水嶺。早期拓荒系列作品《啊,拓荒者!》(OPioneers!1913)、《云雀之歌》(TheSongoftheLark, 1915)及《我的安東妮亞》(MyAntonia, 1918)均根植于美國西部大草原,描寫了早期拓荒移民征服邊疆的艱苦奮斗生活,并以細膩的筆觸塑造了亞歷山德拉、西婭、安東妮亞三位女性拓荒者,譜寫了對拓荒時代的頌歌,被譽為“草原三部曲”。
隨著多元化批評話語和包容性闡釋空間的逐漸形成,國內外對凱瑟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漸豐富。“草原三部曲”的女性拓荒者及其所傳遞的對“拓荒精神”的歌頌,也被重置于各種批評視角之下,成為各種“主義”的拓荒:女性主義者的拓荒[4]——在農活重壓之下不忘自主權的女性群體[5],生態主義者的拓荒——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超越男性個人主義的女性環境主義、移民種族主義者的拓荒[6],以及跨文化群體的拓荒[7]。這些闡釋有其合理性:一方面,拓荒本身所蘊含的開拓、進取和創新精神幾乎是現代各個行業、領域和群體所需要的精神,它有充分的闡釋空間;另一方面,拓荒涉及的主客體之間,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勢必會在實踐中遇到各類矛盾,矛盾的解決也必然會產生新的知識經驗,它的問題指涉和經驗適用范圍很廣。問題也恰恰在此:一方面,對于極具包容性的文學思想、概念、精神或話語,應當配之同樣極具包容性的闡釋框架,以便充分展現它的認知深度,上述各類闡釋視角彼此之間缺乏充分的共識,比較偏向主觀;另一方面,拓荒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實踐,由其發展而來的思想、觀念和話語身份也是在實踐基礎上不斷成型、深化、成熟,是生成性的,批評者需要看到它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從這個層面上說,當下的凱瑟研究明顯有碎片化的痕跡。
當代認知心理學中的圖式概念有望彌補上述研究缺憾。本研究嘗試從懷舊認知圖式切入,對凱瑟的“草原三部曲”進行解讀。本研究從“草原三部曲”創作的時代背景、凱瑟獨特的生活經歷挖掘懷舊情結的觸發機制,認為現代性導致個體產生身份焦慮,凱瑟自幼移民、離鄉求學及寫作事業的挫折等在其心底打上了懷舊的烙印。迫于對歸屬感的需求,凱瑟在“草原三部曲”中建構了平等真誠的愛情紐帶和承載“拓荒精神”的西部草原,以期消解環境斷裂導致的自我連續性危機。凱瑟在作品中的懷舊認知建構貼近現實,容易獲得大眾認可,其懷舊的終極客體——“拓荒精神”經得住實踐的考驗,超越了時代,為大眾共享。“草原三部曲”中的懷舊認知建構折射出作者對“拓荒精神”的歌頌,喚醒人們對現代性危機的警醒。
一、認知圖式下的懷舊
1781年,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首次提出圖式(schema)的概念,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英國格式塔心理學家Bartlett首次將圖式引入心理學,并使圖式理論(schema theory)廣為流行。他在《論記憶:一項實驗與社會心理學研究》(Remembering:AStudyinExperimentalandSocialPsychology)中指出:“圖式是對過去反應或過去經驗的積極組織。”[8]隨后,學界紛紛對圖式進行研究。Moskowitz稱圖式是“對一類事件的先驗知識的抽象集合”[9],而不是對過去經驗和行為的簡單集合。Greifeneder等指出:“圖式的意義非常接近于范疇……它強調一種知識結構或行為慣例。”[10]邵志芳等認為,圖式是“一種經過抽象和概括了的背景知識或人腦結構”[11]。盡管上述對圖式概念的表達方式有所不同,但內涵并無二致。一般來說,圖式是基于人的先驗知識,存儲在人腦中的一種抽象的、有組織的知識架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大量個案進行抽象總結,并在頭腦中形成圖式化認知。一旦圖式在腦海中生成,一些細節就會丟失,取而代之的是結構化的抽象概念。
受限于認知水平,學界通常將懷舊簡化為對家鄉或故土的懷念。20世紀后半葉的“認知轉向”使人們意識到懷舊的圖式性和系統性,懷舊并非與生俱來的情感,而是主體在與環境交互的過程中主動建構出來的系統化的認知架構。從認知角度來看,“懷舊是一種情緒應對,它促進情感系統、認知系統、動機系統和行為系統功能的最大實現”[12]。雖然懷舊一直是文學建構的經典主題,也是人類共享的普遍情感,但大部分人的懷舊情結是特定情境下偶發性的,只有少部分人的懷舊情結可以上升到圖式化層面來解釋。偶發性懷舊是個體懷舊情感的無意識流露,不會對個體的行為產生影響;圖式化懷舊是個體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頻頻使用懷舊認知建構策略,逐步形成根深蒂固的認知情感圖式。只有根深蒂固的圖式化懷舊才能觸發懷舊文學的創作。懷舊認知圖式體現懷舊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個體差異性,也會對懷舊主體產生反作用,進而指導、規劃其行為范式。
借助戚濤[13]的懷舊認知圖式(見圖1)可以更系統深入地闡釋文學中的懷舊現象。懷舊的觸發機制是具有疏離、親附雙重傾向的個體對歸屬感的情感需求與斷裂的現實環境產生沖突,從而使個體產生孤獨感、憂郁感、失落感等消極情緒。為了彌補個體在現實中歸屬感的缺失,懷舊主體借助疏離、理想化、認同等策略進行懷舊認知建構。疏離策略指遠離當下充滿危機的現實;理想化策略指在象征性的時空里建構理想社會紐帶、理想精神家園和邊緣性價值,即“游離于主流價值之外,屬于邊緣、次要的意義”[13];認同策略是通過對邊緣性價值和懷舊身份的確認,重新定義個體的生命意義。成功的懷舊認知建構可誘發歸屬感、存在感、幸福感等積極情緒,維護個體自我連續性。

圖1 懷舊認知圖式
值得注意的是,懷舊認知圖式始于對歸屬感的需求,終于對歸屬感的重構。一直以來,懷舊被認為是對往昔的懷念和回憶,將懷舊的時空局限于“過去”,將懷舊的手段限定于“回憶”,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讀者的視野范圍。在懷舊認知圖式下,懷舊的核心和關鍵是個體對歸屬感的重構,而建構理想社會紐帶和理想精神家園只是補償歸屬感的方法和手段。可見,懷舊是一種補償機制,一切能補償懷舊主體歸屬感缺失的時空(過去、現在、未來,故鄉、他鄉等)和蘊含于其中的理想社會紐帶(親情、友情、愛情等)及懷舊主體認同的邊緣性價值(自由、平等、獨立等)都可以成為懷舊的客體。懷舊的終極客體是歸屬感,遠非表征性的時空、紐帶、邊緣性價值等載體。本研究便是基于這一懷舊認知圖式闡釋凱瑟懷舊情結的觸發機制和“草原三部曲”中的懷舊認知建構及其成效。
二、凱瑟懷舊情結的觸發機制
如前所述,懷舊情結的觸發機制源自個體對現實中歸屬感的需求受環境斷裂影響而得不到滿足。凱瑟懷舊情結的觸發機制就在于她在社會和個人兩個層面上的歸屬感缺失。
(一)社會原因:精神荒蕪、人際疏離
在社會層面,19世紀末的美國社會在工業化、城市化與消費主義文化影響下經歷著重大轉型。1890年,美國官方宣布“邊疆消失”,“無主土地”不復存在,美國西部自此步入“后邊疆”時代[14]160,大量西部人民向東部城市移動。再加上工業革命的影響,美國逐漸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型。然而,物質繁榮發展的背后暗含各種危機。首先,城市化與工業化滋生一系列社會問題。19世紀90年代就有人犀利地指出,“美國城市是受腐敗、貪婪和麻木不仁困擾的悲慘人類的聚合體”[15]17,財富分配不均、階級分化嚴重等問題也使“城市居民彼此之間失去信任,對民主失去信心”[15]17。后鍍金時代的美國社會充斥著焦慮與無助,安全感與歸屬感無處可尋。其次,強大的商品文化和消費主義文化盛行,“勞動使人淪為商品”,也使人“成為物品的奴隸”[16]529,人與勞動、他人和自我之間都產生嚴重的異化關系。人們通過消費商品這種物化的生活方式來定義自己的生命價值,將利益視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第一導向。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帶給人類身體痛苦與精神折磨等副產品。20世紀的美國,“精神的幻滅感就像癌癥一樣席卷社會”,“現代人生活在精神的真空中”[16]623-625,成為漫無目的的精神漂泊者。
現代社會被打上“孤獨”“冷漠”“疏離”的標簽,身處美國社會轉型期,凱瑟意識到現代性情境下潛藏著社會危機:經濟大肆發展的同時,傳統的價值觀被工業社會迅速吞噬。人們向金錢主義和消費主義低頭,漠視道德倫理,在追名逐利中逐漸喪失自我。“在工業化快速推進、商業化日益盛行的時期,薇拉·凱瑟沮喪地目睹了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轉變”[17]44,“這種轉變賦予凱瑟最好的小說以挽歌的特質”[17]45。在充斥著扭曲價值觀念的現代社會中,歸屬感無跡可尋,“她把對現實的憂慮放到往昔的年代中去獲得解放”[18],將田園牧歌式的拓荒視為自己心中理想的精神樂土。
(二)個人原因:環境斷裂、事業受挫
戚濤指出,“懷舊是具有回避、親附傾向的人群在環境變故令自我連續性受損的情況下衍生出來的一種適應性機制”[13]。個人層面上,凱瑟經歷過環境斷裂、歸屬感缺失并在現實中無法實現重構,具有回避與親附傾向。自幼移民、離鄉求學及寫作事業的挫折等,在凱瑟的心底打上了懷舊的烙印。
9歲那年,凱瑟舉家移居內布拉斯加地區,自此她在心里埋下了懷舊的種子。年幼的凱瑟一時無法適應內布拉斯加草原的野蠻環境,內心的孤獨與焦慮難以排遣。為了疏解彼時的消極情緒,她常常拜訪草原上其他移民并逐漸與他們建立了溫情的紐帶關系,甚至將草原當成自己的心靈歸屬地。離鄉后的凱瑟一直對草原生活念念不忘,“無論去了哪里,無論建立了什么樣的紐帶關系,她總是會回到那個平原鄉村”[19]。大學畢業后,凱瑟赴紐約擔任《麥克盧爾雜志》(TheMcClure′s)的編輯,繁重的編輯任務幾乎磨滅了其內心對寫作的熱情。此時,凱瑟結識了對其影響深遠的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朱厄特認為凱瑟在文學創作上極具天賦,建議凱瑟放棄編輯的工作靜心創作。1912年,凱瑟辭去編輯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寫作事業。在經歷反響平平的創作低谷后,凱瑟意識到文學創作應根植于自己的現實生活,于是她將目光鎖定早年生活過的內布拉斯加草原。“帶著懷舊情愫回望西部,她找到了創作素材,找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學聲音,也找到了躲避日益物化社會的心靈港灣。”[20]就這樣,凱瑟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拓荒系列小說。幼年的移民經歷使凱瑟面臨分離焦慮,自小便埋下了懷舊的種子;成年后的離鄉求學、寫作生涯遭遇瓶頸等又使其屢遭歸屬感挑戰,進而強化了凱瑟的懷舊情結。
可見,凱瑟在成長過程中屢次遭受歸屬感危機,環境頻繁斷裂使其無法建立緊密穩定的紐帶,于是她將自身經歷投射到文學作品中,選擇在想象的時空里構建得以寄托歸屬感的社會紐帶,重新定義自我的身份,彌補現實中的歸屬感缺失。
三、“草原三部曲”中的懷舊認知建構
在上文所述的懷舊觸發機制下,凱瑟頻頻借助懷舊認知建構策略在遠離現實的時空中建立理想的社會紐帶和精神家園,從而在象征層面進行歸屬感重構。對凱瑟來說,“草原三部曲”中田園牧歌式的西部草原便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精神家園,這個家園遠離當時空虛的現代社會,承載“拓荒精神”,蘊含平等真誠的愛情紐帶,可以使她重獲歸屬感。凱瑟還在“草原三部曲”中分別塑造了理想的懷舊個體——亞歷山德拉、西婭與安東妮亞,她們身上體現了作者認同卻在現實中難以尋覓的邊緣性價值——女性的自由獨立、不卑不亢、拼搏進取等。通過對懷舊身份的建構,凱瑟重新定義了自我的生命價值。
(一)對理想社會紐帶的懷舊認知建構
現實環境的冷漠疏離及人與人之間的鉤心斗角難以孕育緊密聯系的人際紐帶,有損自我認同感。因此,凱瑟在“草原三部曲”中建構理想的社會紐帶,以此來解決歸屬感危機。她在作品中首選愛情紐帶進行理想化重構。與親情和友情不同,愛情更加松散,容易破碎,往往付出得越多越難長久。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男權主義、個人主義等話語霸權的控制下,傳統的愛情觀與現代社會漠視倫理道德的價值觀產生嚴重分歧。因此,凱瑟在作品中構建平等真誠的愛情紐帶,以消解現代愛情的商品化和碎片化。
對社會紐帶的建構往往協同對“重要他人”和“他者”的建構。理想的“重要他人”多為善良、大度、包容、不離不棄之人[13],有利于懷舊自我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與之相對,“他者”是“那些有損懷舊者自我連續性的人”[13]。在《云雀之歌》中,凱瑟為西婭打造了“重要他人”弗雷德。弗雷德是釀造公司的繼承人,西婭只是一個連學費都付不起的鄉村女孩,他們之間有無法逾越的物質、階級、權力鴻溝。當弗雷德問:“假如我要給你一些東西……芝加哥的一套舒適公寓、森林中的一所消夏小屋、許多的音樂晚會、再加上一群需要養育的孩子……你會覺得那有吸引力嗎?”[21]249對此,西婭覺得很可怕,她深知自己和弗雷德之間地位懸殊,即使深愛弗雷德也還是拒絕了他。西婭從不在金錢上依附男人,當她在追求藝術事業中缺乏資金支持時,她選擇向阿奇醫生借錢,也不肯接受弗雷德的好意;她也從不在感情上浪費時間,“別的女人可為此耗費她們的一生,她們沒有別的事可做”[21]282,但西婭從不會為了愛情放棄自己的事業。同樣的,弗雷德也從不強迫西婭,“我不會試圖強迫你……一旦你想離開我,我不會抓住你不放”[21]260。現實中的愛情往往與金錢、地位、權勢捆綁,西婭與弗雷德之間的愛情寄寓作者對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等另類愛情紐帶的認同。
在《我的安東妮亞》中,凱瑟為安東妮亞塑造了“他者”拉里,表達作者對現代愛情漠視倫理道德、不負責任的譴責。安東妮亞抱著對愛情的美好向往卻慘遭欺騙,未婚先孕后被拉里拋棄。拉里對安東妮亞的欺騙有損安東妮亞的自我連續性和穩定性,但她沒有被挫折打倒,依然堅強地面對一切。凱瑟又為安東妮亞設定了“重要他人”庫扎克,庫扎克不介意安東妮亞的過去,對安東妮亞的私生子視如己出,一直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安東妮亞。他們之間平等真誠的愛情紐帶彌補了安東妮亞歸屬感的缺失,也是凱瑟本人在現實中難以找到的可依賴的社會紐帶。
不難看出,現實中的愛情在現代性擠壓下逐漸商品化,讓步于金錢、地位、身份、權勢等,加劇了兩性地位的不對等,人與人之間互相欺騙、猜忌、防備,缺乏真誠與尊重。為此,凱瑟在想象的時空中借助對平等真誠的愛情紐帶的建構,營造出溫馨和諧的兩性共同體。
此外,凱瑟還在想象的時空中建構理想的懷舊身份,將非主流的邊緣性價值投射其中。“在凱瑟筆下,家園的意義往往通過女性拓荒者與土地之間的融合相通而體現,男性人物則傳達了工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放逐感和疏離感。”[22]女性拓荒者總是堅毅果敢,男性拓荒者卻碌碌無為,這正是作者對男尊女卑父權制社會的駁斥。在《啊,拓荒者!》中,卡爾的父親向來不擅長經營農場;奧斯卡一直墨守成規,不知變通;羅總是手忙腳亂,冒冒失失,分不清事情的輕重緩急。三年大旱期間,目光短淺的村民們紛紛將土地賣掉,拼命逃離野性的草原。與缺乏開拓精神、安于坐享其成的村民不同,亞歷山德拉一直堅守在西部草原上,她堅信有一天地價會上漲,土地本身會比所有的農作物都要值錢,最后她成為一名像富勒那樣有遠見卓識的投資者。亞歷山德拉身上具有開拓者的想象力和魄力,當羅問她怎么知道一定會盈利時,她說:“這我解釋不上來,羅。你們就得相信我的話,我知道,就行了。當你駕著車在這地方到處轉的時候,可以感覺到這個機會正在到來。”[23]39作為美國第一批拓荒者的縮影,亞歷山德拉用拼搏和進取將西部草原打造成了田園牧歌式的精神家園。
借助安東妮亞,凱瑟復活了現實中被壓抑的獨立自主、不卑不亢等女性價值訴求。在《我的安東妮亞》中,安東妮亞獨立自主,不受男人擺布。當雇主哈林先生指責她和行為不檢點的姑娘們搞在一起,讓她放棄跳舞抑或辭去工作時,她不卑不亢,選擇離開哈林家;當她未婚先孕慘遭拋棄時,她不因孩子而覺得蒙羞,沒有自暴自棄,而是積極面對。她甚至為孩子而感到得意,在給孩子照相時不同意用便宜的相框,“換了另外一個姑娘,會把嬰兒藏起來不讓人家看見,可是安東妮亞,當然,非要把嬰兒的照片放在鍍金的大鏡框里掛在鎮上的照相館里展覽不可”[23]360。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女性沒有選舉權,在婚姻里沒有財產權(在一些州,法律強制雇主將妻子的工資直接支付給其丈夫),孩子也不屬于女性。沒有丈夫的同意,妻子不能立遺囑、簽署合同或提起法律訴訟。女性的地位低人一等或堪比奴隸”[24]。可見,女性被父權話語打壓,依附于男性而毫無主體性,她們被局限在家庭中踐行賢妻良母的角色,也不敢與父權社會作斗爭。凱瑟在“草原三部曲”中塑造了理想女性——亞歷山德拉、安東妮亞和西婭,她們復活了現實中被打壓的邊緣性價值。借助三位理想女性的形象,凱瑟為自身建構了一個以自由獨立、不卑不亢、積極樂觀、天真單純等價值為標簽的理想化懷舊身份。雖然這些邊緣性價值在現實中無處可尋,但能與理想紐帶一起在象征層面重拾作者的自我連續性。
(二)對理想精神家園的懷舊認知建構
當理想的社會紐帶、邊緣性價值、懷舊自我等要素建構完成時,懷舊者還需要建構一個理想的精神家園使其得以合理存在。歸根結底,懷舊個體對理想精神家園的建構源自現實環境的斷裂、無序、疏離、冷漠,因而想要逃離現實環境的種種羈絆,在想象中創造一個溫馨、簡單、和諧、純粹的理想時空。懷舊個體采用疏離和理想化策略,將理想時空投放于遠離現實的他時他地,與此時此地形成對比,象征性地獲得歸屬感補償。凱瑟想象的西部草原正是如此,她在“草原三部曲”中借助主人公在西部草原與東部城市的游歷,通過不同空間的對比,樹立了兩個時空的二元對立。
在凱瑟筆下,西部草原總是呈現純粹、安寧、自由、誠實的特質,給人以家園的安全感與歸屬感;而東部城市總是被打上復雜、喧囂、混亂、欺騙的烙印,給人以飄零感與斷裂感。例如,在《啊,拓荒者!》中,卡爾在東部城市游歷多年卻一事無成,而亞歷山德拉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然將長滿紅草的西部草原變成“到處流著奶和蜜的土地”[23]65。土地是誠實的,有幾分投入就有幾分回報,從不辜負人們的辛苦。土地給予亞歷山德拉一種穩定感與安全感,亞歷山德拉也對土地抱有十分的信心,她稱土地“和我們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它起初假裝貧瘠,因為沒有人知道該怎么對付它;后來,忽然一下子,它自己工作起來了。它從沉睡中覺醒,舒展開來,真大,真富,于是我們也就忽然發現自己很富了,是坐享其成!”[23]63-64城市卻到處充斥著流動性與疏離感,卡爾正是城市中萬千漂泊者之一,“在那些城市里有著千千萬萬像我這樣到處滾動的石頭。我們都是差不多的;我們沒有任何聯系,沒有熟人,一無所有。我們之中有人死掉了,別人不知道該把他葬在哪里”[23]67。城市的疏離感與草原的歸屬感形成鮮明對比。在小說最后,當卡爾邀請亞歷山德拉與他一起去東部時,亞歷山德拉稱自己不會永遠離開草原,草原見證了她拼搏和進取的“拓荒精神”,此舉寄寓作者對金色西部草原的懷舊情結。在現代城市冷漠疏離的映襯下,西部草原雖然落后封閉,卻讓人覺得安寧且自由。
在《我的安東妮亞》中,作者塑造了鄉村女孩安東妮亞在城市中受騙又重返鄉村的故事,借此表達她對城市充滿危險與欺騙的批判,以及對鄉村充滿純粹與簡單的贊美。安東妮亞在城市中遭遇愛情騙子拉里的拋棄,未婚先孕后重返鄉村。安東妮亞的天真爛漫與城市的復雜世故格格不入。凱瑟最后安排安東妮亞重返西部草原,在空間上疏離背信棄義、道德淪喪的東部城市。凱瑟借安東妮亞之口表達了自己對城市的消極情緒:“我在城市里總是感到痛苦,我會寂寞得死去。”[23]371而西部草原總是給人一種家園的歸屬感,讓人有根可尋:“我喜歡住在每一堆谷物、每一棵樹我都熟悉、每一寸土地都是親切友好的地方。我要生活在這里,死在這里。”[23]371西部草原承載著天真淳樸與穩定安逸的特質,成為作者寄托歸屬感的精神樂土。
在《云雀之歌》中,凱瑟呈現了鄉村女孩西婭去芝加哥追尋藝術夢想的故事,西婭在鄉村和都市的經歷,形成了兩個時空鮮明的對照。西婭討厭都市的物欲橫流與喧囂混亂,“蕓蕓眾生的奔忙與熱情沒有引起她絲毫興趣。她壓根兒沒注意到那座充滿財富、人欲橫流的西部大城市的喧囂與混亂,只是覺得運貨馬車和有軌電車的隆隆聲使她感到困乏”[21]155。城市的浮躁與喧囂對人的精神產生致命的打擊,當西婭聽完音樂會時,她感受到“外面的世界里有種力量一心要奪走她跨出音樂廳時所懷有的那種情感。一切都似乎要向她撲來,要從她披肩下面把那種感情撕去”[23]162。與此相反,鄉村則顯得溫馨安寧。當西婭回到自己的故土時,“這片土地在她眼中既充滿了青春活力又友善可親,它為從那些令人傷心的國度來的避難者們提供了另一次機會”[21]176。西婭眼中的鄉村具有和藹慷慨的性格、寬闊坦蕩的氣魄及誠實善良的秉性,也是凱瑟本人在現代性重壓之下寄托歸屬感的精神家園。
至此,凱瑟完成了對理想社會紐帶、理想精神家園、邊緣性價值、懷舊身份等因素的懷舊認知建構,多重因素結合誘發多重歸屬感,從而抵御現實中的穩定性威脅。
(三)凱瑟懷舊認知建構的成效
前文提到,凱瑟在“草原三部曲”中通過懷舊認知建構,在象征層面填補了自己在現實中的歸屬感缺失。在現代化社會中,人們處于精神的荒漠,凱瑟作品中經久不衰的“拓荒精神”成為對抗現代性危機的支撐。“今天,高度工業化之后的美國人(不論是哪國人的后裔)的性格和道德觀念似乎已經同書中的人物相距很遠,但是仔細挖掘起來,那種創業精神仍然是構成作為整體的美國人的品質的精華。”[25]即使凱瑟的懷舊認知建構處于象征層面,但“拓荒精神”在現實中不斷被重寫,甚至融入美國的國民性,被大眾認可,為民族心理共享。正如特納在其著作中所言,“美國思想的顯著特征都歸于邊疆”[26]。王邵勵在對美國邊疆、地域和西部的研究中也認為,“邊疆拓殖運動雖然已經結束,但拓荒者在征服邊疆的經歷中所創造的寶貴精神遺產,將繼續在‘后邊疆’時代發揚光大”[14]227,“后邊疆”時代有無數未被攻取的新領域等待新時代的拓荒者去征服,這是“拓荒精神”在新時代的延續,“是拓荒者對邊疆環境的適應性改造才孕育出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特性和開拓進取、樂觀向上的國民性格”[14]247。
“懷舊建構是一個與社會話語協商、博弈的過程。懷舊建構成效的高低,取決于現實度及社會認同度。”[27]據此標準,凱瑟的懷舊建構是高效的。第一,她所建構的愛情紐帶并不是毫無瑕疵、極致完美的,而是經歷磨難與挫折后的精神契合。這種不完美貼近現實,遠非在真空中上演,具有包容性,更容易被大眾接受。三位女性拓荒者在親密關系里不卑不亢,自由獨立,從不依附于男性;男性也沒有大男子主義傾向,或對女性施加性別暴力。這種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的愛情紐帶被社會期許,能夠參與主流話語建構,逐漸在現實中上演。第二,凱瑟的時空選擇具有開放性。小說的結尾體現作者別出心裁的安排:亞歷山德拉不會永遠離開西部草原;安東妮亞在城市受挫后重返西部草原;西婭選擇離開西部草原,留在東部城市繼續自己“藝術上的拓荒之旅”。無論身處何處,西部草原都是三位拓荒者的理想精神家園,寄托其歸家的歸屬感。西婭雖然遠離西部草原月石鎮,但“她的價值觀尺度將永遠是月石鎮的尺度”[21]290,這再次佐證時空只是懷舊的載體,其中蘊含的歸屬感才是懷舊的精神內核。西婭留在東部城市正是作者將“拓荒精神”與現代性結合的大膽嘗試:在城市化與工業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傳統的“拓荒時代”終將退出歷史舞臺,遺留的“拓荒精神”永不泯滅,成為警醒現代性的一劑精神良藥。包容性的紐帶與開放性的時空結合起來,使凱瑟的懷舊建構貼近現實,易于維護,能夠得到大眾認可。
四、結語
基于懷舊認知圖式,本研究深入探究了凱瑟在“草原三部曲”中的懷舊認知建構,包括對理想社會紐帶、理想精神家園、邊緣性價值、懷舊身份的建構。借助疏離和理想化策略,凱瑟在幾部小說中建構了平等真誠的愛情紐帶和田園牧歌式的西部草原。此外,凱瑟為自身設定了一個以自由獨立、不卑不亢、積極樂觀、天真單純等為標簽的理想化懷舊身份,緩解了自我在現實中的身份焦慮。這些懷舊認知建構,一方面勾起人們對農業時代精神文明的緬懷,歌頌“拓荒精神”,另一方面提醒人們警惕工業時代物質文明的沖擊。凱瑟的懷舊認知建構貼近現實,為大眾認可,其懷舊的終極客體——“拓荒精神”成為美國的傳統美德和價值標準,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引發后人對現代生活的反思。本研究通過研究凱瑟在工業時代對“拓荒時代”的懷舊認知建構,讓讀者窺見美國社會轉型期不同價值觀的沖突,發現凱瑟懷舊情結的深層意義,對研究“懷舊”“拓荒精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沖突”“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斗爭”等文學母題有一定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