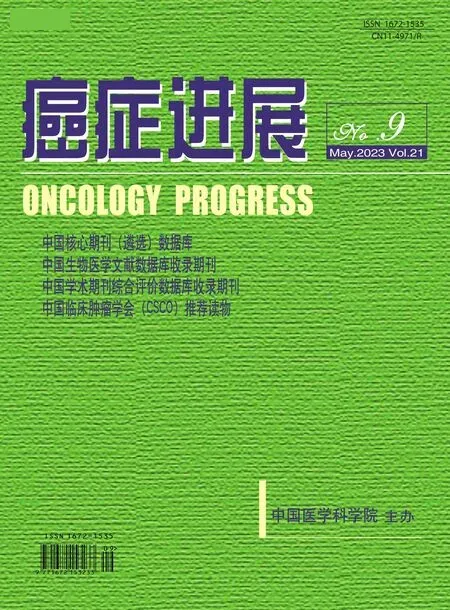骨橋蛋白在常見婦科惡性腫瘤中的研究進展
胡帥,索玉平,武霞,晉雨楠,范裕裕
1山西醫科大學第五臨床醫學院,太原 030012
2山西省人民醫院婦產科,太原 030012
骨橋蛋白(osteopontin,OPN)又稱分泌型磷蛋白1(secreted phosphoprotein 1,SPP1),于1979年首次被發現[1],也稱為早期T 淋巴細胞活化蛋白1(early T-lymphocyte activation 1,ETA1)和骨唾液酸蛋白1(bone sialoprotein 1,BSP1),是一種分泌型磷酸化糖蛋白,是小整合素結合配體N-連接糖蛋白(small integrin binding ligand N-linked glycoprotein,SIBLING)家族成員。OPN 主要由成骨細胞、破骨細胞、內皮細胞、上皮細胞和免疫細胞(如活化的巨噬細胞和T 細胞)分泌,因此OPN 在體內廣泛分布于各種細胞或組織及血液、母乳等體液中[2]。OPN 在成骨細胞和破骨細胞中高表達并參與生物礦化過程,此外,OPN 還具有其他生理功能,并參與多種疾病(如腫瘤)的調控[2-3]。OPN 通過與整合素和CD44 受體結合參與調控細胞基質相互作用、細胞信號轉導及腫瘤發生發展過程[4]。OPN 在輸卵管、子宮等器官中均表達,研究發現,OPN 在子宮內膜中表達并參與胚胎發育的調控[5]。近年來的研究發現,OPN 與卵巢癌、子宮內膜癌、宮頸癌等常見女性生殖系統腫瘤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本文對OPN 在常見婦科惡性腫瘤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旨在了解OPN 異常表達與婦科腫瘤的關系及潛在的調控機制,探討OPN 作為相關疾病診斷、治療及預后標志物的潛在臨床價值。
1 OPN 的結構與生物學功能
OPN 的名稱來源于“骨(osteo)”和“橋(pontin)”的組合,提示其具有連接骨細胞與細胞外基質的作用,此外OPN 的多種生物學過程與多種疾病有關。OPN 主要由成骨細胞、破骨細胞與骨骼肌細胞等合成,也可在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自然殺傷(natural killer,NK)細胞、T 細胞、B 細胞和樹突狀細胞中合成和分泌,廣泛分布于機體各種組織和細胞中。OPN 是第1 個被鑒定的細胞外基質蛋白,Franzén 和Heineg?rd[6]在骨組織中發現了一種高度磷酸化的糖蛋白,由314 個氨基酸組成,即OPN 蛋白,又稱SPP1,由單拷貝基因SPP1編碼,位于人4 號染色體著絲點附近。OPN 具有幾個保守的結構域,包括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RGD)結構域、絲氨酸-纈氨酸-酪氨酸-谷氨酸-亮氨酸-精氨酸(SVVYGLR)結構域、肝素結合結構域、鈣結合結構域、基質金屬蛋白酶切割位點和CD44 受體結合結構域[7]。
目前已經確定了5 種OPN剪接變體,其中OPN-a為全長亞型,包含所有7個外顯子,而OPN-b缺少5 號外顯子,OPN-c缺少4 號外顯子,OPN-4(OPN-d)缺少4 號和5 號外顯子,OPN5包含所有7個外顯子以及3 號和4 號外顯子之間的一個額外的外顯子。獨特的磷酸化位點和谷氨酰胺轉氨酶交聯位點使得不同異構體的結構和功能不同[7]。不同細胞來源的OPN 具有不同的翻譯后修飾(磷酸化、糖基化、硫酸化和水解作用),OPN 的分子量為41~75 kD,可能決定了其細胞特異性的結構與功能。OPN 參與骨重塑、免疫調節、炎癥、血管生成等一系列正常的生理過程。OPN 在生物礦化過程中也發揮重要的調控作用。研究表明,OPN 可抑制礦物沉積和羥基磷灰石晶體形成,還可調節骨細胞的附著力和基質礦化,OPN 將破骨細胞錨定在骨骼的礦物質基質上,調控其對鈣的特殊親和力及礦化區域的免疫定位;此外,OPN 對炎癥反應和組織損傷愈合過程中的先天性免疫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OPN 作為輔助性T 細胞1(T helper cell 1,Th1)細胞因子參與黏膜防御病原體過程,還參與激活先天性免疫反應和組織受損等過程[8]。另有研究表明,OPN 可抑制異位鈣化和過度礦化,并在傷口愈合和防止腎結石形成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9]。
已有的研究表明,OPN基因在多種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OPN不同剪接變體的差異表達可能在不同類型腫瘤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OPN-a 高表達是胃癌患者的不良預后因素,OPN-b 可抑制膠質瘤細胞凋亡,OPN-c在正常乳腺組織中不表達,但在乳腺癌組織中高表達并促進腫瘤進展,OPN-4 和OPN-5 在食管癌中表達,但其調控腫瘤發展的相關機制尚不明確[7]。OPN 表達水平上調可促進結直腸癌細胞增殖、遷移、侵襲和血管生成,可能參與調控多種信號通路,如上皮-間充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腫瘤細胞干性與耐藥、免疫與炎癥相關信號通路[10]。研究顯示,OPN 表達水平與多種類型腫瘤的預后相關,如OPN-c 是乳腺癌潛在的預后標志物,OPNmRNA 和蛋白表達水平是非小細胞肺癌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此外,OPN及其不同剪接變體可能是前列腺癌、胃癌、結直腸癌、肝癌等潛在的預后預測標志物[11]。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OPN 與常見婦科惡性腫瘤如宮頸癌、卵巢癌和子宮內膜癌的發生發展關系密切,可能是相關疾病的潛在標志物或治療靶點。
2 OPN 與宮頸癌的關系
宮頸癌是女性生殖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宮頸癌發病例數居女性所有惡性腫瘤第5 位,死亡例數居第8 位,發病例數呈上升趨勢[12]。高危型人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是宮頸癌的危險因素,持續的高危型HPV感染是宮頸癌的致病因素,同時伴有宿主細胞基因組學和表觀遺傳學的改變。一項基于癌癥基因組圖譜(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數據庫的研究顯示,宮頸癌組織中OPN 表達水平明顯高于正常組織,OPN 表達水平與宮頸癌患者的國際婦產科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分期、淋巴結轉移情況、腫瘤大小和預后有關,與OPN 高度相關的基因主要富集在免疫應答相關信號通路,且OPN 高表達與M2 型巨噬細胞浸潤相關[13],表明在宮頸癌中OPN 可能參與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介導的免疫逃逸機制[14]。多項研究證實,宮頸癌中OPNmRNA 和蛋白表達水平均明顯高于正常組織,OPN 高表達提示預后差,且可能對化療的敏感性較低[15-18]。此外,OPN啟動子區單核苷酸多態性位點(-443T﹥C)可能與信號轉導及轉錄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6 結合位點丟失有關并導致OPN 過表達[16]。早期宮頸鱗狀細胞癌患者主要采用手術治療,晚期患者主要的治療手段為化療,順鉑是宮頸癌常用的化療藥物。Xu 等[18]研究表明,微小RNA(microRNA,miRNA)-181a 表達下調和OPN 表達上調與宮頸癌細胞的順鉑耐藥有關,過表達的miRNA-181a 可抑制OPN 表達,誘導宮頸癌細胞凋亡,抑制宮頸癌細胞增殖和順鉑耐藥,提示OPN 表達水平與宮頸癌化療敏感性相關。生物信息分析顯示,OPN 可參與宮頸癌的多種生物學過程如免疫抑制、缺氧、糖酵解、EMT、細胞凋亡和血管生成,且可能在宮頸癌進展相關的多種信號通路中具有調控作用,如腫瘤蛋白p53(tumor protein p53,TP53)、磷脂酰肌醇-3-羥激酶(phosphoinositide 3-hydroxy 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稱AKT)、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STAT3、雷帕霉素靶蛋白復合體1(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MTORC1)、Kirsten 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信號通路[13],相關機制需更多研究揭示。OPN 是宮頸癌預后標志物和潛在的治療靶點,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3 OPN 與子宮內膜癌的關系
子宮內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統常見的惡性腫瘤,在西方發達國家具有較高的發病率,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子宮內膜癌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均呈上升趨勢[12]。早期診斷的子宮內膜癌可以通過手術切除治愈,晚期易并發遠處器官轉移和腹膜受累,患者的無進展生存率較低。目前,OPN基因與子宮內膜癌關系的研究較少,結論存在爭議。Li 等[19]研究發現,OPN 在子宮內膜癌組織中高表達,OPN 通過PI3K/AKT 和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1/2 信號通路促進人子宮內膜癌細胞HEC-1A 侵襲、遷移和EMT 過程。Al Maghrabi 等[20]采用免疫組化染色法檢測71 例子宮內膜癌組織和30 例正常子宮內膜組織中OPN 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OPN 在所有正常子宮內膜組織中均高表達,在64.8%的子宮內膜癌組織中高表達,OPN 表達情況與子宮內膜癌的組織學類型、FIGO 分期、腫瘤大小、肌層浸潤情況、淋巴管侵襲情況、淋巴結轉移情況均無相關性,但OPN 高表達與預后較好有關,提示OPN 是子宮內膜癌潛在的預后預測因子。另一項研究檢測子宮內膜癌組織中OPN 和大鼠肉瘤癌基因(rat sarcoma oncogene,RAS)的表達情況,結果發現,OPN 在正常增生期子宮內膜組織、不典型增生子宮內膜組織、子宮內膜癌組織中的表達水平呈顯著上升趨勢,OPN 表達水平與組織學分級、手術病理分期和肌層浸潤深度均呈正相關,與淋巴結轉移情況無關[21]。OPN 在子宮內膜癌中的作用可能受多種因素影響,OPN對正常子宮內膜功能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其在正常子宮內膜中表達,并參與胎盤發育、子宮內膜蛻膜化、子宮-胎盤環境等生理生殖過程的調控[22]。
4 OPN 與卵巢癌的關系
卵巢癌是一種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預后較差,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卵巢癌的發病例數和死亡例數僅次于宮頸癌,分別居全部惡性腫瘤第7 位和第9 位[12]。由于缺乏典型的臨床癥狀和特異性,早期卵巢癌易漏診,超過80%的卵巢癌患者在初次確診時處于中晚期。盡管目前已有手術和術后化療或靶向治療方案,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仍較低。尋找新的分子靶點是卵巢癌治療領域的研究熱點。近年來,大量證據提示OPN 作為卵巢癌診斷標志物和藥物靶點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多項研究表明,OPN 是卵巢癌早期診斷和篩查的潛在標志物[23-25]。血漿OPN 水平可以作為卵巢良惡性腫瘤的鑒別診斷指標,基于血漿OPN、糖類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人附睪蛋白4(human epididymis protein 4,HE4)、瘦素(leptin)和催乳素(prolactin,PLR)水平的預測模型對惡性卵巢腫瘤的診斷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為0.96[23]。研究表明,血清巨噬細胞移動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OPN、PLR 和CA125 聯合檢測較CA125 單獨檢測在卵巢癌診斷中表現出更高的靈敏度(76%)和特異度(98%)[24]。此外,一項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臨床研究GOG-0218 顯示,接受卡鉑+紫杉醇聯合或不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血清IL-6 和OPN 水平與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均呈負相關,表明血清OPN 水平升高是卵巢癌預后不良的影響因素[26]。OPN 對卵巢癌預后的影響可能與其參與調控卵巢癌鉑類藥物耐藥有關[27-28]。研究發現,在順鉑耐藥卵巢癌細胞系中沉默OPN-c的表達增加了卵巢癌細胞對順鉑的敏感性;OPN介導的化療耐藥可能與旁分泌途徑有關,腫瘤相關間皮細胞通過分泌OPN 激活腫瘤細胞表面CD44 受體,進一步激活PI3K/AKT 信號通路,促進卵巢癌細胞對鉑類藥物耐藥[28]。此外,OPN 可能作為鈣蛋白酶小亞基1(calpain small subunit 1,CAPN4)的靶蛋白促進卵巢癌細胞增殖、遷移。研究發現,OPN 和CAPN4 在卵巢癌組織和卵巢癌細胞中高表達,沉默CAPN4可下調OPN 的表達,抑制卵巢癌細胞的活力和遷移能力,激活胱天蛋白酶(caspase)3 信號通路,進而促進卵巢癌細胞凋亡,CAPN4 可上調OPN 的表達,通過PI3K/AKT 信號通路促進卵巢癌細胞遷移[29]。有研究通過免疫組化染色法檢測卵巢癌患者中OPN 的表達水平,結果顯示,OPN 表達與卵巢癌患者的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OS 均呈負相關[30]。以上研究表明,OPN 在卵巢癌診斷和治療中具有潛在的價值,血液OPN 可能是卵巢癌早期診斷和預后預測指標,卵巢癌組織中OPN 的表達可能是鉑類藥物耐藥和預后不良的標志物,OPN 是卵巢癌潛在的治療靶點,但相關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探究,如OPN 在卵巢癌中的不同表達模式及不同OPN剪接變體在卵巢癌中的調控機制。
5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OPN 在常見婦科腫瘤的發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腫瘤組織中OPN 表達水平升高可能是婦科腫瘤預后不良的影響因素,血清OPN水平是卵巢癌患者潛在的預后標志物。OPN 作為常見婦科腫瘤的潛在診斷指標、預后標志物及治療靶點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臨床意義。目前,OPN 在卵巢癌、宮頸癌和子宮內膜癌中的研究多體現于蛋白層面,而OPN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及表觀遺傳學層面的研究較為少見,此外不同的OPN剪接變體、基因-基因、基因與環境層面的不同作用機制有待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