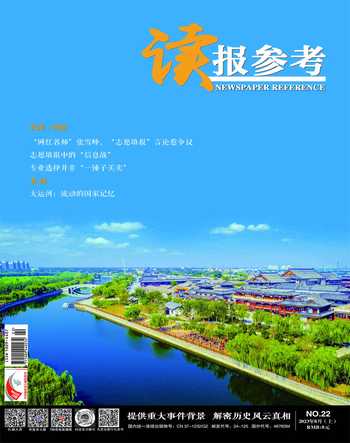7月6日:地球最熱的一天
7月6日的人類,熬過(guò)了地球上最熱的一天。這一天,這顆人類賴以生存的星球平均氣溫達(dá)到了17.23℃——這是全球各地,包括海洋與兩極的溫度均值。而基于樹木年輪和冰芯推測(cè)的以往溫度數(shù)據(jù),一些科學(xué)家認(rèn)為,我們遇到的“最熱一天”也可能是12.5萬(wàn)年來(lái)地球上最熱的一天。
一
7月6日這一天,孕育古文明的兩河流域酷暑難耐,伊拉克首都巴格達(dá)早上9點(diǎn)鐘的氣溫就到了38℃,到12點(diǎn)氣溫飆升至45℃。伊拉克國(guó)家氣象局4日前就宣布,熱浪會(huì)從7月6日這一天開始襲擊伊拉克。像往年夏天一樣,伊拉克不出意外地停電了。每逢這樣的夏日,當(dāng)?shù)氐碾娏?yīng)就到了最緊張的時(shí)刻,政府迫不得已采取限電措施,可高溫并不會(huì)消停。
大地被炙烤,熱浪裹挾街道。相對(duì)富裕的人家可以花錢購(gòu)買私人發(fā)電機(jī),或驅(qū)車前往山區(qū)避暑;其他人家的空調(diào)、風(fēng)扇都停止運(yùn)轉(zhuǎn)。當(dāng)天,一名住在巴格達(dá)的婦女,只好在停電時(shí)拿起紙張,給赤身裸體的孩子扇風(fēng);一些男人選擇一頭扎進(jìn)底格里斯河,躲避地面的高溫?zé)崂恕?/p>
從全球平均氣溫地圖上看,7月6日這一天,地球的三分之二都被炙烤成鮮艷的紅色,很容易從中找到伊拉克的位置,那是北半球少有的呈現(xiàn)白色的區(qū)域,像是烤得焦紅的土地上滲出了一撮鹽巴。那代表著地球上最炎熱的地方,平均氣溫往往超過(guò)40℃。這一天,非洲撒哈拉沙漠也是如此。
阿爾及利亞的城市阿德拉爾當(dāng)天的氣溫異常高,夜間氣溫也從未低于39.6℃。氣候?qū)W家馬克西米利亞諾·埃雷拉表示,這是非洲有史以來(lái)最熱的夜間氣溫。擁有空調(diào)的人有機(jī)會(huì)安度夏日,但這里只有5.6%的人用得起空調(diào)。實(shí)際上,這個(gè)世界上仍有約7.5億人連電都用不上。
北半球的夏季,并非只有兩河流域和撒哈拉遭受著極端高溫的威脅。東歐、阿拉伯半島、中亞、東南亞、東亞、北美洲都被長(zhǎng)久地籠罩在熱浪翻滾的蒼穹之下。很多地方的新聞報(bào)道都在用“史無(wú)前例”“有史以來(lái)”“創(chuàng)紀(jì)錄”這樣的詞匯形容高溫。但用的次數(shù)多了,曾經(jīng)史無(wú)前例的事,也漸漸成為一種常態(tài)。
南半球也在創(chuàng)造一些與氣溫有關(guān)的紀(jì)錄。7月6日,南半球平均氣溫為12.62℃,比1979年有記錄以來(lái)的任何一年的7月6日都要溫暖,比平均值異常高出1.05℃,而南極的平均氣溫比平均值異常高出3.70℃。
要知道,在南半球,現(xiàn)在是冬季,寒冷才是主角。但澳大利亞正經(jīng)歷著一個(gè)溫暖的冬天,因6月入冬后降雪不足,新南威爾士州雪山的斯雷德博度假村在社交媒體上宣布,“本周末將禁止滑雪或單板滑雪”。這是該雪場(chǎng)今冬首個(gè)周末的滑雪活動(dòng),訂好酒店和雪場(chǎng)門票的滑雪客不得已放棄了行程。也許南半球異常溫暖的初冬,早就預(yù)示了北半球又一個(gè)“有史以來(lái)最熱的夏天”。
7月4日,世界氣象組織(WMO)發(fā)布聲明稱,厄爾尼諾現(xiàn)象7年來(lái)首次在熱帶太平洋出現(xiàn)。WMO秘書長(zhǎng)佩特里·塔拉斯表示:“厄爾尼諾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將大大增加打破溫度紀(jì)錄的可能,并有可能在世界許多地區(qū)和海洋引發(fā)更極端的高溫。”
不少科學(xué)家都認(rèn)為,今年前所未有的極端高溫是人類引起的全球變暖與厄爾尼諾現(xiàn)象等自然現(xiàn)象疊加造成的。盡管全球變暖和厄爾尼諾現(xiàn)象并不直接導(dǎo)致災(zāi)害性事件,但它們被認(rèn)為加劇了災(zāi)害性事件的嚴(yán)重程度,比如干旱、熱浪、洪水、野火、饑荒、瘟疫等。
二
對(duì)人類來(lái)說(shuō),陸地上的高溫容易被感知,海洋世界的異常卻往往被忽視。海洋占據(jù)著地球面積的三分之二,原本它在拉低地球平均氣溫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拋開海洋的數(shù)據(jù),7月6日陸地平均氣溫會(huì)遠(yuǎn)比17.23℃高得多。但這一次相反,海洋在拉升地球平均氣溫這件事上,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這對(duì)海洋生物和人類來(lái)說(shuō),都不是一件好事。前些年的海洋熱浪,重創(chuàng)過(guò)海洋生態(tài)和漁業(yè),曾使阿拉斯加灣的太平洋鱈魚數(shù)量減少過(guò)70%,10萬(wàn)噸大西洋鮭魚、銀鮭魚和鱒魚死亡,西澳大利亞州的扇貝、藍(lán)梭子蟹、鮑魚和太平洋的牡蠣,都曾出現(xiàn)過(guò)大規(guī)模死亡和繁殖失敗的現(xiàn)象。通常在海底固定不動(dòng)的底棲無(wú)脊椎動(dòng)物,在海洋熱浪期間更難免遭受致命一擊。
7月6日這天,全球海冰面積縮減至今年以來(lái)的最低水平——930.6萬(wàn)平方公里。此時(shí),南極洲的海冰正處于生長(zhǎng)階段,但這里的海冰面積,自4月以來(lái),一直維持在歷史同期的最低水平,處于持續(xù)打破最低紀(jì)錄的狀態(tài)。世界各地的冰川也在加速消失。
當(dāng)創(chuàng)紀(jì)錄的“全球平均氣溫”數(shù)據(jù)在7月出現(xiàn)時(shí),聯(lián)合國(guó)秘書長(zhǎng)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說(shuō):“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情況就是氣候變化失控的證明。如果我們堅(jiān)持推遲采取必要的關(guān)鍵措施,我認(rèn)為,我們將陷入災(zāi)難性的境地。”有科學(xué)家推測(cè),已經(jīng)創(chuàng)下的紀(jì)錄會(huì)在不久后就被刷新,但哪天將成為地球最熱的一天,很難確定。也許是明天,也許是后天,但最好永遠(yuǎn)保持在7月6日這一天。
(摘自《中國(guó)青年報(bào)》李強(qi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