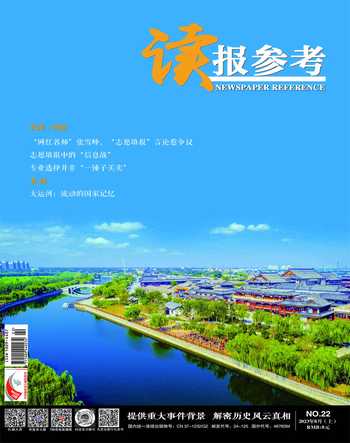販賣焦慮:是誰在炒作“暑期最可怕”
“一年級的暑假是最可怕的”“三年級的暑假是最可怕的”“六年級的暑假是最可怕的”……隨著暑期來臨,類似視頻在網絡上大量涌現,讓一些看了視頻的家長直呼——備感焦慮。
記者調查發現,無論線上線下,暑期不少教培機構都在“販賣焦慮”,培訓老師(主播)們“情真意切”地告訴學生家長“××階段是最重要的”,暑期得趕緊學習,否則孩子開學了就跟不上,或會被同齡人快速反超。
“最”視頻應接不暇
某視頻號今年6月發布的一條短視頻中,屏幕的四分之三幾乎都被“老師”的臉占了——他戴著眼鏡,手掌隨說話的節奏擺動著,眉毛微蹙,一股“資深教師”的范兒。額頭前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成績一般想要翻盤,五年級暑假這樣做。”
在視頻中,他一本正經地說道:“五年級成績一般,你到了六年級以后啊,也還是會一般,到了初一就會更一般。”想要逆風翻盤,應該怎么辦?這位“老師”把學習比作賽跑,稱“小升初”的成績是最終反映孩子“小學學得好不好的標準”。
很多孩子都是六年級下學期開始準備小升初考試,這名“老師”則建議,應該從五年級開始,提早進入復習。隨后,他話鋒一轉,開始推銷起某教材輔導書……
在短視頻平臺,此類“販賣焦慮”的視頻大火,從幼小銜接、小升初到初升高,幾乎每一個年級都有覆蓋——在短視頻博主口中,每一個學期的暑假都是“逆襲”的關鍵節點。
從課程門類上看,“語文是分水嶺”“英語要提前學”“奧數是敲門磚”……科科都必須重視。不過,當視頻快要結束的時候,博主隨即就會給出購書、購課建議。
不僅如此,在一些視頻的宣傳語上,還寫著“××年級是最可怕的”“暑假別再玩了,××年級就是分水嶺”“不利用好這個暑假基本就和高中無緣”等。夸張的語氣,配上令人緊張的音樂,讓一些看了視頻的家長“備感焦慮”。
記者看到,這類賬號大多開通了購物櫥窗,視頻左下方鏈接點擊進去,是各種學習教材、輔導課程的銷售。教材價格不等,有的賣三五十元,有的100多元。某小升初暑假預習資料顯示已售38萬件。輔導課程購買則更為復雜,定價看似低廉,但其實僅為咨詢報名費,后續還需要支付一定費用才能開啟正式課程。
6月28日,抖音發布第五期打擊“借熱點事件蹭熱炒作”公告,販賣暑期“教育焦慮”內容成為治理重點。集中發布“小學生二年級的暑假‘很危險‘最可怕”“二年級暑假不作好預習,三年級成績一落千丈”“暑假來了,不浪費暑假60天”等營造“教育焦慮”內容的賬號,因違反平臺規則已受到嚴格處置。目前,抖音已處理相關違規視頻961條,并對81個賬號采取了禁止發稿、限制電商帶貨權限等處罰。
刻意制造群體焦慮
“販賣教育焦慮”不僅僅在線上,線下同樣普遍存在。來自上海浦東新區的沈州(化名)曾從事教育培訓行業,他告訴記者,網上“販賣教育焦慮”的話術早已存在,都源自線下培訓機構,“先渲染焦慮再引導家長報班買書,線下培訓機構玩剩下的搬到短視頻平臺上,又騙了一批家長”。
沈州向記者透露,他所在的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附近就有一些培訓機構存在“販賣教育焦慮”現象,這些補課機構涵蓋小學到高中各個階段,只要有應試需求的科目,都能在這里上課,渲染焦慮是這些機構的主要招生方式。
沈州說,教培機構通常會發動學生家長,讓他們在親友中宣傳機構。有的機構還承諾每招來一名學生,介紹人可以獲得一筆提成,或是介紹人的孩子可以以優惠價格入學。于是,學生家長群體中混進了許多“機構托”。
“這些‘機構托會利用閑聊時間和家長會等場合,向其他家長傳播焦慮。這樣一來,周圍家長的焦慮情緒被極大調動,紛紛咨詢該怎么做。這個時候再說出機構名稱,一些家長便會十分信服,趕緊去交錢報班。”沈州說。
家長的焦慮心理每到寒暑假就會被放大數倍,似乎不趁著這段時間惡補,孩子在開學后就會被同班“學霸”甩在身后,甚至被其他同學“彎道超車”。
記者發現,這類焦慮甚至從幼兒園階段開始,就在一些家長之間傳播,并且線上線下涌現出許多補課培訓班,從才藝特長到學科輔導應有盡有。家長急得焦頭爛額,孩子忙得不可開交。
面對家長陷入的“教育焦慮”,學生更是“有苦難言”。安徽宿州的小宋向記者吐槽說,在學校,老師會說“不提前預習就會跟不上下一學期的教學安排”,要求家長幫助學生利用假期的時間提前把下一學期的課程自學,所以,學生就會有兩套教材,一套提前買來自學,一套學校統一發放正式上課時用。
“成績下滑一點,家長就要給我報補習班,一對一輔導,晚自習輔導,課間輔導,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時間,假期幾乎不存在。”小宋回憶說,尤其是在中考結束后的那個暑假,她好像直接無縫銜接到高一,根本沒有暑假。
抵制販賣焦慮行為
記者發現,機構銷售課程時“販賣焦慮”已是常態。這種宣傳活動是否合法?北京中征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孫維認為,機構通過廣告來增加曝光度,以期獲得更好的銷售結果沒有問題,但在廣告中以“販賣焦慮”的方式來尋求營銷效果十分不妥。
孫維說,《廣告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教育、培訓廣告不得含有下列內容:對升學、通過考試、獲得學位學歷或者合格證書,或者對教育、培訓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證性承諾。”雖然“販賣焦慮”并未直接體現為一種保證性承諾,但通過“如果不……就會……”的方式反向表明了其教培課程或教材、書籍在升學、通過考試、獲得學歷學位等方面的必要性,實質上是一種暗示的保證性承諾,該行為違反了《廣告法》的規定。
同時,《廣告法》第三條規定,廣告應當真實、合法,以健康的表現形式表達廣告內容,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第四條規定,廣告不得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不得欺騙、誤導消費者。嚴格意義上來講,“販賣焦慮”屬于一種“不健康的表現形式”,其內容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和誤導性,不符合《廣告法》對于廣告內容的要求。
對此,線上平臺該履行何種責任?線下培訓班打“販賣焦慮”的廣告應該如何規范?
孫維說,根據《廣告法》第二條之規定,線上平臺屬于廣告發布者,其就所發布的廣告應當承擔法律規定的監管審核職責。《廣告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建立、健全廣告業務的承接登記、審核、檔案管理制度。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依據法律、行政法規查驗有關證明文件,核對廣告內容。對內容不符或者證明文件不全的廣告,廣告經營者不得提供設計、制作、代理服務,廣告發布者不得發布。”
“如果認定某些教育培訓類廣告違反了《廣告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廣告發布者對此明知卻仍繼續發布的,監管機構有權根據情節嚴重程度,依據《廣告法》,對發布者處以罰款、暫停廣告發布業務或吊銷營業執照等行政處罰。”孫維說。
孫維認為,廣告依法應當具備可識別性,線下培訓機構的廣告內容應當能夠使廣大家長學生辨明這是廣告,而不是試圖以一種“科學”的角度闡述教培課程和教培書籍的必要性,通過“販賣焦慮”這種引導性的內容導致消費者產生誤解。對此,行政機關應當積極履行監管職責,進一步規范線下培訓機構發布廣告的行為。
(摘自《法治日報》韓丹東、王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