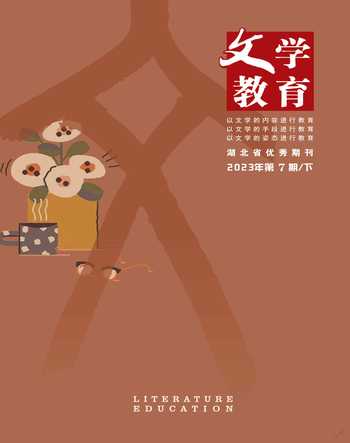初中教材中敘事散文和小說的比較
焦瑞
內容摘要:敘事散文和小說是初中語文教材中很重要的兩種文體,雖然二者都具備記敘類文本的特征,但在故事的真實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情節的完整性以及環境描寫方面均有較大差別。當前的語文教學中,教師往往會忽視二者的異同,這會使教師在解讀方式和教學方法上存在誤區,本文將以《散步》和《植樹的牧羊人》兩篇課文為例來闡述敘事散文和小說二者之間的異同點,以期對廣大教師的教學以啟發。
關鍵詞:敘事散文 小說 真實 典型
王榮生老師認為,中小學語文中的“散文”特指“現代散文”,關于散文的分類也不用將其放在古代文學的的視域下進行考察,這樣關于散文的分類就會比較簡單。[1]葉圣陶提出散文的三大分類原則:一要包舉;二要對等;三要正確,將散文分為敘事散文、抒情散文、議論散文。因此我們暫且將初中語文教材中的散文分為以上三類。其中敘事散文側重于再現作者生活中的真實經歷和見聞,以此來傳達作者的情思,敘事散文的情感抒發往往是含蓄內斂的,熔注于所敘事件中。同樣屬于敘事類的文本的還有小說,二者雖是不同的文體,但文本中都注重敘事,因而有必要對二者進行區分。
一.敘事散文和小說在課程標準中的學習要求
在最新發布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以下簡稱“課程標準”)學業質量評價中提到:“七到九年級的學生要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文學作品,在閱讀過程中能把握主要內容,并通過朗讀、概括、講述等方式,表達對作品的理解;能理清行文思路,用多種形式介紹所讀作品的基本脈絡;能從多角度揣摩、品味經典作品中的重要詞句和富有表現力的語言。”[2]通過解讀課程標準,我們發現課程標準當中對散文和小說的教學要求并沒有分開進行具體闡釋,而是將二者放在一起來要求,一定程度上將二者只視為一種文體來對待,并沒有基于文體意識而給予嚴格的劃分。課程標準一定程度上是課程教學的指向標,當教師沒有了課程標準的指引,勢必會在備課和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有較大的隨意性,會基于敘事散文和小說同屬記敘類文本的特征,不加區分的將敘事散文按照小說的傳統教學模式來進行分析和教學,散文教學的審美性將無從體現。
二.敘事散文和小說在單元導讀中的學習要求
《散步》選自部編版初中語文七年級上冊第二單元,本單元還包括一篇回憶性散文、兩首散文詩以及兩篇文言文,本單元的學習要求是:重視朗讀,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調,注意語氣、節奏的變化。在整體感知全文內容的基礎上,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3]《植樹的牧羊人》則位于該冊教材的第四單元,這個單元還包括一篇議論文、一篇哲理性記敘散文以及一篇文言文,編者在單元導讀中對學生的學習建議是:繼續學習默讀,在課本上勾畫出關鍵語句,并在你喜歡的或有疑惑的地方做標注,在整體把握文意的基礎上,學會通過劃分段落層次、抓關鍵語句等方法,理清作者思路。[4]
通過對敘事散文和小說單元導語的解讀,我們能感受到散文教學的重點是對作者情感的感悟,而小說則注重對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的分析,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散文就缺少情節、人物要素,但情節和人物只能作為表達情感的蹺蹺板,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對情感的把握和分析上。
三.敘事散文和小說的差異性
敘事散文和小說都屬于記敘類文本,但在敘事方面卻有很大的不同。小說的敘事往往是客觀的,往往通過一個完整的事件,塑造一個典型的形象,而散文的敘事則主觀性更加強烈,通常選取生活中真實且令人感觸頗深的一個片段,借此表達作者自身的感受和體驗,因此筆者將以《散步》和《植樹的牧羊人》兩篇課文來具體論述敘事散文和小說的差異性。
(一)事件的真實性
從敘事散文的特征出發,我們會發現,敘事散文更強調所敘事件的真實性,一般描述的都是真人真事,都是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給自己留下深刻記憶,讓自己難以忘懷的事件。在《散步》這篇敘事散文中,作者莫懷戚擷取自己全家三輩四口人散步的真實場景。散步是我們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再小不過的一件事,但是為什么作者會偏偏寫這件事呢?敘事散文中作者所描寫的片段并不是隨隨便便選取的,而是那個可以引起作者產生某種獨特情感的場景,我們可以將散文比作生活的浪花,敘述的過程一定是觸發了作者的心緒。作者莫懷戚寫這篇散文是在1985年,父親不久前去世,母親的身體也大不如前,也需要人照顧,因此作者才提議一家人出門散步,去感受大自然,放松心情。而尊老愛幼本就是中華悠久的傳統美德,作者的外國朋友是非常贊譽這種文化傳統的,而反觀自己卻對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并不重視,而散步這段生活片段,使作者對對此深有感觸,提醒自己要守住這份傳統,而不應該等到“樹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時候再去盡孝。作者在描繪一家人去散步的原因時寫道:“母親本不愿出來的。她老了,身體不好,走遠一點就覺得很累。我說,正因為如此,才應該多走走,母親信服地點點頭,便去拿外套。她很聽我的話,就像我小時候很聽她的話一樣。”[5]這段話讓我們感受到了,身為兒子的作者對母親的關愛,也體現了他們母子之間濃濃的親情,我們也會為之動容,往往只有真情是最打動人的,因此我們會自然相信這是作者基于自己的親身經歷而寫成的文章,我們很難懷疑其真實性。作者將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一個場景,描繪地自然而感人至深,當讀者的經歷與作者的經歷發生交匯,便能很自然的與作者共情,進而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真情實感。
而小說的本質特征則是虛構,幾乎所有的作家都強調小說的虛構性,作家虛構一個故事,讓讀者通過閱讀去體驗別人不同的人生,讓讀者產生讀了一本小說就像體驗了一次不一樣的人生之感,這便是小說的價值。《植樹的牧羊人》是法國作家、電影編劇讓·喬諾寫的一篇小說。小說講述了一位名叫艾力澤·布菲的老人,用一根鐵棍將荒原變為綠洲的偉大事跡。讀完小說我們無不為老人的壯舉感到由衷的欽佩,文中的每一處描寫都寫的那么真切,就好像一切都在我們眼前一樣。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其實小說中的事件是作者虛構的一個故事。1953年,美國的一個雜志向讓·喬諾約稿,希望讓·喬諾以“你曾經見過的最非凡、難忘的人是誰”為主題寫一篇文章。從該主題來看,編輯的初衷肯定是希望他寫一個真實的人物,但他卻恰恰虛構了一個人物,但誰也不會去懷疑這個人物是否存在,這個故事到底是不是作者親身經歷的。相信每一個讀過作品的人都被震撼了,編輯也不例外,他為了證實故事的真實性,不惜千里迢迢去調查,后來在作者讓·喬諾發表的聲明中,人們才知道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他虛構的,如果沒有他的澄清,估計沒有人會懷疑故事的真實性。
有些小說我們可能會因為所敘事件的感人至深而將之認為是散文,但是經過對作者人生經歷以及寫作動機的了解之后,便可發現原來這些不過是作者的虛構。與敘事散文相反,小說不追求故事的真實可靠,往往帶有一定的虛構性。因此在日常的教學過程中,判斷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真實性時,教師在教學前需要了解作者的寫作動機以及人生經歷,做到知人論世,才能更好的教學,還原作品的底色。
(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敘事散文并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典型性,因此在人物刻畫方面并沒有費特別多的筆墨,不會特別突出某個人物的形象特點,而是將人物放在同一個平面,沒有差異化對待。在《散步》這篇敘事散文中,我們沒有對哪個人物形象印象很深刻,因為作者展現的是一家四口的群像,相比于對人物刻畫,作家更看重的是講述故事本身和表達真情。相比于敘事散文,小說則注重對人物形象的刻畫,讀完《植樹的牧羊人》這篇課文,我們會對艾力澤·布菲這位老人印象深刻,但是這篇文章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顯得較為獨特,作者并沒有集中描寫老人的形象,而是描寫的較為分散,開頭說他有“慷慨無私、不圖回報”的精神,后面對他的形象的塑造都體現在他所做的事情當中,通過“我”三次到訪,看到荒漠變綠洲的奇觀,使我大受震驚,讓讀者更覺艾力澤·布菲的偉大,體現的是側面烘托的作用。
敘事散文和小說二者雖然同為記敘類文本,但在人物的塑造上卻體現出了較大的不同,典型的人物形象是小說重要的靈魂,能讓人過目不忘,成為千古流傳的佳作,為什么我們至今仍然對《水滸傳》中行俠仗義的武松、率真忠誠的魯智深以及有情有義的宋江都印象深刻,我想這就在于施耐庵對人物形象塑造的高超技藝。因此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在教學小說時要注重對典型人物形象進行解讀,而散文教學不必苛求對人物形象的分析。
(三)故事情節的完整性
敘事散文以“情”為要義,重在所敘的事件,敘事散文通常不需要包含記敘文的每個要素,它的“敘事”不需要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一般的記敘文相比形式也更靈活。《散步》這篇敘事散文,故事很簡單,作者也沒有花過多的筆墨在描繪這件事,只是簡單幾句,通過一次全家三輩四口人散步這樣一件小事,來表達自己對生命的思考,體現了濃濃的親情。敘事散文不要求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和完整,重要的不是講清楚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而是注重情感的表達。
故事情節是小說的三要素之一,是塑造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人物是存在于情節中的,小說的故事情節通常是完整且有邏輯順序的,是按照開端、發展、曲折、高潮、結局五個部分組合而成的。在《植樹的牧羊人》這篇小說中,講述的是一個長達三十幾年的故事,小說中的“我”三次來到這片荒原,見證了它的蛻變和神奇的誕生,情節相對完整,符合小說對情節完整性的要求。因此在教學敘事散文時,教師應該讓學生重點體會作者的情,而不是所敘的事,透過現象看本質,通過所敘之事,來體會真情。而小說的教學,教師則需要帶領學生去理清文章的發展脈絡,分析各個情節場景的精妙之處,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四)環境描寫的寫實性
敘事散文的環境描寫是經過作者“加工”之后呈現出來的,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被作者寫入散文中的景,往往都會成為情感的寄托物,《散步》中描寫景物的地方有兩處。第一處在第四自然段:“大塊兒小塊兒的新綠隨意地鋪著,有的濃,有的淡;樹枝上的嫩芽兒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著水泡兒……這一切都使人想著一樣東西——生命。”[6]作者借對春天萬物復蘇的描寫,引出文章的中心主題“生命”。近來母親因為父親的離世,而常常悶在家里,作者提議全家人出去散步,作者借綠色滿滿的春景,來表達對生命的熱愛。第二處在第七自然段:“那里有金色的菜花、兩行整齊的桑樹,盡頭一口水波粼粼的魚塘。”這里描寫的是小路的景色,在一家四口散步時,產生了走大路還是走小路的兩難選擇,作者因為心疼母親,擔心走小路腿腳不便,所以提議走大路,而母親因為寵愛孫子提議走小路,兩種選擇都是在為對方考慮,體現了祖孫三代之間濃厚的親情,和諧美好的家庭氛圍躍然紙上。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敘事散文中的環境描寫有烘托感情的作用,往往帶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如果刪去了這部分內容,會使文本缺少畫面感,使敘事散文黯然失色,只是敘事而少了情感和深意。而小說中的環境描寫則比較注重寫實,通常用白描的手法來寫,景物只是起烘托的作用,并不代表作者情感,《植樹的牧羊人》中的場景描寫其實是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服務,這篇課文既沒有詳細的寫老人牧羊以及植樹的過程,而把主要的篇幅用來寫“我”三次到訪普羅旺斯看到荒原發生的變化,帶來的視覺震撼,第一次見面“我”看到的場景:“這里海拔一千二三百米,一眼望去,到處是荒地。光禿禿的山上,稀稀拉拉地長著一些野生的薰衣草。”第二次見面:“1910年種的橡樹,已經長得比我都高……這片樹林分為三塊,最大的一塊,有11公里寬。”第三次見面:“一切都變了,連空氣也不一樣了。以前那種猛烈而干燥的風,變成了飄著香氣的微風;高處傳來流水般的聲音,那是風穿過樹林的響聲”。作者對三次“我”所見之景的描寫是為了讓我們看到老人這幾十年對這片荒原所做的貢獻,正是他的執著和無私使得這里的人們也過上了幸福的生活。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中的場景描寫一般比較簡單,帶有較強目的性,不是為人物服務,烘托人物形象,就是為主題服務,突出主題。本篇課文中的場景描寫是作者對所到之處環境的描繪,也是推動情節發展的一部分,最終是為了文章的主題服務,表現老人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的偉大壯舉。
通過上述對比,我們發現敘事散文和小說在課程標準中并沒有明確二者之間的教學區別,而明辨文體體式是進行文本解讀的前提,也是進行閱讀理解基本路徑,因此教師需要在日常的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文體意識,文體不同,教學的重心也會不同,只有區分不同類型的文體,才能進行合理的閱讀和理解,發現文章的本真。
參考文獻
[1]王榮生.散文教學教什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25.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19.
[3]向東佳.學會記事抒親情——七年級上冊第二單元整體教學設計[J].語文教學通訊,2021(Z2):18-23.
[4]張娜.統編版初中語文綜合性學習實施策略研究[D].青島大學,2022.
[5]教育部.義務教育教科書語文七年級上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19-65.
[6]孫志廣.夏穎.看似平常卻奇崛——莫懷戚《散步》解讀[J].中學教學參考,2021(24):6-7.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