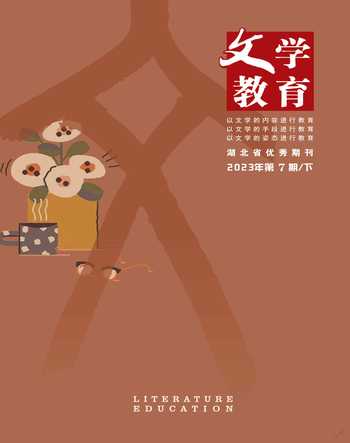論傅山遺民心態的復雜性
靳彥
內容摘要:清初遺民與貳臣交往心態十分復雜。著名遺民傅山與仕清官員魏一鰲在順治年間交往密切,其交游心態可作為清初遺民與貳臣交往的典型。在考察他們交游情況的基礎上,主要以傅山為視角,對其與魏一鰲交游過程中尋求政治庇護、生活幫助的功利性心態與對魏一鰲欣賞、同情、理解的心態略作分析。
關鍵詞:傅山 遺民心態 魏一鰲 書信
廣義的遺民一般指的是改朝換代后不仕新朝的群體。而從“夷狄華夏”的儒家傳統觀念出發,中國封建王朝中漢族王權喪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只有元、清二朝,因而宋、明之季仍不仕新朝的群體乃是嚴格意義上的遺民。貳臣是指易代時出仕兩朝的臣子,廣義上在前朝參加科舉獲取功名,易代后在新朝任職者亦屬貳臣。一般來說,遺民與貳臣是水火不容的兩個群體,但清初遺民與貳臣交往卻較為普遍。
傅山(1607-1684)是清初重要的遺民之一,其人高風亮節,明亡后投身反清復明,晚年力辭博學鴻詞,堅決不仕清朝,堪稱明遺民之代表。傅山與較多仕清官員有交往,魏一鰲是其中交情最深、影響較大的一位。傅山與魏一鰲的交游可為清初遺民與貳臣交往之典型。由于魏一鰲《雪亭文稿》中留存關于傅山的書信只有一封,因此考察傅山與魏一鰲的交游主要以目前發現的傅山寫與魏一鰲的書信為主,并以相關的少量詩歌唱和為輔。
一.傅山與魏一鰲的交游
魏一鰲(1613-1692)字蓮陸,直隸新安人。崇禎壬午年(1642)舉人,第二年因語多譏刺中官而進士落第。明清鼎革后順治二年(1645)清朝政府為網羅人才鞏固統治舉行科舉,魏一鰲被迫參加考試,得一等,八月授山西平定州知州,一年后因意外事件被謫,補山西布政使參軍,順治六年(1649)升布政司經歷,后署任沁州知州、太原同知。順治十年(1653)轉授泗州知州,因其弟魏一鯤與父魏梁棟去世遂守喪平定未能赴任。順治十三年(1656)丁憂期滿后授山西忻州知州,兩月后旋即辭官返回故鄉保定[i]。魏一鰲為官期間,清正廉潔,為民紓困,有實干才能,又與明遺民為善,因順治二年魏一鰲就已拜孫奇逢為師,辭官后的他便跟隨老師研究理學,是孫奇逢最重要的弟子之一。
根據傅山致魏一鰲書信第一札,“棲棲三年,以口腹累人,一憶閔安道,輒汗浹背”[ii],“棲棲三年”是指甲申(1644)國變后的三年,這是傅山寫與魏一鰲的第一封書信,可知他們于順治三年訂交。在這封信中傅山幾乎通篇使用佛教語以表明自己此時逃禪的立場:“果見知容,即求以清凈活命乞食之優婆夷及一比丘為顧,同作蓮花眷屬。即見波羅,那須頓施朱題之寶,令出家人懷璧開罪也”,可知傅山很清楚與仕清官員交往意味著什么,對與魏一鰲的交往保持著距離和警惕。同時傅山在信中提到了魏一鰲《吊朱莆城》一文,這是追悼甲申年李自成攻城時堅決不降、投井而死的陜西蒲城知縣朱一統的文章。傅山很欣賞此文,這意味著他贊賞魏一鰲表彰忠烈、同情遺民的行為,這也是傅山與之交往的前提和基礎。
(一)魏一鰲對傅山的幫助
魏一鰲在山西為官期間,傅山常向其尋求幫助。有時候是所用書籍:“爾楨家藏之廿一史,久已為戴二哥買去,孫大哥要此,似難復。再道省中尚有一部,弟當圖之。”有時候是書寫所用的墨錠:“行笥中有點書朱錠,急須一二塊,可得否?不然,且須絕高銀硃亦可。”有時是招待客人必須用到的酒:“弟本不飲,而此時為老親生日,人情始擬酬謝,頗需此。欲親教時,領一村力負兩壇,還不知能助瓦盆之興否?魏一鰲有時也會主動送酒給傅山“酒道人以酒遺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甚至建造房屋給傅山住。順治十七年(1660)傅山母親去世,他托魏一鰲代求理學大師孫奇逢為其母作墓志銘,這是魏一鰲《雪亭文稿》中唯一一封關于傅山的書信:“惟冀毀不滅性,加餐自珍。兼聞欲求征君老師作墓志,囑弟等為之先容”[iii]。
除了物質上的幫助,傅山還常請魏一鰲利用職權為自己處理一些不得已的事情。像順治六年傅山在平定為子傅眉操辦婚事,想將母親由太原接至平定,但太原當時因姜瓖起義而戒嚴,因此請魏一鰲幫忙:“老親擬有平定孫婦之娶,而適丁郊壘閉之,太原縣城戒嚴不能出,謂翁臺可代為山謀而引手也。”或是順治九年(1652)請魏一鰲幫忙免除自己老家忻州的地稅:“寒家原忻人,今忻尚有薄地數畝……今為奸胥蒙開實在糧石下,累族人去催比,累兩家弟包陪,苦不可言。今欲具呈于有司,求批下本州,查依免例,不知可否?”或是請魏一鰲幫助親友子弟科舉考試:“古度所白事由封上,其意尚須與軍廳一稟……張童名頵,卷子急蹙不就,但求冊中一名可耳。”或是請魏一鰲幫忙打官司,傅山書信中有九札所言皆為朱四命案一事;或是從魏一鰲處尋求政治庇護,如順治十一年(1654)的“朱衣道人案”,這在第二部分中展開。
(二)傅山的回報
“明清鼎革并不是一場社會革命,它并沒有對舊有的社會文化結構予以本質上的改革。改朝換代對傅山的政治經濟地位雖有直接的損害,但他的文化聲望并沒有受到影響,他依然擁有不可低估的文化資本”。何況對于傅山這樣的在當時就已經贏得聲望與名譽的書法大家、社會名士、故國遺老,不少人都想要求得傅山的真跡,甚至在民間,傅山似乎是一個“文化象征符號”的存在。傅山雖然不愿意將書法作為一種應酬來對待,也不愿“為人役”所累,但有時不得不如此。魏一鰲便屬于傅山不能拒絕的人物,傅山為其書寫主要有這幾種情況:一種是遇到突發事件,作為朋友傅山必須得寫,像順治十年魏一鰲父親魏梁棟和胞弟魏一鯤去世,魏一鰲請傅山作挽聯與傳記:“賢仲之戚,正擬遣家弟代申一奠,行另勒致誠……所命挽章,不得卒辦,少需數日,定有報也。”在傳記中傅山贊揚了魏梁棟事親至孝感天地、為政體恤民生、樂善好施的品質。另一種是出于回禮或交情贈與魏一鰲,如“酒道人濱行,宗生黃玉與家弟止約我輩三五人為屏材,而囑筆僑黃……決不可令一俗人見也”。還有一種情況是魏一鰲應別人之托請傅山寫,如“與淄川作字即奉命,但題后須及尊意,不知當如何書,又不諳此君性情何如,尚求一教”。
傅山為世人所知,還在于他的醫名與醫術。傅山不僅有許多醫學專著,甲申以后更是游行世間,以醫道活人,在民間被稱為“仙醫”,其醫術之高超在晉地家喻戶曉。傅山與魏一鰲書信中有五封涉及詢問魏一鰲身體狀況及為其家人診治之事,像順治十三年為魏一鰲診病:“火病之藥,無過平心。春肝用事,君焰易張,聽政之時,切忌暴怒。待弟至,再一切之,可斟酌一常服丸方,濟門下平和之用,萬無燥急加劇。”或是為魏一鰲弟弟診病,并給出調理建議:“切賢仲脈,六分病耳,喜未大數也。微察其意,以未得適理。養病亦須造適,而食息起居不時,監之以一嚴君,此中不無愛而不得其愛之法。”
二.傅山與魏一鰲交游的心態
(一)功利導向
傅山曾說自己“生平不登宦人之堂”,對本朝官員都是如此,何況是仕清的魏一鰲呢?這不得不考慮到明遺民在政治、經濟各方面艱難的生存處境。明清鼎革之際,新的勢力崛起,舊王孫及士人群體失去原有的政治經濟特權,加之戰爭對經濟的摧殘以及清朝政府對遺民的暴力鎮壓態度,因此明遺民或是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求助及接受貳臣的接濟,或是參與反清復明以尋求貳臣庇護。國變后傅山秘密聯系義軍常流寓山西各地,過著舉家無定的清貧生活,在物質上常常匱乏,因此他在生活物資上常向魏一鰲求助,魏一鰲也常主動接濟傅山,這在第一部分中已有說明,此處不再贅述。需要注意的是,物質上的困難是傅山諸多遺民朋友如戴廷栻等人可以幫忙解決的,但政治上的庇護以及必得用職權才能完成的事便非魏一鰲不可了。
傅山參與了幾次反清復明活動,與魏一鰲有緊密聯系的是順治十一年的朱衣道人案。“朱衣道人案”起因于南明朝廷秘密聯絡各地抗清義士的宋謙,此人在順治年間多次到過山西各地,順治九年到十年之間到汾陽會見傅山。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宋謙預備在晉冀豫交界的涉縣索堡山起義,不幸于起義前兩日事泄被捕,嚴刑下供出傅山等人,招供后宋謙即被處死,六月傅山被捕。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們已不可知,傅山雖在供詞中極力擺脫與宋謙之關聯,但根據宋謙供詞中對傅山的年齡、衣著、位置知曉得甚為精確,再加上傅山本就有反清復明之志,這次秘密活動其母貞髦君也知曉,“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iv],可知傅山確實是知曉此次密謀活動并欲參與其中的。經過清朝大員多方營救,傅山于次年七月才得以出獄,其中魏一鰲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白謙慎先生的專著《傅山的交往和應酬》中有專節研究,此處作一梳理:
1.傅山在一入獄時的供詞中提到了他在拒絕宋謙時,魏一鰲親見,可為其作證:“書也不曾拆,禮單也不曾看,又拒絕了他。他罵的走了。彼時布政司魏經歷正來求藥方,在坐親見。”魏一鰲此時確實是在平定州丁憂,但事實上對此事并不知情,這從王余佑《魏海翁傳略》可知:“值青主遭意外之禍,受刑下獄,昏惑中,夜夢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與其子,俱不解。及再審問,官詰其有無證人。青主忽及公,強指以為證。”所幸魏一鰲“不顧利害,極以青主之言為然”,才使案情有了緩解。在這危急關頭傅山指魏一鰲為證以及魏一鰲力證傅山清白,說明傅山確實是以魏一鰲為庇佑,而魏一鰲也有保護傅山的能力。
2.除了傅山友人的周旋與幫助,在“朱衣道人案”審判的過程中,山西省官員邊大綬、中央官員龔鼎孳等人在營救傅山的過程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魏一鰲六次為傅山作證后,六月底太原知府邊大綬為傅山開脫:“至于傅山,因被賊禍,久作黃冠,云游訪道,審未交結匪類。”七月初三守寧道參政董應徵和巡寧道僉事盛復選為傅山開脫:“至傅青主山者,既系生員,才學又優,何不博取功名,以圖效用,輒爾棄家游食,甘為傲世肆志之形狀?……奉旨有云不得連累無辜,應否別議,統侯裁奪。”十月七日,三法司任濬、龔鼎孳、尼堪等人為傅山開脫:“俱傅山供稱,有姓宋道人二次求見,山并拒絕,未曾見面,有布政司魏經歷親見。及加嚴訊,復供若宋謙認得山,請愿甘罪。情似無干。且當日宋謙口供,止言其在汾州一帶游食訪人,原未云所訪何人。謀叛大案,豈容以一語懸坐?”直到次年正月山西巡撫判決傅山無罪,七月三法司判決釋宥,傅山才得以出獄。試問,若沒有魏一鰲首當其沖冒險作證,還會不會有那么多官員為傅山開脫呢,即使有,他們敢不敢這樣做呢?由此可知,魏一鰲冒險為傅山開脫在案件推進及博取審案官員同情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除了政治上的保護,傅山與仕清官員魏一鰲結交以尋求庇護還體現在生活中意外發生的事件上。傅山致魏一鰲書信中有九札所述順治七年(1650)朱四命案發生后,傅山尋求魏一鰲幫助打官司最終勝訴的事。
事情起因于傅山與友人在好友楊爾楨兄長莊園相聚,內侄張仲的女婿朱四蕩秋千時意外卒于架下,因楊爾楨兄長素與鄉約不合,朱四的兄長又是無賴兇頑人,傅山擔心原本的意外事件會被當地鄉約借機報復,所以請魏一鰲幫忙從中周旋。這是發生在陽曲縣的案件,據艾俊川考證魏一鰲此時任太原府同知,因此魏一鰲不僅是陽曲縣令的上司,而且有辦理刑事案件的實權[v]。一開始傅山希望魏一鰲能越級直接審理此案,“懇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行”,以免去很多刁難和打點的財物。之后魏一鰲派人查驗,朱四順利入殮,但其兄突然反口,狎昵滿人,并挑唆村人誣告,傅山無奈只得再次求助魏一鰲:“弟輩所恃惟在臺下,若臺下還用大法力杜此兇計,亦不須別用弟輩委曲;倘此輩吞詐之心不已,孺子袖中已具有呈文,將先發制之。或撫或司道,總求指示而先容之,并為審處宜如何如何,期于鎮壓懲創此輩”,傅山希望魏一鰲或是先強力鎮壓使其打消上訴的想法,要么就先發制人,張孺子呈文,魏一鰲負責疏通關系。與此同時朱四一方也采取措施聚集勢力,不僅將朱四尸體隱處割破企圖誣陷,而且向臬司狀告傅山與弟傅止,陽曲縣差欲搶先審理此案。這次魏一鰲親自驗尸,最終以鄉約被判十五大板、朱四兄長被判刑發配結束了案件。
(二)理解之同情:傅山與魏一鰲的友情
一些明遺民與貳臣交游是因為他們在明未亡時就已是好友,國變后雖立場不同,但難忘故交不忍絕交。傅山與魏一鰲雖不算舊相識,但他與魏一鰲交往不只是抱有功利性的心態,“友誼和功利的結果并不相悖”,傅山對魏一鰲亦有惺惺相惜的真情在。
首先,魏一鰲與傅山個性氣質的相似使得傅山十分欣賞這位尚俠的好友。傅山送給魏一鰲辭官之際的行草十二條屏寫道:
當己丑、庚寅間,有上谷酒人以閑散官游晉,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輒自號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宗生璜囑筆曰:“道人畢竟官也,胡不言官?”僑黃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則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道人方將似有志用世,世難用而酒以用之。
中國古代通常“茶、酒”對舉,“茶”和“酒”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與品性,“茶與酒跟中國文人性格的形成大有關系……文人的‘熱腸或‘幽韻,都可能跟酒和茶的特性有關。”[vi]魏一鰲自稱“酒道人”,傅山也避而不談魏一鰲仕途生涯,反而以“酒”來總結、稱呼其人,可見魏一鰲是“熱腸”的,或者說是俠義的,這從他多次自捐俸祿安葬貧不能葬的明朝故宦,代替州民贖回因官事被迫賣掉的女兒,以及他多次仗義幫助傅山等行為來看,這種氣質與傅山很相像。傅山也是個好酒的人,他的書信中有很多次提到酒,魏一鰲也幾次送酒給傅山。同時傅山身上也有一種游俠氣質,而立之年他領導學生運動為老師袁繼咸伏闕訟冤的壯舉被認為是晉地反抗閹黨的政治斗爭的勝利。氣質的相似,自然能夠互相吸引而結成好友。
其次,明清之際士人的出處成為一個很敏感的點,遺民們深惡痛絕仕清的降臣,傅山對此也曾發表過議論。但傅山并不以“貳臣”看待魏一鰲,他對魏一鰲有著深深的理解。如上何以傅山不談論魏一鰲為官的生涯?這與傅山不愿出仕清廷的心態有關,還與魏一鰲出仕清廷的原因有關,這一點傅山定然是理解魏一鰲的。魏一鰲本性恬淡,嗜好讀書,明清鼎革后本不欲再參加科舉,迫于清政府的政治高壓無奈被逼赴選,這是外因。另外,清初政局不穩,戰亂頻繁,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這是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知識分子所不忍心的,唯有忍辱出仕,盡快穩定時局,恢復民生,魏一鰲便是這樣做的。他深知這樣做的性質,也真切地感知到維持世運、鼓舞來學其實是比隱居更難的事情:“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楚才之諫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謂為靜修易,為楚才、平仲難。”[vii]然為官八年后魏一鰲辭官隱去是出于對官場的失望:好友張元玉“負經濟才,倜儻有大志,不能媕婀以悅上官”卻因卷入“疏縱故明藩王”案而慘遭冤殺,這對魏一鰲刺激很大。并且,魏一鰲是個同情、理解遺民的人,面對清廷不斷使其查辦遺民相關案件,他感到十分痛苦與為難,也看清了清廷的本質。[viii]這諸種心曲,傅山是理解的,他理解魏一鰲為何好酒,為何出仕,又為何最終辭官隱居,故而才能說出“道人方將似有志用世,世難用而酒以用之”,而不以簡單的“貳臣”來定義魏一鰲,這樣說來,傅山可謂是魏一鰲的知己了。
如此,傅山屢屢向魏一鰲吐露心曲:
六月廿五之別,未忍剌剌,面墻無語,情不勝鳴,是有小詩八句,起頭則曰:“皆違老母久,吾所不忍留。”當時亦遂不敢出諸口。別三日遂大漸,不食又八日,幾死復生,至七月廿二扶病出獄,至今荏苒沉彌,不能自支,不知當如何理。總是無恥丈夫,那堪自對,是有出獄口占之句,曰“有頭朝老母,無面對神州”也。
這是傅山朱衣道人案出獄后寫給魏一鰲的書信,信中不僅描述了自己在獄中絕食反抗的情景,更是表達了自己不能以死報國委曲求生的羞愧和無奈。傅山此種心態是極其矛盾復雜的,在獄中雖抱著慷慨赴死的決心,卻又以絕食拒不招認,且在供詞中始終不承認自己與宋謙有染,又托朋友多方援救,可見傅山是不想也不愿輕易死在牢獄中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只有先保全自己,才有以后繼續抗清的可能;另一方面,傅山老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贍養,他無法置母親于無依無靠的地步。出獄后的傅山認為自己茍活于世有愧于為國捐軀的眾多義士,也無顏面對被清兵入侵的神州大地,因而自責悔恨不已。傅山很少對人提起這段人生中意外的插曲,卻對魏一鰲推心置腹訴說自己難以向人言說的情愫,可見其交情之深厚。
再如順治十三年傅山寫給魏一鰲告病辭官之時的書信:
衰病日浸……人心之不可測,何必平定?只是自尋一不惹人地步。古德桑下一宿即抽身,豈復慮桑能害人?正自勇于割舍,所以一瓶一缽,形如飛鳥,便于動轉耳……弟連日復受外侮,無法御之,正在苦惱中,復聞舊游仳離之信,益深悒悒。
傅山對魏一鰲的離去充滿不舍,同時要注意的是,這是寫于順治十三年的書信,這一時期正是明遺民們心態搖擺不定、遺民意識淡化的時期。隨著清朝局勢的穩定和人們對清政府的承認,漸漸地士人們紛紛出仕,一些原來保持抵抗態度的明遺民們也慢慢轉變態度,繼續保持不出仕的明遺民的生存處境異常艱難。黃宗羲也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ix],戴廷栻也在族人的逼迫下不得不使自己的兒子參見科舉考試。傅山更是深刻感受到世人不可測之人心之涼薄與奴性,他們不僅對參加舉義的義士們冷嘲熱諷,并且視傅山這樣不肯出仕的遺老為“妄人”,認為誰與其交游便為“廢人”,恨不能“引領望如何得殺我一妄人而快”,傅山在信中對魏一鰲訴說自己連日受侮的艱難處境,可見當時境況之險惡。
清初遺民與貳臣交往的心態十分復雜,傅山與魏一鰲的交游正可作為這種關系的典型,對我們研究遺民與貳臣關系以及清初政治、文化生態具有很大價值。傅山與仕清官員魏一鰲從順治三年訂交,直到傅山辭世,他們的交游貫穿傅山半生,其中以順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魏一鰲在山西為官時最為密切。傅山與魏一鰲的交游心態,既有為生活所迫而接受魏一鰲資助、為反清復明獲取政治庇護的功利主義傾向,同時,傅山對魏一鰲也有著深厚的友情。傅山不僅十分欣賞他這位俠義的朋友,對魏一鰲仕清也懷有深深的理解,不以貳臣論其人,還對魏一鰲推心置腹訴說自己的諸種心曲。另外,遺民與貳臣的交往有其特定政治、歷史時期的特殊性,不能因為他們與貳臣交往就懷疑其遺民立場與遺民情愫,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整個遺民群體的人格氣節,而是“應抱著了解之同情,體恤明遺民生存的艱難、依附的無奈與隱忍的苦心”[x]。
參考文獻
[i]白謙慎.傅山的交往與應酬 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ii](清)傅山著.尹協理主編.傅山全書第二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iii]魏一鰲.《雪亭文稿》[M].康熙手稿本.
[iv](清)孫奇逢著.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v]艾俊川.傅山致魏一鰲手札編年[J].文匯學人,2017(09).
[vi]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vii]孫奇逢.孫征君日譜錄存[M].光緒十一年刻本.
[viii]張艷.以魏一鰲為中心考察清初漢官的仕隱[J].濱州學院學報,2022(03).
[ix](清)黃宗羲著.黃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x]薛以偉.“明遺民”與“貳臣”交游論析——以“明遺民”為視角[J].北方論叢,2016(06).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