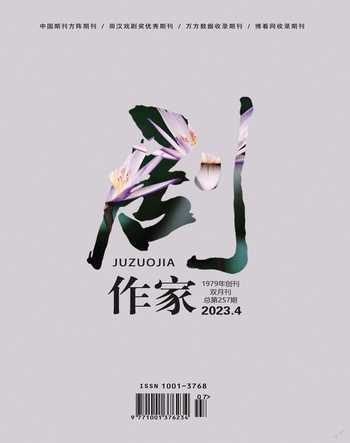弗洛伊德人格結(jié)構(gòu)理論視角下的《孤寂在棉田》解讀
張夢(mèng)婕
摘 要:《孤寂在棉田》是法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劇作家科爾泰斯的作品,獨(dú)特的戲劇語(yǔ)言歷來(lái)是他最顯著的創(chuàng)作特色。本文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角度,揭示科爾泰斯創(chuàng)作的深層心理動(dòng)機(jī)在這部作品中的投射,用人格結(jié)構(gòu)論拆解作品中買賣雙方的博弈,實(shí)為一種特殊的獨(dú)白形式,是作者潛意識(shí)精神活動(dòng)通過(guò)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進(jìn)行的自我表達(dá)。科爾泰斯用交易的形式呈現(xiàn)人在文明教化中的深度分裂,以及圍繞欲望展開的自我博弈。
關(guān)鍵字:弗洛伊德;人格結(jié)構(gòu)論;科爾泰斯;《孤寂在棉田》
貝爾納-瑪麗·科爾泰斯被認(rèn)為是法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但國(guó)內(nèi)讀者對(duì)這位西方劇作史上的重量級(jí)人物卻知之甚少。科爾泰斯作品最顯著的特色就是他獨(dú)特的戲劇語(yǔ)言,尤其是對(duì)獨(dú)白的使用。瑪麗-克洛德·于貝爾曾提到,“科爾泰斯終生致力于挖掘獨(dú)白這種戲劇話語(yǔ)形式的無(wú)限可能性”[1]。在他眾多大量運(yùn)用獨(dú)白的作品中,《孤寂在棉田》顯得有些特別。該劇只有兩個(gè)角色,每人18段“準(zhǔn)獨(dú)白”[2],皆為晦澀、詩(shī)性、哲理度極高的戲劇語(yǔ)言。但歷來(lái)從學(xué)者和舞臺(tái)創(chuàng)作者的角度,都將商販與顧客之間的交流作為對(duì)白來(lái)看待和處理。在此前提下,《孤寂在棉田》中買賣雙方的交易物究竟是什么成為一個(gè)難解之謎。但如果將《孤寂在棉田》中兩者的博弈視作一種特殊的獨(dú)白形式,也許能回答這個(gè)問(wèn)題。
弗洛伊德認(rèn)為,“就偉大的藝術(shù)作品而言,不利用精神分析學(xué),有些方面就永遠(yuǎn)不可能被揭示出來(lái)。”科爾泰斯的劇作無(wú)疑屬于偉大的藝術(shù),而作品恰恰是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意圖和情感活動(dòng)的有力表現(xiàn)。在作品的顯性文本中由表及里逐層深挖才能找到隱藏其中的潛在文本,達(dá)到對(duì)藝術(shù)家及其作品的深度理解。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dòng),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藝術(shù)家精神建構(gòu)和思想表達(dá)的過(guò)程,其來(lái)源可能涉及藝術(shù)家被壓抑的欲望,并在創(chuàng)作中被符號(hào)化地表現(xiàn),造成觀者理解意義上的缺失,但也同時(shí)勾勒出缺失的輪廓,以提供觀者追溯其表象之下內(nèi)容的線索。
一、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找尋自我的漫長(zhǎng)之旅
科爾泰斯出生于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的法國(guó)中產(chǎn)家庭,十歲被送入冉森派寄宿學(xué)校學(xué)習(xí),從小受到正統(tǒng)而規(guī)整的教育。冉森派信奉原罪說(shuō),寄宿學(xué)校的宗教氛圍又十分濃厚,提倡宗教讀物,強(qiáng)調(diào)虔信品德。從“自我”的人格發(fā)展來(lái)說(shuō),“本我”所受到的抑制顯然是很強(qiáng)大的。科爾泰斯成年后中途輟學(xué),去往紐約旅行,在那里接觸到美國(guó)六十年代的特殊文化語(yǔ)境,并在回國(guó)后開始投入創(chuàng)作。科爾泰斯的前期作品被認(rèn)為是“在先鋒文藝潮流影響下的產(chǎn)物,情節(jié)跳躍、閃回、拼接,是非線性而碎片化的”[3]。他對(duì)這些作品并不滿意,甚至拒絕承認(rèn),直到逝世后這些作品才被陸續(xù)出版。1975年因抑郁試圖自殺前的三年他都沒(méi)有作品問(wèn)世,但這空白的三年之后,迎來(lái)了他創(chuàng)作上的集中爆發(fā)。之后的作品煥然一新,甚至表現(xiàn)出一種古典主義的美感。
科爾泰斯熱愛(ài)旅行,其對(duì)異質(zhì)文化的執(zhí)著被投射進(jìn)他成熟期的所有重要作品中。科爾泰斯曾在二赴塞內(nèi)加爾前給友人的信中說(shuō):“我以為那是我的根之所在,我回去看,但我又一次發(fā)現(xiàn)我的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此地,慢慢地重新想象我的根在哪里。”[4]科爾泰斯成年前生活并不動(dòng)蕩,他的不斷行走和冒險(xiǎn)更像是對(duì)自我的探索和重構(gòu)。而作為一個(gè)藝術(shù)家,藝術(shù)創(chuàng)作顯然是將這種探索和思考的過(guò)程由內(nèi)而外的最佳途徑。
二十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的法國(guó)雖然受到美國(guó)同性戀平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影響,在制度上逐漸放松了對(duì)同性戀群體的處罰力度,但文化大環(huán)境的制約仍有很大影響,直到1982年才廢除制裁同性戀的法案。讓-馬克·朗特里曾結(jié)合精神分析理論和科爾泰斯從非洲寄給親友的信函分析《黑人與狗之戰(zhàn)》中白人姑娘對(duì)黑人Alboury的愛(ài)欲源自于科爾泰斯?jié)撛诘耐灾2⑶遥茽柼┧箤?duì)非洲及黑人文化的偏好也處處見于其作品。從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語(yǔ)境來(lái)看,白人青年科爾泰斯的真實(shí)“自我”很難得到正常的展現(xiàn),由此產(chǎn)生相關(guān)的創(chuàng)作沖動(dòng),在作品中隱晦地袒露成為一條釋放的路徑。
二、戲劇人物:“本我”與“自我”的角力
法語(yǔ)是科爾泰斯的母語(yǔ),法語(yǔ)中亦有“販賣/交易”一詞,但劇作開篇他卻選擇了英語(yǔ)的“DEAL”作為題眼。除了“交易(尤指販毒)”英語(yǔ)單詞DEAL另有“成交”的意思,也常在口語(yǔ)中用作“交易達(dá)成”的口頭表述。劇本伊始這段說(shuō)明性的文字,是除36段準(zhǔn)獨(dú)白以外唯一的訊息,更顯出其特殊的地位。這段文字是針對(duì)劇本中“販賣”一詞的界定,“販賣就是對(duì)嚴(yán)格控制或禁止的物品進(jìn)行一場(chǎng)商業(yè)交易,它是在中性的、不確定的、不可預(yù)見的場(chǎng)所成交的……”[5]從字面解讀,此處的販賣顯然意指“不被允許的商品”,再結(jié)合劇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欲望”一詞,綜合理解就是“不被允許的欲望”。不被允許的欲望意指在世俗或宗教意義上并不道德,甚至是一些驚世駭俗的存在,從弗洛伊德人格論的角度就是代表“本我”,是最原始的欲望。劇本中那個(gè)高處亮著的一扇窗戶意指符號(hào)化的“超我”,代表社會(huì)規(guī)范和倫理道德,而“自我”就是此時(shí)此刻的黃昏偶然闖入潛意識(shí)的這位顧客。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結(jié)構(gòu)論,“本我”是最深層、最原始也最不易接近的,代表了混亂的潛意識(shí)。“本我”是人類最本能的欲望,沒(méi)有善惡也無(wú)謂道德,只服從于快樂(lè)原則。“本我”在人類社會(huì)化的過(guò)程中逐漸受到壓制,從而發(fā)展出符合社會(huì)基本標(biāo)準(zhǔn)的“自我”,在某些文化語(yǔ)境中譬如宗教教義、社會(huì)制度、家庭倫理等的制約下,還可能產(chǎn)生代表“理想中自我”的“超我”,不斷監(jiān)察“自我”、壓制“本我”,以實(shí)現(xiàn)“更完善的人格典范”。“本我”與“自我”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特殊的聯(lián)系,因?yàn)閮烧弑臼且惑w卻又始終對(duì)立。欲望雖然受到壓制,但并不會(huì)消失,只能進(jìn)行轉(zhuǎn)化,經(jīng)常披上偽裝的外衣尋找突破口,有些成了夢(mèng)境,有些成了藝術(shù),有些則成了時(shí)不時(shí)一閃而過(guò)的那些“惡念”。
從這個(gè)角度再看劇本開篇這段說(shuō)明性的文字,“中性的、不確定的、不可預(yù)見的場(chǎng)所”很接近人的潛意識(shí)形態(tài),因?yàn)椴还軌?mèng)境、藝術(shù)還是那些一閃而過(guò)的念頭,都不受控。而“不分時(shí)刻,無(wú)論白天黑夜,在法定商業(yè)地點(diǎn)及營(yíng)業(yè)時(shí)間之外任意進(jìn)行,但總在它們歇業(yè)時(shí)”這句可進(jìn)一步論證,因?yàn)槿说臐撘庾R(shí)通常只在無(wú)意識(shí)或接近無(wú)意識(shí)狀態(tài)時(shí)才得以浮出水面。“交易”既是文眼,自然貫穿全劇,也是作者表達(dá)的核心。“本我”與“自我”的交易涉及最基本的哲學(xué)命題,即自我認(rèn)知。弗洛伊德在對(duì)精神病患者進(jìn)行治療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患者的“自我”會(huì)自動(dòng)抵抗“本我”,建起牢固的防御高墻,阻止那些被壓抑的欲望進(jìn)入意識(shí)層,而清醒時(shí)則表現(xiàn)為自責(zé)和自我懲罰。而正常人也一樣有著類似的壓抑,只是能運(yùn)用心理機(jī)制去調(diào)和兩者的沖突,不至于致病,但對(duì)這些欲望和壓抑通常不愿宣之于口,因?yàn)椤白晕摇笔抢硇缘模又俺摇辟x予的世俗羞恥感,更不會(huì)輕易表現(xiàn)出來(lái)。但日常生活中,“本我”與“自我”卻常常會(huì)在“中性的、不確定的、不可預(yù)見的”時(shí)候發(fā)生角力。“本我”被壓抑得越深,積聚的能量就越大,會(huì)通過(guò)遺忘、夢(mèng)境、藝術(shù)等方式來(lái)獲得釋放,而無(wú)法協(xié)調(diào)時(shí),則表現(xiàn)為精神疾病。更多的時(shí)候,“本我”與“自我”在某一微小的時(shí)刻進(jìn)行著無(wú)聲的交鋒,前者壓倒后者就會(huì)發(fā)生感性的放縱,后者壓倒前者就產(chǎn)生理性的克制。兩者膠著不下即表現(xiàn)為焦慮和痛苦,甚至短暫地觸及神經(jīng)官能癥。《孤寂在棉田》中商販與顧客這場(chǎng)關(guān)于自我認(rèn)知的博弈就是作者眼中始終無(wú)法達(dá)成交易的心靈之殤。
三、交易的形式:對(duì)話與攻防
弗洛伊德在《釋夢(mèng)》中用《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作為案例來(lái)解釋觀眾從“弒父”主題的悲劇中獲得快感的心理機(jī)制,源于人類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被藝術(shù)家用具有豐沛審美力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過(guò)偽裝后表現(xiàn)出來(lái),既讓觀眾享受到曾被壓抑如今間接釋放的愉悅,又維持了現(xiàn)實(shí)意義中的倫理道德。“超我”是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固化而成的,人們無(wú)法允許自己被如此赤裸地呈現(xiàn),原始的情結(jié)必須經(jīng)過(guò)高明的藝術(shù)處理才能使人獲得審美的快感。
《孤寂在棉田》將作者的困惑與思考用兩個(gè)角色進(jìn)行呈現(xiàn),并以“交易”的形式作為偽裝,可能源于同樣的創(chuàng)作機(jī)制。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就是藝術(shù)家的白日夢(mèng)。漢斯·薩克斯說(shuō),白日夢(mèng)是由兩個(gè)不相等的部分組成的,一個(gè)是遵循現(xiàn)實(shí)原則支配、與觀眾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部分,另一個(gè)則是想方設(shè)法將潛意識(shí)帶入的混亂的、沒(méi)有秩序性和連貫性的部分[6]。因此,《孤寂在棉田》的文本顯得抽象、跳躍而具有詩(shī)性。科爾泰斯就是弗洛伊德定義的“杰出藝術(shù)家”,能夠巧妙地表達(dá)自我同時(shí)精心修飾,使作品既帶有極強(qiáng)的個(gè)人印記又能被廣泛欣賞。
商販與顧客的交易通過(guò)對(duì)話來(lái)完成,有幾個(gè)始終處于焦點(diǎn)、反復(fù)出現(xiàn)的比喻,值得細(xì)細(xì)解析。首先是“人與獸”,商販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人與獸”相遇的時(shí)刻,這也符合“本我”與“自我”碰撞時(shí)的語(yǔ)境。初生的嬰兒與動(dòng)物幼獸沒(méi)有區(qū)別,都憑借本能索取所求,要生存、要安全、要愛(ài),沒(méi)有任何道德禁區(qū)和倫理顧慮。從大部分語(yǔ)境中可以看出,商販代表了“獸”的一方,更原始、更主動(dòng)、更具攻擊性;而顧客代表“人”,是理性的、力量弱、姿態(tài)強(qiáng)。“人與獸”的關(guān)系也是文本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有時(shí)是互相攻擊、撕咬,有時(shí)是彼此猜疑、懼怕。這個(gè)比喻非常形象直觀地表現(xiàn)了交易雙方的常見狀態(tài),不管交易物是具象的商業(yè)內(nèi)容、抽象的力量博弈還是人在潛意識(shí)層“本我”與“自我”的角力。作家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只要是交易,必然存在對(duì)抗,有時(shí)是強(qiáng)烈甚至殘酷的互搏。
此外,交易雙方的攻防心態(tài)也非常符合“自我認(rèn)知”矛盾性的展現(xiàn)。交易既是表達(dá)真實(shí)創(chuàng)作意圖的形式,也是偽裝,但由于顯性文本與隱性文本之間的高度關(guān)聯(lián)性而顯得充滿哲思又耐人尋味。譬如顧客說(shuō)自己“知道如何說(shuō)‘不',也喜歡說(shuō)‘不',我能用我的‘不'字迷惑您,讓您發(fā)現(xiàn)說(shuō)‘不'的所有方法,就是先用所有的方法說(shuō)‘是'”。商販回答:“我從來(lái)沒(méi)有學(xué)過(guò)說(shuō)‘不',也絲毫不想學(xué)。但所有說(shuō)‘是'的方式,我都知道。”這段對(duì)話幾乎高度概括了所有交易的精要。類似這樣的顯性文本在劇本里比比皆是,通過(guò)各種形式的“顧左右而言他”實(shí)際上是在批判文明導(dǎo)致“本我”與“自我”的分裂。高度發(fā)達(dá)的社會(huì)化機(jī)制下,每個(gè)人都離“真正的自我”越來(lái)越遠(yuǎn),向內(nèi)撕裂幾乎無(wú)法避免,要么就淪為一個(gè)個(gè)沒(méi)有自我意識(shí)的個(gè)體。厭棄西方文明、欣賞非洲的野性與原始是科爾泰斯貫穿所有劇作的母題,也反映在其作品中的多個(gè)潛文本中。
四、欲望的內(nèi)容:暴力與性
精神分析學(xué)說(shuō)將人的本能分為生本能與死本能。前者是人所有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的動(dòng)力根源,即“力比多”,尤指性本能。后者具有破壞性,包括憎恨、攻擊和暴力。而弗洛伊德更是將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視為被壓抑的性本能的“升華”,是藝術(shù)家將自己被壓抑的欲望即“力比多”的能量轉(zhuǎn)移到社會(huì)道德所允許的活動(dòng)中,并使之得到宣泄的結(jié)果。不管科爾泰斯是受到潛意識(shí)影響還是自身有意識(shí)地投射,他的作品中都充滿了暴力與性的內(nèi)容,并且沒(méi)有停留在暴力與性的層面,而是深達(dá)其背后的欲望本質(zhì)。《孤寂在棉田》更是一場(chǎng)通篇圍繞欲望二字展開的自我叩問(wèn),這36段分解成對(duì)白的獨(dú)白就是作者關(guān)于欲望、暴力與性的表達(dá)。
商販對(duì)顧客的第一句話“此時(shí)此刻在此地走過(guò),那一定是渴望得到自己沒(méi)有的東西”,直接點(diǎn)題。那些“不可輕易言說(shuō)的欲望”本就是“自我”被迫丟棄在潛意識(shí)里的,因此商販無(wú)論是開始的循循善誘還是后來(lái)的暴力相脅,都旨在引導(dǎo)“自我”承認(rèn)自身的欲望。在雙方針對(duì)“行走路線”這一點(diǎn)針鋒相對(duì)地辯駁時(shí),商販說(shuō)“哪怕您堅(jiān)持說(shuō)您所行走的路線是筆直的,它或許曾經(jīng)是筆直的,但在您發(fā)現(xiàn)我的那一刻就已經(jīng)扭曲了”,再次暗示相遇是從顧客主動(dòng)發(fā)現(xiàn)的那一刻開始的。“自我”由“本我”發(fā)展而來(lái),并如弗洛伊德所言,始終對(duì)本能滿足所帶來(lái)的快感念念不忘。“本我”的原始“力比多”又具有永不枯竭的活力,竭盡全力要攻入意識(shí)層。因此,“自我”一直處于抗拒“本我”強(qiáng)大吸引力的狀態(tài),一旦在某個(gè)時(shí)刻,即“您發(fā)現(xiàn)我的那一準(zhǔn)確時(shí)刻,就是您的道路變扭曲的那一準(zhǔn)確時(shí)刻”,相遇就發(fā)生了。商販再次強(qiáng)調(diào):“這扭曲并不是讓您遠(yuǎn)離我,而是讓您靠近我,否則我們永遠(yuǎn)都不會(huì)相遇,您本應(yīng)離我越來(lái)越遠(yuǎn),因?yàn)槟菑囊稽c(diǎn)徑直到另一點(diǎn)的速度行走的,而我則永遠(yuǎn)不可能追上你。我的行走方式不是為了從一點(diǎn)到另一點(diǎn),而是在一個(gè)固定的地方,窺伺從我面前經(jīng)過(guò)的人,等待他輕微地改變一下他的路線。”只有當(dāng)“自我”主動(dòng)降低心理防御的時(shí)候,才有可能來(lái)到潛意識(shí)層看到“本我”。而商販接下來(lái)的一段話更是具有辯證色彩,他說(shuō):“或許實(shí)際上您根本沒(méi)有偏離方向,只是所有的直線都是相對(duì)于一個(gè)平面才存在的。歸根結(jié)底,只有一個(gè)事實(shí),那就是您的目光投向了我。所以不管您最初所走的路線是多么絕對(duì)、多么筆直,它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得如此相對(duì)、如此復(fù)雜。”作者通過(guò)商販之口想表達(dá)的就是人性之幽暗曲折,沒(méi)有絕對(duì)的真理。而顧客一開口就是拒絕的姿態(tài),并強(qiáng)調(diào)自己屬于身后高處亮著的窗戶,來(lái)到這里只是迫不得已。“我們住得越高,空間就越圣潔,那么墜落也就越難受……走到這一切的中間——那一堆陳年腐爛的記憶!這正是我們?cè)诟咛幍娜怂磺樵傅模 卑凑崭ヂ逡恋碌木穹治鰧W(xué)說(shuō),遺忘的記憶正是被壓制到潛意識(shí)層的“本我”核心。顧客所言高處之圣潔正是指代“超我”,在理想典范的長(zhǎng)期稽查下,“自我”已忘卻了自己的來(lái)處,而唯高高在上的道德倫理馬首是瞻,反而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本我”。這是人長(zhǎng)久浸淫在社會(huì)框架里,習(xí)慣于對(duì)自己那些“不被允許但未必是錯(cuò)的”欲望進(jìn)行自我批判的典型象征。
雙方對(duì)于欲望展開的對(duì)話也極具象征意義。顧客說(shuō):“我的欲望所求,您肯定不會(huì)有。我的欲望,如果還是個(gè)欲望,要是我還能對(duì)您說(shuō)得出來(lái),它將燙傷您的臉,讓您尖叫一聲把手縮回去,然后逃到暗處去,就像一只跑得飛快的狗,連尾巴都看不清。”從顧客此時(shí)的高姿態(tài)來(lái)分析,他所說(shuō)的欲望應(yīng)該自認(rèn)特別高尚,屬于“超我”的范疇,是“自我”一直心向往之而未能至的“道德高地”。但他隨即卻說(shuō):“但是,不!這個(gè)地點(diǎn)和這個(gè)時(shí)刻令我忘記了我那曾經(jīng)有過(guò)的欲望,我已經(jīng)想不起來(lái)了。”這正說(shuō)明“自我”靠近潛意識(shí)層后開始不由自主地偏向本能,從而忘記了“超我”的規(guī)范和要求。因此他又立即否定說(shuō):“不!我的欲望微乎其微,我也沒(méi)什么能給您。”連續(xù)兩個(gè)“不”反映了顧客的內(nèi)心搖擺和驚惶,他訝異于自己輕易地遺忘了那高尚的欲望,這才用否認(rèn)自己、放低自己來(lái)穩(wěn)定局面。他要求商販“自己刪除自己”,因?yàn)椤澳枪饩€,在那高樓上,雖然已被昏暗籠罩,還是不斷地閃爍著,它穿透了這夜色,就像一支點(diǎn)燃的火柴,穿透那企圖捂滅它的破布”。這高樓上的光線如前所述代表“超我”,盡管“自我”受到潛意識(shí)影響,但并沒(méi)有完全失去理性,認(rèn)為只要“本我”讓開就能解決眼前的困局。面對(duì)商販關(guān)于“行走路線”的有力舉證,顧客顯得有些沉不住氣,開始指責(zé)商販“擋了他的道兒”,說(shuō)自己最反感的就是這種目光,“它斷定人滿懷不正當(dāng)?shù)钠髨D且早已習(xí)以為常”,甚至嚴(yán)重到“只要這目光的重量一壓向我,就使我那潛藏在體內(nèi)的童真瞬間感到被強(qiáng)奸”。顧客甚至承認(rèn)了商販對(duì)其造成的重重壓力——“您的目光足以讓杯底沉淀的污泥翻騰到水面……而那條筆直的線也正是因?yàn)槟兊门で耍刮也荒茏园巍!敝链耍櫩筒辉俜裾J(rèn)商販已對(duì)他造成影響,只是要把責(zé)任推給對(duì)方。劇本中還有多處顧客“意圖甩鍋”的證據(jù),在此不做贅舉。實(shí)際上,這是“自我”的防御機(jī)制,當(dāng)人在偏離正軌、脫開道德倫理制約的時(shí)刻,常常用這種方式規(guī)避來(lái)自“超我”的譴責(zé)。
雙方博弈的焦點(diǎn)在于,誰(shuí)都不肯率先捅破欲望的窗紙,展示欲望的內(nèi)容。根據(jù)弗洛伊德的學(xué)說(shuō),潛意識(shí)的欲望本質(zhì)上都是關(guān)于性本能。而當(dāng)性本能受到抑制,暴力隨即出現(xiàn)。因此,欲望的內(nèi)容雖未具象化,但都含有“性”的意指。性與暴力實(shí)際上都是力量的博弈,皆有攻防。商販在對(duì)峙中曾一再?gòu)?qiáng)調(diào)自己的力量,說(shuō)“我本可以撞上您,如同一塊破布落在蠟燭的火焰上”,甚至“任意在您身上踐踏,就像靴子踩在油紙上”。但他顯然并不愿意付諸暴力,他認(rèn)為自己是個(gè)名副其實(shí)的商人,“當(dāng)一切都能買能賣時(shí)還去偷或者免費(fèi)饋贈(zèng)就是粗魯?shù)男袨椤薄I特湹哪康牟⒉皇恰皾M足欲望”,而是“召喚欲望,迫使欲望有個(gè)名字,將它拖到地面,賦予它一個(gè)形態(tài)和一份重量”。商販不斷對(duì)顧客施壓,只是要他親口說(shuō)出自己的欲望。作者似乎想通過(guò)這一點(diǎn)來(lái)證明,自我認(rèn)知是個(gè)艱難的過(guò)程,面對(duì)自己的欲望,承認(rèn)自己的欲望要經(jīng)歷多么曲折難解的心理對(duì)抗,甚至最后階段雙方都數(shù)次提到了“武器”這個(gè)具有明確暴力指向性的詞語(yǔ)。但本劇中內(nèi)化的暴力與作者其他作品中外化的暴力并不相同,更多的是作為手段,作為力量的象征。而性本能在劇本中被藏得更深,幾乎都以零散碎片的符號(hào)呈現(xiàn),只在這一段中出現(xiàn)了較為連貫的意指:“很久以來(lái),我以為不準(zhǔn)男孩脫褲子是為了避免他暴露自己的激情或難耐的煎熬。但是今天我懂得了更多,明白了更多,明白了更多我不懂的。太多次我在這個(gè)時(shí)刻待在這個(gè)地點(diǎn),目睹過(guò)往行人。我注視著他們,有時(shí)會(huì)把手放在他們的胳膊上,太多次了,什么也不懂、也不想去懂,但卻堅(jiān)持這么做……我很清楚在那掩埋的激情或煎熬里并沒(méi)有什么不當(dāng)之處,而且應(yīng)該不知所以然地遵循著規(guī)則。”然而這一段在上下文中找不到任何邏輯關(guān)聯(lián),更像是作者隨意放置、似是而非的“迷霧彈”。弗洛伊德曾斷言,藝術(shù)作品中某些文本的解釋,只能通過(guò)精神分析才能完成[7]。如前所述,藝術(shù)作品是隱喻的產(chǎn)物,也是經(jīng)由偽裝、扭曲和重構(gòu)而成的圖景。因此潛文本的探索只能追循有限的線索去臆測(cè)、推演和建構(gòu),這也是弗洛伊德藝術(shù)理論在文藝批評(píng)方面給出的一個(gè)路徑。
五、結(jié)語(yǔ)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認(rèn)為潛意識(shí)和“力比多”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審美活動(dòng)的重要?jiǎng)右颉_\(yùn)用人格結(jié)構(gòu)論對(duì)藝術(shù)家及作品展開分析,揭示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和前文本是文藝批評(píng)的一個(gè)獨(dú)特視角。盡管東西方學(xué)者歷來(lái)認(rèn)為其文藝?yán)碚擉w系忽略了文藝的社會(huì)價(jià)值和審美價(jià)值。朱光潛也曾說(shuō)過(guò):“這樣一種藝術(shù)觀如果不是完全錯(cuò)誤,也至少是片面和夸大的。”[8]但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人的精神活動(dòng)密切相關(guān),對(duì)創(chuàng)作者的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進(jìn)行挖掘和探索不失為一個(gè)行之有效的向內(nèi)研究的方法。《孤寂在棉田》是一部獨(dú)特的作品,也是走近科爾泰斯的重要橋梁之一。科爾泰斯終身向往非洲文明,也許恰恰是他潛意識(shí)里想要回歸“野性和原始”的表現(xiàn)。動(dòng)物沒(méi)有“自我”,沒(méi)有文明與道德,卻比人更懂得控制欲望。它們會(huì)在吃飽時(shí)休憩,有個(gè)窩就能安枕,而人,小到個(gè)體大到種族,永不知足。更荒誕的是,人還造出一個(gè)“自我”來(lái)欺騙自己,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一絲不掛地行走于孤寂棉田,也無(wú)法直面真正想要的東西。
注釋:
[1]瑪麗-克洛德·于貝爾:《貝克特之后法國(guó)戲劇的發(fā)展》,吳亞非譯,《戲劇藝術(shù)》,2012年第2期,第13~16頁(yè)
[2]于貝斯菲爾德對(duì)“準(zhǔn)獨(dú)白”的界定是“指向一個(gè)不作答的人的言說(shuō)”。趙英暉在《科爾代斯戲劇獨(dú)白研究》中提出科爾代斯戲劇話語(yǔ)中的獨(dú)白因其情境的多樣性,對(duì)以往劃定的獨(dú)白與對(duì)白之間的邊界提出了新挑戰(zhàn)。
[3]趙英暉:《科爾代斯戲劇獨(dú)白研究》,南京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7年,第6頁(yè)
[4]趙英暉:《科爾代斯戲劇獨(dú)白研究》,南京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7年,第8頁(yè)
[5]科爾泰斯:《孤寂在棉田》,寧春艷譯,北京: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所引文本皆出自該版劇本)
[6]沈文婷:《欲望的潤(rùn)飾與升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藝術(shù)理論及其影響研究》,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博士論文,2017年,第73頁(yè)
[7]沈文婷:《欲望的潤(rùn)飾與升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藝術(shù)理論及其影響研究》,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博士論文,2017年,第74頁(yè)
[8]朱光潛:《悲劇心理學(xué)》,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3年,第191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宮寶榮:《貝-納·科爾代斯——法國(guó)當(dāng)代劇壇一巨匠》,《戲劇》,2001年第1期
2.沈光鵬:《論弗洛伊德的藝術(shù)觀》,河北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1年
3.王佳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評(píng)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與實(shí)踐研究》,安徽師范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0年
(作者單位:上海戲劇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 岳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