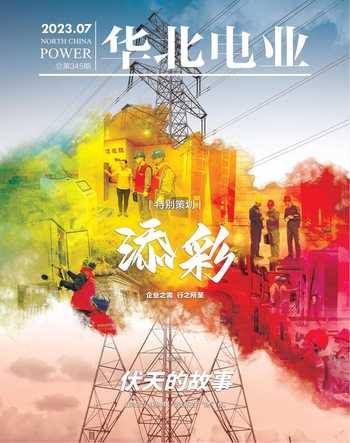于一方食事 品歲月悠長
李艷青

蘇東坡有詩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北宋時期,嶺南一帶地脈荒涼,常為官員遭貶之所。時隔千年,近現代的嶺南面目煥然,風云興變。美食,志士,情義,家國……蒼茫世事,輪轉光陰,如百川河流融匯于葛亮筆下,造就了一部蕩氣回腸的粵港百年變遷史《燕食記》。
“燕食”,意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周朝確立“三餐制”,也奠定了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俗理。《燕食記》從粵港吃茶點的習俗生發開來,沿著嶺南飲食文化的發展脈絡,以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的傳奇身世及薪火存續為線索,記錄了辛亥革命以來粵港經歷的時代磋磨與蝶變復興,描繪了一幅鮮明生動的嶺南文化圖景。
作為葛亮的忠實粉絲,初讀此書其實有些忐忑。我是一個純正的北方人,對粵港地區的歷史了解停留在粗淺的紙面,只怕水土不服,辜負了好故事。可當我真正翻開書頁,一上來就被花色豐富的各路美食吸引,讀得津津有味,毫無隔膜。食物在華夏人心中就是有這樣的魔力,能夠在瞬息間打破因地域、語言、風俗和觀念造成的強大壁壘。
蓮蓉月餅、水晶蝦餃、菊花鱸魚、紅燜山瑞、太史豆腐……可稱琳瑯滿目,活色生香。葛亮的文字功夫堪稱一絕,對當地的茶樓酒肆又進行了長時間的實地探查,細節豐滿,不疾不徐,對粵食、滬菜的許多經典菜品進行了深入研究。爐火純青的考據功夫,成就了小說細密扎實的肌理;行文中粵方言的點染使用,更傳遞出獨特的嶺南氣韻。從配料到做法,從火候到刀工……《燕食記》對每一種菜品的前世今生及其間的掌故都述證詳實,開闔自若,如數家珍,娓娓道來。
食物可安頓身心,亦可定格歷史。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燕食記》里,時間流逝、人世翻新、眾人熙來攘往,如夢華錄、如上河圖,這盛大人間中,舌上之味、耳邊之聲,最易消散,最難留住,也最具根性,最堪安居。”有時候,一件事或一個人原本已在記憶中淡去,卻在你吃到某樣食物時歷歷在目地回想起來。葛亮透過粵港食系發展歷程中的百年人事,從容舒緩、文火慢熬地向讀者展露其寫作的真正題旨——記憶與傳承,人性與宿命。
同欽樓最負盛名的“大按”師傅榮貽生,因打得一手好蓮蓉聲名遠揚。他的一生融于時代大潮,起伏跌宕,身后有無數傳奇般的際遇。生母月傳為護他早逝,臨走留下一些金銀和一封書信,信上寫:“吾兒貽生:為娘無德無能,別無所留。金可續命,唯藝全身”;養母慧生念著與月傳的深厚情誼,含辛茹苦將他撫養成人;初代蓮蓉教主葉鳳池為愛人忍受著病痛折磨,一心將手藝傳給榮貽生;陳五舉天賦異秉,自小拜在榮貽生門下,卻為情所困,叛出師門,從此撐起了上海本幫菜的一片天……《燕食記》的故事底色是良善的。作者對書中的每個人物都懷著由衷的悲憫,時時流露出一種儒家的,綿長深切的不忍與寬恕。太史第的興衰瞬變,月傳的通透出塵,慧生的堅韌果敢,榮貽生的沉靜溫平,五舉的癡情隱忍,七少爺錫堃的神龍首尾,大少奶奶頌瑛的孤勇破局,每一個人物都形象鮮明,呼之欲出。此外,《燕食記》在情節架構上也頗有巧思,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每段都有一個主線人物,每章都是一片柳暗花明。當讀者以為一個人的故事就此結束時,卻又總能通過一道菜、一個物件抑或旁人對他過往的幾句不經意描述而回憶起那人的一生。
除了世俗的不滅煙火,一個民族的百年亂世,更有烈烈風骨,千秋家國。葉鳳池身懷炒蓮蓉絕技,卻不肯以七尺之身安居后廚,反清廷,抗倭寇,刻入血脈的民族義氣,是他經年不變的堅守;七少爺錫堃滿腹墨水,才學八斗,在與日本間諜對談時機警過人,先看破日本戲劇的手勢,繼而用美食激發其體內毒素,神不知鬼不覺地除掉了倭人間諜。這些看似只存在于說書人口中的故事,與真實的歷史事件融為一爐,虛實相生,舉重若輕。葛亮曾說,從《朱雀》到《北鳶》到《燕食記》,核心的部分都是歷史觀。他從不吝以最大的熱忱書寫華夏民族從萎頓到新生的歷程。這其中多少飄搖風雨,生死關頭,都離不開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靜水流深的不懈奮斗。
一位作家曾這樣描述中華民族樸素的生命觀:他們在埋頭種地和低頭吃飯時,總不會忘記抬頭看一看天。中國人的哲學是含蓄寬仁,是豁達圓融,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候。《燕食記》以美食做引,將豐富的道理與情義寄于一筷之上,讓我們能在一食一飲的漫長歲月中,體味百年嶺南,乃至整個近代中國的載浮載沉與青山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