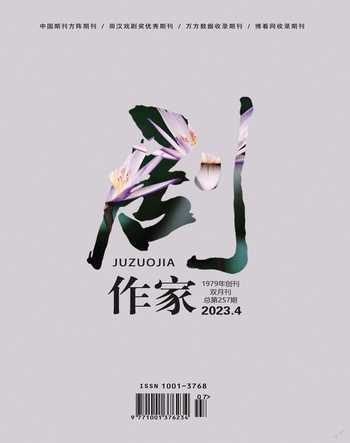論相聲劇、舞臺劇和捧逗的關系
那瑛琦
摘 要:所有的舞臺劇、話劇只要有包袱存在,必然如相聲劇一般存在捧逗關系。即使一個人的話劇,當有笑料產生也是一個人完成了捧逗關系,所以相聲劇是依據相聲、話劇、舞臺劇而誕生的藝術形式。
關鍵詞:相聲劇;舞臺劇;逗哏;捧哏
相聲劇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戲劇結構,它是由相聲這門藝術演變而來的一種嶄新的戲劇形式。相聲劇以相聲為基礎,是相聲的拓展和延伸。
相聲是一門傳統的曲藝形式,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相聲分為單口相聲、對口相聲、群口相聲,其中在舞臺上演出最多的就是對口相聲。說到對口相聲,就不能不說逗哏演員與捧哏演員的關系。顧名思義,逗哏是相聲中的主要角色,負責包袱的鋪墊、劇情的陳述和對事件、人物的諷刺,逗哏的要求是“鋪平墊穩”。捧哏是起到烘托作用,負責抖包袱,也就是當逗哏說得不貼合實際,諷刺事物、事件鋪到包袱時捧哏要看準時機地將包袱抖出來起到讓觀眾發笑的作用,也就是捧哏抖包袱的尺寸要“遲急頓挫”。群口相聲中除捧逗之外還有第三位就是膩縫了。膩縫就是咱們常說的補刀的。想打造一段精品相聲作品在舞臺上呈現,就需要演員之間人物關系非常默契,只有達到默契的程度才能配合得天衣無縫。
那么默契如何培養?
相聲二者一逗一捧,相輔相成,臺上演劇情,臺下處人情。只有臺上臺下相融,合作才能長遠,藝術才能長青,達成良好的默契。從老一代相聲表演藝術家到現階段活躍在舞臺上的曲藝從業人員,逗哏演員與捧哏演員相互包容、合作愉悅的并不多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也是相聲業內普遍承認的事實。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在一起工作的時間比夫妻相處的時間還要長,生活當中難免產生碰撞;二是藝術觀點時常會產生分歧,難免互不謙讓;三是利益分配不均,難免產生猜疑;四是在藝術發展中貢獻不均,難免產生爭議。所以,一對相聲演員不僅是舞臺上的合作人,更是生活中的伴隨者。相聲有句老話叫“搭伙三年,不火自賺”,說的就是默契。
但是捧逗之間的關系處理不好只能是“裂穴”了(術語指不再合作)。怎么樣處理好逗哏和捧哏的關系呢?許多老一輩相聲表演藝術家為我們樹立了標桿。逗哏演員與捧哏演員的疊加關系體現在兩個方面。
1.對待藝術要攜手共攀。在藝術追求上,兩個人擁有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相互激勵、相互奉獻、相互支持、相互努力。曾有一對相聲搭檔,逗哏演員為作品茶不思飯不想,幾晝夜都在打磨參賽作品,而捧哏演員不但不參與,反而不斷滲透消極情緒,使得兩個人的合作關系走到了終點。這樣的對立關系,終究不會長久。所以,在藝術發展和追求中,二者應該共同擔當,共同前行,只有攜手共攀才能達成好的默契,好的默契是需要兩位演員用一生來呵護的。
2.對待生活要攜手相誠。相聲行內把逗哏演員和捧哏演員形容為舞臺上的“兩口子”,由于工作關系兩個人相處的時間大大超過了夫妻,在這種情況下,坦誠相待、真情相處、互為包容、像親兄弟一樣,就非常重要了。北京曲藝團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王謙祥、李增瑞合作五十余年,被曲藝行內稱為黃金搭檔,他們德藝雙馨的藝術品格,在全國曲藝界廣為流傳。所以,在藝術發展的進程中,逗哏演員與捧哏演員的默契關系至關重要。
說完相聲的捧逗人物關系,咱們再由相聲說到相聲劇。相聲劇之所以稱之為劇,與相聲是有很大區別的,但是無論怎么演變其根源都離不開“相聲”二字。
相聲劇里的人物關系復雜,不是單純的兩個人甚至幾個人來表演。相聲刻畫人物是一人分飾多角,根據一段相聲的需要,捧哏與逗哏兩人需要跳進跳出,刻畫多重角色,而刻畫的角色只需要表面表現出角色特點就可以,不需要太深入的刻畫。而相聲劇里的人物就像話劇、戲劇、舞臺劇一樣是一人一個角色貫穿全劇,并且要深入所刻畫的角色,要根據時間、地點、人物處境與內心變化來展現角色的狀態。
相聲里有捧哏與逗哏之間的人物關系,那么相聲劇里也存在捧逗之間的關系嗎?這個是可以肯定的,只不過不像相聲單純捧逗關系表現得那么明顯。相聲劇是由相聲演變而來的,它與話劇、舞臺劇和其他劇種不同的是,在演繹整體故事情節時,最關鍵的環節就是包袱(相聲術語:讓觀眾發笑的情節和語言),只要有包袱存在就會存在捧逗關系。這種關系還有以下幾類劃分。
1.“開心麻花”出品的舞臺劇《烏龍山伯爵》就是以包袱為主,那么劇中誰是捧哏誰是逗哏呢?可以這么說,艾倫所演的角色就是捧哏的角色,馬麗、沈騰都是逗哏的角色(這是劇中的基本設定),但是根據劇情的需要、包袱的需要,三個人的關系也可以及時變化——可以艾倫和馬麗捧沈騰,那么沈騰就是抖包袱的主要角色;也可以沈騰和艾倫捧馬麗,那么馬麗就是抖包袱的主要角色。這就是相聲劇里的一種人物關系——互為捧逗。
2.只有兩個人的話劇《喜劇的憂傷》,劇中只有陳道明和何冰飾演的兩個角色,但是這個話劇充滿了包袱,整場爆笑連連。有包袱就有捧逗關系,大家都會認為陳道明老師是主角他肯定是逗哏,何冰老師是男二號肯定是捧哏,這個定義是表象的,實際上人物關系是錯誤的。何冰飾演的是一個編劇,他寫出了自認為最好的喜劇,所以他向總編陳道明老師展示自己的劇,并要求陳道明老師配合,實際上這一舉動已經讓何冰飾演的角色站到了逗哏的一邊。由于這個編劇寫的劇本非常無聊,陳道明反諷這個劇本枯燥無味,何冰說一句劇本里的臺詞,陳道明老師就說一句“我樂了嗎”,陳道明所運用的就是地道的捧哏手法。所以整個話劇表面是陳道明逗哏、何冰捧哏,可是當他們表演劇中所寫的喜劇時,何冰變成了逗哏而陳道明變成了捧哏,這就是隱藏的互為捧逗關系。
3.老舍先生寫的話劇《茶館》中有一個章節,清政府滅亡,松二爺失去生活依靠,吃了上頓沒下頓,但是仍然愛鳥如命,手里拎著鳥籠子來到了茶館,一如既往地要將鳥籠子掛在茶館里的繩子上。這時老板說道:“沒了,二爺這沒繩子了。”這句話加上松二爺的神態引得臺下觀眾哄堂大笑。這段兩個人物沒有過多的臺詞但是可通過人物神態、動作及道具鳥籠子來進行包袱的鋪墊,而老掌柜一句話將包袱抖出來就是捧哏的特性,所以可以分辨出松二爺是逗哏,老掌柜是捧哏,那么松二爺手里的鳥籠子就是逗哏,主要的輔助道具,也就是說這個鳥籠子也屬于老掌柜的捧哏,所以這類屬于借物互為捧逗的關系。
4.在話劇《窩頭會館》中田翠蘭與金慕容打嘴架,包袱層出不窮。引起事件的起因是田翠蘭晾大腸不小心將金慕容晾的膏藥弄翻在地,金慕容氣不過與田翠蘭展開了罵戰,從兩人語言來看,金慕容屬于逗哏,田翠蘭屬于捧哏,但是從事件起因來看,田翠蘭是此次事件的發起者,是逗哏的特性,金慕容屬于反駁者,是捧哏的特性,所以田翠蘭是逗哏而金慕容是捧哏。兩人打到后來出現了房東苑國忠,在兩者之間攪渾水插科打諢,他就屬于膩縫的人物。在包袱當中捧與逗各有一位,而膩縫的可以有很多位。劇中完成田翠蘭、金慕容罵戰包袱的不光是房東苑國忠,前清舉人古月宗在二人罵戰中也充當了補刀的角色,同樣是膩縫,那么根據包袱的需要、劇情的進展,抬起劇中包袱的角色可以更換,但是捧逗膩縫的人物關系是不變的,這個就是互為捧逗膩縫的關系。
結合這幾個例子而言,在舞臺劇中出現的包袱都是存在捧逗關系的,相聲是一捧一逗,相聲劇里出現的包袱是互為捧逗的關系,而烘托捧逗關系的其他角色都可以稱之為膩縫。
5.喜劇《吃雞》是王景愚表演的單人無實物幽默啞劇,結合“有包袱就有捧逗關系”的論證,一個人怎么區分捧逗?這個就要說到《吃雞》中的無形道具——燒雞,王景愚先生買了一只燒雞打算好好享用,結果這只燒雞韌性十足,想盡辦法也吃不到嘴里,可謂是給王景愚出盡了難題,從主動權這方面來看這只無形的道具燒雞是逗哏,而王景愚將吃雞的神態動作展現得淋漓盡致,包袱也都是王景愚抖出來的,那么他就是捧哏,這個還是表面的定義。實際是王景愚自身來發展故事情節,作為后面吃雞的包袱鋪墊,所以王景愚還是逗哏的角色,手里無形的燒雞配合王景愚的種種神態動作將包袱完美地展現出來,那么這個無實物的燒雞就充當起概念性的捧哏了,換句話說就是王景愚先生自己逗哏,同時也利用無實物燒雞為自己捧哏,自己逗哏又自己進行捧哏,這個就是單人互為捧逗。這個形式也就是相聲當中單口相聲的形式。
相聲中的捧逗人物關系需要默契,那么相聲劇中的眾多演員存在默契嗎?答案是肯定的。相聲演員在生活中培養默契,相聲劇的演員也基本都是相聲演員來完成,他們自帶的默契不言而喻是高于其他戲劇形式的。而且相聲演員生活中經常在一起,平時喜歡砸掛(就是互相開玩笑),這也極大地提高了演員與演員之間的默契程度。將包袱的手法與形式融會貫通,活學活用,讓演員沒有任何劇本就可以根據當時的環境、語言邏輯、思維轉換來抖包袱,這對演員個人專業素質、生活閱歷的積累是一個很高的考驗。所以相聲劇中的默契需要相聲中捧與逗之間的默契,但是也超脫了捧與逗之間的默契。
這種捧逗之間的默契只有相聲演員演出的相聲劇才能達到嗎?并不完全是。既然有包袱就有捧逗關系,那么引申出來就是“有捧逗關系就需要默契”。“開心麻花”劇組成員中,沈騰、馬麗、艾倫三個人在舞臺劇中的配合就非常默契,包袱嚴緊,節奏縝密,觀賞性強,觀眾反饋熱烈,說明三個人配合極其默契。這種默契有的人說是排練排出來的,這一說法并不完全,想達到這種默契就需要像相聲中捧哏、逗哏搭檔那樣在生活中建立起良好的相處關系,有共同的經歷與共同的價值觀。沈騰、艾倫、馬麗他們在生活中就經常砸掛,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以前三人還沒成名時就常在一起打磨作品,揣摩各自的人物特點,在排練中互相磨合,這樣三個人才演繹出了一系列經典而搞笑的喜劇作品。優秀的喜劇作品都離不開演員良好的默契與配合,相聲劇就更突出了良好的默契所帶來的高質量包袱。
相聲圈里有黃金搭檔,前面例舉的王謙祥、李增瑞兩位表演藝術家搭檔數十載,依然和諧默契。相聲劇就需要很多這種黃金搭檔,來共同完成一部優秀的相聲劇。相聲的捧與逗是小兩口,這個比喻很恰當;相聲劇則是一個大家庭,演員與演員之間都是互為捧逗的關系,在完成劇中人物刻畫的同時,還要將包袱很有默契地抖出來。
所以相聲劇和其他舞臺劇中只要有包袱就存在捧哏與逗哏的關系,而論逗哏與捧哏的良好默契關系那就是:臺上十分鐘是藝術的體現,臺下十年功是生活的檢驗。兩者融合才能展現最好的作品。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曲藝團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岳瑩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