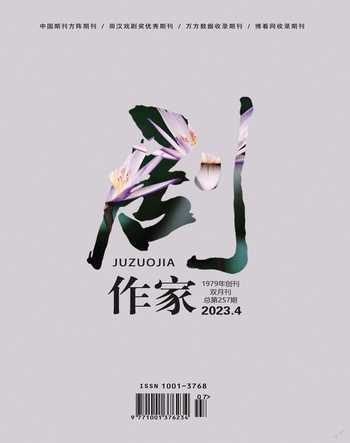審美學(xué)視域下民族音樂劇表演的藝術(shù)特征
孫顯赫
摘 要:民族音樂劇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之一,沉淀積累了眾多中國歌劇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靈感,蘊(yùn)含近現(xiàn)代民族文化的精華,具有特殊的審美藝術(shù)魅力。然而民族音樂劇因我國民族文化的風(fēng)格多樣性被細(xì)分成眾多個類別,具有一定的個性化審美差異。本文以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中的人物角色形象塑造為案例進(jìn)行逐層分析,從審美視角分析民族音樂劇表演中的藝術(shù)特征,不僅有利于表演者在創(chuàng)作中賦予劇中人物多維度的美感和生命力,還有利于推動當(dāng)代民族音樂劇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當(dāng)下民族音樂劇實(shí)踐表演提供理論借鑒。
關(guān)鍵字:審美視域;音樂劇表演;人物形象;角色塑造
伴隨著中西文化的發(fā)展與交融,民族音樂劇也成為了各國進(jìn)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兼容并蓄、融合了較多西方審美藝術(shù)的當(dāng)代中國民族音樂劇,其表演模式和人物形象塑造思維也在不斷改變,逐漸形成了帶有中國民族特點(diǎn)的藝術(shù)形式,即以戲劇為內(nèi)容載體,音樂為呈現(xiàn)手段,融合舞蹈、歌唱、雕塑等多樣化的綜合藝術(shù)。一部優(yōu)秀的民族音樂劇不僅能為受眾帶來震撼的視聽體驗(yàn),同時也能呈現(xiàn)出一個動人的故事。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由著名青年作家錢曉天創(chuàng)作,作曲家張巍譜曲,以紅色精神的傳承為主線,以慷慨悲壯的舞臺藝術(shù)呈現(xiàn),突出了帶有地域性的民族文化特色,讓紅色精神的傳承得到了凸顯,也讓我們更加精準(zhǔn)地感受到了作品中的藝術(shù)風(fēng)格。
一、革命題材藝術(shù)的和諧之美
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以著名的湘江戰(zhàn)役為故事創(chuàng)作背景,講述了陳湘率領(lǐng)紅軍部隊(duì)在激戰(zhàn)中與瑤族人民結(jié)下深厚情誼,真正凝聚群眾力量,實(shí)現(xiàn)軍民同心的感人故事。在音樂劇表演中,通過音樂與舞臺形象的呈現(xiàn),將故事中蘊(yùn)含的紅色文化與軍民同心的豪邁、雄壯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引發(fā)了受眾的共鳴,同時也讓劇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傳神,故事主題更為深刻,真正體現(xiàn)了革命題材故事表達(dá)與藝術(shù)呈現(xiàn)的和諧之美。
(一)藝術(shù)民族化的呈現(xiàn)
民族音樂劇作為當(dāng)代音樂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方式,把握藝術(shù)性與革命題材文化的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通過軍民關(guān)系的藝術(shù)化設(shè)計(jì),賦予了劇中戰(zhàn)士與百姓鮮活的民族特色。在以往紅色題材藝術(shù)作品的人物塑造中,紅軍戰(zhàn)士的形象都是堅(jiān)毅勇敢、一成不變的,這種固定思維難免會讓受眾產(chǎn)生審美疲勞。在《血色湘江》的故事發(fā)展中,一些紅軍戰(zhàn)士因食不果腹偷吃了瑤族鄉(xiāng)親們的食物,也正是因此事鳳鳴和陳湘結(jié)緣。二人相見后,鳳鳴便唱起了詠嘆調(diào)《瑤族的女兒》,歌詞“上古的戰(zhàn)神呦”生動地將瑤族音樂中的山歌特色完美地呈現(xiàn)出來,隨后而來的快板將鳳鳴想要報(bào)仇的迫切心情形象地再現(xiàn)出來。隨著伴奏中蘆笙與豎琴的交織,將瑤族妹子那種對愛情的向往表達(dá)得淋漓盡致,同時也提升了音樂劇的感官藝術(shù)性,呈現(xiàn)出了民族藝術(shù)之美。
(二)戲劇化的故事渲染
與以往革命題材藝術(shù)作品情節(jié)不同的是,瑤族人民對于紅軍戰(zhàn)士的到來不是敲鑼打鼓地歡迎,更多的是緊閉門戶、驚慌失措,這也是當(dāng)?shù)剀婇y壓榨百姓的一種慣性的映射,當(dāng)?shù)鼐用竦膽T性認(rèn)知導(dǎo)致了對紅軍戰(zhàn)士的錯誤認(rèn)識。故事由閉門抗衡再到結(jié)下友誼,這樣戲劇化的情節(jié)設(shè)計(jì)為整個故事的發(fā)展增添了不少色彩。在《血色湘江》中,陳湘因情況所迫亟需瑤族鄉(xiāng)親的支援,而鄉(xiāng)親們的慣性認(rèn)知讓部隊(duì)不得不找機(jī)會消除軍民之間的誤會,這一系列的誤會無疑為軍民關(guān)系的融合發(fā)展提供了戲劇化的原動力,從最初的誤會到軍民關(guān)系的升溫,唱段《信任》更是通過加強(qiáng)咬字重音的演唱將戰(zhàn)士們對黨的信任,對戰(zhàn)友、鄉(xiāng)親的信任有力地呈現(xiàn)出來。在第52節(jié)中“信任黨中央”的連貫聲音和漸強(qiáng)演唱為曲目注入了英雄的氣概,同時也為作品注入了一種革命的藝術(shù)美。
(三)愛情關(guān)系的隱喻暗示
音樂劇與其他戲劇形式相比的優(yōu)勢便是多樣化情感的呈現(xiàn),而愛情作為現(xiàn)代音樂劇中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也承擔(dān)了深化主題的重要作用。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以革命軍團(tuán)與瑤族百姓互動為人物關(guān)系的主線,推動整部作品故事的發(fā)展。主人公陳湘與瑤族女兒鳳鳴的愛情故事設(shè)置也助推了整個劇情的發(fā)展。通過二人愛情關(guān)系的隱喻,暗示紅軍是一支備受人民愛戴的軍隊(duì)。在鳳鳴偶遇陳湘教導(dǎo)戰(zhàn)士為自己犯下的錯誤道歉賠償后,她便打破了對戰(zhàn)士們的刻板印象,并幫助陳湘部隊(duì)突圍,將最愛的金刀作為信物送給陳湘。送金刀這一情節(jié)設(shè)置不僅僅是二人愛情關(guān)系的確立,更是紅軍戰(zhàn)士與瑤族鄉(xiāng)親實(shí)現(xiàn)軍民融合的一種暗示。這種暗示也實(shí)現(xiàn)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與音樂劇藝術(shù)形式的融合,呈現(xiàn)出一種和諧之美。
二、融入地域音樂特色的意境之美
意境作為中華文化獨(dú)具特色的審美元素,直接決定著一部作品的藝術(shù)價值水平。在當(dāng)代民族音樂劇的藝術(shù)發(fā)展進(jìn)程中,創(chuàng)作者也愈發(fā)重視民族音樂劇意境美的營造。《血色湘江》作為一部融合廣西少數(shù)民族地域文化的民族音樂劇,巧妙地將帶有廣西地域特色的瑤族音樂《蝴蝶歌》融入其中,不僅提升了作品的舞臺表現(xiàn)力,同時也極大程度地增加了音樂劇的民族性。
(一)民族化的表意呈現(xiàn)原生態(tài)文化
《蝴蝶歌》作為廣西地區(qū)的傳統(tǒng)音樂,其應(yīng)用的場景較為廣泛,作品本身歡快俏皮的旋律能夠與音樂劇的部分劇情實(shí)現(xiàn)完整的契合。加之《蝴蝶歌》中一些帶有民族特色的唱段能夠?qū)幾灏傩諑в忻褡逍缘纳盍?xí)慣和風(fēng)土人情展現(xiàn)出來,在表現(xiàn)上具有一定的場景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受眾的好奇心,提升音樂劇的舞臺氛圍感。在演唱中《蝴蝶歌》長音和短音相結(jié)合使得唱段的節(jié)奏性更強(qiáng),“咿呀”“哎”等語氣詞的應(yīng)用也提升了樂曲的民族性,展現(xiàn)了瑤族音樂文化的一種原生態(tài)面貌。
(二)民歌的改編推動劇情的發(fā)展
在以往音樂劇的民歌改編應(yīng)用中,改編后的民歌不僅要應(yīng)用在作品的風(fēng)格表意中,還要應(yīng)用在劇情的渲染上。《血色湘江》中將《蝴蝶歌》改編后貫穿在展現(xiàn)瑤族百姓美好生活和最后戰(zhàn)士英勇犧牲的場景中。在革命戰(zhàn)士保衛(wèi)家園、誓死如歸的最后時刻,音樂響起,讓慘烈的舞臺場景增加了一種美好的懷念,這懷念既是戰(zhàn)士們在犧牲時對故土的懷念,也是軍民情誼的一種交融。音樂的表現(xiàn)讓受眾能夠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革命戰(zhàn)士寧死不屈、誓死捍衛(wèi)家園的勇氣,同時也渲染了對戰(zhàn)士們的敬佩之情,是瑤族人民意象的一種呈現(xiàn),也是對瑤族風(fēng)土人情的一種還原,改編后的《蝴蝶歌》帶給受眾的既有瑤族村寨的美好景象也有對戰(zhàn)士的敬佩和感恩。
(三)瑤族元素的應(yīng)用突出作品主題的表達(dá)
瑤族百姓多居住在山水秀麗、萬壑綿延的地區(qū),因其生活環(huán)境因素,瑤族兒女喜唱山歌,通過歌唱的形式將家鄉(xiāng)的美景、生活、勞動表達(dá)出來。他們歌唱勞動、歌唱生活、歌唱愛情,歌聲中贊頌著瑤族家鄉(xiāng)的宜人景色,瑤族人民的勤勞善良,表達(dá)著自己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之情,傳承著豐厚的民族文化底蘊(yùn),也展現(xiàn)出瑤族淳良的精神品格,有著重要的藝術(shù)欣賞和研究價值。《血色湘江》中的瑤族元素集中呈現(xiàn)在一幕三場,如唱段中的“哎”“嘿”原生態(tài)的延長音將受眾引入了瑤族村寨的風(fēng)土人情中,讓人仿佛置身于瑤族鄉(xiāng)間,伴隨著笛子和蘆笙的響起,瑤族百姓的美好生活場景浮現(xiàn)在眼前。創(chuàng)作者通過《蝴蝶歌》拉開了瑤族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場景,展現(xiàn)了沒有戰(zhàn)火的美好生活。用瑤族土語演唱的《梧州歌》,經(jīng)過作曲家的編創(chuàng)后,融入了更多的瑤族元素,賦之于甜美的唱腔和柔美的曲調(diào),展現(xiàn)出瑤族人民淳樸的民風(fēng)和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這些音樂元素的融入也為劇情發(fā)展中陳湘與鳳鳴的相愛、瑤族人民與革命戰(zhàn)士的情感融合埋下伏筆,既渲染了舞臺氣氛又突出了主題表達(dá)。
三、人物形象塑造闡釋的情感之美
民族音樂劇的劇情不僅展現(xiàn)在歌劇的演唱中,還展現(xiàn)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中。有的創(chuàng)作者曾指出戲劇化的敘事主要目的是為了塑造人物的某種舞臺形象,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戲劇的主題表達(dá)。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通過優(yōu)秀的人物塑造打動觀眾,讓觀眾在觀賞劇目的同時感受劇中人物的情感變化,從而延伸到對革命戰(zhàn)爭的認(rèn)同并產(chǎn)生情感共鳴。
(一)節(jié)奏呈現(xiàn)出的意識共鳴
劇中主人公陳湘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以紅軍34師師長陳樹湘為原型,對歷史事件真實(shí)場景進(jìn)行策劃提煉,塑造了一位為共產(chǎn)主義信仰而戰(zhàn)的英雄形象。陳湘為了保證紅軍順利通過湘江,在碰到昔日同學(xué)黃復(fù)興時義無反顧地亮出了隨身攜帶的鋼刀,在拔刀的那一刻他身上的浩然正氣一覽無余,唱段《鋼刀對鋼刀》演繹出了一種宿命的對決,二人以鏗鏘有力的節(jié)奏展現(xiàn)出一種悲壯的對峙。唱詞中所述“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正是革命者陳湘內(nèi)心獨(dú)白的再現(xiàn),引發(fā)了受眾的情感共鳴。
(二)敢愛敢恨表現(xiàn)真性情
《血色湘江》中的女主人公鳳鳴作為族長的女兒,常年受到軍閥勢力的殘害,其父親受軍閥迫害致死,鳳鳴發(fā)誓要為父親報(bào)仇雪恨,這也造就了她魯莽的性格,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但自從目睹了戰(zhàn)士們保家衛(wèi)國不畏犧牲、朱大姐含淚自盡等事件后,她變得更加成熟。從潑辣到沉穩(wěn)的成長也是鳳鳴敢愛敢恨的一種展現(xiàn)。唱段《瑤山的女兒》第三部分節(jié)奏較快,由最初的“血債血償”到后期“我是瑤山的女兒,云海密林是梳妝的閨房”,斷音的演唱表現(xiàn)出了鳳鳴無論如何都要保衛(wèi)家園的堅(jiān)定決心。這種真性情的呈現(xiàn)也感染著臺下的每一位觀眾。
(三)保家衛(wèi)國展現(xiàn)革命信仰
劇中的英雄人物朱大姐是紅軍某政治部師長的愛人,她自己的身份則是一名醫(yī)院的大夫,由于與丈夫在渡江時失聯(lián),導(dǎo)致自己脫離了隊(duì)伍。全劇中,朱大姐的唱段精練而短小,但卻是推動劇情發(fā)展的重要人物。詠嘆調(diào)《不要救我》是朱大姐在夜晚生下女兒后所唱的一個慷慨激昂的唱段,生產(chǎn)后的朱大姐拖著虛弱的身體,唱道“不要救我,命若游絲啊”,“命”字重音,“游絲”直至胸腔,“絲”字帶有顫抖音。“不要救我”的多次重復(fù)也反映出朱大姐時刻準(zhǔn)備犧牲的決心。為了不拖累部隊(duì),她將女兒做了臨終前的托付。最后一段朱大姐在舒緩的音樂中唱道:“戴上紅軍帽,把信仰注入血肉。”平穩(wěn)而扎實(shí)的低音為演唱增添了更多的氣勢,這樣的氣節(jié)讓人無不動容。“請你們輕裝往前走,往那勝利的方向”唱出了朱大姐的舍生取義,肝腸寸斷的表達(dá)展現(xiàn)出了革命人的堅(jiān)定信仰。
民族音樂劇的審美元素涉及到肢體美學(xué)、情景美學(xué)、音樂美學(xué)、語言美學(xué)等多個領(lǐng)域,審美視域下的民族音樂劇更加注重中華傳統(tǒng)文化審美在作品中的應(yīng)用。民族音樂劇《血色湘江》的問世既是紅色精神的傳承,也是民族文化信仰的一種呈現(xiàn)。與其他流行音樂劇不同的是,《血色湘江》中的念詞少、演唱多,融入了瑤族地域文化特色,在展現(xiàn)革命隊(duì)伍與少數(shù)民族人民軍民一心的同時也呈現(xiàn)出了廣西地區(qū)的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等,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強(qiáng)大的生命力與凝聚力,在振奮人心的音樂中讓受眾感受到了人民英雄的偉大與革命信仰的崇高,激勵著當(dāng)代人傳承和發(fā)揚(yáng)這種精神之美。
參考文獻(xiàn):
1.董迎春,覃才:《紅色經(jīng)典的藝術(shù)探索與價值——以〈血色湘江〉為例》,《南方文壇》,2021年第5期
2.黎莉:《廣西瑤族“蝴蝶歌”在現(xiàn)代音樂作品中的運(yùn)用——以音樂劇〈血色湘江〉中的“蝴蝶歌”為例》,《名家名作》,2021年第8期
3.全婕:《流淌在血情中的英雄贊歌——評音樂劇〈血色湘江〉》,《當(dāng)代廣西》,2021年第4期
4.張玢:《一曲悲歌慟天地 長征路上筑英魂——評音樂劇〈血色湘江〉的宏大敘事與紅色精神傳承》,《藝術(shù)評論》,2019年第11期
5.曹光哲:《一曲英雄主義的悲歌——評原創(chuàng)音樂劇〈血色湘江〉》,《當(dāng)代廣西》,2019第21期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
責(zé)任編輯 姜藝藝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