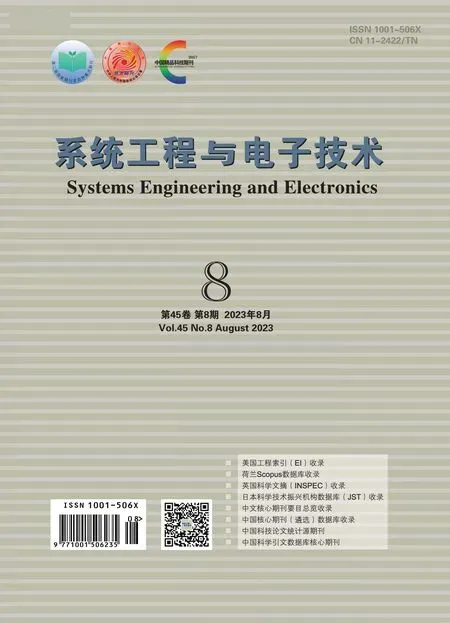基于作戰態勢和改進CRITIC-TOPSIS的目標威脅評估模型
蘇 倩, 鐘元芾, 曹志欽, 張英朝
(中山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00)
0 引 言
現代化戰爭中,隨著各種新興前沿技術的發展及應用,戰場態勢越來越復雜,現代作戰面臨更多的威脅。在作戰指揮過程,指揮員根據目標的信息分析敵方作戰態勢,若既能準確地評估敵方目標在短時刻內的威脅程度,還能結合對方作戰體系信息評估敵方目標的長期威脅程度,則能給己方的作戰人員結合作戰需求合理選擇決策偏好,超前決策與部署、奪得戰場先機提供支持。因此,對作戰中目標進行靈活合理的威脅評估,顯得尤為重要。
當前,國內外眾多學者對目標威脅評估進行了研究,威脅評估主要分為建立評估指標體系,確定指標權重,計算威脅度3個步驟。對于評估指標體系的建立,霍潤澤[1-2]等選取目標速度、飛抵時間、目標距離等敵方目標相對于己方的態勢指標。鮑俊臣[3]等選取目標的機動能力、電子能力等靜態屬性作為評價指標。方誠喆[4-6]等綜合選取目標的類別、速度、作戰能力等作為評價指標,綜合考慮目標動態與靜態屬性。以上評估指標選取從敵方目標個體層面考慮其相對于我方的態勢信息,對于目標短時刻內對我方的威脅程度可以較好地評估。但是在作戰過程中,敵方目標個體與個體之間存在復雜關系,敵方作戰體系內較為重要的節點對我方具有更長遠與持續的威脅,當前的指標選取對敵方目標個體之間的態勢分析不夠全面,未能較好地利用敵方作戰網絡中的體系信息,不能較好地評估目標的長遠威脅。
對于指標權重的確定,Wang[7-9]等人選取了貝葉斯網絡、直覺模糊法等方法確定主客觀權重,并能夠對小樣本數據、缺失數據進行較好地處理。徐宇恒[10]等使用客觀賦權法(criteria importance though intercrieria correlation,CRITIC)確定權重,能綜合考慮指標對比性與矛盾性客觀賦權,但是對于目標大小、意圖等直接賦值型指標會使矛盾性權重過大,影響評估結果。張才坤[11-13]等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多準則妥協解排序方法(vlsekriterijumska optimizacija i kompromisno resenje,VIKOR)等多屬性決策方法計算威脅度,能夠在定性或定量考慮多個屬性的情況下,選出相對最優的方案。但以上方法大部分是靜態評估,只考慮了當前時刻,并未考慮歷史時刻的信息。張堃[14-15]等考慮了時間因素,分別采用正態分布和泊松分布函數考慮時刻數遠近來判定時刻的重要程度,但仍未能利用時間變化過程中目標及其作戰網絡態勢變化的信息。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了基于作戰態勢和改進CRITIC-TOPSIS的目標威脅評估模型,評估多個目標的相對威脅度,得到對應的威脅排序。首先,針對指標考慮不全面、不能較好地評估目標長遠威脅的不足,在考慮敵我態勢指標的基礎上,通過目標意圖結合作戰環理論,建立敵方目標間態勢指標體系。其次,針對CRITIC法中對于矛盾性指標權重過大,影響TOPSIS評估結果的問題,提出改進的CRITIC-TOPSIS方法,弱化矛盾性指標權重。最后,針對時間權重只考慮時刻遠近的不足,提出了基于目標態勢變化程度的時間賦權法,根據前后時刻目標狀態變化程度生成時間權重,動態加權處理多時刻態勢信息,得到綜合威脅評估結果。
1 基于作戰態勢的評估指標體系
威脅評估指標體系的建立主要包括指標的選取以及量化。根據防空作戰目標特點及戰場態勢,選取指標體系如圖1所示。

圖1 威脅評估指標體系Fig.1 Threat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1.1 敵我關系態勢指標選取與量化
根據傳統經驗和現有研究,本文參考文獻[16]等選取敵方目標的大小、飛行高度、距離、飛行速度等作為敵我態勢的威脅指標,通過隸屬度函數對其進行量化計算。
1.1.1 目標的大小類型
雷達檢測到的目標通常分為3類:大型目標、中型目標、小型目標,其威脅隸屬度值分別定義為0.85、0.68、0.43。
1.1.2 飛行高度
目標的威脅高度越低,對我方目標的威脅程度越高,則定義飛行高度威脅隸屬函數為
(1)
式中:k=10-8;h為敵方目標高度,單位為km。
1.1.3 雙方距離
雙方距離是指敵方目標與己方目標直線的距離,距離越小,目標對我方的威脅越大,則定義雙方距離威脅隸屬度函數為
(2)
1.1.4 飛行速度
敵方目標的飛行速度越快,我方攔截難度越高,對我方的威脅越大,則定義敵方目標飛行速度的隸屬度函數為
x(v)=1-eav
(3)
式中:a=-0.004;v為目標飛行速度,單位為m/s。
1.1.5 飛抵時間
敵方目標飛抵我方時間越短,留給我方指揮人員反應的時間越短,對我方威脅越大,則定義敵方飛抵時間的隸屬度函數為
(4)
式中:k=2×10-7;t為飛抵時間,單位為s。
1.1.6 戰術意圖
在作戰中,考慮敵方的戰術意圖能有效發掘敵方作戰單元的潛在威脅。基于對敵方作戰單元戰術意圖的判斷,建立戰術意圖威脅值,如表1所示。

表1 目標戰術意圖威脅值
1.2 敵我關系態勢指標選取與量化
1.2.1 基于目標戰術意圖的作戰環建模
在作戰中,處于敵方作戰體系重要位置的目標對我方的威脅也會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基于目標戰術意圖結合作戰環理論建立敵方作戰體系,分析敵方目標間的相互關系。作戰環理論是國內學者在OODA(observation, orientation, decision, action)環的基礎上提出的,指在作戰中為了完成特定的作戰任務,武器裝備體系中的偵察類、決策類、影響類等武器裝備實體與敵方目標實體構成的閉合回路。作戰環將裝備實體分為目標類實體、偵察類實體、決策類實體、打擊類實體等四類[17]。
本文將己方基地作為作戰環中的目標類實體,其他目標通過其作戰意圖,將其對應于以上實體,對應規則定義如表2所示。

表2 意圖-節點對應表
作戰網絡邊是指作戰體系中各種作戰實體之間的物質、信息交流,定義連邊規則[18]如下:
(1)行動控制邊D→I:表示決策類實體對打擊類實體下達相關作戰指令。
(2)偵察攻擊邊S→I:表示作戰過程中,不通過決策類實體,偵察攻擊一體化,高效作戰,并規定偵察類節點跟其較近的打擊類節點相連。
(3)攻擊目標邊I→T:表示打擊類實體對攻擊目標進行攻擊。
(4)偵察目標邊S→T:表示偵察類節點對我方基地進行偵察、監視等。
1.2.2 敵方作戰網絡節點指標選取與量化
對作戰環建模得到敵方作戰體系,共選取5個評價指標。其中,選取節點度、接近中心性、PageRank這3個指標[19],另外根據作戰網絡節點屬性及連邊意義不同的特點,本文提出可被替代性指標、連邊威脅性指標,具體定義如下。
(1) 可被替代性:節點與其周圍共屬性的點最短距離與總距離之比,該值越小,則其相對可被替代性越強,節點的重要程度越低,計算方法如下:
(5)
式中:m為節點屬性個數;n為與該節點同屬性的節點數量;Sx為第x類屬性節點之間距離。
(2) 連邊威脅性:基于第1.2.1節的連邊規則,建立連邊威脅值如表3所示,連邊威脅值占比越大,則威脅性越高,連邊威脅性計算公式如下:

表3 連邊威脅值
(6)
式中:Etij表示節點i與j連邊的威脅值;Eti表示節點i的連邊威脅值;X表示與節點相連邊的數量。
2 改進CRITIC-TOPSIS的威脅評估模型
2.1 基于改進CRITIC-TOPSIS的威脅度計算
在指標賦權法中,CRITIC法能考綜合指標的對比性與矛盾性確定權重,減小指標間相關性的影響得到合理的結果。基于現有研究,使用CRITIC法確定目標威脅指標權重存在以下不足:① 指標的沖突性應只與指標的相關性程度有關,與正負無關,故需要消除相關系數的正負符號;② 若指標中存在直接賦值型屬性或相關性較低的指標,CRITIC法會對這類指權重過高,導致此類指標會直接決定目標的威脅度和排序,故需要弱化沖突性。針對以上,本文提出改進的CRITIC法計算步驟如下。
步驟 1數據標準化計算。
步驟 2對比性計算。以上兩個步驟同文獻[10],詳細計算公式不再贅述。
步驟 3矛盾性計算,為消除相關系數正負符號的影響,改進后的矛盾性計算公式為
(7)
式中:rij表示指標i與j之間的相關系數,使用皮爾遜相關系數。
步驟 4信息承載量越大,則認為權重越大。根據原始CRITIC方法求得的權重計算最大差距,根據差距進行信息承載量計算,改進后的計算公式如下:
(8)
(9)

威脅度計算則使用TOPSIS法,TOPSIS法[20]能確定各個指標的最優與最劣理想值,然后通過精確地計算各個方案與最優最劣方案的歐式距離,找出相對的最佳方案,是一種客觀的綜合評價方法,受主觀影響較少,其具體計算步驟不再詳細闡述。
2.2 基于態勢變化的時間權重計算
作戰過程中目標所執行的作戰任務可能會發生變化,目標的威脅程度也會隨著變化。本文認為,對于態勢前后變化程度較高的相連時刻應該賦予較高權重,并且對這兩個時刻中威脅程度相對高的時刻取高權重,其中態勢變化程度通過目標指標權重的變化計算求得。本文提出基于態勢變化的時間權重計算方法,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步驟 1將目標前后時刻同一指標的權重變化程度視為其態勢變化程度,則權重變化計算公式為
Δwij=|wij-w(i+1)j|2,i=1,2,…,T-1;j=1,2,…,n
(10)
步驟 2計算時間權重變化率:
(11)
步驟 3通過時間權重變化率與對應前后兩個的指標權重加權,計算基于態勢變化程度的時間權重值,計算公式如下:
(12)
式中:wij為第j個指標在第i個時刻的權重;αi(i+1)為最大化因子,其計算公式如下:
(13)
2.3 綜合評估
將兩類態勢威脅度結合時間權重進行組合,得到敵我態勢及敵方目標間態勢威脅評估結果,計算公式如下:
(14)
式中:Ci分別是第i個目標的威脅值;Cij為第i個目標在第j個時刻威脅值;Wj為第j個時刻的時間權重。
最后,基于敵方目標的敵我態勢威脅度和敵方目標間態勢威脅度的分析,得到綜合威脅程度計算公式:
(15)
式中:C1i和C2i分別是第i個目標的敵我態勢威脅和敵方目標之間態勢的威脅值;Ci為第i個目標的最終綜合威脅值;γ為態勢決策系數,γ>0.5則偏向考慮敵我態勢威脅,評估目標的短期威脅,γ<0.5表示偏向考慮敵方目標之間威脅態勢,評估敵方目標的長遠與持續性威脅。
2.4 基于改進CRITIC-TOPSIS的威脅評估流程
本文提出的威脅評估方法分為3個步驟,分別包括指標體系建立、威脅度計算與綜合評估結果計算,具體模型的流程如圖2所示。

圖2 威脅評估流程Fig.2 Threat assessment process
首先,基于敵我態勢與敵方目標間態勢,分別選取相應的影響指標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基于改進的CRITIC-TOPSIS計算目標威脅指標權重,得到目標威脅度。最后,考慮防空作戰目標的動態性,根據目標的態勢變化程度計算時間權重,把目標的多時段威脅度結合時間權重進行加權,得到最終的綜合評估。
3 案例分析
假設某次作戰中,某海軍由1艘導彈驅逐艦和4艘導彈護衛艦組成水面艦艇編隊在某開闊海域巡邏,其中導彈驅逐艦為指揮艦,指揮艦位置位于北緯15°41′7″,東經112°42′10″,編隊航向200°(以正北為0°,順時針方向),航速16 kn。編隊依靠自身雷達對空中目標進行探測,編隊中任意一艘艦發現目標,其他艦都可以共享信息。紅方預警機發現前方有12批可疑的空中目標,通過雷達獲取到藍方一段時間內經緯度、高度和雷達反射面積的數據。根據文獻[21-24]得到12個目標的相關原始數據,如表4所示。

表4 目標原始數據
3.1 指標量化
3.1.1 雙方態勢指標量化
根據第1.1節方法得到目標t1時段的威脅隸屬度如表5所示,同理可得其他3個時段的隸屬度。

表5 雙方態勢目標威脅隸屬度
3.1.2 藍方目標間態勢指標量化
基于第1.2節的理論方法進行作戰網絡建模,4個時刻目標位置與對應意圖為圖3根據表3目標意圖-作戰環實體節點對應規則和作戰環連邊規則建模,4個時刻的目標作戰網絡如圖4所示。

圖3 4個時刻目標位置及對應意圖Fig.3 Target location and corresponding intention of four moments

圖4 4個時刻作戰網絡及連邊權重圖Fig.4 Combat networks and weight of the edge of four moments
并通過第1.2節方法得到藍方目標之間態勢t1的初始威脅因子如表6所示,同理可以得到其他時刻的威脅因子矩陣。

表6 藍方目標間態勢的初始威脅因子
3.2 確定指標權重和時間權重
通過第2.1節的改進CRITIC法,分別得到4個時間段雙方態勢指標權重W1,藍方目標間態勢指標權重W2。

由第2.2節求得時間權重分別為:ηi1=〈0.006,0.987,0.007〉,ηi2=〈0,1,0〉。其中αi(i+1)取0.7,通過態勢變化求解得到時間權重矩陣分別為WT1和WT2。

3.3 雙方態勢評估結果與對比分析
利用TOPSIS法求解威脅度,最后通過第2.3節方法計算時間加權后的動態威脅值,并將本文結果與未改進的CRITIC-TOPSIS法進行對比,得到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雙方態勢動態威脅度
對表7的結果進行分析,兩者主要的差別是在目標85和39、60和30、36和93的相對排序上。分析三者的雙方態勢信息,目標39雖然是大目標,但其高5.2 km,速度只有96 m/s;目標85速度高達302 m/s、高度只有1.4 km,飛抵紅方時間只需692 s、并且其戰術意圖為攻擊,故目標85的威脅應遠大于39,且威脅度排名靠前。目標30的速度持續為137 m/s,高度為7 km,距離為215 km;目標60的速度持續為112 m/s,高度為9.4 km,距離為207 km,其飛抵紅方時間更長,雖然目標60為大目標,但綜合其他態勢因素,目標30的威脅程度更大,應比目標60更高。目標36和93的初始速度分別為215 m/s和240 m/s,雖然目標93為大目標,但是目標93后半段時刻速度驟減至低于10 m/s,而目標36仍維持原來速度,其他態勢因素基本相近,故兩者相比目標93的威脅度應更高。
由以上分析可得,未改進的CRITIC-TOPSIS會使目標大小這類賦值性屬性權重過高,改進的CRITIC-TOPSIS能有效地解決這個不足,使評估結果更為合理。
對表8的結果進行分析,其中文獻[14]的時間權重方法計算結果與本文在目標91、30與39的相對排序不同,結合目標雙方態勢信息分析,目標30和目標39的速度分別為130 m/s和95 m/s,作戰意圖為偵察、監視,目標91后半段時間速度為100 m/s,但前半段時間速度為200 m/s,遠高于目標39和目標30,其他態勢因素基本一致。綜合考慮,目標91速度在一段時間速度發生急速變化,推測具備高速作戰的能力,故三者的威脅排序應為91、30、39。以上可以看出,本文的評估結果可以綜合考慮目標整段時間的態勢變化信息,對目標進行合理的動態威脅評估。

表8 結果對比1
3.4 藍方目標間態勢評估結果與對比分析
利用TOPSIS法求解威脅度,最后通過式(14)計算時間加權后的動態威脅值,以及與未改進的CRITIC-TOPSIS結果進行對比,對比結果如表9所示。

表9 藍方目標間態勢動態威脅度
本文方法的結果中,目標85和目標42在作戰環中擔任攻擊節點,作戰任務重要性較高,其中目標85在后半段可被替代性極低,故其威脅性最高;目標37是整個作戰網絡中唯一的掩護節點,該節點可被替代性極低;目標51雖然作戰意圖為攻擊,但其位置與任務可被同類型目標85和目標42替代,可被替代性較高。目標36、31、60的作戰意圖為其他,重要性極低,目標93和目標72在作戰過程中處于邊緣節點,且周邊同類型目標較多,可被替代性極強,故威脅性判斷較低。而未改進的CRITIC-TOPSIS方法與本文的方法結果相差較大。分析原因發現,未改進的CRITIC-TOPSIS方法由于對PageRank指標的權重過大,導致最后的評估結果排序中PageRank值較高的目標如39、36、72、31等目標排序非常靠前,影響評估結果的合理性。
將文獻[14]的泊松分布逆形式時間權重計算方法與本文的方法對比,結果如表10所示。可以發現,文獻[14]的時間權重計算方法和只考慮t4時刻的結果完全相同。藍方目標間態勢在t2至t3時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目標93和目標51前半段時間威脅程度極低,在后半段威脅程度才與目標42和目標37較為接近,而目標42和目標37等整個時間段內威脅值都較高,故目標93和目標51的威脅程度應該比目標42和目標37低更為合理。故本文提出的基于目標態勢變化的時間權重,能較好地考慮整個時間的態勢信息,對目標的威脅做出更為合理的評估。

表10 結果對比2
3.5 綜合評估結果與分析
根據第2.3節計算綜合評估結果,其中取γ=0.8得到偏向考慮雙方態勢的動態威脅評估,結果如表11和圖5所示。

表11 綜合威脅度

圖5 結果分析Fig.5 Results analysis
由圖5排序結果可得,雙方態勢威脅會更偏向于考慮當下時刻的威脅度,如目標意圖為攻擊、當前速度極快、距離極近的目標51、42、85,在僅考慮雙方態勢的情況下威脅排序最高,而距離較遠、速度較低的節點如36、72、93等威脅值較低。基于藍方目標間態勢的威脅排序更偏向于考慮藍方目標在其作戰網絡中的重要性,即對紅方的長遠與持續威脅,如目標39、91、30等意圖為偵察、監視,構成多個作戰環的決策類節點,威脅性最高。而目標72、36、85等在作戰環中擔任打擊等任務執行節點、可被替代性強,這類節點的威脅性較低。故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根據決策者的偏好與需要,靈活選取態勢因子,既能考慮當下時刻的威脅又能評估長遠與持續威脅,使目標威脅排序能更為合理。
4 結 論
本文針對防空作戰中目標威脅評估指標體系選取不全面、忽略時間變化過程中態勢動態變化等問題,提出了基于作戰態勢和改進CRITIC-TOPSIS的威脅評估模型。
(1) 所構建的基于作戰態勢的威脅評估指標體系,在考慮雙方態勢的基礎上,基于目標戰術意圖結合作戰環理論,建立敵方目標間態勢指標體系,能較好地利用敵方作戰體系信息,充分考慮目標的長遠與持續威脅,決策者可以結合戰場決策偏好與需要評估目標威脅,具有較強的靈活性。
(2) 該模型使用改進的CRITIC-TOPSIS計算威脅度,能改進在賦權中某一類指標權重過大影響最終評估結果的不足,同時結合態勢變化程度考慮多時刻信息,克服了只考慮單一時刻或者僅根據時刻遠近判斷時刻重要性的不足,能充分利用作戰過程中目標的態勢變化,使評估結果更為合理。
(3) 實驗結果表明,所提的基于目標態勢和改進CRITIC-TOPSIS的目標威脅評估模型能根據決策者的偏好與戰場需要,通過目標態勢變化動態評估,給出較合理的目標威脅評估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