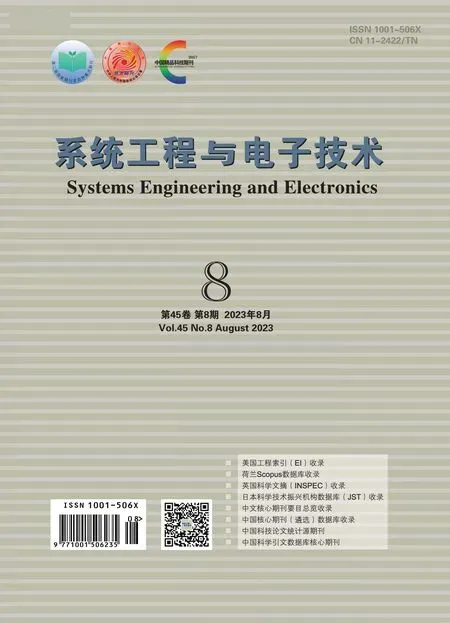基于網絡化指標的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模型研究
黃炎焱, 王凱生, 史宇昂
(南京理工大學自動化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4)
0 引 言
近年來的現代戰爭表明,殺傷手段越來越離不開網絡信息的支撐保障。無論是OODA(observation, orientation, decision, action)作戰鏈,還是美國空軍提出的F2T2EA(find,fix,track,target,engage,assess)殺傷鏈系統,即由“發現、定位、跟蹤、瞄準、交戰、評估”6個環節組成的鏈路,都離不開網信服務體系的支撐及保障,基于網信支撐的 “殺傷鏈”作戰已成為常規作戰形式[1-2]。
殺傷鏈能力是建立在數據鏈及指控鏈等網信體系上的殺傷手段。信息化戰爭就是在數據鏈的支撐保障下通過充分利用信息資源連通對敵殺傷鏈路,實現對敵有效打擊的戰爭形態[3-4]。各類作戰單元間通過數據鏈打破壁壘,達到全域范圍內的態勢共享,互聯、互通、互操作,從而實現“1+1>2”的涌現效應,進而促進殺傷鏈作戰循環的進行[5-7]。數據鏈作為信息化戰爭的神經網絡,其裝備建設必須滿足“殺傷鏈”作戰帶來的技術需求[8-10]。數據鏈是以網絡為基礎,以信息為主導的數據處理鏈路,即將作戰要素數據進行分類整合,形成作戰要素描述信息;將信息按需分發共享,整合信息形成作戰決策;依決策分配任務,采取行動;對行動效果進行評估并處置,實現指控單元到武器單元間信息的無縫鏈接,完成對目標的精確、快速殺傷。數據鏈對殺傷鏈的作戰保障能力直接影響了殺傷鏈的作戰效能[11-12]。因此,對數據鏈的作戰保障能力展開評估,對完善數據鏈的裝備建設、提高殺傷鏈作戰效能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13-14]。
目前,針對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的研究存在以下問題:① 當前研究對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概念的詮釋還不夠明確,缺乏專業的網信融合評價指標,網信保障質量難以表達,作戰保障能力指標體系不易構建;② 數據鏈不直接參與殺傷,其保障能力不能直接用殺傷鏈的效能表達,需要借助殺傷鏈匹配的效能指標進行間接及隱性的表達[15-16];③ 數據鏈能力指標體系呈現網絡化結構,而非傳統裝備能力指標的顯性樹狀結構指標。傳統評估多采用顯性的樹狀結構指標,而數據鏈領域數字化、網絡化特征顯著,作戰保障能力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相互交互的指標聯合構成,難以強行分拆,為尊重客觀現實,需要一種網絡化指標體系形式,涵蓋數據鏈組網要素的特征能力[17-18]。④ 傳統線性的評估方法難以適應網絡化指標體系的變化,評估過程需要大量邏輯數據進行分析,過去研究往往比較缺乏對數據的具體分析[19-20]。
為此,鑒于數據鏈能力相關的信息感知、網絡信息分發、網信作戰保障質量等評估指標是相互邏輯耦合,難以強行分拆。為尊重數據鏈這種客觀現實,需要構建一類網絡化指標體系,涵蓋數據鏈組網要素的特征能力。為此,本文擬圍繞數據鏈這類網絡化評估指標體系,對照新一代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展開評估研究。
1 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總體框架建立
1.1 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特點
信息化戰爭即是在數據鏈的支撐保障下,通過融合多域多維度的信息,實現作戰能力高效協作統一的作戰樣式。信息化作戰形態下,作戰行動與殺傷鏈作戰效能發揮、數據鏈裝備體系優化間的關聯圖如圖1所示。

圖1 信息化作戰形態結構圖Fig.1 Information warfare form structure chart
作戰殺傷鏈通過戰術數據鏈信息共享網絡的支撐保障,實現態勢信息共享、指控信息協同,運用于對機載作戰、防空作戰、陸地作戰、導彈作戰、空中偵察、空域管制、反潛作戰、火力支援、登陸作戰、搜救營救等戰術行動。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通常從以下方面得到體現運用。
(1) 綜合組網運用。戰術數據鏈通過高效組網的功能,快速接入新的作戰平臺構筑網絡,實時掌握所有網絡成員的網絡狀態、平臺狀態、位置狀態、運動狀態等信息,為作戰過程的互相支援與高效協同提供支持。
(2) 戰術信息保障。戰術數據鏈通過通信鏈路的跨域貫通,及時、高效地將多維戰術信息傳輸給組網內的各個網絡成員。
(3) 戰場態勢共享。戰術數據鏈通過對各類傳感器平臺探測到的目標信息進行分布式處理,在組網內形成一致的目標態勢圖,供各個網絡成員共享,從而將作戰部隊的態勢感知范圍由原始的傳感器探測范圍擴大為裝備體系內部所有傳感器探測范圍的并集,大大提高了作戰部隊的態勢感知能力。
(4) 電子戰應用。戰術數據鏈通過將組網內的電子戰平臺獲取的信息進行融合處理,可提高對隱身目標、遠距目標、小目標等不宜偵察目標的識別效率,結合共享戰場態勢可以大大提高我方電子戰能力。
(5) 戰術協同運用。戰術數據鏈通過對實時信息的高效融合處理與靈活傳輸,為多種協同策略的實現提供了保障,能夠對多個作戰平臺間可能出現的沖突干擾及時進行協調消解,同時提高了我方作戰體系的協同作戰能力。
(6)指揮控制保障。戰術數據鏈通過增加作戰平臺間的連通性,還通過指控互操作配套服務,使得傳感器平臺與火力平臺間的信息交互更加高效快速,極大提高了我方殺傷鏈路相對敵方的指揮控制速度與精度,進而提高了我方作戰體系快速精準先敵打擊的優勢。
1.2 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評估總體框架
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是對數據鏈裝備的建設、應用能力發揮程度的評定和計算,目的是對裝備的戰斗力現狀有清晰把控,以助力改進及合理應用。
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應用于高動態性、高對抗性的復雜體系對抗作戰中,應用場景的特殊性使得靜態評估方法在此并不適用。數據鏈通過把作戰的能力池聯通,為殺傷鏈提供足夠的能力選擇,因此通信組網能力是數據鏈的主要能力之一。同時,殺傷鏈需要配合這些能力及武器,如果交互受阻也不能形成快速殺傷鏈閉環,因此數據鏈需要共享態勢及協同感知能力。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是以作戰概念為背景,以作戰任務為驅動,對數據鏈支撐保障殺傷鏈作戰能力進行評估的過程,因此以網絡信息服務的質量為指標的數據鏈服務能力是動態的能力,需要動態的評估指標體系來描述。其本質是研究在特定應用場景下,數據鏈裝備對殺傷鏈應用需求的滿足度,進而對數據鏈裝備體系進行針對性完善升級。基于以上分析,搭配上動態的評估方法,本文所設計的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動態評估總體框架如圖2所示。

圖2 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動態評估總體框架Fig.2 Overall framework for dynamic evaluation of data link operational support capability
本文所提的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動態評估總體框架由作戰概念牽引,分為信息層、業務層與評估層。其中,信息層描述了從頂層作戰任務清單落實到底層作戰裝備清單的過程,數據鏈裝備在數據層間流動中發揮支撐作用;業務層由信息層映射而成,描述了從使命任務分配到物理平臺的過程,數據鏈裝備在數據層內流動中發揮支撐作用;評估層是圍繞數據鏈裝備的研發建設而搭建的動態評估框架,通過對數據鏈裝備的作戰保障能力刻畫、接收來自業務層的輸入信息與各關鍵數據庫的數據信息,運用合理的評估方法輸出對裝備能力的評估值。
本文所提框架將殺傷鏈作戰效能發揮、數據鏈支撐作戰能力、動態評估框架三者之間的聯系進行了闡述:戰術數據鏈支撐殺傷鏈作戰效能發揮的發揮,殺傷鏈的作戰效能發揮水平為動態評估框架提供關鍵指標數據,動態評估框架迭代優化數據鏈支撐作戰能力。
2 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網絡化指標體系構建
指標體系是由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屬性指標構成的有機整體,用以在評估活動中對評估對象進行全面性描述。指標體系的結構反應了評估對象的內部組成結構與邏輯,而該結構與邏輯直接影響了評估對象的能力構成與效能發揮。因此,做好指標體系的結構設計工作,是評估系統運行的前提和關鍵。
2.1 指標體系結構分析
指標體系結構主要有樹狀和網絡化兩種基本類型。樹狀指標體系結構清晰,但構建的前提是指標間相互獨立,需要對評估對象特性進行分析解耦,不適用于大型復雜系統。而網絡化指標體系由于其結構與復雜網絡相呼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描述復雜系統內部的耦合關系,然而其復雜結構也使得評估過程不夠直觀具體。
數據鏈的作戰保障能力評估涉及到組網、共享、協同、交互等信息域、認知域以及社會域的范疇,指標之間相互關聯、互為因果、綁定釋義的情況普遍存在,要采用傳統的樹狀指標體系,難以對評估對象進行刻畫評估。如何尋求一種新的指標體系表達方式,是本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考慮到數據鏈領域數字化、網絡化特征顯著,本文基于復雜網絡理論與網絡分析(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法建立新型效能評估指標體系,對戰術數據鏈的作戰保障能力進行刻畫。
2.2 效能指標集構建
建立戰術數據鏈裝備基礎效能指標集是構建數據鏈裝備效能指標網的關鍵。指標集的建立需要以數據鏈裝備的運行過程為基礎,結合仿真實驗數據,提取能夠反映數據鏈體系效能的要素因子凝練成體系效能基礎指標,并構建基礎指標計算模型。效能指標集的構建應遵循以下原則:
(1) 系統完備性。效能指標的選取應遵從系統論的思想,從各個層次、不同角度來對評估對象的特征進行描述,綜合表征對象的發展狀態與變化趨勢。
(2) 客觀獨立性。效能指標的選取應能與現實系統建立聯系、能夠真實地反映評估對象的各項性能與特征。同時,在指標選取前需要對評估系統的復雜性、耦合性進行分析,對備選指標的關聯性進行分析,使得最終確定的效能指標集內部的耦合性最小、指標內涵的重合度最低。
(3) 簡化可測性。在能滿足評估要求的情況下,應選取盡可能少的關鍵指標來構建效能指標集,還應考慮選取容易定量計算的關鍵指標。針對無法量化的定性指標,應采用專家評價等方法轉化為可量化計算的指標。
2.3 保障能力指標網構建
定義數據鏈保障能力評估系統的保障能力指標集模塊包含的N個指標集為{{S1},{S2},…,{SN}},其中每個指標集{Si}都可用復雜網絡中的加權圖進行刻畫,描述為{Si}=〈V,E,W〉。其中,V為該網絡中節點集合,即為該指標集中保障能力指標的集合;E表示網絡中節點的聯通關系(邊),描述了指標集中保障能力指標間的關聯性;W表示網絡中邊的權值(也可理解為邊的長度),描述了指標集中保障能力指標間的關聯度。基于復雜網絡理論建立的數據鏈裝備保障能力指標網如圖3所示。

圖3 能力指標網Fig.3 Performance index network
2.4 基于ANP的新型保障能力評估指標體系構建
為了合理有效地對數據鏈裝備的作戰保障能力開展保障能力評估,指標體系的合理、完備構建尤為重要。ANP模型將評估指標體系框架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控制層,包括評估目標及評估準則。第二部分為網絡層,由所有受控制層支配的指標集組成,其內部是互相影響的網絡結構,指標之間互相依存、互相支配。典型ANP層次結構如圖4所示。

圖4 典型ANP評估層次結構Fig.4 Typical ANP evaluation hierarchy structure
ANP在層次分析法的基礎上,考慮到了各指標或相鄰層次之間的相互影響,利用“超矩陣”對各相互作用并影響的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其混合權重。然而,數據鏈支撐作戰保障能力指標結構具有復雜網絡的特征,而不是復雜網絡,太過抽象的體系結構不利于指揮員依據結果進行指揮決策。本文依據典型ANP評估層次結構,在網絡層根據已建立的基礎保障能力指標集進行關聯性分析,根據關聯關系涌現出基礎指標的網絡結構,并在控制層通過直接指標與間接指標對網絡結構進行重新標定,構建滿足實際使用場景需求的新型數據鏈保障能力指標體系。改進后的評估指標體系結構如圖5所示。

圖5 改進型ANP評估層次結構Fig.5 Improved ANP evaluation hierarchy structure
通過基礎保障能力指標集建立評估層次結構中的網絡層后,通過網絡連接強弱涌現出一批帶有性能傾向性的直接指標。再通過定義一批顯性的間接指標將評估目標與直接指標進行連接,從而建立好評估層次結構中的控制層,進而完成對新型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
3 基于新型指標體系的保障能力評估方法研究
新型評估指標體系需要與評估方法進行匹配,為此,尋找與新的指標體系互為一體的評估方法進而構成整套評估模型,是目前數據鏈評估領域的期待解決的主要焦點問題,本節將以ANP為例對此展開研究。
3.1 構建評估層次結構
依據評估的實際應用場合結合評估對象的特殊性,確定評估問題的目標、準則與可能結果。構建網絡化評估指標體系框架用以描述在確定評估目標下的指標或指標集的關系,包括確定由評估目標與評估準則組成的控制層與根據指標集確定的網絡層。
3.2 指標重要度打分
指標重要度是指標的多項屬性、特質共同作用的外在涌現形式,難以采用技術方法進行定量分析,因此采用專家打分法,對專家意見進行統計、處理、分析和歸納,客觀地綜合多數專家經驗與主觀判斷是當前研究中較為合理的處理方法。根據所建立評估體系框架中各指標之間的影響關系制作問卷,并聯系數據鏈作戰保障領域專家依據重要度相對尺度表對各層級以及各評估指標之間的重要度比值進行打分。重要度相對尺度表如表1所示。

表1 重要度相對尺度表
3.3 計算各指標權重
(1) 構建無權重超矩陣
以控制層為主準則,以網絡層上任一指標集{Si}中的指標sij為次準則,對指標進行成對比較建立判斷矩陣,從而得到歸一化特征的向量。將各指標間的內外依賴、反饋關系依次進行比較,得到無權重超矩陣WS。同理,以其他控制層為基礎,建立無權重超矩陣WS,如下所示:
(1)
(2) 構造權重超矩陣
以決策目標為主準則,以指標集為此準則,兩兩比較建立判斷矩陣aj,得到歸一化特征向量(a1j,a2j,…,anj)T,進而得到權重超網絡AS,如下所示:
(2)
(3) 極限超矩陣
由于ANP具備依賴關系和反饋關系,所以相對AHP指標優先權的確定程序比較復雜,可利用超矩陣的迭代反映指標的復雜間接關系。指標優先權可以通過求解極限超矩陣而得,計算公式如下:
(3)
4 案例分析
以戰術數據鏈支撐某次殺傷鏈作戰任務為背景,對兩套戰術數據鏈應用方案的作戰保障保障能力進行對比評估分析,進而對本文所提的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動態評估模型的有效性進行分析驗證。為評估模型使用方便,所用實驗數據都已使用指標項對應效用函數進行歸一化處理,評估計算過程都已通過Matlab實現。其中,兩套戰術數據鏈應用方案描述如下。
方案 1使用基于傳統語音通信+多傳感器網絡的戰術數據鏈。
方案 2使用基于傳統語音通信的戰術數據鏈。
4.1 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動態評估模型構建
戰術數據鏈通過保障在數據鏈網絡中的各成員間的態勢信息共享、指控信息協同來支撐作戰行動的順利開展。依據指標選取的系統完備性、客觀獨立性與簡化可測性原則,選取的基礎保障能力指標如表2所示。

表2 基礎保障能力指標
基于上述基礎保障能力指標,依據專家經驗建立基礎指標的網絡化結構,并基于復雜網絡理論,涌現出6項結果類直接指標,如表3所示。
依據前文分析,數據鏈裝備作戰保障能力可通過綜合組網運用保障能力、戰術信息保障能力、戰場態勢共享保障能力、電子戰應用保障能力、戰術協同保障能力、指揮控制保障能力等方面進行刻畫。故本案例中的間接指標定義如表4所示。

表4 間接指標定義
為簡化計算分析流程,在本案例中,效果類間接指標與結果類直接指標為一一對應關系。根據以上指標定義及指標間連接信息,構成了如圖6所示的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指標體系。

圖6 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評估指標體系Fig.6 Data link operational support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ices system
4.2 面向數據鏈作戰保障能力的指標權重計算
網絡層中基礎指標為復雜網絡結構,運用前文所提基于ANP模型的求解方法求解基礎指標對直接指標權值,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基礎指標對直接指標權值矩陣
控制層中數據鏈作戰保障效能與效果類間接指標為典型樹狀結構,運用AHP模型求解間接指標對作戰保障效能權值,結果如表6所示。直接指標對間接指標的權值為六維1矩陣。通過基礎指標對直接指標權值矩陣與間接指標對作戰保障效能權值矩陣,可求得基礎指標對作戰保障效能權值矩陣如表7所示。

表6 間接指標對作戰保障效能權值矩陣
4.3 數據鏈作戰保障效能計算
(1) 本節所用數據來源于基于某殺傷鏈循環的作戰仿真系統。以方案1的保障效能評估為例,歸一化后的數據如表8所示。基于歸一化仿真數據可得效果類間接指標效能值,如表9所示。

表8 歸一化仿真數據

表9 方案1效果類間接指標保障能力值
根據仿真數據可得,在該應用場景下,數據鏈作戰保障效能值E1為0.891 6。
(2) 同理可得,在方案2下,基于歸一化仿真數據可得效果類間接指標效能值如表10所示。

表10 方案2效果類間接指標效能值
根據仿真數據可得,在該應用場景下,數據鏈作戰保障效能值E2為0.515 2。
(3) 對比分析兩種方案支撐效能,雷達圖如圖7所示。

圖7 保障能力對比雷達圖Fig.7 Support capability comparison radar map
分析評估結果可知,在方案1的戰術數據鏈應用方案下,數據鏈的作戰保障效能獲得極大提升。由圖7可知,在多傳感器網絡的協助下,戰術數據鏈在綜合組網運用保障能力、電子戰應用保障能力等方面獲得提升最多。評估結果符合預期,且能夠支持對結果進行細化分析,證實了本文所提評估方法的有效性。
5 結 論
本文針對數據鏈作戰保障效能的有效評估問題,在充分考慮了殺傷鏈作戰樣式的前提下,對數據鏈的評估必要性與評估指標的耦合關聯性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種面向數據鏈能力的網絡化評估模型。通過對數據鏈保障效能指標體系結構進行分析,構建基礎效能指標集,進而構造保障能力指標網,并對匹配評估模型的求解方法進行了分析。結合可獲得的作戰過程仿真結果數據,通過基于想定案例的對比評估案例,對數據鏈支撐殺傷鏈作戰的保障能力進行了有效的對比評估分析,驗證了本文所提方法的可行性與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