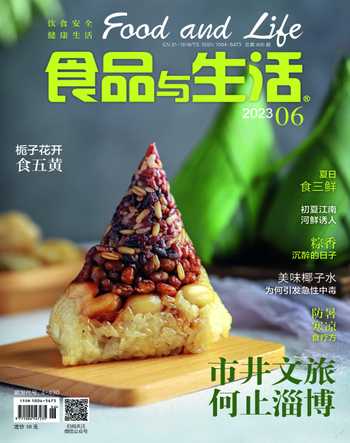夏日食三鮮
喬志遠

上海通志館助理館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以筆描食,以文述史。
6?月已至,悶熱的漫長夏季也將拉開帷幕。不過對老饕們來說,“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這句詩可能更符合他們此時的心境?:比起難耐的酷暑,他們更愛獨屬于這個時令的美食,也就是“三鮮”。
“鮮”一指新鮮、鮮嫩,二指鮮甜、鮮美,而夏季的“三鮮”兩重含義兼具,指夏季獨有或在夏季滋味較佳的食物。“三鮮”的說法由來已久,古時皇帝要在立夏當天親率百官出宮迎夏,用新采摘的瓜果、五谷與現宰殺的豬羊祭祀蒼天,祈佑風調雨順、穰穰滿家。這一儀式后來流入民間,逐漸演化成“嘗鮮”的習俗。不過,當時的“鮮”還沒有固定的數詞搭配,最早能追溯到的說法是清朝《揚州畫舫錄》一書中的“八鮮”,分別是菱、藕、芋、柿、蝦、蟹、車螯、蘿卜,后來民間根據季節與食材來源的不同進行了細分,數詞也不斷減少,繼而成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夏季“三鮮”。

除了皇室祭祀的影響,民間食“三鮮”還有預防疾病的作用。俗話說“夏至三庚數頭伏”,夏至過后就進入三伏天,烈日炎炎、暑氣逼人,很容易出現頭暈目眩、食欲不振等病狀,古人稱其為“苦夏”,也就是受夏日之苦的意思。這時吃些平日難見的鮮貨,能一定程度上緩解疲勞、增進食欲,食“三鮮”的習俗也由此代代相傳。
倘若你在不同的地方過夏,見到的“三鮮”也是不同的,如果將其悉數歸納,可能“三十鮮”“三百鮮”都不止。以江蘇為例,“三鮮”就包括黃瓜、杏子、刀魚、香椿、青梅、麥子、櫻桃、蒜苗、莧菜、蠶豆、豌豆、鮮筍、黃魚、萵苣、鰣魚、螺螄、鮮蝦、霉豆腐、烏米飯等等,這一時節田里種的、河里游的、廚房里做的基本都包含在內,可謂不一而足。老南京人分得更細,“三鮮”分作“地三鮮”“水三鮮”“樹三鮮”,兩派說法不同,一派認為莧菜、蠶豆、蒜苗是“地三鮮”,鰣魚、白蝦、茭兒菜(野生茭白)是“水三鮮”,枇杷、櫻桃、楊梅是“樹三鮮”;另一派認為莧菜、蠶豆、豌豆糕是“地三鮮”,螺螄、河蝦、鰣魚是“水三鮮”,櫻桃、青梅、香椿頭是“樹三鮮”。總之,對于“三鮮”的說法眾說紛紜,各有道理。
入選“三鮮”的標準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為求個好彩頭,比如蠶豆又叫“發芽豆”,吃它是為了討個“發”字的吉利,又比如莧菜煮完后湯水發紅,喝它能夠“紅”運當頭?;二是為了開胃生津,比如青梅、杏子等,盛夏時分正是酸甜脆爽的時候,多吃些能夠祛除暑氣,緩解倦怠與疲勞,避免生病?;三是純粹的時令美食,過了夏天就再也品嘗不到這般滋味,比如各類河鮮,錯過了就只能等來年。至于烏米飯、霉豆腐等,則與地方風俗相關,權且不表。
與江蘇相比,上海人的“三鮮”就簡單許多,有兩種主流說法,一說是青梅、酒釀與鮮蛋,另一說是櫻桃、蠶豆與竹筍。部分地方的“三鮮”會與江蘇的更貼近,比如崇明地區會“吃青頭”,也就是綠色的食物,包括螺螄、青梅、蠶豆、鴨蛋、烤鳳尾魚、竹筍,算是“三鮮”的延伸。

古時上海地區的“三鮮”就更加明確了,《上海縣竹枝詞》中記載“麥蠶吃罷吃攤粞,一味金花菜割畦”,說這“三鮮”是麥蠶、攤粞與苜蓿。麥蠶不是蠶豆,而是一種用麥子制成的小食,人們將灌漿階段的麥子研磨成粉,加入白糖后蒸制,出爐的食物色澤青綠、口感脆韌,與蠶豆近似,故被稱作“麥蠶”;攤粞是用苜蓿嫩芽(草頭)制成的小食,將它與米粉混合,
攤成餅狀,用油煎至金黃,《滬城歲時衢歌》里說它“味甚香脆”。此外,還有用苜蓿與芋頭制作的名為“攤菜”的煎餅,也是古時一道不可錯過的美食。不過,這些美食如今都已經見不到了,如果您有興趣,可以在家里試著做做看,感受一下古人在夏季的吃食,也是種難得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