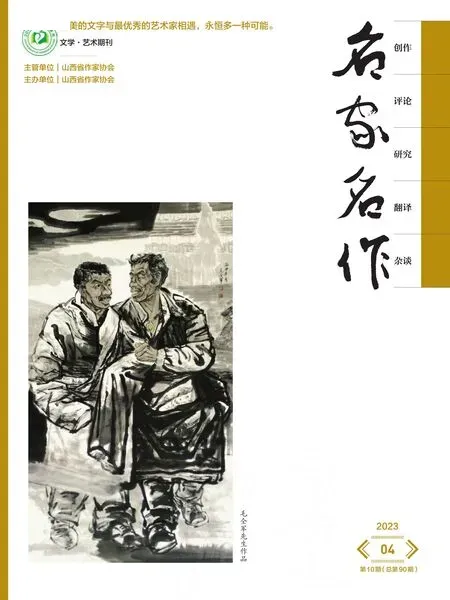欲望燃盡等待之夜
——精神分析視域下《小團圓》的欲望言說
田 雨 崔家駒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譜系中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一生的創作涉及小說、散文、電影劇本等多種文體,還有文學論著和書信集存世。《小團圓》是張愛玲創作于1975年的長篇小說,2009年2月由宋淇之子宋以朗將其出版。《小團圓》力圖將小說中有關女性情欲書寫、墮胎敘事及主題意旨等問題,與相關的傳記資料聯系起來。張愛玲曾在往來書信中表示,“《小團圓》是寫過去的事,雖然是我一直要寫的”,可見這部小說于其內心之分量。學界一般將其視為小說“自傳”,但與其說《小團圓》是一部虛構的“自敘傳”,不如說它寫的是小說主人公九莉經歷張愛玲人生匯成的“歷史的重寫”,其中既涵蓋對昔日回憶的溫存,又飽有今日冷眼的張看。
精神分析理論家齊澤克曾指出,“重寫歷史”時,“我們恰恰是在制造符號性現實,即發生于過去的、早已遺忘的創傷性事件的符號性現實”[1]。在《小團圓》中,這種創傷以“欲望”的形式歸來、分化,又“由欲入情”死于“等待”這一恒久的意象之中,形成一個含義復雜、指向曖昧但意蘊豐富的復雜意義結構。
一、“親族”與創傷——《小團圓》中的對情感之欲望
在《小團圓》末尾,九莉突然想到孩子問題:“她從來不想要孩子,也許一部分原因也是覺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會對她壞,替她母親報仇。”這種經歷自然與九莉本人的孩童經歷相關,而由這種認識使她的思緒飄到“《寂寞的松林徑》”“之雍”則極有余味,更何況這場夢能令她“快樂了很久很久”[2],但“大考”的噩夢更占據其生活,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征兆”,即拉康的“被壓抑物的回歸”產生欲望的想象。作者通過展現九莉意識流動中的“癥候”將其潛意識的形態浮現出來。
劉思謙教授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中指出:“不過她主要是寫那種自己做不了主的婚姻。”[3]婚姻與親族情感的“不團圓”是張愛玲小說中的重要元素,甚至是情節推動的動力之一。但回歸于張愛玲其身,來自父母、親族婚姻的“不團圓”成為其童年焦慮甚至“實在界”創傷的對象。而這種童年的創傷分外重要,書中流動的“欲望”就產生于“銷毀”這種符號性殘余的隱性過程之中,也許這正是張愛玲最終沒有對宋淇口中“第一、二章太亂”[1]進行刪減的原因。所以,對其童年隱傷、父母在欲望結構中的位置進行考察是異常重要的,甚至服務于小說的敘事核心本身。
不同于小說《茉莉香片》、散文《私語》等中出現過的“蠻橫”“易怒”“怪異”的“遺老父親”形象,《小團圓》中的父親雖然依舊是一個危險的“他者”,但其威勢已遠稱不上“大他者”。九莉在柴房中發燒時做夢,“不禁想起閻瑞生王蓮英的案子,有點寒森森的……跟乃德在一起,這一類的事更覺得接近”,其父親想象伴隨著愛的期待與危險的“死亡驅力”,同時這種關系其實也與隱藏的欲望勾連。張愛玲將其等同閻瑞生案件聯系,實則暗示兩者之間存在的巨大“溝壑”甚至可以與赤裸的“金錢/肉體交易”關系相關,影射其溝通既存在一種“欲望”交換性質,又存在某種“本體化風險”,而拉康“父名”背后來自“父權親情”卻在被九莉的“身體想象”里被意外消解,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結構性“缺位”。
而缺位的“大他者”則由母親蕊秋“補位”,我們可以發現這組“母女”的關系曖昧。在母親于牌桌上輸掉八百港幣后,“一回過味來,就像有件什么事結束了”[1],錢的“輸去”與“對母親的愛”的消失對等,背后也存在一件“情感貞潔問題”,即母女之愛的“貞潔”問題:九莉對母親的支持伴隨成長而被消磨,這種消磨的原因不在于兩人生活的疏離,而在于九莉認為母親對其的情感不等,她隱藏的痛苦與仇視源于對母親的“愛”,而且“感情用盡了就是沒有了”。這使得九莉對母女之愛理解的異位,而后來將“男胎”沖進馬桶時感受到的“恐怖”,也無疑包含著與蕊秋“母女關系”的“回聲”,這也是一重“鏡像”。
可以發現,“愛”的欲望在九莉與親族的生命關系之間反復“燃燒”,將含情脈脈的目光燃盡,化為難言的蒼涼,化為對“對體”的恐怖,成為“美夢”般的“夢魘”。
二、“皮膚濫淫”與“意淫”——《小團圓》中的“欲”與“淫”的維度
《紅樓夢》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中,警幻仙姑曾向賈寶玉闡述“淫”的分類:“如世之好淫者……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4]即“物質性欲望”與“精神性欲望”,而《金瓶梅》中也有關于“本錢”的討論。作為“蘭陵笑笑生”與曹雪芹的學習者,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延續了這種二元的“欲望”模式。
《小團圓》較張愛玲早期的作品,其中不乏明顯突出的“皮膚濫淫”描寫,這種書寫橫亙于九莉的親族與愛情之間,同時多以苦澀作為底味。
首先是對親族的描寫,也存在多組“物質性欲望”。存在于親屬間的多組“不倫”,例如蕊秋與簡煒的“曖昧”等,其實深刻影響其后代的“欲望”觀念。九莉與九林聽余媽“講古”談論“神話”中的“兄妹亂倫”,古老的背德神話以一個“凝視者”的身份出現,化作虛無縹緲的幻象客體,構成一種持續的“凝視”,同時傳喚出一種古老的激情與生命,使得他們“不朝九林看”“他當然也不看她”[2],但同時這一“神話”的“露”又反而在倫理中造成“隔”,將兩者之間的關系“異化”,阻礙“愛”的傳達,成為兩者兄妹關系之間永遠的“屏風”,也象征著一種“愛”的“禁欲”——“親情”下“物欲”的永不到達。但同時,“禁止”與“在場”是一體兩面的關系,來自真實界的“執爽”也通過與其相悖的“禁欲”指令產生。
其次,在九莉與邵之雍的愛情交往中也存在一系列“物質性欲望”的描寫。其中有一則格外引人注意:“獸在幽暗的巖洞里的一線黃泉就飲……她是洞口倒掛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遺民,被侵犯了,被發現了,無助,無告的……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難忍的愿望里:要他回來,馬上回來”[2]。這段精妙的比喻關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暴露的恐怖”,九莉嘗試通過邵之雍給予的“痛苦”確認身體的“存在”,避免內心中焦慮與恐怖的“能指”被發現,她需要一種“補足物”。雖然這種補足中含有“一夫多妻”的痛苦,但她依舊咽下了這種苦果,同時接受了男性背后的經濟、文化權利,這種“交換”毫無疑問是“物質性”的。申明這點并非否認九莉對邵之雍存在“精神愛情”,而是指出:在情感之外,九莉絕非“男權”肆意“玩弄”的對象,至少在物質層面她始終以其“主體”體驗為綱。承載這種“痛苦之浴”,亦是九莉處于生活的“無奈”,但其中也包含一種“以弱克強”的“利用”主張,這種“物質性欲望”的描寫中隱藏著女性深切的“本體化誘惑”與“身體自覺”。
九莉與邵之雍等人自然也存在“精神性欲望”,但其與“比比”的情感則更為“特異”。在兩者的“女性情誼”之中,九莉對其則有超乎尋常的依賴,這種投射也使得兩者的接觸超過了“符號化禁區”,產生一個更接近于“想象界彌合”的情感空間:既可“共枕眠”,也有“共患難”。這種描述也使得這種行為被“純潔化”“理想化”,營建了一個與“九莉”守望相助的“有情”形象,令人想到馮夢龍于《情史》中提出的“情教”模式,達到所謂“精神情愛”的理想空間,形成一種超越性的“精神性欲望”范例。
三、由欲入情——《小團圓》中的“原樂”與“等待”意象
許子東教授曾指出:“這些人倫關系雖然奇特甚至‘畸形’,卻在某種意義上連接了《海上花》的傳統倫理精神與今天中國的現實道德困境。”[5]
《小團圓》中的一個經典問題就是——“欲望”與倫教文化的沖突。無論是九莉、蕊秋抑或是邵之雍都處于直視“欲望”的“實在界”恐怖之中,符號的剩余時常以“欲望”問題“回歸”,一種于“無力”而肇始的“等待”情緒就蔓延于全文。
回到《小團圓》中貫穿全書的“大考之夢”,一種有時間限定的“期限”橫亙于“欲望”與“實現”之間,在小說中不斷以“父母離異”“情感沖突”“戰爭”等各式各樣的面目出現。齊澤克在《斜目而視:通俗文化看拉康》中曾以“西西弗斯神話”厘清“需求”“要求”“欲望”,指出“欲望”背后的“循環”模式。而這種循環的“欲望”營造了一種永恒的“等待”,也是九莉焦慮的底色,亦是“原樂”的不可實現。
邵之雍與盛九莉婚書中的“歲月靜好,現世安穩”[2]其實正是題目中的“小團圓”,也是九莉“欲望”最直接的投影,或者說是“原樂”的異形。而這種“團圓”不斷被打斷,化為恐怖的“等待”。這種“等待”也同樣可以在《茉莉香片》結尾聶傳慶“等待”再次見到言丹朱的“恐怖”、《封鎖》中呂宗楨“等待”這段“封鎖”的結束、《連環套》結尾霓喜“等待”借助下一個男人改變生活等處看到。這不能不說是張愛玲小說中極其重要的元素,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主題”,這種“等待”由欲望始,又由欲望的消磨為終。
張愛玲曾指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2]其實也從另一個層面承認了其作品與個人的距離極近,用新近理論言說的話:《小團圓》毫無疑問是一部關于張愛玲與其作品序列的“元小說”。其“元”既體現于張愛玲將過往眾多情節“復現”與“重寫”,組織成一個完整的“生命系統”,這一“系統”又與其“真實家史”相連;同時,其“元”也指《小團圓》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張愛玲人生的“原樂”,同時概括出其恒久的“等待形象”,將“蒼涼的手勢”由“文學指涉”轉化為一種“生命言說”,這種深入的“暴露”亦是張愛玲多次對本作的“自毀”傾向的重要原因。
而這種“遠近之間”就產生了文學曖昧的空間,正如法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家馬舍雷在《文學分析:結構的墳墓》一文中所言:“實際上,作品就是為這些沉默而生的。”[6]在張愛玲的言說與沉默中“欲望”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學敘述,不類同于“曲筆”,亦并非“直言”,而是在有無之間產生與真實的距離。而這種“距離”與“疏隔”使得讀者只能在霧中窺伺寫作者的虛影,又不同“私小說”中完全重合的距離。《小團圓》中的虛構與真實如同園林回廊般曲折,峰回路轉、別有天地,頗有《閑情偶寄》中園林“取景在借”[7]之法。而這種文學景深,反而又使得讀者窺伺的欲望與作品內部紛繁復雜的“欲望書寫”構成一個相互觀望的空間,從而呼喚一種新的文學觀看方法的產生,而檢閱“欲望”、展示其結構、回向更隱秘的心理結構,正是張愛玲小說的“妙法”。
四、結語
劉思謙教授曾于《張愛玲〈小團圓〉中的“胡張之戀”——兼談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一文中如此結尾:“她是知足的。愿她在另一個世界里有安寧與歡樂。”[8]張愛玲在《小團圓》一書中營造了一個詭譎奇幻的“欲望城國”,傳遞著復雜而精致的“個體言說”。通過這一言說,我們不僅走進了張愛玲的生命深處,還完成了對其人生的私人化“檢閱”。這種有距離的“凝視”與“窺伺”,猶如靜聽張愛玲在爐邊的“私語”:我們陪伴她在又一個等待之夜,輕咀濃茶,相顧無語,目送“欲望”與時間燃盡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