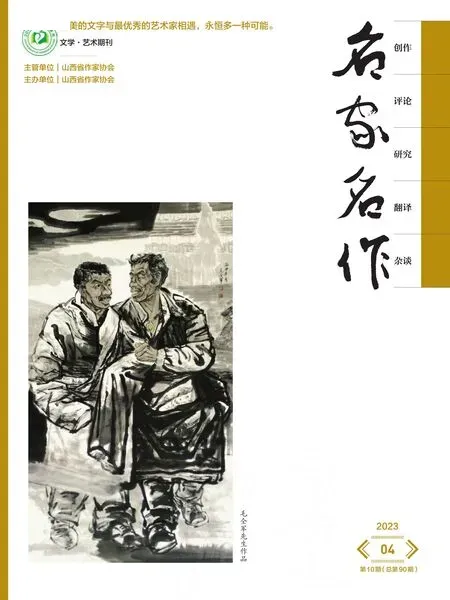敦煌飛天的隱喻
——應用哲學工具的探詢
王 屹 李 驊
一、敦煌飛天的符號哲學
敦煌石窟中飛天形象的豐富程度在世界和中國佛教石窟寺中是獨一無二的。在敦煌莫高窟現存的492個洞窟中,幾乎每窟必有飛天,常書鴻先生在《敦煌飛天》大型藝術畫冊序言中指出飛天造型“總計4500余身”。敦煌飛天自身所攜帶的多元文化基因與其獨特的文化象征早已成為敦煌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飛天”在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最早記錄見于北魏時期的《洛陽伽藍記》:“有金像輦,去地三尺,上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云表。”①龔云表:《詩心舞魂:中國飛天藝術》,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從飛天的神話傳說來看,飛天本身顯著體現出人類兩大符號體系,即圖符與聲符的復合,即便是以圖案形式出現的飛天依然具備音樂的圖符化表達特征。
“符號”一詞的古希臘含義是“被扔到一起的東西”,現實中則是古希臘人在交往中所使用的一種信物,如一分為二的銘牌在受委托雙方使者手中合二為一時,則表明其可信性。《說文解字》中“符”的釋義為:“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本意為古代朝廷傳達命令或調兵將用的憑證,雙方各執一半,以驗真假。以哲學視角的符號來探究敦煌飛天美學意義的真實性與具體性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因為對敦煌飛天美學含義的解讀不能僅僅停留在表象的審美直觀,或孤立的飛天個體化剝離,須知符號只有存在于整體中才是有意義的,其所承載的“信”才有可能被主體所接納。符號學是研究事物符號的本質、符號的發展變化規律、符號的各種意義以及符號與人類多種活動之間關系的學科。20世紀初,瑞士作家、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了符號學基礎系統。20世紀20年代,德國哲學家卡西勒提出了符號形式的哲學(美學符號論),認為人類的一切文化現象和精神活動,如語言、神話、藝術和科學,都是在運用符號的方式來表達人類的種種經驗,藝術是符號的語言,是特殊形式的創造,即符號化了的人類情感形式的創造。
如果說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那么敦煌飛天所攜帶意義的感知共性恰恰可以表現為敦煌飛天作為符號表象多樣性的意義歸屬。符號主要體現為聲音符號與圖案符號兩大類,是人類主體能動性、創造性的集中體現。敦煌飛天并非存在于現實之中,但其本身源于客觀的現實世界。敦煌飛天并不是僵化的符號呈現,而是一種具有共同意義的多樣化存在,也就是說一種具有共同意義的圖案以豐富的表現方式實現了敦煌飛天符號的高度一致。敦煌飛天的豐富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主體對符號自身表達多樣性的認知,這種意義普遍被人類的經驗所接納,形成跨文化認知的普遍意義。因此,敦煌飛天所體現的符號就體現為一種意義共同性基礎上的符號多樣性表達。敦煌飛天表象的豐富性不只是簡單審美的需要,而是符號意義表達的重要哲學手段,這種哲學手段以人類共同經驗為意義歸屬,是敦煌飛天符號對主體意義價值的高度凝結與自然流露。
敦煌飛天是由符號元素組合成的符號集合體,其主要元素包括人物形象、衣飾、人物持握物品等,需要注意的是,這幾種構成敦煌飛天的符號基礎元素同樣也是敦煌壁畫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基本構成,并不能保證敦煌飛天的“飛”。然而可以保證“飛”的符號元素,例如翅膀或羽毛并沒有出現在敦煌飛天符號元素的主要構成之中。這不同于公元3世紀之后融合了古希臘羅馬藝術、古印度藝術與波斯藝術的犍陀羅藝術中的帶翅膀的天人,也不同于中國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中身有羽翼的仙人。《論衡·無形第七》對這種仙人形象的描繪是:“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于云則年增矣,千歲不死。”從符號認知角度來看,直接將自然符號象征進行組合從而形成新的意義附加是多種文化藝術所共有的基本方式,例如距今5000多年的瑪雅文化中的圭形神柱上所刻畫的帶翅創世神、公元前6世紀波斯宮殿石刻藝術中肩生雙翼的波斯之神等。羽人(神)的形象變化是一個由人獸混雜逐漸向人格清晰的發展過程,例如良渚玉器中常見的人、獸、鳥三者合一的圖騰形象,到了夏商時期則體現為人類形象更為明顯的帶翅羽神,而到秦漢時期則形成了具有顯著人格化特征的羽人。在敦煌壁畫中同樣存在不少帶有翅膀的羽人形象,例如莫高窟249窟(西魏)窟頂西坡就描繪有長耳獸面、臂生雙翼、下身著犢鼻褲的回首向須彌山中飛奔的羽人形象。從符號表達角度來看,這種有翅而不飛、似人更類獸的形象描繪是符號曲折表達意義的生動體現,符號元素“翅膀”并沒有完全表達其應具有的意義——“飛行”,亦不能將此等形象等同于飛天,呈現為符號與其意義承載的矛盾與統一。從符號構成角度來看,飛天形象沒有翅膀符號——不能飛;沒有羽毛符號——不能飛;沒有攜帶火焰噴射等反重力系統符號——不能飛;也沒有借助繩索、鋼絲等物懸掛。從敦煌飛天所具備的符號元素來看,飛天是人的形象——人沒有飛行能力;飛天擁有美麗的衣飾——衣服和飾品不能飛;飛天持有各種樂器——樂器不能飛;飛天有飄帶和花——飄帶和花可以飄但不能飛……然而敦煌飛天無翅無羽,在不使用“翅膀”等飛行符號或元素的狀態下卻體現出強烈的空間動態,以自由的飛行姿態翱翔天際。宗白華在《中國古代的繪畫美學思想》一文中指出:“由于把形體化為飛動的線條,著重于線條的流動……這從漢代石刻畫和敦煌壁畫(飛天)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線條不一定是客觀實在所有的線條,而是畫家的構思、畫家的意境中要求一種有節奏的聯系。”①宗白華:《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從哲學角度來看,這是一種主體追問符號象征的抽象與真實具象的意義統一,是一種美學的價值承載與表達的統一,同時也是對符號自身表達邊界限制的突破,難道“飛”就一定需要翅膀嗎?
二、敦煌飛天的哲學表達
敦煌飛天的哲學無關敦煌飛天的古代創造者是否懂得“哲學”這樣新奇的字詞,也不需要勞神費力地給他們冠以什么“洞窟哲學家”之名,正如人類的哲學思維并不是因為有了“哲學”這個名詞才存在的。《老子》指出:“名可名,非常名。”意思基本是指作為“道”的“常名”并不是可以說得出來的“名”。陳鼓應在《老子今注今譯》中引用了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中的話:“真知是否可以用名言來表示!這是中國古代哲學中的一個大問題。道家以為名言不足以表述真知,真知是超乎名言的。”②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4。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從未依靠榜題(名言)來證明自己,這與敦煌壁畫中供養人詳細的名稱題記形成鮮明反差,對供養人大書特書的題記往往占據顯著位置,特別是唐代洞窟中供養人畫像由小型開始向大型多幅轉化,其往往位于洞窟醒目之處,榜題內容詳細;至于五代時期的瓜州曹氏供養人畫像更是以巨幅家譜形式出現,原本卑微的供養人愈發高大起來,成為宣赫家族功績的見證。供養人的以“名言為實”與敦煌飛天的“無名自在”形成具有強烈哲學意蘊的主體感知,形成主體經驗世界的邊界突破,敦煌洞窟壁畫中的飛天與供養人形成了一種“名可名”與“非常名”的生動圖像信息傳達與對比,由此所構成具有整體觀的飛天與供養人之間的關系連接具有顯著的哲學含義。供養人與飛天到底誰是“真實”的?雙腳站在大地的供養人與漫天翱翔的飛天是什么關系?“名言為實”與“無名自在”是否是超乎“名言”的“道”的一體兩面?這種聯系對敦煌文化的意義何在?
敦煌飛天不是僵化的文化符號,也不是孤立的審美對象,敦煌飛天的多元文化融合現象是敦煌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體現。文化的多元融合不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模糊整體觀層面,文化的多元融合如果不能進入具有歷史特性的“元”文化研究,則既缺乏科學依據又易于淪為玄而又玄的語言游戲。從這個角度來看,敦煌飛天多元文化融合的哲學觀察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表象的單純美學探究與抽象的哲學辭令,而應當運用實證哲學的理論和觀點對敦煌飛天文化元素進行“元”層面的科學分析,從“敦煌飛天是什么”的形下猜測進入“敦煌飛天為什么”的哲學追問,從而接近敦煌飛天與現實土壤之間的真實連接。對敦煌飛天從整體的模糊描述進入細致具體的哲學“元”文化實證是十分必要的,符號化的敦煌飛天元素同樣為這種敦煌飛天“元”文化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哲學工具。哲學的“元”文化研究是挖掘與弘揚“敦煌精神”“飛天精神”的重要理論來源與科學依據。
作為一門科學的系統論,由美籍奧地利人、理論生物學家L.V.貝塔朗菲于1932年提出,認為開放性、自組織性、復雜性、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衡性、時序性等是所有系統共同的基本特征。而系統思想則源遠流長,如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古代樸素整體觀則是現代系統論的一條基本原則;對中華傳統文化與哲學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易經》具有顯著的系統思維模式,陰與陽之間的對立統一、相互依存、互為轉化的思想蘊含著豐富且復雜的系統論思想。敦煌文化的多元性、融合性與代際性是敦煌文化系統的基本內核,也是認識敦煌文化系統的重要理論視角之一。敦煌文化的發展不是單一創造者的不斷重復,而是體現為文化積累與創造性延伸,是具有過程性的繼承與創新,這種文化的系統性在敦煌壁畫中同樣得以體現,表現為壁畫內容所描繪的宗教、技術、政治、法律、經濟活動、社會風俗、日常生活等文化系統的各個方面,從系統論角度觀察敦煌飛天是對敦煌文化系統完整性加以確認的重要哲學方法之一。從探究手段來看,哲學“元”文化探究與系統論思想相互結合是加深敦煌飛天內涵探詢的重要哲學方法之一,符號學則為探詢敦煌飛天的意義、敦煌的價值追問提供了具體的理論工具,是敦煌飛天藝術形象向“飛天精神”深化的認識過程。
敦煌石窟保存有自十六國時期至元代的飛天形象,跨越十幾個朝代,歷經千余年。十六國時期的飛天形象與西域石窟特別是龜茲石窟中的飛天形象基本雷同,造型粗獷、線條狂放、色彩濃烈,四肢僵硬無動感,帶有鮮明的西域風格,稱之為“西域飛天”;北魏晚期到西魏的敦煌飛天形象受到道教與“魏晉風度”的審美影響,表現出南朝的畫風特征,飛天造型修長、眉清目秀,長袖當空,飄逸靈動,體現出西域畫法與中原審美相融合的顯著特征;隋代敦煌飛天形象的裝飾性進一步加強,出現了數目龐大的“團體飛天”,如莫高窟第427窟(隋代)窟頂一周繪有飛天形象108身,體現了一種昂揚向上、昌盛繁華的精神風貌;唐代飛天在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日趨成熟,飛天形象描繪更加生動,畫面布局生動,以吳道子風格為代表的中原畫風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繪畫手法也更加豐富多樣,西域鐵線描與中原蘭葉描等技法相互融合,形成了成熟的飛天藝術形象。由于佛教經典中對于飛天形象的描繪相對模糊,這恰恰為經變畫中的飛天藝術形象的豐富多彩提供了巨大的創作空間。馬克思提出“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深刻地揭示了創造和需要的關系。歷代飛天藝術形象的描繪者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將強烈的藝術感情與表達傾注于對飛天的描繪之中,從而使飛天這一藝術形象成為承載更多意義與表達的藝術載體,呈現出一種敦煌“飛天”雖飛于天然則近人的深刻思想內涵,形成一種具有哲學色彩的“飛天的隱喻”。
三、敦煌飛天的哲學實踐路徑
敦煌文化藝術是不斷發展的,以相對靜態方式存在的敦煌石窟藝術也不應將其視為凝固不變的歷史遺存,敦煌文化的動態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動態發展,第二是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性參與,總體來看則是人與自然相互融合的動態歷史發展過程。因此,所謂敦煌文化藝術的“復原”大約也只能是某種再創造,融合與發展才是敦煌藝術文化的不懈追求。
敦煌文化藝術體系是敦煌“元”文化相互交融的體現,是敦煌藝術“元件”的具體體現,這種敦煌藝術元件是需要實證分析的具體科學,如果缺失了對敦煌文化藝術“元件”的實證科學研究,則極易導致某種類似于經院哲學的玄思與空疏,也可能導致研究方法的單一與禁錮,從而造成敦煌藝術文化遠離現實土壤的孤芳自賞。從敦煌飛天層面來看,如果將敦煌飛天完全飄浮在空氣中,只用單一的視角來觀察,則很難窺見敦煌飛天背后的隱喻。敦煌飛天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與高度的藝術審美價值,而且體現了系統整體性的文化生態構成,表達了一種追問與探詢、矛盾與統一相交融的哲學意蘊。
敦煌文化是人類精神勞動的創造性產物,是人類賦予對象世界意義,從而確證人自身的重要見證,這種敦煌文化的哲學根基深植于現實,體現了豐富性、包容性與開放性。敦煌飛天所包含的符號學、“元”理論與系統論認知是探詢敦煌文化意義與價值的哲學工具,是揭示敦煌飛天背后人對人自身基于現實性的自我創造與價值追問,展示了人基于現實的理想性與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