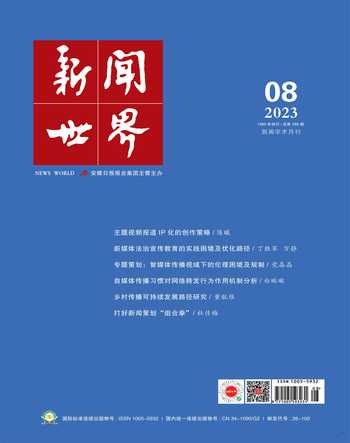進化與異化:ChatGPT浪潮下虛擬主播再思考
張艾末 陳婉婷 韓凱琦
【摘? ?要】ChatGPT的浪潮席卷而來,其所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將對虛擬主播領域產生巨大影響。本文從ChatGPT與虛擬主播的結合入手,對虛擬主播的發(fā)展進行深度思考,明確ChatGPT等新技術的嵌入能夠使虛擬主播更加人格化,為用戶提供定制化、場景化的個性服務,同時,描述了進化過程中存在的人對機器的身份困惑、傳播雙方溝通失效以及交往異化的困境。最后對ChatGPT浪潮下虛擬主播的未來發(fā)展做出了展望,并指出人機協(xié)同是虛擬主播未來的進化方向。
【關鍵詞】ChatGPT;虛擬主播;人機協(xié)同;人格化;身份困惑
一、問題緣起:ChatGPT能夠為虛擬主播注入“靈魂”
2022年11月,美國人工智能公司推出了一款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Cha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瑞銀集團的研究報告顯示,僅推出不到3個月,ChatGPT的活躍用戶就已經(jīng)達到約1.23億。作為一款由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智能內容生成新應用,ChatGPT具備語義理解與文本創(chuàng)作的能力,其生成文本與人類的認知、價值觀等有較高的匹配度,能夠與用戶進行長時間、連續(xù)性的深度對話。ChatGPT的出現(xiàn)代表著AI技術能力的提升,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著陸將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新的發(fā)展機遇。
愛因斯坦曾言,“智慧的真正標志不是知識,而是想象力。”不同于過往的分析式人工智能,ChatGPT對個體需求的識別更加精準,能夠對其加以合理想象。目前,已有多家國內外互聯(lián)網(wǎng)科技公司宣布接入ChatGPT等模型,進一步研究其與虛擬數(shù)字人的結合與應用,促進虛擬數(shù)字人領域的發(fā)展。將這一語言模型嵌入虛擬主播,既可以高效助力其語言能力的提升,又能夠使其以更細膩的方式觸達用戶內心、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推動虛擬主播行業(yè)的升級與進化。但與此同時,在科技迅猛發(fā)展的實踐背后,隱憂和機遇共存,最初用于提升傳播效能的人工智能合成技術不斷發(fā)展,卻也讓人機交往互動過程中的種種困境開始浮現(xiàn)。ChatGPT等新技術與虛擬主播的結合,同樣帶來了技術異化的風險,這也提醒著我們應當在新興技術發(fā)展的浪潮下不斷進行再思考。
二、進化:技術賦能虛擬主播銳化升級
(一)人格化:作為“交流者”進行深度對話
“人格化”意味著將人格特質賦予某一物體或抽象事物及現(xiàn)象,人格化傳播能夠增加傳播者的親和力,使傳受雙方建立起一定的情感聯(lián)結,提高人際之間溝通的親切感,從而更好地提升傳播效果。不同于以往作為工具性的信息傳遞者而存在,經(jīng)過人格化后的虛擬主播成為了具有溫度、擁有個性的“真實”的“人”,更加符合受眾期待,能夠滿足受眾的現(xiàn)實需求。作為率先接入ChatGPT技術的科技公司之一,世優(yōu)科技成功推出了虛擬主播“慕蘭”,并在抖音直播間開啟了一場其與觀眾的互動。在ChatGPT的加持下,面對觀眾拋出的不同問題,慕蘭始終對答如流、精準表達,與觀眾進行了一場高質量的情感互動。這種定制化與充滿個性的人格開發(fā),使得虛擬主播不再只是后臺內容的簡單傳達者,而是成為擁有更加智能的思考能力、對話能力的信息處理者。通過深度理解和學習人類的語言,虛擬主播能夠真正像人類一樣聊天、交流,與用戶進行深度對話,提供給其更加親切和互動性更強的服務。
(二)定制化:作為“數(shù)智人”提供個性服務
隨著智能技術不斷發(fā)展進步,可以說虛擬主播的定制化趨勢已經(jīng)初步顯現(xiàn),以多維度的受眾畫像為基礎,虛擬主播可以為不同用戶提供不同的個性化服務。例如,北京廣播電視臺打造了側重于服務用戶方向的智能交互虛擬主播“時間小妮”,在北京時間APP中為用戶播報新聞、講解知識,能夠24小時不間斷地提供交互問答等服務。而在更強的AI技術加持下,虛擬主播所提供的個性化服務可以更加細膩和精準,例如,齊魯晚報·齊魯壹點的技術團隊就在其已有的采編業(yè)務中加入了ChatGPT算法模型,在壹點智能創(chuàng)作平臺中,記者能夠使用ChatGPT一鍵生成相關內容,輔助新聞稿的撰寫,在壹點用戶運營的微信群中,嵌入了具有ChatGPT互動能力的機器人“小壹”,能為用戶提供更精準有效的對話,在節(jié)省人工運營成本的同時,大大提升了私域用戶群的服務能力。可以預見,在不斷更新的AI智能技術的基礎上,未來的人機交互水平將持續(xù)提高,作為擁有“AI大腦”的“數(shù)智”主播,還將繼續(xù)為用戶提供更加精準化、智能化的個性化服務。
(三)場景化:作為“陪伴者”融入用戶日常
《“十四五”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規(guī)劃》提出,“要深化人工智能、虛擬現(xiàn)實等技術融合,拓展多領域應用,支持實體消費場所建設數(shù)字化消費新場景。”當前,虛擬數(shù)字人技術已經(jīng)在多種不同的應用場景中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在金融行業(yè)出現(xiàn)的有浦發(fā)銀行虛擬數(shù)字員工“小浦”,在文旅領域出現(xiàn)的有秦腔藝術推薦官“秦筱雅”等。對于虛擬新聞主播來說,除了新聞播報,還可以拓展出在醫(yī)療、教育、黨政等不同領域和場景的業(yè)務,例如在教育領域,搭載了ChatGPT的虛擬主播能夠生成自然語言教育的內容,與學生進行互動,優(yōu)化其學習效果;同時,也可以開拓出虛擬主播在單身經(jīng)濟、銀發(fā)經(jīng)濟等新應用場景的發(fā)展方向。將ChatGPT引入虛擬主播,能夠豐富其情感體驗,模擬出不同現(xiàn)實場景中的社交行為,使其能以“陪伴者”的身份在多種場景中與用戶進行深度情感互動和交流。也許在未來,虛擬主播可以借助技術根據(jù)不同場景需求靈活調整自身外形外貌、人格特征等,使共處場景更加生活化,從而深度融入用戶的日常生活,讓用戶都能獲得專屬于自己的虛擬伙伴,滿足其對親密關系和情感陪伴的需求,在不同場景中都擁有穩(wěn)定、豐富的情感體驗。
三、異化:虛擬主播進化中的困境浮現(xiàn)
(一)身份困惑:虛擬主播的可靠性廣受質疑
盧卡奇認為,在商品邏輯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轉化為商品之間的客體關系,這種關系有著“虛幻的客觀性”。這提醒著人們,在技術不斷進化的今天,除了關注其為我們帶來的福音,也不能忘記思考提供技術的源頭。在人機互動交往過程中,受眾會產生“與我交流的對象是誰?”的疑問,始終存在著對作為交流主體的虛擬主播的身份困惑。對于虛擬主播來說,其進化的思路可以分為兩條:一是通過模仿實現(xiàn)擬人化,二是通過背后的技術編程實現(xiàn)個性化。無論哪種進化方式,受眾對于虛擬主播都會存在“真”或“假”的判斷,這種判斷或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人們對虛擬主播的關注焦點。隨著技術的更新迭代,越來越多嗅到資本紅利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開始不斷拓展“主播”的業(yè)務范圍,與ChatGPT、元宇宙等熱點相接合,而同樣作為交流主體的受眾卻并不能意識到虛擬主播的產品屬性,更無法感知自己與虛擬主播的一次次交流與互動具有多大的商業(yè)價值。正如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所提到的,媒介營造出了“超真實”世界,超真實的編碼時刻包圍著我們,使人逐漸喪失了對現(xiàn)實與幻象的辨別能力。對于虛擬主播來說,其應用的全過程都帶有人為選擇的色彩,一旦控制技術背后的人用惡性價值觀去訓練它,將會產生負面影響,再加上人們難以辨別這種披著唯美外殼的惡,那么將會為人類帶來無法想象的災難。
(二)溝通失效:口語傳播的靈韻逐漸消逝
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書中,本雅明提出“靈韻”這一概念,指出了傳統(tǒng)藝術是不可復制、獨一無二的,因而原作本身散發(fā)著帶有生命氣息的“靈光”,即“靈韻”,而機械復制技術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種靈韻,使原作的藝術形式失去了原真性、獨特性。當虛擬主播所具有的“仿真的形象”“有趣的靈魂”與“獨特的個性”被不斷復制與量產時,受眾很難不產生審美疲勞,口語傳播交流中真實的靈韻也會隨之消失。由于ChatGPT等語言模型的應用提供了既定的語言播報與反應的文本,在面對受眾對觀點、態(tài)度的需求時,虛擬主播也只能按照設定好的邏輯與其交流,而無法根據(jù)受眾情緒的起伏與之產生共情,即便擁有一定的共情能力,也意味著在其背后以ChatGPT為代表的新技術已經(jīng)測算、提取出了一種平均情緒,這體現(xiàn)出了人機互動中雙方交流地位的不平等。與此同時,在播音主持創(chuàng)作與傳播過程中,有聲語言與無聲非語言相輔相成,為口語傳播中的有效交流感提供支撐,而虛擬主播不具備真人主播能夠靈活運用內外部技巧進行語言表達的能力,更難具備包括體態(tài)語、物化語等在內的無聲非語言表達,因而會在表達與對話中因缺少交流感導致溝通失效。即便在未來,技術進步能夠賦予虛擬主播對無聲非語言及時捕捉與靈活運用的能力,但其中人性的缺失會讓口語傳播缺乏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導致其藝術“靈韻”無法彰顯,溝通失效的困境或將一直存在。
(三)交往異化:受眾的主體性受到威脅
在哈貝馬斯看來,要想使會話順利進行、達到理想狀態(tài),就要和“系統(tǒng)”保持相對獨立,而實際情況是會話總會受到“系統(tǒng)”制約,具體表現(xiàn)為會話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并不平等。盡管虛擬主播背后的技術研發(fā)者正在致力于通過改善技術來增強其感知與互動能力,但在虛擬主播與受眾交流對話的情境中,受到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術設置的“系統(tǒng)”制約,“人格化”后的虛擬主播仍舊會使受眾感受到互動的假象。在“系統(tǒng)”的設定下,作為技術主體的虛擬主播在人機會話過程中不斷憑借機器邏輯去感知,而與此同時,作為現(xiàn)實主體的受眾很難不被機器的思考方式影響,于是理性思考在工具邏輯的影響下逐漸被擱置,主體認同被虛擬認同所取代,造成“交往異化”。當意識到被新技術深度影響甚至改變后,受眾對技術的態(tài)度會由最開始接觸時的好奇轉為恐懼和憂慮,感受到技術對人主體性的壓迫。除了技術邏輯帶來的恐慌,同樣會讓人產生恐懼的原因還包括虛擬主播日趨逼真的外部形象,正如日本機器人專家森昌弘(MasahiroMori)在“恐怖谷理論”中強調的,當機器人在外表、動作上與人類相似到一個較高臨界點,人們的反應會從認同變?yōu)榕懦狻⒖謶值确聪蛐睦怼.斨饾u感受到嵌入ChatGPT后的更加智能的虛擬主播在不斷對人進行深度模仿,甚至感覺技術奪走了受眾掌控自己身體的權利時,受眾將對自身的主體性產生懷疑。
四、討論與啟示:對未來虛擬主播發(fā)展的再思考
在ChatGPT浪潮的席卷下,虛擬主播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成為了學界與業(yè)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搭載上ChatGPT技術的虛擬主播正在煥發(fā)著新的生機,通過深度理解學習人類的語言和思維而越來越接近真實的人,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異化的風險,ChatGPT等技術的加持使得原本的人格化傳播主體陷入了技術黑箱,原本存在于傳播主體之間的交流互動空間也變得狹窄。人創(chuàng)造出虛擬主播的初心,是為了實現(xiàn)對真人之間的交流互動進行模仿或還原,原本是為了追求人的主體性,但在實際過程中卻陷入技術異化的困境,屬于人的主體性正在逐漸喪失。
對ChatGPT浪潮下虛擬主播的未來發(fā)展之路進行反思與展望,實際上是在對人機互動關系進行再思考。馬克思交往理論認為,回歸交往的本質應該是人在交往中的主體性得到充分發(fā)揮。這提醒著我們在技術不斷進步的過程中應當關注人文價值的體現(xiàn)與貫穿,以人為本地創(chuàng)造和建構虛擬主播的人格、促進虛擬主播的進化,例如在情感傳遞上,除了利用ChatGPT等增強虛擬主播對情感的識別與認知,還應當充分挖掘其對情感的“觸發(fā)”能力,使受眾能夠在其引導下主動地生成自身的、屬于人的情感。與此同時,還應當關注技術與人文精神上的協(xié)調統(tǒng)一,平衡好傳遞信息與聯(lián)結情感之間的關系,既要不斷探索虛擬主播更高階的離身與具身認知、交互能力,更要注重主持傳播過程中語言與表達的藝術性,重視交流中“靈韻”的體現(xiàn)。正如哲學家馮象所說,“機器必須理解人類美好生活的含義”。換言之,我們必須教育機器。作為主體的人類創(chuàng)造了人工智能,亦有責任教育好人工智能,充分發(fā)揮好人的主體性,引導著技術向上向善發(fā)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ChatGPT與虛擬主播的結合將會更加緊密,其運用場景與實踐領域也會愈加廣泛,這意味著人類與機器之間的關系從來不是一場博弈,而是協(xié)調互補、耦合共生。一方面,人類擁有天生的主體性與適應性、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與藝術性以及復雜的溝通能力,這使得人在傳播活動中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而與此同時,人類會出現(xiàn)的緊張情緒、知識盲區(qū)以及生理極限等正常反應也決定了人類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虛擬主播憑借技術的不斷更新與嵌入能夠保持高效率、高準確率的工作,避免了很多傳播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但隨之而來的亦有關于技術黑箱、工具理性等帶來的負面影響問題。這都說明人與機器各有長短,需要進一步明確人與虛擬主播的工作邊界,用機器的智能高效彌補人類的弱項,而保留合乎人類價值與意義的活動,形成各顯其長、各得其所的人機互動關系。因此,伴隨著ChatGPT的浪潮,在未來虛擬主播的發(fā)展之路上,不斷優(yōu)化人機協(xié)同既是進階邏輯的起點,更是進化過程永恒不變的追求。
參考文獻:
[1]趙瑜,李孟倩.擬人化趨勢下的虛擬主播實踐與人機情感交互[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3,45(01):110-116.
[2]於春.傳播中的離身與具身:人工智能新聞主播的認知交互[J].國際新聞界,2020,42(05):35-50.
[3]宋存杰.虛實之間:虛擬主持人的發(fā)展歷程及思辨展望[J].傳媒,2022,379(14):52-55.
[4]高貴武,趙行知.進化與異化:AI合成主播的言說困境[J].新聞與傳播評論,2023,76(02):5-16.
[5]崔潔,童清艷.解構與重構:“人格化”虛擬AI新聞主播再思考[J].電視研究,2022,387(02):62-64.
[6]喻國明,蘇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傳播革命與媒介生態(tài)——從ChatGPT到全面智能化時代的未來[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05):1-10.
(作者:均為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數(shù)字媒體與智能傳播方向2022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