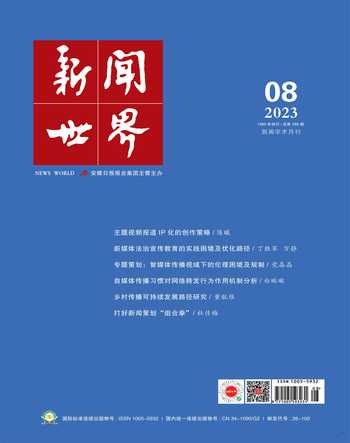互動儀式鏈視角下播客節目創新傳播研究
周玉蘭 項雯雯 戴安娜 呂張蕾
【摘? ?要】知識經濟的盛行使播客迎來了新一輪發展,作為國內首檔聲音戀愛綜藝節目,《我們會見面嗎》成為中文播客內容創新切口。本文就該節目如何形成完整的互動儀式鏈進行分析解讀,并從商業模式、節目內容和傳播方式等方面入手,探討播客的未來發展。
【關鍵詞】我們會見面嗎;播客;聲音;互動儀式鏈
播客(Podcasting)誕生于2004年,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李立等從構詞法的角度出發,認為“播客”的“播”展示的是其視聽媒體屬性,“播客”的“客”彰顯的是其內容生產傳播者的主體性,因此可將“播客”視為能適應不同技術條件和社會環境、使用語境的數字視聽自媒體。[1]目前,中文播客市場以對談類為主,內容缺少突破創新,《我們會見面嗎》從形式上破局,以聲音戀愛綜藝開發具有更豐富、更多樣的內容形態的音頻節目。
一、《我們會見面嗎》節目概述
近年來,我國綜藝節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但節目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內容上缺少突破。《我們會見面嗎》是國內首檔聲音戀愛綜藝節目,一反傳統戀愛綜藝的視覺引導,回歸最原始方式,僅以聲音進行敘事。3位男生和3位女生,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通過線上聲音交流,經歷節目組設置的幾輪約會后,選擇是否要見面。
節目以“正片+花絮+節目組reaction+聲音小紙條”的形式呈現,“節目組reaction”是一種創新模式,擁有上帝視角的主持人通過向觀眾提供更豐富的信息,帶領觀眾挖掘節目中的細節,一起體驗“磕糖”的快樂。“聲音小紙條”是觀眾主動參與節目互動的形式,以語音表達對嘉賓的祝福和對節目的建議。這樣的形式和內容顛覆了以往戀愛綜藝節目的形態,為當下信息過載的人們提供了新出口。
二、互動儀式鏈理論
在涂爾干儀式研究基礎上,歐文·戈夫曼結合個人研究提出了“互動儀式”的概念。從微觀層面出發探討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互動問題,他指出并非只有宗教儀式具有情感能量,社會活動中的表演儀式亦如此。蘭德爾·柯林斯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出版了《互動儀式鏈》一書,他指出,互動儀式的核心機制是“高度的相互關注,即高度的互為主體性、高度的情感連帶以及通過身體的協調一致、相互激起參加者的神經系統結合在一起,從而導致形成了與認知符號相關聯的成員身份感;同時也為每個參加者帶來情感能量,使他們感到有信心、熱情和愿望去從事他們認為道德上的容許的活動。”[2]
柯林斯提出,互動儀式由四個要素組成:一是兩人及以上聚集在同一空間,二是對局外人設限,三是將關注點放在同一對象上,四是共享相同的情緒或者情感。在互動儀式產生后主要會有四種儀式結果:群體的團結、個體情感能量、代表群體的符號和道德感。
三、《我們會見面嗎》中互動儀式的構成要素
(一)兩個人以上虛擬在場:聲音傳遞,緩解視覺空間過載
互動儀式鏈強調互動儀式中的“親身在場”,但在數字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下,可以打破時空限制實現虛擬在場,拓展了這一理論的應用空間。《我們會見面嗎》將聽眾聚集于播客平臺,解決了視覺空間過載的問題,使人們的注意力可以暫時從電子屏抽離,緩解視覺疲憊。
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提到,“如果坐在黑暗的屋子里談話,話語就突然獲得新的意義和異常的質感。”[3]戴上耳機,收聽播客,就好像走入了一間黑暗的屋子,旁聽屋內的談話。《我們會見面嗎》的聽眾談到,很多時候就像在聽酒館隔壁桌相親對象的竊竊私語。節目“旁聽”的是一對對未曾謀面的年輕人的約會過程,聽眾通過想象延伸空間,實現虛擬共同在場。
就第二個要素“相互影響”而言,節目主理人隨易認為:“耳朵比眼睛離心更近。”在僅用耳朵進行信息接收的過程中,大腦會更活躍的思考,聽眾通過男女嘉賓的語氣、用詞、笑聲、試探或回縮,借助自己過往接觸異性的經歷,在個體情感的影響下對雙方形象及互動過程產生想象。網絡音頻節目突破了聲音轉瞬即逝的缺點,突出了聲音的時間連續性和伴隨性,明確、完整的語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節目所要傳達的內容邏輯,從而使節目和聽眾之間相互影響。
(二)對局外人設限:用戶參與,聲音文本意義再創造
互動儀式過程中通過特定內容設置局內人局外人界限,從而保證局內人互動的一致性,以提升信息的傳播效率。作為一檔聲音播客,《我們會見面嗎》更多的是通過線上的無形界限來區隔局內人和局外人。
數字賦能下,聽眾擁有了更強的主動性。在節目的互動儀式過程中,聽眾主動參與節目互動,形成區隔其他局外人的界限。除常規的正片,節目還設置了“聲音小紙條”板塊,以收集聽眾對于節目的想法。這些來自不同聽眾最真實的聲音,會使其他聽眾更有親近感,產生情感共鳴。
此外,評論和點贊也是節目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我們會見面嗎》評論區中的積極反饋,能夠引發聽眾思考,提高節目的影響力。“時間戳”功能突破了傳統互動的滯后性,讓情緒更針對性地停留在了某個時間點,使作品產生更多情感交際。節目所在平臺小宇宙APP的精準點贊功能有效化解了朋友圈點贊的空洞化,除了以點贊來表達對節目的支持外,通過每期節目音頻進度條上反映用戶點贊量的“熱度直方圖”,直觀反映節目的起伏節奏。
作為純聽覺媒介,播客對聽眾的專注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導聽眾,激發聽眾主體性,積極互動以促進聲音文本意義的再創造,形成了聽眾與節目的正向連結。
(三)共同關注對象:分享擴散,交流共筑興趣社區
處于互動儀式中的人要對某一事物形成共同的關注,在交流過程中,使參與者之間確認關注焦點。這是發展共享符號的關鍵,符號可以作為區分其他群體的標志,在符號的討論中不斷提高群體認同感。
根據《2021播客聽眾調研報告》,我國播客用戶多屬于中高收入人群。小宇宙APP專注播客社區服務,首頁的“發現”每日根據用戶標簽推薦3條優質的內容,并不斷精細化用戶畫像,提升信息的契合度,推動興趣社區的打造。
在《我們會見面嗎》中,將“聲音戀愛綜藝”作為聽眾共同關注的焦點,聚集一批本身對“戀愛約會”話題感興趣的聽眾,并通過節目主創們豐富的知識面增加節目的吸引力,在他們擁有的星座、塔羅、MBTI等知識帶動下,復盤節目中男女嘉賓的約會過程,知識普及和專業分析的結合與聽眾產生更強力的互動,加固興趣社區的邊界。在節目后程,基于推薦而對節目產生興趣的聽眾以點贊、評論的方式不斷加入興趣社區。一些對于往期節目所傳達價值具有認同感的聽眾,實際已經處于興趣社區的同溫層中,具有更強的認同感,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興趣社區也有更強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作為思維載體,播客所具有的專業、豐富、垂直的內容能滿足人們的知識獲取需求,在低經濟成本的前提下,聽眾可以更自由地選擇收聽的頻率和深度,讓其逐漸演化為年輕人交流觀點的場所。
(四)共同的情緒:情感陪伴,創新音頻社交模式
當受眾針對共同關注的焦點交流輸出、情感互動后,處于儀式中的人們會更強烈地感受到情感的共享,成員間關系不斷加固,完成互動儀式。這其中,“情感能量”是重要驅動力。播客伴隨性的特征使其與空間和環境有著極高的適配性,根據互動反饋,《我們會見面嗎》是大多數聽眾通勤、居家和戶外活動的陪伴者。其本身的關鍵詞“戀綜”“反效率”“反經驗”聚合了一批興趣和價值觀基本一致的聽眾,不同于傳統物理空間上的社區,數字社會下通過媒介技術在線上打造的虛擬社區,打破物理距離,能夠使受眾在其中獲得滿足感和心理依存感。
《我們會見面嗎》本身也是節目組的情感表達出口。主創人員來自各行各業,在“節目組reaction”這一板塊中,三位主創人員的討論話題廣泛,通過聲音傳達的觀念與聽眾產生情感共振,逐步引導聽眾展開深入思考,甚至是通過點贊、評論等形式提出自己的觀點,進行情感互動。
《我們會見面嗎》的嘉賓和聽眾都保持匿名,在沒有現實暴露的風險下,可以更放松地表達自己。產生的交流基本上是基于節目內容的精神交流,不受現實社會關系的影響,這種純粹的交流容易形成高共鳴的互動,從而創造良性的社交場域。節目組還開通聽友群,延伸互動渠道,聽眾可以根據個人意愿加入,和思想契合的聽友進行實時深度交流,通過社群實現社交空間的拓展,共筑情感共同體。
四、播客未來發展路徑
(一)商業模式的探索,保障創作者穩定收益
與國外成熟的播客體系相比,國內播客還未形成規模效應,商業化程度不高。目前中文播客的主播多出于個人興趣投身于節目的制作,但因精力有限,無法保證播出頻率,影響聽眾的體驗感。
商業化是高質量內容產出的保障,播客需要成熟的商業模式,以可觀收入推動主播職業化。目前,在喜馬拉雅等主流音頻媒體的影響下,用戶已經有了知識付費的意識,但只能作為商業化路徑之一,難以支撐播客內容創作者進行持續的高質量內容輸出。
要抓住聲音媒介陪伴性和情感性的特質,獨特的平臺社群屬性使聽眾對于平臺的商業化并不抵觸,廣告商業組織IAB和愛迪生對播客廣告所做的研究表明,相較于其他平臺的廣告,受眾對于播客節目的廣告有更大的接納度。國內已有播客變現的實踐,如《忽左忽右》在內容建設上采取定制化路線,為不同企業定制節目,也有出版品牌看到了播客的優勢,主動出擊把握發展主動權,如后浪出版社的《后浪劇場》。
播客要積極與品牌達成廣告合作,把握“耳朵經濟”的優越性,以高黏性、高轉化性為切口,推動播客廣告的發展,為內容制作者提供經濟保障,從根本上推動商業化發展,不斷擴大播客的影響力。
(二)傳播內容多元化,打破圈層化
作為舶來品,播客的受眾多為知識分子,節目主要是泛文化類的兩人對談或多人對談。對于聽眾而言,一方面滿足自身的求知欲,另一方面通過節目可以快速地找到自己的“圈子”,有利于進行社會交往。但這一高門檻的模式不利于播客的發展,平臺需要創新節目模式,以精彩的內容和多樣的形式,打開受眾市場。將綜藝載體轉移到耳機是一種全新的嘗試,作為國內首檔聲音戀愛綜藝,《我們會見面嗎》成為內容多元化發展的先例。在未來發展中,播客需要抓住能引發人的自主思考這一特點,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更多的突破,逐漸填補國內播客在新聞類、敘事類、深度閱讀類等方面的空白。
學者史安斌在《播客的興盛與傳媒業的音頻轉向》一文中強調播客作為主流媒介和敘事平臺的優勢,他認為隨著5G、智能音箱、智能語音技術的普及,播客將成為下一個全球傳媒業的“風口”。[4]隨著中文播客的快速發展,播客平臺和主流媒體需要加強合作,既能夠填補國內播客平臺權威新聞的空缺,也能夠促進主流媒體將播客作為重要的新宣傳陣地。
(三)突破播客的場景壁壘,注重場景適配性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作為聲音媒介,播客是人聽覺的延伸,具有伴隨性的特質。聽眾對播客的收聽場景有很強的依賴性,如習慣在通勤途中收聽播客的人,一旦進入假期模式,就會很難投入到播客的互動儀式中。
從最初的移動車載場景到現在5G背景下的智能場景,播客需要實現從純物理空間到物理空間疊加虛擬空間的突破。未來,播客需要更重視場景化傳播,通過建立或利用直接的受眾關系來留住聽眾。在內容方面,需要結合傳播場景了解聽眾需求,了解聽眾的興趣愛好,以“個性化”打動用戶,同時也要體現播客本身特色,以多元的精彩內容抓住聽眾。在技術方面,播客需要把握用戶的活動場景,在場景中呈現一定的誘導性。播客平臺需要持續監測用戶場景信息,分析用戶與內容產生互動的方式和原因。從場景入手,激發用戶在某場景下對于特定內容的興趣,激發求知欲。因此,播客在用戶把握自主選擇權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場景化傳播增加音頻消費行為的可能性。
五、結語
在被視覺媒介裹挾的當下,人們的目光再次重新聚焦在以口語傳播為主的播客上。播客既能為聽眾打造小眾興趣圈,進行精準交流,還能為聽眾提供參與感、滿足感,具有較強的用戶黏性。播客放大了聲音伴隨性的優勢,通過聲音的傳遞不斷引導聽眾進行思考、互動,促進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傳播,并提供了顯著的情緒價值,滿足用戶的陪伴需求。目前播客還尚未完善,未來需要在商業模式上繼續探索,把握數字社會下的場景化特征,以多元傳播內容和聽眾形成良性互動,不斷開拓規模。
注釋:
[1]李立,宋錦燕.突破認知困境看播客——從Web2.0時代到5G時代[J].中國廣播,2019(04):15-18.
[2]蘭德爾·科林斯.互動儀式鏈[M].林聚任,王鵬,宋麗君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2.
[3]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 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6.
[4]史安斌,薛瑾.播客的興盛與傳媒業的音頻轉向[J].中國廣播,2018(10):95.
參考文獻:
[1]李靜.美國播客的內容生產和變現分析研究[J].中國廣播,2017(06):23-27.
[2]美國播客市場年入8個億,中國的播客從業者能從中學到什么?[DB/OL].(2021-10-15). https://36kr.com/p/dp1442126641072
771.
(作者:周玉蘭,浙江傳媒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項雯雯,戴安娜,呂張蕾,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傳播學院2022級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