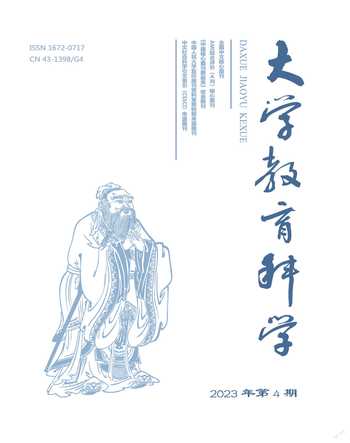文化自信視角下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問題與對策
侯俊軍 蒯文婧 徐航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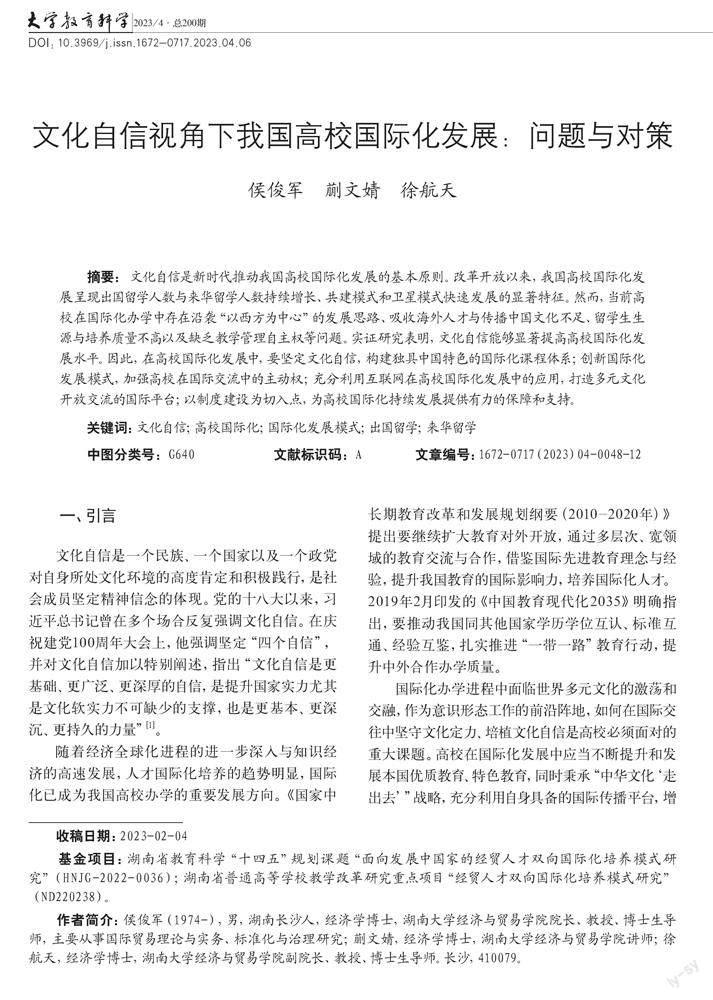


摘要: 文化自信是新時代推動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呈現出國留學人數與來華留學人數持續增長、共建模式和衛星模式快速發展的顯著特征。然而,當前高校在國際化辦學中存在沿襲“以西方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吸收海外人才與傳播中國文化不足、留學生生源與培養質量不高以及缺乏教學管理自主權等問題。實證研究表明,文化自信能夠顯著提高高校國際化發展水平。因此,在高校國際化發展中,要堅定文化自信,構建獨具中國特色的國際化課程體系;創新國際化發展模式,加強高校在國際交流中的主動權;充分利用互聯網在高校國際化發展中的應用,打造多元文化開放交流的國際平臺;以制度建設為切入點,為高校國際化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關鍵詞:文化自信;高校國際化;國際化發展模式;出國留學;來華留學
中圖分類號:G6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3)04-0048-12
一、引言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所處文化環境的高度肯定和積極踐行,是社會成員堅定精神信念的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文化自信。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上,他強調堅定“四個自信”,并對文化自信加以特別闡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提升國家實力尤其是文化軟實力不可缺少的支撐,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深入與知識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才國際化培養的趨勢明顯,國際化已成為我國高校辦學的重要發展方向。《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繼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通過多層次、寬領域的教育交流與合作,借鑒國際先進教育理念與經驗,提升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培養國際化人才。2019年2月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指出,要推動我國同其他國家學歷學位互認、標準互通、經驗互鑒,扎實推進“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提升中外合作辦學質量。
國際化辦學進程中面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蕩和交融,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如何在國際交往中堅守文化定力、培植文化自信是高校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高校在國際化發展中應當不斷提升和發展本國優質教育、特色教育,同時秉承“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自身具備的國際傳播平臺,增強國際影響力。本文基于文化自信的視角,從我國高校國際化辦學模式的發展與演進著手,分析高校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因文化不自信而引致的一系列問題,并提出提升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水平的對策。
二、高校國際化發展的相關研究評述
基于文化自信視角分析高校國際化發展,其相關研究文獻可從高校國際化的起源與內涵、我國高校國際化的發展實踐以及文化自信視域下我國高校國際化的認識三個方面進行綜述。
(一)高校國際化的起源與內涵
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會主席Clark于1980年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國際化”這一概念;國內則是由龔放和趙曙明最早提出[2]。事實上,高等教育國際化歷史悠久,可追溯到古希臘和古埃及的高等教育,具體表現為當時的“跨國”和“游學”[3]。高校國際化屬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范疇。一方面,高校國際化需要依托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大環境和趨勢;另一方面,高校國際化也是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手段之一。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國際大學聯合會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籠統地定義為:“是把跨國際和跨文化的觀點和氛圍與大學的教育工作、科研工作和社會服務等主要功能相結合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變化過程,既有學校內部的變化,又有學校外部的變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還有學校自身的政策導向。”
國內學者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理論層面開展了系列研究。舒志定提出的高校國際化的三層次理論,涵蓋信念系統(認識)、功能系統(結構)以及運動系統(規范),并指出應不斷借鑒世界一流大學在以上三方面的辦學模式,從而改造、完善本國高校體系[4]。有學者將高校國際化歸類為高校職能,指出高校應具備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以及國際化合作這四種職能[5];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高校國際化主要以學術交流為載體,也就是說,不同大學之間進行學術互動、合作是其主要特征[6]。與此同時,劉蘭芝提出全球發展學說,即在高校國際化的過程中,不僅要服從民族和本國利益,而且還需培養具備包容性胸懷的國際型人才[7]。此外,相關學者還從高校國際化的動因、路徑以及國際比較方面展開研究。汪旭輝從經濟、教育、科技等多個維度深入分析高校國際化的原因及其必要性[8];袁本濤和潘一林則以清華大學為例,個性化分析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念以及在國際化合作方面的具體舉措,明確指出應建設適合我國國情的高水平大學[9]。
(二)我國高校國際化的發展實踐
在實踐層面,以2001年11月加入WTO為分界線,可以將2001年之前劃分為我國高校國際化的起步期,之后劃分為快速發展期[10]。在初步探索階段,我國高校的教育開放程度較低,國際化辦學規模小,影響范圍窄[11](P150-155)。這一時期,復旦大學中美法學班、中國人民大學中美經濟學班等中外合作示范培訓班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加入WTO之后,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我國高校國際化快速發展,呈現出多種辦學模式。其中,應用最為廣泛、也是延續至今的經典模式,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其具體指的是本土大學與海外大學、國際研究機構、海外非政府組織或者政府機構開展國際合作研究或者聯合培養項目,包括但不限于國際交換生項目、訪問學者項目、聯合培養項目等[12]。
21世紀初,共建模式轉變為我國高校國際化辦學模式新興的探索方向。共建模式在我國的主要表現形式為合作辦學,其特點是獨立于母體機構且需要取得當地的辦學資質。共建模式的典型代表是2004年經教育部批準成立的寧波諾丁漢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具有獨立校園、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該學校沿用國際化質量評估體系,通過與全球知名高校及企業的密切交流合作,為學生提供海外學習與全球暑期夏令營機會,實現國內外優質高校資源的結合,標志著我國高校國際化進入注重雙邊互動、平等交流的新階段。
此外,國內采用衛星模式、實現“走出去”辦學的高校近年來層出不窮。諸如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北京語言大學東京學院,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衛星模式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海外辦公室、海外分支校園以及海外研究中心等;其特點是擁有獨立的財務核算和管理團隊,但并不獨立于母體機構,與母體機構仍共享認證體系與資源。
共建模式與衛星模式起源較早,是不斷發展完善中的辦學模式,而教育集群模式則是近年來正處于初步嘗試階段的辦學模式,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教育集群模式是將本土與海外的高等院校集聚于某一特定區域,提供公認的學分體系,形成教育集群或教育園區。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政府與紫竹國家高新區共同出資建設的上海紫竹國際教育園區和地處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的蘇州獨墅湖科技創新區均是將產學研結合、通過國際化學術交融開展多樣化人才培養的高校集聚園區。
(三)文化自信視角下我國高校國際化的認識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新時代大學生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其堅守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弘揚傳統文化是增強大學生文化自信的基礎,強化主流文化是增強大學生文化自信的核心,正視西方文化則是增強大學生文化自信的關鍵。一些學者從國家認同這一角度切入,指出高度的國家認同來源于充分的文化自信,認為當下全球化浪潮削弱了大學生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文化自信等,并在此基礎上探索了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礎以及增強大學生文化自信的路徑[13-14]。另一些學者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提出可通過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提升高校國際化水平,并強調文化自信在國際學術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5]。還有學者指出,高校應充分發揮文化課堂的教育主導作用,強化大學生的文化自信;加強新媒體教育平臺的構建,推動網絡在文化自信方面的引導作用[16]。
當前,由于外部環境的復雜多樣性,我國高校在大學文化構成、學術話語權、國際合作交流等方面存在由西方主導的問題。對此,我國高校應以堅定的文化自信為引領,著力進行改革、創新,構建自主話語體系,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打好基石[17-18]。“十四五”規劃提到,我國教育正處在復雜多樣的大環境下,應乘風破浪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具體來說,應堅持教育的對外開放,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教育合作[19];與此同時,應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助力我國高校的國際化發展[20]。孔子學院是高校國際化的典型案例,王坦基于文化自信視角,詳細闡述了孔子學院在外開辦“降速”的原因及其對策[21]。
現有研究顯示,高校師資國際化是高校國際化中較為重要的一環,需要不斷強化教師課程培訓、學術會議等各種國際合作形式,培養開放型人才,提升教育服務水平[22]。除了提高教師的道德、授課以及科研水平,還需增強教師培養學生文化自信的能力,從而建成服務于國家意識形態的教學體系。陳婷婷分析了我國高校國際化過程中文化自信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對策,認為高校應拓寬國際化辦學的廣度和深度,并強化教職工和在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23](P237-238)。此外,在合作辦學的過程中,國內高校應將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合作辦學基本原則。
三、文化自信視角下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的現狀與問題分析
(一)我國高校國際化辦學現狀
整體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最近二十年,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出國留學人口持續增長,規模不斷擴大。由圖1-a可知,2003~2019年,出國留學人口從11.73萬人增至70.35萬人,來華留學人口從7.77萬人增至39.76萬人。同時,出國留學學成回國人數穩步增加,高層次人才回流趨勢明顯。出國留學生在完成學業后,選擇回國發展的比例從25%上升到65%。由圖1-b可知,2003~2019年來華留學生中接受學歷教育的外國留學生占比從32%上升到46%,來華留學生教育結構不斷優化。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03~2019年期間,留學生的來源國也從175個增至205個,國際化交流范圍更廣。
此外,共建模式發展迅速、日趨成熟,中外合作機構不斷增加。中外合辦大學的主要承建方包括地方城市和外方學校,即地方城市提供財政和政策支持,外方學校給予技術指導。截至2020年底,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已達2 332個,其中本科以上的機構和項目1 230個①。中外合辦大學校園主要分布于我國東南沿海區域,依托長三角和珠三角集聚發展。由表1可知,擁有獨立法人辦學資格的10所大學,其學科門類覆蓋廣泛,在校生規模龐大。這批中外合辦大學,主要采用全英文教學,結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以及外方學校的優勢學科,引進一系列延續外方教育模式的學位課程,力求培養高層次人才。
衛星模式近年來快速擴張,為高校國際化辦學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截至2019年9月,我國共計84所高校(來自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境外設立和舉辦了128個辦學機構和項目。①北京語言大學曼谷學院是我國第一個走出國門的漢語教學辦學實體,它的建立標志著我國高校開始從“引進”向“輸出”轉型。除北京語言大學曼谷學院外,我國還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學新加坡研究生院、大連海事大學斯里蘭卡校區、成都中醫藥大學葡萄牙寶德分校、老撾蘇州大學、云南財經大學曼谷商學院等20個符合《中國高等教育境外辦學指南》標準的海外分校[24]。為了宣傳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這些學校大多開設了漢語言文學課程。作為中國大學的海外分校,這些學校多采用英文授課,以“1+3”、“2+2”或全海外分校學習的教育模式培養學生(如表2所示)。
(二)文化自信視角下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存在的問題
我國高校在國際化辦學與發展過程中尚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過程中主要沿襲了效仿西方的發展思路,缺乏堅定的文化自信支撐。傳統的高校國際化發展由西方國家主導,形成的“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定式成為阻礙當前高校國際化良性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照搬英美等國的模式與經驗,導致建立的教育體系與本國國情及教育文化理念匹配度不足。另一方面,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在國際化教育中的主要職能體現為機械性地吸引國際學生進入與知識輸出,而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乏善可陳。西方中心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即表現為英語在國際化交流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雖然單一語言在促進國際溝通合作中具有積極意義,但卻有可能阻礙以多元化為基礎的高校國際化發展,使得非英語國家在參與教育國際化體系時面臨較高的進入門檻。根據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根據需要,可以使用外國語言文字教學,但應當以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為基本教學語言文字。”然而實際上,在現有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中,英語仍是最主要的基本教學語言,直觀體現了我國高校在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對自身文化的不自信。
第二,目前中國高校的國際化辦學整體仍處于起步階段,在吸收海外人才、傳播中國文化方面存在明顯不足。一方面,在經典模式與共建模式下,國內高校在國際文化與理念交流中更多地扮演著被動接受的角色。多數情況下我國與西方國家在高校國際交流中是不對等的,西方國家在共享優質教育資源和體系的同時也在通過知識和文化滲透的方式擴大其意識形態影響[11](P150-155);另一方面,大部分采用衛星模式開展合作辦學的機構依然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境外分校少且師生規模小,需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高校境外合作辦學的教學評估體系和學位認證制度,以便在該模式中更多地扮演主動輸出的角色,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提高我國優質教育資源的國際影響力[25]。此外,少數高校在國際化辦學中過于注重形式而忽視教學資源的深度開發以及教學組織的精細化管理,這也是當前國際化辦學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第三,在出國留學人員與來華留學人員規模均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留學生培養質量與生源質量引起廣泛擔憂。傳統的高校國際化主要基于規模增長的邏輯,存在激進擴張與過度商業化的問題。當全球化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時,國際學生規模持續增長,尚能維系基于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邏輯的教育商品化運行體系,而一旦受到突發事件或經濟下行的影響,使得生源規模下降,那么商品化與激進擴張的發展模式將難以為繼。以新冠疫情為例,由于其導致國際流動受阻以及部分學生支付能力下降,使得在澳大利亞境內學習的國際學生數量大幅減少,對澳大利亞教育產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復蘇帶來嚴重干擾[26]。克服激進擴張與過度商業化形成的潛在威脅,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后發國家推動高校國際化良性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在高校國際化過程中注重知識學習而忽視文化教育。高校國際化是助力多樣文明互鑒和世界共同進步的重要途徑,主要目標在于培養具有國際領導力和跨文化領導力的創新型人才,其中也蘊含著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照本土文化傳承與本國利益的訴求。然而在近些年的高校國際化辦學中,淺層國際化、空心國際化等問題逐步顯現,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在跨國學習時處于孤立狀態,長時間處于由其本國成員所形成的封閉社群內。在這種國際化過程中,學生很難真正融入國際化的環境中,自然也就無法實現深入的跨文化體驗。究其原因,這既與東道國社會環境所形成的屏障有關,也與高校國際化初期形成的制度偏向與路徑依賴有關。
第五,不少國內高校在開展國際化辦學的過程中僅在意經濟收益,一味地被海外高校主導,放棄教學管理自主權[23](P237-238)。這些辦學不主動、過度依賴海外高校的現象,表明我國高校并未完全擺脫對西方國家的教育依附,在與西方國家國際合作交流中處于被動弱勢地位,直接造成國內高校教育資源輸出不足。這些問題反映到學生層面,則是價值取向和政治信念的偏移。例如部分通過交換項目、聯合培養項目送出去的學生,沉浸于發達國家的文化氛圍,而拙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月亮是外國的圓”。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認知相對粗淺,無法分辨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因而未在對外交流過程中自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全球化視野下,大學生能通過網絡快速接觸大量信息,接受的西方文化沖擊也遠遠大于過去。因此,如何在高校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加強對大學生的教育、引導,幫助他們樹立文化自信,避免其在價值取向和政治信念上出現重大偏差,同樣是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文化自信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實證分析
本文中,高校國際化是指普通高等教育機構在教學、科研、管理等方面融入全球化進程,通過國際合作與交流提高辦學水平,拓展辦學視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力的人才等。其中,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與在校人數是衡量高校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鑒于數據的可得性,為了實證檢驗文化自信與高校國際化發展之間的關系,本文使用留學生的在校人數和畢業人數作為衡量高校國際化的指標,選取基于2012~2020年中國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建立分析文化自信程度與高校國際化水平關系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從而進一步分析兩者之間的相關性。
(一)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參考伍德里奇的計量經濟學理論[27],本文建立如下雙對數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該模型在經濟學、教育學等領域被廣泛應用[28-29]。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it為被解釋變量,lnCulManuit為核心解釋變量,X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外貿規模以及交通便利程度),δi為省份固定效應(控制省份層面不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變量),γt為年份固定效應(控制可能存在影響的所有樣本且隨時間變化的不可觀測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本文主要關注系數β1,其含義為外國留學生規模的文化自信彈性,即文化自信每增長1%,外國留學生規模的變化幅度。需要說明的是,高校國際化發展水平是由綜合因素決定的,文化自信只是其中之一。上述實證模型中盡可能控制了除文化自信以外的其他可能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因素,從而使得β1的含義為: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文化自信與高校國際化發展之間的定量聯系。
在指標選取上,核心被解釋變量為各地區的高校國際化發展水平,并且以接受中國教育的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lnGrad)和在校人數(lnCurStu)來表征,這主要基于以下兩點原因:第一,中國尚處于高校國際化發展初期,各地區在接收外國留學生規模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相比于培養質量而言,培養規模無疑是反映各地區高校國際化發展水平的恰當指標;第二,培養質量是綜合性指標,不同學者建立的評價體系可能得出不同的結果,而培養規模是客觀指標,測度標準統一,有助于提高實證研究的可靠性以及不同研究結論之間的可比性。
核心被解釋變量為文化自信程度(lnCulManu),通過各地區人均文化制造業法人單位數量測度。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多樣化文化產品的消費成為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主要途徑。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能夠高度代表各地的文化自信程度。首先,文化產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群眾文化消費的需求,也體現了當地的文化產品供給能力。大規模的文化產品需求與高質量的文化產品供給是培植各地區文化自信的基礎條件。其次,文化產業的發展反映了對當地文化資源的發掘程度。歷經千年發展,中國各地均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豐富的文化遺產。相比于其他商品,文化資源具有不可移動的顯著特征。如果能夠充分利用本地文化資源,開發周邊產品,則必然會形成規模龐大的文化相關產業。在文化及相關產業中,文化制造業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2020年規模以上文化制造業企業營收占所有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營收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因此,人均文化制造業法人單位數量能夠合理表征各地的文化自信程度。此外,有學者認為文化產業的發展能夠反哺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提升也將成為產業發展與升級的新動力[30];也有學者認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協同并進是增進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31]。結合上述文獻,本文認為文化產業發展一定程度上能夠近似代替文化自信水平,因而實證分析中得到的結論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控制變量包括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以及交通便利條件,分別通過對數形式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nPerGDP)、人均進出口總額(InPerTrade)和人均客運量(InPerPas)表示。以上變量可能同時影響文化自信程度與國際化發展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導致實證分析出現偽回歸問題。
以上變量中外國留學生數據來自《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13-2021年)》,文化制造業法人單位數據來自《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2013-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以及其他省級數據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13-2021年)》。變量的描述性分析見表3。
(二)基準回歸結果與討論
表4展示了模型①的回歸結果。第(1)~(3)列的被解釋變量為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其中第(1)列的解釋變量僅包含文化自信程度,第(2)列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第(3)列進一步加入了省份層面的控制變量。在逐步加入變量的過程中,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始終保持正向顯著,表明在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的條件下,文化自信程度越高的省份,其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越多。根據第(3)列的系數可知,文化自信程度每提高10%,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將提高2.78%。
第(4)~(6)列的被解釋變量為外國留學生在校人數,回歸中加入的解釋變量分別對應于(1)~(3)列,其中核心解釋變量依然始終保持了正向顯著,表明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控制變量中,在控制了文化制造業的規模之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不再顯著,代表交通便利水平的人均客運量的系數在第(3)列中顯著,而在第(6)列中不顯著,表明其影響作用不穩定。代表對外開放水平的人均進出口總額始終顯著為正,且系數較大,表明當地的對外開放水平是影響其高校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文化自信在推動高校國際化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地應當充分挖掘當地的文化資源,提升文化產業的發展規模,為當地提供高質量的文化產品。此外,對外開放是高校國際化的基礎,決定了高校國際化的發展環境。在國際化建設過程中,高校要提高對校區所在地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視程度。
(三)影響渠道檢驗
基準回歸的結果表明,文化自信對于高校國際化具有顯著影響,然而其具體的作用路徑尚不清晰。根據文化的傳播特征和高校的發展規律,結合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本文認為文化自信主要通過提高互聯網使用程度以及提升制度質量來促進高校國際化發展。本文接下來將對這兩條影響渠道進行實證檢驗。
1.提高互聯網使用程度渠道
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是信息傳播的重要途經,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通道。擁有較高文化自信的區域,一方面能夠通過互聯網展示自身文化底蘊、引領新型文化交流,使其特色文化得到認可;另一方面,其借助電子商務、跨境電商等互聯網平臺,能夠開拓更多市場,從而擴大文化產品及價值觀的影響范圍。因此,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高互聯網使用程度。隨著對互聯網運用的不斷深入,不同民族、國家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增強,文化背景不同的學生對彼此國家的理解與認同也隨之提高,從而為高校國際化的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為了檢驗上述影響渠道,本文參考心理學研究領域常用的中介效應模型構建如下模型[32]。
其中,M表示中介變量,Z表示相關控制變量,其他符號與模型①中的含義相同。首先,將中介變量替換為人均互聯網域名數量(lnDN),用以表示互聯網的使用程度。表5第(1)列報告了模型②的回歸結果,第(2)列和第(4)列報告了模型③的回歸結果,第(3)列和第(5)列報告了模型④的回歸結果。
第(1)列的結果顯示lnCulManu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文化自信能夠提高互聯網的使用程度,而第(2)~(3)列的結果則表明,互聯網使用程度能夠顯著提高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也即促進高校的國際化發展。第(4)~(5)列以外國留學生在校人數為被解釋變量,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以上分析驗證了互聯網使用程度是文化自信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渠道之一。
2.提升制度質量渠道
提高制度質量是加快高校國際化發展、提升我國高校國際競爭力的必然要求。文化自信是推動各地區開展制度創新、提升制度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擁有文化自信的地區更善于從豐富的歷史傳承中獲取制度資源。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形成了內容豐富、流派眾多的管理與制度思想體系。從歷史底蘊中不斷汲取制度建設的智慧,是完善制度體系的堅實基礎。歷史發展表明,在面對國際趨勢及其他地區的優秀制度時,文化自信更堅定的地區更加傾向于保持開放的胸襟與兼收并蓄的價值取向,從而使自身的制度體系更加多樣化,最終形成高效、高質的制度環境。以高質量制度體系為基礎,不同文明交流時所面臨的文化差異、理念沖突與制度壁壘等問題將得到妥善解決,從而消除高校國際化發展的主要障礙。
表6同樣以模型②~④為基礎,將中介變量替換為樊綱指數(非國有經濟發展指數,PrivateEco)①,表示制度質量。從第(1)列可知,文化自信顯著提高了地區制度質量,而制度質量也能顯著提高外國留學生畢業人數與在校人數。上述結果表明,制度質量是文化自信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又一渠道。
以上分析表明,文化自信對高校國際化發展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即文化自信程度較高的地區,通常高校國際化程度也更高。此外,互聯網發展程度與地方制度質量可能是文化自信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兩個渠道。因此,在推動高校國際化發展時,要進一步提高文化自信,并且加強對互聯網技術的應用,重視制度建設。
五、文化自信視角下推動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對策
文化自信視角下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的主要目標在于實現中外不同教育理念、不同教學內容的匯聚,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堅定文化自信,從而培養高素質國際化人才,為我國優秀文化、智慧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動力,進而提升我國高校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
(一)推動文化自信教育,構建獨具中國特色的國際化課程體系
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要以文化自信為引領,發揮文化資源優勢,打造符合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需要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校園文化、教育資源、課程體系等。首先,我國高校應當進一步增強自身的文化軟實力,積極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校風、學風,塑造具有中華文化底蘊的校園氛圍。其次,要挖掘本國的優質教育資源,將更多的中國元素納入到國際化辦學體系中。如在聯合辦學的高校里積極推行以普通話和漢字為基本教學語言和教學文字、結合中國歷史文化打造特色課程體系等。同時,應注重培養精通漢語的國際留學生,由他們向其同胞介紹中國文化,積極輸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而更有效地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傳播中國聲音。最后,高校應以不同民族、文化的共通之處為載體,打造獨特的國際化通識教育課程,開拓學生眼界,助力民族團結與文化融合。
(二)創新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增強高校在國際交流中的主動權
在高校國際化秩序深刻調整的變局中,中國高校應敏銳感知時代趨勢,抓住機遇建立與文化交流相適應的中國高校國際化發展模式。具體來講,高校應該積極探索除經典模式、共建模式和衛星模式等現有模式以外的其他國際化辦學模式,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契機下,應以“中華文化‘走出去”為戰略目標,通過滿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校國際化的需求,向沿線國家輸出優質教育資源,打造出既具有中國特色又符合全球潮流的中國高校國際化模式。以在地國際化為例,相比于傳統的學生跨國流動,在地國際化通過引入世界名校本土辦學,或者與國外名校在本國合作辦學,將國外名校的優質教育資源轉移至國內,既能滿足國內學生的“留學”需求,也能吸引其他國家優秀留學生的到來,從而降低傳統高校國際化可能導致的意識形態風險。
此外,我國高校國際化要堅持質量導向,積極探索“走出去”與“招進來”同步發展的國際化道路。一方面,在國際化過程中,我國高校不能一味地依賴海外高校,而需加強教學管理主動權,在增強自身實力的基礎上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積極參與國際文化交流與互鑒。另一方面,對待國際上的優質文化與教育資源,應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通過引進并吸收海外先進辦學理念與優質教育資源,提升本國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水平,通過“走出去”將我國的高等教育深度融入國際體系,從而提高我國在國際高等教育領域的話語權。
(三)加強互聯網技術在高校國際化中的應用,打造多元文化開放交流的國際平臺
實證結果顯示,互聯網的使用程度是文化自信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渠道之一。因此,高校首先應充分利用互聯網搭建國際化交流平臺,加強國際高校之間交流合作,增強全球化視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比如,高校可以利用社交媒體和在線溝通工具,如微信、Facebook、Zoom等,與國際高校建立聯系,加強交流和合作。通過這些平臺,本國學生可以與海外學生和學者進行互動,分享經驗和知識,同時也能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增強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其次,高校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國際學生招募和交流平臺,為海外學生提供便捷的入學申請和交流渠道。這不僅有助于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我國高校學習,還能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之間的交流和互動,拓寬學生全球化視野。
此外,高校可以通過推廣互聯網技術在校園里的應用,建設數字校園,打造智能化校園。譬如在學習上,可以創建在線選課、網絡課程、在線作業和在線圖書館等數字化平臺,為留學生提供更加全面優質的學習資源;在生活上,通過完善智能餐廳,智能教室等便捷服務,使得留學生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適。通過提高國際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體驗感,增強其對中國高校教育環境和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四)以制度建設為重點,提高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制度水平
實證分析表明,地方制度質量是文化自信影響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又一渠道。首先,地方政府應該加強制度建設和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優化服務質量,增強政策執行力度,為高校國際化發展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其次,地方政府應該加強與高校的溝通協作,了解高校的實際需求和困難,積極協助高校解決各類問題,共同推進高校國際化發展。此外,地方政府應該建立高校國際化發展的評估機制,定期對高校國際化水平進行評估,制定相應政策和措施,為高校國際化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地方制度質量與高校制度質量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優秀的地方制度可以為高校國際化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時發揮高校高質量的制度優勢也可以為地方培養更多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高層次人才、積聚科技和創新力量。因此,高校應以制度建設為重點,通過建立完善的留學生制度,提升學校的整體競爭力和聲譽。同時,制度建設也能夠幫助高校更好地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和挑戰,使國際化發展更加穩健和可靠。通過優化國際化發展的制度水平(例如完善留學生管理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提高校園安全等措施),為留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提高留學生的安全感和滿意度,推進高校國際化發展。
六、結語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證明了中華民族擁有強大的文化創造力。在當今世界文化大發展與碰撞中,堅定文化自信是我國國際形象和地位高層次躍升的前提條件和基本要求。本文梳理了我國高校國際化的發展歷程和基本模式,揭示了我國高校國際化發展中存在的文化不自信現象,提出了提升我國高校國際化水平和國際影響力的路徑,即高校國際化發展過程中需積極發揮文化自信的價值引領作用,以文化自信為基石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具體來說,中國高校應堅定文化自信,形成獨具特色的國際化發展模式,積極探索學生“走出去”與“招進來”同步發展的高校雙向國際化道路,拓寬高校國際化發展的寬度和深度,提高辦學自主性。在國際化辦學過程中,要重視互聯網信息技術在高校國際化發展中的應用,打造多元文化開放交流的國際平臺與良性機制,加強制度建設,確保高校國際化發展有序推進。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J].求是,2019(12):4-12.
[2] 龔放,趙曙明.大學國際化——高等教育發展趨勢[J].高等教育研究,1987(04):29-35.
[3] 陳學飛.高等教育國際化——從歷史到理論到策略[J].上海高教研究,1997(11):57-61.
[4] 舒志定.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特征與啟示[J].全球教育展望,1998(03):55-59.
[5] 陳昌貴.國際合作:高等學校的第四職能——兼論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8(05):11-15.
[6] 魏臘云.對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哲學反思[J].理工高教研究,2002(03):33-34,39.
[7] 劉蘭芝.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趨勢[J].學術交流,2002(04):151-155.
[8] 汪旭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動因與模式——兼論中國大學國際化的路徑選擇[J].遼寧教育研究,2007(08):90-93.
[9] 袁本濤,潘一林.高等教育國際化與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清華大學的案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9(09):23-28.
[10] 陸小兵,王文軍,錢小龍.“雙一流”戰略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反思[J].高校教育管理,2018(01):27-34.
[11] 李琳璐.突圍與創新:高等教育國際化辦學模式在中國的演進與發展[J].教育評論,2021(04).
[12] Knight,Jane.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J].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5(02):107-121.
[13] 杜蘭曉.當代中國大學生國家認同教育的路徑探析——基于文化自信的視角[J].思想教育研究,2012(12):99-102.
[14] 徐國正,劉文成.新時代大學生愛國主義教育:挑戰、原則與路徑[J].大學教育科學,2022(03):102-109.
[15] 何芳,都寧.高校外語教育國際化與中國文化對外傳播[J].高教發展與評估,2019(06):44-49,109-110.
[16] 任佳偉,孫向宇,劉靜.論新時代大學生文化自信的培養[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05):137-141.
[17] 孫成武.文化自信與新時代大學精神的培育和發展問題探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3):119-124.
[18] 黃建軍,黃嬌.構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話語體系[J].中國高等教育,2019(01):45-47.
[19] 朱旭東,劉麗莎,許芳杰,李愛霞.論我國“十四五”教育發展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基于復雜多樣的國內外環境分析[J].中國教育科學(中英文),2021(02):31-44.
[20] 于紅波,孫百才.論我國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應把握的“中國特色”[J].大學教育科學,2021(04):39-45.
[21] 王坦.文化自信:高等教育國際化應有的精神立場——以孔子學院為例[J].高教發展與評估,2020(04):34-44,108-109.
[22] 潘駿.高校師資國際化與教學變革探析[J].教育與職業,2014(26):84-85.
[23] 陳婷婷.文化自信視域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路徑探析[J].中外企業文化,2022(01).
[24] 徐墨.中國高校境外辦學本土適應性研究[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22:61-67.
[25] 林金輝,劉志平.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探新[J].教育研究,2008(01):43-47.
[26] 廖霞.后疫情背景下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戰略及其走向——基于《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戰略2021-2030》的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22(11):42-51.
[27] [美]伍德里奇.計量經濟學導論:現代觀點[M].費劍平,林相森,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50-163.
[28] 邢春冰.教育擴展、遷移與城鄉教育差距——以大學擴招為例[J].經濟學(季刊),2014(01):207-232.
[29] 袁知柱,張小曼.會計信息可比性與企業投資效率[J].管理評論,2020(04):206-218.
[30] 曾麒玥.文化自信的實現路徑——習近平的文化自信觀探究[J].社會主義研究,2017(04):9-14.
[31] 項久雨.新發展理念與文化自信[J].中國社會科學,2018(06):4-25,204.
[32]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4(05):731-745.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HOU Jun-jun? KUAI Wen-jing? XU Hang-tian
Abstract: Cultural confidence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shown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ed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as well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and satellite models.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such as Western-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insufficient absorption of overseas talents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low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ivation and student source, and a lack of autonomy in teaching management.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cultural confide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novat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and strengthen the initiative of universities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fully util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multicultural open exchange, tak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rovide strong guarantees and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studying abroa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責任編輯? 李震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