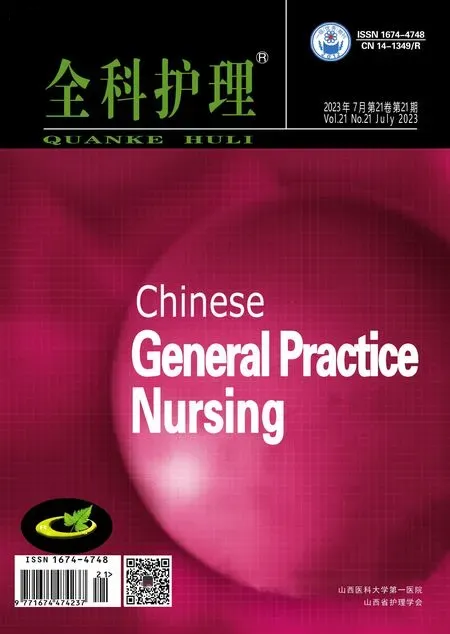炎癥性腸病病人創(chuàng)傷后成長研究進展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種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慢性炎癥性疾病,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CD)。該病多發(fā)于15~30歲的青年人,臨床表現(xiàn)為腹瀉、腹痛、便血等癥狀,易發(fā)生梗阻、穿孔、癌變等并發(fā)癥。IBD反復發(fā)作,目前尚無法治愈[1]。因在職業(yè)生涯高峰患病,常給社會生產力和個人生活質量帶來較大影響。目前,我國公眾對該病知曉率低,且因腹瀉、便血等癥狀具有隱匿性,病人較少得到社會大眾的理解[2]。該病對病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有較大的負性影響,可使病人產生尷尬、焦慮、抑郁和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等心理體驗[3-5]。研究發(fā)現(xiàn)個體創(chuàng)傷后可通過復雜的認知調整體會到積極改變,稱之為創(chuàng)傷后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PTG)[6]。PTG相關研究多涉及重大災難性事件和慢性重癥疾病,其中在慢性重癥疾病方面,相關研究目前多聚焦于癌癥、艾滋病等,而IBD相關報道較少。本研究旨在對PTG的概念和測量,國內外IBD病人PTG的內涵、影響因素和促進方式進行綜述,以期為理解IBD病人PTG體驗及深入研究提供參考,幫助臨床工作者做好IBD病人心理護理,提高病人生活質量。
1 PTG的概念和測量
1.1 PTG的概念
PTG這一概念首先由Tedeschi等[7]提出,也有學者將其稱為益處發(fā)現(xiàn)(finding benefit)、心理活力(psychological thriving)、逆境中成長(adversary growth)、感知益處(perceived benefits)、壓力相關性成長(stress-related growth)等[6]。PTG是指個體在與高挑戰(zhàn)性生活危機斗爭后所體驗到的積極正性變化,這一改變使個體至少在某一方面產生成長并超過原有水平[6],一般個體在遭受到重大威脅或打破原有的觀念之后才能產生顯著的PTG。PTG是一個持續(xù)進行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的結果,常與顯著的心理痛苦并存[6-7]。
1.2 PTG的測量
目前,主要采用量表對PTG進行測量。Tedeschi等[7]于1996年編制了創(chuàng)傷后成長評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是目前在PTG方面應用最廣泛的量表之一。該量表測量的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分別是自我認知改變,人際關系改變和人生哲學改變[6]。這三部分又可總結為個人力量增長、人生新的可能性、人際關系改善、過更有價值的生活和靈性感知改變5個維度[7-8]。加拿大學者將PTGI應用于包括IBD在內的慢性病病人中,結果顯示其信效度較好[8]。Ewais等[9]在將正念認知療法應用于患有抑郁癥的IBD病人中時,采用PTGI作為次要結局PTG的測量工具。Hamama-Raz等[10]對IBD病人PTG相關因素進行探究時,也采用PTGI作為其測量工具。
汪際等[11]于2011年將PTGI修訂為中文簡體版本,并用于我國意外創(chuàng)傷病人,結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目前尚無研究檢測中文版PTGI在IBD病人中的信效度。2009年Kilmer等[12]對PTGI進行了修訂,形成兒童版創(chuàng)傷后成長量表修訂版(PTGI-CR)。陸朋瑋[13]采用PTGI-CR對194例包括IBD病人在內的青少年慢性病病人調查發(fā)現(xiàn),青少年慢性病病人會產生PTG,但是成長水平較低。其他用來測量PTG的工具還有與壓力有關的成長量表(SRGS)、態(tài)度改變問卷(Ci OQ)、成長評定量表(TS)、疾病認知問卷(ICQ)、益處感受評定量表(PBS)、益處發(fā)現(xiàn)評定量表(BFS)、心理活力量表(thriving scale)等[14]。目前,對IBD病人進行PTG測量的研究較少。今后需采用合適的量表測量我國IBD病人的PTG水平,為針對性臨床干預提供參考。
2 IBD病人的PTG內涵
在一項在線調查中,約有近73%的病人報道,IBD在某種程度上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積極影響[15]。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IBD病人進行深入訪談后發(fā)現(xiàn),PTG的內涵主要包括人際關系更親密、個人成長、發(fā)現(xiàn)新的可能性和人生哲學的改變。
2.1 人際關系更親密
一項研究顯示IBD病人最常見的積極變化是病人與他人的關系更親密,而在親密關系的背后,是社會的理解與支持[15]。IBD病人在診斷和治療的過程中可以獲得多種途徑的社會支持,并且這些支持將不斷內化,進一步增強內在自我,從而促進PTG[16]。社會支持主要體現(xiàn)在家人、朋友和病友中。1)家人:家人支持表現(xiàn)在親人對病人不離不棄的陪伴、安慰和鼓勵,其被認為是最容易獲得和最基本的支持形式[16-17]。有青少年病人認為IBD是父母表達愛和支持的一個機會,并讓家庭變得越來越有凝聚力[18]。一項有關IBD病人在父母角色下患病體驗的質性研究報道指出,不少病人表示自己作為父母會因患病而收獲到孩子更多的關心和體諒[19]。此外,家庭支持不只存在于心理層面,還存在于生活的飲食結構中,表現(xiàn)為家人為配合病人改變飲食結構[16]。2)朋友:部分病人可以在患病過程中獲得朋友更多的關心、支持和理解,促使雙方間情感增進[17]。同時,部分病人也會評估現(xiàn)有友誼,確定誰是真正有同情心并能理解他/她的人,從而實現(xiàn)對人際關系的篩選,促進人際關系質量的提升。3)病友:部分病人通過支持小組、在線社區(qū)和醫(yī)療預約等方式與其他IBD病人見面或在線交流,并通過相互分享信息、提供情感支持等建立友誼[15]。在病友這個群體中,IBD病人不像社會中那樣孤獨,各自的經歷和經驗為對方提供強有力的身心支持。
2.2 個人成長
在個人成長方面,多篇質性研究報道,IBD病人認為自己因為患病而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主要體現(xiàn)在4個方面。1)觀念更開放。部分IBD病人因患病而掙脫了自我束縛,觀念變得更加開放。例如,有病人開始不隱瞞自己生病的事實并愿意談論病情及其他原本羞于談論的事情[19-20],一位病人這樣解釋:“如果你能談論腸道,你就能談論任何事情[19]。”部分病人也不再害怕因患病而麻煩他人,變得樂于依靠他人或向他人求助[21]。2)思維更靈活。IBD使得病人正向重構了看待自己、疾病及相關治療的方式,使之能以更加靈活的方法去處理事情[21]。例如,有病人把他的回腸造口術看作是一個與人交談的理由,而不是一個恥辱的缺陷[21]。也有病人以積極的方式利用貼在自己身上的“殘疾”標簽,使之在就業(yè)方面產生好處[21]。3)精神更強大。病人在患病過程中經歷了疾病發(fā)作的痛苦,承受了與之相關的各種壓力,但他們在克服這些困難后意識到自己的精神比想象中更強大、意志比想象中更堅定[10,12,14-16]。因此,在此之后他們做任何事情都帶有更強的決心,勇于解決問題,并獲得了在管理壓力、應對疼痛和處理情緒方面的新技能[15]。如一位IBD病人這樣描述自己的體驗:“我意識到IBD給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東西,……它使我成為一個更堅強的人,如果我未被診斷為CD的話,我將是一個和現(xiàn)在完全不同的人[20]。”4)人格更成熟。患病使部分病人變得更加獨立,比如他們開始獨自做決定[20]。也表現(xiàn)在可以獨自行動,正如一位病人所說:“變得獨立了。反正就很多事情自己能做,就自己來做[22]。”有病人表示,因為自己對抗疾病的經歷和經驗與病友產生共鳴,而希望自己可以幫助他人。一位IBD病人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對于患有炎癥性腸病的人來說,生活并不容易,我愿意為剛確診的病人提供情感咨詢和疾病指導”[16]。另外,病人還因IBD而更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15,18,23-25],從而做出利他行為。
2.3 發(fā)現(xiàn)新的可能性
逐步接受疾病和外部支持可以幫助病人積極思考未來,為未來提供新的可能性和方向[16]。IBD可引導病人發(fā)展新的興趣,或為進一步教育、新的職業(yè)打開大門[15]。有病人因IBD而出現(xiàn)人生轉折:“我的伴侶說我確診之前的人生像是浮萍,而在這之后我變得堅定,我重返校園完成了我的學位,……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然后我去買了自己的房子[23]。”有病人因為IBD而找到自己的職業(yè)道路[26]:“我決定回學校讀心理學博士,這樣我就能和慢性病病人一起工作了[15]。”還有病人因患病而習得新領域的知識:“我開始接觸我本不會涉及的知識領域,比如中醫(yī)[15]。”
2.4 人生哲學的改變
IBD促使病人產生人生哲學的改變,主要包括價值觀、人生觀和精神信仰方面。1)價值觀的改變。首先,部分IBD病人重新排列了事情的優(yōu)先級[17]。有病人把健康放在首位[15-17,24],也有病人把幸福感、安全感等精神財富放在首位[17]。其次,有病人認為“活著便是價值”,不再執(zhí)意追求其他自身價值,因為他們認為活著能彰顯個體和家庭的完整性,還意味著孝和機會[17]。2)人生觀的改變。疾病使病人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從對生活的感知到對生活認知的再造[16]。有病人選擇以積極的方式看待生活,活在當下,正如一位病人所說:“我知道我受到了很多限制……但是這不是我宅在家里郁悶消沉的理由[25]。”他們珍惜所擁有的,并通過自我放松、培養(yǎng)興趣和參加活動等方式實現(xiàn)精彩生活[17]。3)靈性成長。病人可能會在更大程度上思考靈性問題并進行祈禱,以此為他們的疾病帶來希望或意義[15]。通過宗教信仰獲得的信念使病人在面對痛苦時更加平靜,例如有病人說:“只要你有精神信仰了,人處在很痛苦、很惡劣的環(huán)境,也可以讓你容易度過。我就有這個信念來支撐,才慢慢變得平靜[17]。”也有病人這樣說:“我在現(xiàn)有宗教之外獲得了一種強大的精神,這給了我力量,讓我不能完全放棄[15]。
3 IBD病人PTG的影響因素
目前關于IBD病人PTG影響因素的報道較少。人口統(tǒng)計學、疾病因素、人格特質、心理彈性、反芻性沉思及社會支持等因素可能會影響IBD病人PTG水平,但具體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3.1 人口統(tǒng)計學因素
有研究顯示,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職業(yè)類型、家庭月收入[27-28]等人口統(tǒng)計學因素可影響病人的PTG水平。但也有研究表明,年齡和性別等因素與PTG水平無明顯關聯(lián),這可能與文化背景、測量方式、疾病類型等存在差異有關[27]。針對人口統(tǒng)計學因素對IBD病人PTG的影響,也有文章表明,只有家庭婚姻情況與之(弱)相關,因此尚需進一步驗證[10]。
3.2 疾病因素
疾病因素主要包括病程和對疾病的認知。有學者認為,PTG需在病人度過急性應激反應期后才逐漸達到穩(wěn)定,并顯示出長效的價值[29]。相關研究顯示腦卒中[30]、血液透析[31]等病人的PTG水平隨著病程的延長而提高。一項包含16例IBD造口病人的質性研究[21]發(fā)現(xiàn),部分病人在疾病的開始感受到巨大痛苦,但在得知診斷結果并開始接受治療后,他們逐漸適應了疾病所帶來的限制,開始用一種積極的方式看待生活,這提示病程可能是IBD病人PTG的影響因素之一。疾病認知包括無助、接受和感知利益,其中無助強調疾病的厭惡含義,接受強調減少厭惡的含義,以及感知的好處強調為疾病增加了積極的意義。在Hamama-Raz等[10]的研究中,無助的疾病認知與PTG呈負相關,接受的疾病認知與感知利益的疾病認知與PTG呈正相關。
3.3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是指在組成人格的因素中,能引發(fā)人們行為和主動引導人的行為,并使個人面對不同種類的刺激都能做出相同反應的心理結構[32]。相關研究發(fā)現(xiàn),偏外向人格者PTG水平較高[33],開放性、樂觀性、宜人性、盡責性能促進PTG的發(fā)生[34],而精神質、神經質個體的PTG水平較低[33]。有調查顯示,IBD病人開放性的人格特征與全國常模相比有顯著性差異,提示該人群在人格特質上有偏愛常規(guī)、缺少生氣的特點[35]。查倩倩[36]和張晨[22]的研究表明,樂觀的人格特質可直接影響IBD病人的PTG水平或通過降低疾病感知、促進積極應對間接影響PTG水平。
3.4 心理彈性
心理彈性也稱心理韌性,是指能使個體從創(chuàng)傷性事件中恢復的能力[37]。較高水平的心理彈性有助于個體在面對創(chuàng)傷性事件時更加積極地調整認知,采取靈活的應對措施,從創(chuàng)傷性事件中恢復過來,進而獲得成長[31]。有研究對不同疾病病人的心理彈性與PTG的關系進行探討,結果證實具有高水平心理彈性的病人其PTG水平也較高[31,38]。目前IBD病人心理彈性總體處于中等水平[39],但其與PTG的相關性仍待驗證。
3.5 反芻性沉思
反芻性沉思是指個體經歷創(chuàng)傷性事件及負性改變后的認知加工過程,可分為侵入性反芻性沉思(個體對創(chuàng)傷事件反復、被動的關注)和目的性反芻性沉思(個體對創(chuàng)傷事件積極、主動的思考)[40]。有研究表明,目的性反芻性沉思有助于個體理解創(chuàng)傷性事件、構建事件意義及解決問題[41],可提高病人的PTG水平,而侵入性反芻性沉思與PTG的關系尚未有一致結論[42]。總體而言,反芻性沉思與IBD病人的抑郁和焦慮相關,而負性心理與PTG存在顯著的相關性[43],但目前無相關文獻探究不同類型反芻性沉思對IBD病人PTG的影響,未來可以此為方向,以豐富IBD病人PTG的相關研究。
3.6 領悟社會支持
領悟社會支持是指個體所感受、理解到的來自家人、朋友等外界的支持程度。在相同客觀支持條件下,個體所能感知到的支持可不同[44]。一項英國縱向研究調查了影響IBD病人PTG的相關因素,結果表明,感知到較多社會支持的IBD病人,其PTG水平也較高[45]。加拿大一項針對IBD兒童和青少年病人的質性研究也提到,家人和朋友等的社會支持是影響病人如何看待和體驗IBD的重要因素[18]。查倩倩[36]對300例IBD病人PTG現(xiàn)狀調查后發(fā)現(xiàn),影響因素中社會支持維度得分最低,而自我認知和家庭維護水平較高,這說明國內IBD病人的PTG水平主要受社會支持度、包容度等的影響。
3.7 其他因素
影響PTG的因素有很多,如個體創(chuàng)傷前水平、個體感知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心理內部優(yōu)勢資源(如自我調節(jié)、生活滿意度、適應等)、事件的客觀嚴重性、與他人關系改變等[46]。但上述影響因素不針對IBD病人PTG,因此不具有疾病特殊性,建議增加相關研究,使結果更有說服力。
4 促進IBD病人PTG的干預方法
現(xiàn)有促進個體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的方式有認知行為療法、正念認知療法、自我表露法等多種經典成熟的心理療法[47]。但目前查閱到的有關促進IBD病人PTG水平的研究極少,可在此基礎上借鑒其他疾病的相關研究,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
4.1 自我表露法
自我表露是指個人將創(chuàng)傷性或應激性事件及其影響,以及個體對該事件最深層的想法和情感通過交談和書寫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過程,其主要分為表達性寫作、語言表露以及基于網絡的自我表露3種[48]。有研究表明,自我表露干預可減少病人的侵入性反芻性沉思,促進目的性反芻性沉思、心理社會資源、積極情緒以及重新評價等,從而提高PTG水平。一項質性研究結果顯示,部分IBD病人在支持性和隱秘性的氛圍中談論病情后能夠體驗到相應的益處[18]。IBD病人普遍存在感知病恥感[2],阻礙了病人談論自身的患病經歷,從而少有自我表露的機會[49]。因此,自我表露干預通過營造安全的表達環(huán)境,增加IBD病人的患病表達,可能是提高病人PTG水平的方法之一。
4.2 認知行為療法
認知行為療法是指聚焦于病人的不良認知,通過改變病人的思維、信念或行為來消除不良情緒和行為的一種心理療法。認知行為療法可通過糾正消極的內部語言,用正面的、積極的自我對話達到矯正異常行為或者心理障礙的目的,從而促進PTG[50]。馬蘭等[51]通過治療性溝通、小組輔導等認知療法和功能鍛煉、放松訓練、冥想等行為干預提高了乳腺癌病人的PTG水平。鞏樹梅等[52]對意外創(chuàng)傷者進行認知行為團體干預,結果顯示該干預促進了病人的PTG水平。有研究報道,IBD病人焦慮抑郁發(fā)生率較高,而抑郁常伴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偏差[53]。因此,對IBD病人進行針對性認知行為干預,改變IBD病人認知偏差,減輕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促進病人積極轉變[49],可能是提高病人PTG水平的方法之一。
4.3 正念認知療法
正念認知療法是對麻省大學醫(yī)學中心的Jon Kabat-Zinn和他的同事開發(fā)的正念減壓療法的一種改編[54],與認知行為療法不同,它不以改變錯誤認知為目標,而是通過轉移注意力、專注于當下的方式來減輕痛苦,增強元認知意識[55]。Ewais等[9]認為相對于正念減壓療法,正念認知療法更加專注于抑郁癥,該學者對患有抑郁癥的IBD病人進行正念認知療法,結果顯示干預組的抑郁情況明顯較低。IBD病人最常見的人格特征是神經質,活動期的IBD病人比緩解期更容易產生焦慮、抑郁和不安全感,所以在IBD病人中較為適用[56]。Petruo等[57]的研究認為在IBD活動期進行預防性正念治療可以抵抗神經質帶來的負性情緒反應,從而促進PTG。
5 小結
IBD至今尚無法治愈,病人終身患病,身心健康都受到較大影響。PTG相關研究的開展能為IBD病人針對性心理干預提供依據,從而促進病人心理健康,提高病人生活質量。近年來,針對IBD病人PTG的質性研究增加,但總體來說,IBD病人PTG相關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許多問題:病人PTG水平尚待調查驗證;PTG的影響因素尚不明確;PTG干預方式仍需探索。因此,今后需要大量不同類型的研究來進一步深入探討該研究主題,為有效提高IBD病人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