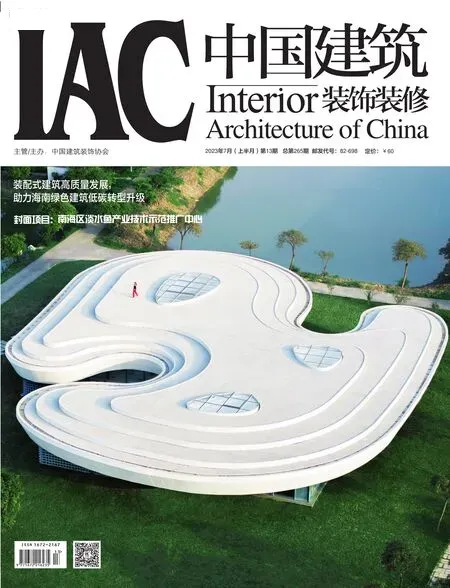歷史建筑在鐵路客運車站項目中的再利用策略研究
楊 威
鐵路客運車站作為公共交通建筑其不僅需要具備交通建筑的高效率,還需要關注公共建筑的高質量。高鐵建設快速發展的今天,鐵路站房的建設融入了站城融合的理念。隨著人們對鐵路出行要求的不斷提高,一些既有站房已經與鐵路發展的理念不符的情況。本研究通過分析國內外鐵路客運車站歷史建筑再利用的案例,試圖總結出既有車站改造中歷史建筑再利用的策略,以期為鐵路客運車站改擴建設計提供參考。
1 鐵路客運車站建設現狀
鐵路建設是我國發展的重要任務。在“十四五”期間,在建和已批項目的規模高達3.19 萬億元。預計到2025 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約170000 km,高鐵(包含城際鐵路)約50000 km。鐵路將覆蓋城區人口在20 萬以上的城市,高鐵將覆蓋98%城區人口50 萬以上的城市[1]。歷經多年的鐵路建設,我國現有車站已經達到5000 多個。這些車站當中有很多站房已經使用多年,無法跟上站城融合的發展方向和人民日益增長的出行要求。老舊火車站也出現了諸如站域空間的活力不足、城市空間碎片化、站域空間與城市發展不協調等問題[2]。因此,對這些車站進行改造升級是未來需要納入考慮的事情。改造升級必然面臨著拆除和新建,從歷史建筑保護的視角出發來處理鐵路客運車站的拆除和新建,對既有車站改擴建策略研究具有指導作用。
2 歷史建筑保護在鐵路客運車站改擴建中的價值
2.1 文化藝術價值
歷史建筑保護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這是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文化及藝術的地位得到提升的表現。歷史建筑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產物,對其進行保護和再利用十分有意義。首先,歷史建筑的建成有其時代背景和意義。在多年的使用過程中已經扎根在人們的記憶當中,成為了當地文化的一部分。其次,歷史建筑的藝術價值能夠被保留。由于時代不同,建筑技術、材料科學迭代更新,歷史建筑也變得獨一無二,是藝術的活化石。
2.2 經濟價值
鐵路運輸是資金密集型產業,鐵路線路及相關產業的變更成本高,其中也包括鐵路客運站。《鐵路客站及樞紐設計規范》(TB 10099—2017)[3]中規定:“改、擴建工程應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物和設施設備。”從建設成本上考慮,與就地重建和異地搬遷相比,歷史車站進行保護性改擴建是更經濟可行的方案。
3 歷史建筑保護在車站設計中的體現
近年來國內的項目也越來越重視歷史建筑的價值。老火車站是歷史與時代的印記,是鐵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支撐。老火車站的歷史建筑保護項目在國外十分常見,國內也有一部分。國內外常見的火車站中里歷史建筑的處理手法有很多種。處理手段根據干預由弱到強的程度,可以將其分為在建筑局部擴建、建筑改建、保留部分建筑構件、建筑整體重建等方式。
3.1 建筑局部擴建
鐵路客運車站擴建項目是以站房為主體,在建筑外部建設相應設施以滿足新的需求。這種擴建的設計方式能較完整的保留歷史建筑主體,并將歷史建筑主體納入新車站中。
法國斯特拉斯堡火車站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案例。斯特拉斯堡站位于法國東北部,下萊茵省省會斯特拉斯堡,是法國東部第三大火車站。站房由1918 年建成的古建筑體和2007 年改造時加建的弧形玻璃立面組合而成。老車站和玻璃罩之間25 m 的空間被當作車站入口的轉換空間,為有軌列車、巴士、地鐵、火車提供服務。這樣的處理不僅將歷史建筑保存的更為完好,還能置入新的功能以滿足新的運營需求。玻璃幕墻的加建使得老建筑增加了詩意的視覺效果。
在面臨火車站需要擴建跨線設施,強化火車站連接城市的功能時,可以在老站基礎上增加新的建筑跨線站房。通過對歷史建筑的局部改造,將新舊建筑功能串聯起來。
例如,位于瑞士的巴塞爾火車站。巴塞爾車站在舊站房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升級改造,將原先與月臺相連的地下通道替換成抬升于軌道上方的帶有商店設施的步行走廊。步行走廊寬敞明亮,可以同時容納候車旅客和穿行的市民。走廊沿線布置商業服務設施,使其成為了火車站的商業街,為其增添了城市屬性。老火車站的改造中,在其面對站臺的立面增設了連接跨線設施的扶梯、樓梯以及坡道,其他部分則不需改動,可以全部保留。這樣的最小干預手段,既延續了歷史建筑的生命,又能滿足新的功能需求。
3.2 建筑改建
相較于建筑局部擴建,建筑改建的干預程度更大。鐵路客運車站改建項目是以原站房為主體,配合擴建建筑部分對其內部結構、流線、空間進行改動,以使其適應新的功能要求。在建筑中置入新的空間,能使歷史建筑煥發新生。
位于英國的國王十字火車站就是建筑改建的一個著名案例。改建工程將車站的入口由南側改為西側,西側的廣場占地4500 m2,并且在西側廣場上方修建了具有標志性的漏斗狀屋頂。這個屋頂是歐洲最大的單跨式結構,由16 條樹枝裝的鋼柱呈漏斗狀散發開來,極具視覺沖擊力,使得西廣場成為了車站的核心空間。原車站西側的車站歷史建筑與新的屋頂結構結合在一起,是視覺、結構、功能的整合,為歷史建筑賦予了新的生命。同時,原車站的南面不再承擔進站功能,經典的南立面得以完全展示出來[4]。
3.3 保留部分歷史建筑
在鐵路客運車站的建設過程中,也有一部分火車站由于改造難度太大或者歷史事件,不得不消失在歷史當中。但是原有的建筑作為歷史的一部分會被部分的保留下來。
位于瑞士的盧塞恩現在的車站興建于1991 年。上一個車站始建于1896年,其標志性的玻璃穹頂成為了當地的地標。但這座不幸的建筑在1971 年的2 月遭遇了一場大火,標志性的玻璃穹頂也從盧塞恩的天際線消失。之后通過競標,新的車站在1991 年建造。與此同時,老車站的入口大門也被重建,用來致敬1896 年的建筑遺產和42 m 高的穹頂。
這種處理的手法在國內也在被運用在設計當中。嘉興火車站的設計中,設計者將嘉興站的歷史站房進行了復建。嘉興火車站初建于1907 年,于1909 年投入使用,是當時滬杭線上重要的交通樞紐。1921 年,部分中共一大代表乘火車來到嘉興。火車站也成為了中共一大召開的歷史見證者,但后來于1937 年被日軍炸毀。設計者與古建專家、學者合力,對大量歷史影像資料及《嘉興市志》中殘存線索進行數字復原和分析,實現了老站房歷史原貌的1 : 1 復原。新車站的設計也只有一層的高度,站房平臺和候車大廳都設置在了地下,尊重了老站房的尺度。老站房修建好以后,將作為博物館為大眾提供服務。在嘉興站的設計中,將歷史建筑擺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5]。
歷史建筑的重建恢復了歷史車站的部分場景,讓歷史和故事得以傳承。
4 鐵路客運車站設計的新趨勢
4.1 站城融合
站城融合趨勢就是不再將鐵路與地方割裂開來,而是實現共同開發。通過體制的創新可以打破土地紅線和開發強度的束縛,從城市設計的角度對整個區域進行整合。樞紐片區可以形成以車站為核心、多功能復合、多組團布局的一體化城市空間,既能夠實現有效的開發又可使城市與車站的結合更為緊密。通過路地雙方的密切配合可以將城市開發的利益與公共空間的塑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4.2 高度連接
新的車站設計十分注重人的活動和心理,力求做到可到達、可穿越、可逗留。可到達是指車站的交通十分便利,有多種交通方式與城市其他區域連通。可穿越是指車站四周形成立體的交通方式,不會造成城市的割裂,增加交通的壓力。可逗留是指將車站區域打造為優質的城市公園,讓旅客和市民愿意在此停留,賦予這個片區生機與活力。車站與城市的高度連接,不僅縮短人們與車站空間上的距離,也增加了心理上的親近感。
4.3 綠色低碳
隨著“碳中和”“碳達峰”目標的樹立,大型樞紐建筑開始全面推進綠色交通,通過互聯網+能源的模式開展多元化城市交通運輸系統的建設。首先,在建筑設計中引入自然采光和通風,實現建筑降低能耗。其次,在建筑中運用了先進的材料及設備,助力實現低能耗的運維。除此之外,大型樞紐項目還與光伏發電項目結合在一起,采用“自發自用、余電上網”的模式,為車站的運行提供清潔能源。低碳的概念也在逐漸從內而外的對車站設計產生影響。
5 鐵路客站歷史建筑再利用策略
5.1 功能復合化
我國的新建鐵路客運車站已經走向了站城一體化模式。這種模式不僅將鐵路客運車站作為城市的交通樞紐,還將建筑本身和所在片區打造為集交通、辦公、居住、娛樂的大型綜合設施,使之成為城市次級的商業辦公中心,減輕城市中心區的壓力。位于奧地利的薩爾茨堡中央車站,建筑師將地下通道拓展成購物長廊,同時還連接了數個區域的城市空間。沿著軌道,平臺上方一個重新設計的寬敞連續弧形屋頂使陽光可以灑向寬闊的月臺和購物長廊,原有的陰暗通道變成了開闊的步行區。同時,現存的歷史建筑的結構融入到了薩爾茨堡中央車站的新方案之中,歷史建筑這一有吸引力的特色促成了其獨特綜合設施的形成。
老車站的單一功能已經無法滿足現在城市開發的需求,在老站的再利用設計中需與車站改擴建部分統一設計規劃,功能相互促進。從城市設計的視角,將車站的更新改造與樞紐片區的資源整合相結合,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路地雙方的創新合作,可以通過車站更新契機,彌補該樞紐片區的不足,將其打造為城市的亮點。
5.2 交通流線復合化
位于城市的鐵路客運車站可以分為2 類:一類是建設之初就設立在城市中心或城市中心區的邊緣,方便市民出行;另一類則是在建設之初位于城市邊緣,隨著城市規模擴張,逐漸位于城市中心地區。對于第2 種類型的車站,加強客運站兩側的交通連接則顯得十分重要,車站更新需要考慮更多通過式的交通空間,使其具有城市街道的屬性。與城市的各項功能相輔相成,打造具有活力的城市片區。
原有歷史鐵路客運站的流線只能滿足乘客上下車的基本需求,而新的車站需要增加城市通廊。基于對歷史建筑保護的考慮,城市通廊有2 種接入方式:一是位于軌道上方與站房相接,將站內天橋與城市通廊結合;二是位于軌道下方與站前廣場相連,將進站地道與城市通廊結合設計。
通過站前廣場的改造,可以實現人車分流、多向進站。地面廣場減少了交通車流的干擾,不僅可以步行進站,還可以打造為高品質的城市空間,吸引游客和市民來此休閑、放松。
地下廣場實現城市交通與車站樞紐的高效換乘。通過城市軌道交通與客運車站的互通,可以增加到達車站的便利性,同時也減輕車站周邊的交通壓力。
通過這些措施的應用,可以讓車站的改造真正實現與城市的高度連接,做到可到達、可穿越、可逗留。
5.3 設計語言的融合
鐵路客運車站歷史建筑本身具有時代性,而且其城市門戶的形象已經烙印在了市民心中。老火車站在一個地方存在的時間往往長達十幾年或幾十年,已經成為了一代人的記憶。改擴建項目的設計語言需要與歷史建筑相匹配,可以從歷史建筑中提煉設計語言,也可以用較為現代的手法做出新與老的對比。例如1989 年建成的哈爾濱鐵路客運站,在2015 年開始進行了改建工程。站房的部分進行了拆除重建,新的站房運用了1904 年老哈爾濱站的設計元素。由此可見,市民對老站房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情感聯結[6]。
隨著低碳設計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新材料與新形式在建筑中逐漸被運用。老建筑的新生也應將代表低碳的新材料、新形式與老材料、老樣式和諧的搭配在一起,讓老建筑與新技術融合在一起,跟上低碳設計的腳步。
5.4 歷史建筑的取舍
在對既有歷史車站利用和改造前,應該對其進行全面的評估。歷史車站的落成及其發展有其特定的時代烙印,也是其不可復制的重要原因。有歷史價值的部分可能是其經歷了特別的歷史事件,也可能展示了特別的制作工藝、設計風格等。經濟方面,對于過于老化或者既有面積過小的站房,改造所需的資金可能比就地重建所需的資金更多。在文化及藝術價值方面,需要對建筑鑒別,并保留比較有價值的部分,舍棄后期加建的無價值部分。此選擇性保留一方面可以刪掉歷史建筑上無用的附加信息,另一方面可以使改擴建有更大的自由度。
5.5 打造核心空間
既有歷史車站改造的目標不僅是車站升級,還要激活整個片區。激活整個片區需要車站改造工程成為一個城市客廳般的場所,具有公共性和地標性,吸引旅客和周邊的市民。
位于紐約新落成的莫伊尼漢列車大廳就是利用了打造核心空間的方式,將一個未被充分利用且早已黯然失色的老建筑重鑄成一扇全新的城市門戶。這個列車大廳設計包含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天窗,讓光線充盈整個大廳空間。列車大廳擁有多個入口,建筑師將入口重新設計以創造誘人的氛圍吸引旅客進入。大廳的周邊建筑內設置了餐廳、辦公、零售等功能,將這個大廳變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都市生活中心,重新定義并且豐富了既有歷史車站的核心空間。
依托于既有歷史車站的吸引力,創造一個舒適、高效、引人駐足的現代化建筑空間是既有歷史車站改造需要考慮的問題,這種空間也是既有車站改造中的核心空間。
6 結語
本文通過國內外既有歷史車站的改造應用案例,按照干預的程度不同,可分為建筑局部擴建、建筑改建、保留部分歷史建筑3 種類型,分析總結出鐵路客運車站歷史建筑在改擴建項目中的再利用策略,對于鐵路客站的改造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以期能為鐵路客運站改造類項目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