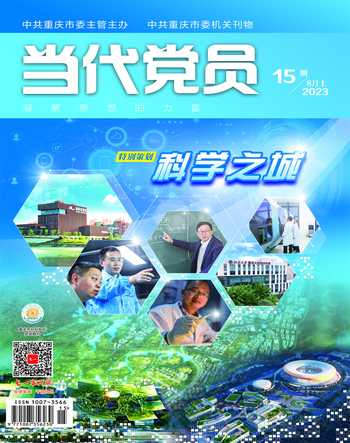鮮活在古代游記文字中的美景
周丁力
中國古代文人筆下的游記,著筆于山川景物、風土人情,呈現的是附著于景物的感動與省悟,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和“心靈滋養指數”。游記寫景不僅僅是對自然景象的描摹,更是對精神之旅的記錄。相較于攝影,游記與心靈的契合度更高,對情感的觸動也更深。筆者認為,這些文字中營造的景象,至少在下列幾個方面是現代攝影作品所無法超越的。
靜景活寫,文字中的美景是心靈之景的呈現。宋代蘇軾游赤壁寫下了著名的《赤壁賦》,寫景狀物包含了優美的想象和微妙的心理活動,其中“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的景象描寫為歷代文人雅士稱道。這是月亮在斗宿與牛宿之間徘徊的景象,是經過想象的發酵而出現的美妙景象。這景象細細揣摩過去,仿佛有,又仿佛沒有,令人有迷離之感。這奇特之景,從作者角度看,只有文字功夫高超的大家,方能描摹出;從欣賞者角度看,大約只有通過對文字寫景的細細品味,充分發揮想象,方能有所領略。這種效果是任何相機都無法呈現的。
精細加工,文字中的美景是巧妙的組合。相較于攝影,文字對景物的組織更加自由隨性。好的文字游記,往往取景于自然,然后通過作者內心醞釀、巧妙加工,在對自然的超越后回歸自然。因而,其所描繪之景,常常更靈活、更生動、更逼真。唐代柳宗元在《小石潭記》中寫道:“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因潭水極其清澈透明,百來條小魚好像懸在空氣中,陽光照射下來,還將它們的身影投射在潭底。這景象的描寫絕非完全寫實,也非完全虛構,而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結合,妙趣橫生。其中文字表現出來的靈動,是鏡頭難以超越的。
文字中“散點透視”的筆法,是多視角之景的匯集。一般說來,在一個鏡頭所取之景中,無論從攝影者的角度,還是從觀賞者的角度,都只有一個視角。而明代張岱在其記游文章《湖心亭看雪》中,寫景狀物采取的就是國畫中“散點透視”的筆法,用這種多視角表現景物的方法描繪景象,并將其巧妙地組裝起來,形成多視點呈現的獨特視覺感受。這是單張的攝影圖片所無法表現的:“霧凇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這段文字中至少具有兩個視角:前半句是遠景——平視;后半句是特寫——俯視。這種多視角之景在似乎靜止排列的文字中,被巧妙地放在一起,令欣賞者似有“目不暇接”之感,形成了一種非常美妙的視覺效果。
神思飛揚,文字中的美景是啟智之景的截取。“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蘇軾在《記承天寺夜游》中寫景,卻并未停留在寫景層面,而是要于特定之景中體悟出人生的某種感想,景閑易得,心閑難得。后人閱讀這些文字時,不僅能欣賞到景致的美妙,還能得到哲理的啟發,獲得審美的愉悅。這在一般的鏡頭拍攝中很難做到。
另外,宋代王安石在《游褒禪山記》中,也是通過寫景狀物揭示出其中蘊含的哲理:“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所謂“無限風光在險峰”,這已然由“景語”,上升為啟人心智的“哲語”。讀這樣的文字,會令人產生透過景象探知內蘊后的愉快感與透徹感。
鮮活在古代游記文字中的美景遠遠不止上述這些。宋代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模仿這句式,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文字記游,寫景不在乎山水之形,而在乎記錄山水在我們心中激起的想象與感受。文字記游之樂,在于與天地山水擁有同一顆跳動不已的心。這中間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能產生巨大的人格、情操的滋養力。因此,筆者認為,鏡頭永遠無法完全替代文字,也無法替代文字實現其特有的文化傳承與涵養功能。
(作者系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