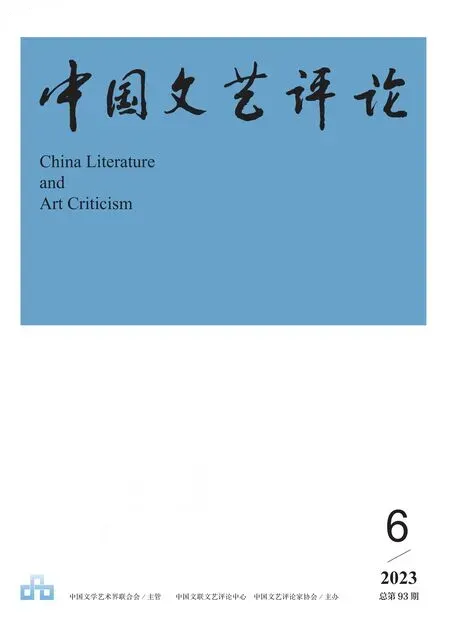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與文藝評論的話語更新
■ 周志強
一百年來,中國社會從緊跟歐美工業發展體系的現代化(近代)、以民族獨立和國家生存為目標的現代化(現代)、解決制度與生產關系矛盾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建設)、融入世界體系為旨歸的現代化(改革開放),到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命題,顯示了中國發展道路的延續性和新時代全面發展的新可能性。這一命題的提出,基于幾百年來全球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結合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特點和未來狀況,為研究和討論當前諸多領域的現象和問題創建了基本框架和內在理念。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中國式現代化”被敘述為五個領域的現代化,也就等于提出了當代中國社會領域五個重大的發展命題: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頁。。其中,與中國當代文藝評論事業關系直接相關的論述格外值得關注。知識大眾的崛起、文藝倫理的定向、精神價值的重塑、生態美學的構建與人類視野的確立諸議題,成為當前文藝評論話語更新的核心。
中國式現代化與當代文藝評論的話語生成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闡述中,“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充分表達了當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礎和現狀。“十四億多人口的規模,資源環境條件約束很大,這是中國突出的國情,這也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不能照搬外國模式,發展途徑與推進方式必然有自己的特點。這么大規模人口的現代化,其艱巨性和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2]孫業禮:《解讀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大特征》,2022年10月24日,https://news.cctv.com/2022/10/24/ARTIdWTncOLVsVKaMkwZdeQt221024.shtml。人口規模巨大一直以來都是文化現代化的核心議題。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就是推動文化啟蒙。人口眾多成為文化教育高成本的根本原因之一。為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以便于聽得懂的語言取代便于看得懂的語言;簡體字取代繁體字,以更容易辨認和書寫的文字來取代筆畫煩瑣、不易學會的文字。在文藝領域,“文藝大眾化”“面向工農兵寫作”等命題的出現,也是因應這種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要求的結果。在今天,越來越多的“大眾”接受了較好的教育,“知識大眾”崛起,文藝的社會整合價值和功能進一步強化,文藝評論的引導工作變得尤為重要,這也正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命題所闡述的文藝評論領域的文體建設和理論探索需要面對的現實境遇。
而“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同樣隱含了對當前文藝繁榮的核心主題的表達。事實上,無論中國處在哪一個歷史時期,人們生活的改善、社會的全面發展都是近現代以來所有文藝作品發生的支配性符碼(Master Code)。那些被看作是現代文學經典的作品,都隱含著中國式現代化主題。魯迅的《故鄉》指向對衰敗鄉土中國的拯救意識、巴金的《家》《春》《秋》中知識分子“自救乃救國”的文化思想、路遙《平凡的世界》中苦求正常生活的悲情與格非《望春風》中作為“剩余物”的人的被拋離感,都指向這一支配性符碼。這也就內在地規定了文藝評論的價值倫理和美學理想:文藝評論的美學標準必須與這一潛在的中國式現代化符碼相吻合。
同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則打開了文藝評論的倫理視野。共同富裕是社會的全面發展,而兩種文明的協調則是人的全面發展。“以往一些國家的現代化一個重大弊端就是物質主義過度膨脹;強大的物質基礎、人的物質生活資料豐富當然是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人只追求物質享受、沒有健康的精神追求和豐富的精神生活,成為社會學家描述的那種‘單向度的人’,豐富多彩的人性蛻變為單一的物質欲望,那也是人類的悲劇。這個為我們所不取,我們追求的是既物質富足又精神富有,是人的全面發展。”[1]孫業禮:《解讀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大特征》,2022年10月24日,https://news.cctv.com/2022/10/24/ARTIdWTncOLVsVKaMkwZdeQt221024.shtml。顯然,文藝評論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文藝服務,更是在此基礎上為形成良性的“本能革命”(instinctual revolution)[2][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100頁。而確立自己的批評原則服務。物質豐裕社會的壓抑性代價需要被識別和破除,任何為了維持某種特定集團利益和秩序的統治目的而進行的社會控制,往往通過文藝作品形成自我合法化的辯護,通過合理性、合情性的敘事,最終形成對人的本能的壓制,也就是所謂的“額外壓抑”[3]同上,第25-27頁。。中國式現代化命題下,中國文藝評論工作的核心任務正是要去偽存真,祛除虛偽的權魅假說,恢復人們對自身真實處境的意識,凸顯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文藝評論宗旨。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體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把現代化的發展從馬克思所批判的“偉大的破壞性與偉大的創造性并存”[4]浮士德召來靡菲斯托和他的“力士”,趕走了老夫婦,并在他們的土地上進行了重建;然而老人的死,讓浮士德感受到“發展”的罪惡。參見[美]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徐大建、張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86-90頁。的悖論中拯救出來,走一條中國特色的人與自然共生的現代化之路。這也就需要中國當代文藝評論引入生態批評的思想視野,關注文藝作品中的人類中心主義、歐美中心主義和父權制思想,形成文藝批評生態理論的品格。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具備新的人類意識和歷史觀念。“我們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我們的旗幟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這是我們制度決定的,也是我們的文化決定的。”[5]孫業禮:《解讀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國式現代化有五大特征》,2022年10月24日,https://news.cctv.com/2022/10/24/ARTIdWTncOLVsVKaMkwZdeQt221024.shtml。自薩義德以來,后殖民主義文藝評論崛起。但是,這種文藝評論乃是建立在以帝國、宗主國、反歐洲中心主義話語基礎之上的,與中國近現代以來文藝作品中民族獨立與階級解放的議題不完全交融。事實上,和平崛起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發展的道路,而不是三百年來全球化旗號下少數國家壓制和剝削大多數國家的道路。中國的發展,不是立足于國家實用主義和保守主義目的的對全球進行新的掠奪和資本再分配,而是對人類夢想——馬克思所主張的徹底解放的追求和探索。[1]參見周志強、劉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種闡釋視野》,《學習與探索》2022年第4期,第8-15頁。因此,當代中國文藝評論要具備一種新型的“人類視野”,要意識到人的命運與人類的命運乃是文藝作品中的真正的命運,把對人的真實生活的表達作為文藝評論的根本性標準,確立反異化、反遏制性的批評精神和態度。
顯然,中國式現代化命題的提出,為當代中國文藝評論的“中國式問題”提供了理論建設的方向和批評意識的基礎。在這里,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命題,指導文藝評論定位社會角色、確立價值理想、創新批評倫理、引入生態批評和重構精神品格。
中國文藝評論的三種話語
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中國文藝評論的發展需要完成自身的話語更新,即文藝評論需要確立以面向知識大眾為核心的有機性話語、注重全面發展的辯證性話語和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遍性話語;三種話語相互融合,構建起新型文藝理論話語。而實現三種話語的更新與融合是當前中國文藝評論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自黑格爾論述了現代社會的基本體系以后,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么理解社會?從現代社會確立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誰來領導社會、誰來主導社會的問題。由此,知識分子就逐漸因其社會職能的差異而分化為三種類型。[2]法國哲學家福柯在接受訪談時提出,“二戰”之后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發生了轉變。“一種新的‘理論與實踐’的連結模式已然建立。知識分子的工作不再具有‘普遍的’、‘示范的’、‘唯真的’形式。他們習慣了在特定的地方工作。他們的生活或工作條件使他們置身彼處(住所、醫院、精神病院、實驗室、大學、家庭、性關系)。”相應地,福柯也就區分了普遍性知識分子、專才知識分子。參見[法]米歇爾·福柯:《米歇爾·福柯:〈真理與權力〉(1991)》,陳榮鋼譯,2018年10月10日,https://www.sohu.com/a/258528764_559362。事 實上,福柯本人卻又不同于普遍性知識分子和專才知識分子,而是更多地扮演了有機知識分子,或者說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角色。參見[美]加里·古廷:《福柯》,王育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25頁。
第一,普遍性知識分子。在筆者看來,普遍性知識分子恰如福柯所說,執行與真理有關的思想行為,如康德、黑格爾、愛因斯坦等。普遍性知識分子主要生產看起來與當下社會生活沒有直接關系的問題,諸如“物自體”“精神現象學”,等等。事實上,正是普遍性知識分子為社會提供的“命題話語”,即通過關于知識范式、觀念范疇等的反思、解析和創生,為人們提供認知方式和思想視野。
第二,有機知識分子,或者叫作批判性知識分子。這是由依托一定學術和理論背景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大眾構成的群體。這一類知識分子在今天不斷生產“問題話語”。有機知識分子致力于思考我們的社會、人生或生活如何才能更好、更有價值和意義。他們秉持歷史批判和現實反思的精神,解析人的各種活動和社會關系的內涵,并為人們提供信念支持和行為路徑。從馬克思到弗洛伊德,從馬丁·路德到達爾文,一代又一代批判性知識分子提供了不同時代的問題意識,也創造了不同時期的文化政治。
第三,專才知識分子,或者叫作技術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以醫生、律師、法律的制作者以及大眾媒體的從業人員等為主體。專才知識分子主要為社會提供“話題話語”,諸如社會管理方式、經濟運行策略、健康醫療保障或者社區衛生安全等問題。專才知識分子是當代社會國家治理和生活運轉的基礎,是一個社會領域自我生產和組織的技術保障和機制依托。
簡單來說,從命題、問題到話題三個層面的知識分子分別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話語類型。當前中國,普遍性知識分子話語相對缺失,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學科推動知識范式更新的命題話語很少出現。知識分子人才的生產,過多倚重于專才知識分子的生產,這導致普遍性知識分子話語命題意識的單薄。而命題話語的缺失帶來的問題乃是,匱乏命題意識的技術知識分子話語在當前中國社會當中成為主流話語。這就造就了中國社會知識話語群的種種值得反思的現象:口香糖主義泛濫——一種思想就像口香糖,大家嚼來嚼去,滋味單一,思想同質化嚴重;實用主義思想盛行——“好好讀書、長大了掙大錢”,鑲嵌在青少年教育的家庭環境和私人情景之中;藝術創作和文藝評論呈現出明顯的同質化、同類化和扁平化問題,“口水文化”泛濫。
與之相應,有機知識分子處于兩難境地。問題話語本應該在觀念意識上影響社會,成為社會話語構建的主要力量;但是,當今有機知識分子問題話語遭遇了價值兩難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有機知識分子“微思想化”,依賴于微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思想;第二,思想碎片化,無法形成系統思想的生產力,有機知識分子學院化,大量知識分子采用的學術話語無法回答和觸碰社會的真實問題;第三,知識分子體制化,其工作主要圍繞科研學術課題展開,使得知識分子的專能被捆綁在技術層面,話語的想象力被壓制。有機知識話語的專才化導致思想生產的標準化,其話語生產服從話題生產支配,只能通過公共性新聞體語言形成自己的話語方式和知識資源。
普遍性話語、有機性話語和專才性話語的現狀,凸顯了當前中國文藝評論話語建設的困境:相對而言,目前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的形態,專才性話語較為強大繁榮,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文藝社會學知識資源、80年代以來形成的文藝美學知識資源成為專才性文藝評論的核心話語;而文藝評論元話語力量不足,尤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當代發展為指導的理論話語匱乏普遍性意識,不能形成具有理論輻射力的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這也就造成了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缺乏辯證力量和分析能力的困窘,“所見即所得”而不是“反思有所得”成為評論家的思維缺陷。出現血就是血腥暴力,看見肉就是性混亂,聽見口號就是在歌頌,遇到淚水就是負能量……文藝評論普遍性話語的乏力、辯證性話語的僵硬和有機性話語的淺薄,正在影響文藝評論的思想魅力和美學感染。
文藝評論與文藝評論的想象力
中國式現代化命題的提出,是建立在對現代社會復雜狀況的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之上的,其理論范疇是對歷史問題、現實困境和未來趨勢的高度抽象和闡釋。它所提出來的命題,應該是作為支配性符碼(Master Code)的方式指導文藝創作,也就相應不能以簡單的主題批評、思想評論、審美表述和形式論斷的方式,對文藝作品的內在邏輯進行直白評論。發揮文藝評論的政治想象力,建構具有辯證性、震撼性和理想性的批評話語,正是構建文藝評論政治想象力的關鍵。
換言之,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命題,顯示出典型的社會學和哲學的理論想象力。它呈現出與之前關于中國發展道路和歷史使命的描述有所不同的“總念”(concept)特性。即中國式現代化對于中國當前和未來狀況的陳述,是以哲學性和命題性的話語形式對當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所作的歷史概括,也是普遍性話語構建的入口和富有啟示性的方向;與之相應,文藝評論話語的更新,也就集中體現在立足普遍性話語基礎之上的有機性話語的創生和發展。在專才性話語中,引入普遍性話語的總體意識和批判性話語的辯證思維:即“文藝評論”以專才性話語為主體、以普遍性話語為主導、以批判性話語為主旨。在這里,“中國式現代化”對于中國問題的表述呈現出強烈的辯證意識和總體性特征;與之相應,文藝評論也必須實現與這一命題表述的“同構”,即文藝評論必須摒棄“所見即所得”“以經驗共鳴”為核心的話語邏輯,而致力于建設批評的總體性精神和闡釋的辯證性力量。簡言之,在三種話語的更新建設中,“辯證性話語”的建設應該成為重點。
因此,文藝評論的辯證性話語的建設,一方面就要重申文藝評論建基于總體性意識基礎之上的概括能力;另一方面,立足于對文本之獨特性經驗進行挖掘的辯證闡釋。在這里,文藝評論不能僅僅停留在認識一個作品方面,還要進一步真實地想象一個時代,也就是在“總體性意識”的支配下對于一個時代不可見的支配性矛盾進行建構和發掘,才能實現對一個具體作品的完整把握。而所謂“總體性意識”,歸根到底乃是抽象地理解現實所生成的那種自我意識。由此,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命題,正是構造了當前文藝評論話語建設的“總體性意識”:無論是社會的發展還是當前所面臨的文化、政治、經濟和生活四大領域的核心矛盾,恰是這五大命題作為“總念”所激活的中國社會文藝評論想象力的自我意識。
事實上,中國式現代化命題蘊含著這樣一種新的自我意識,對于現實的理解和把握,乃是一種對于世界進行改造性實踐的謀劃。“中國式現代化”歸根到底乃是改變生存環境、解決社會矛盾、發展民生民權、創生和諧環境和實現全球進步的現代化,是一種以馬克思主義“改造世界”為核心命題的現代化。這就要求文藝評論的想象力首先要具備這樣一種“政治性”:文藝評論不是僅僅為文藝服務的——這是文藝評論的核心使命,而是為文藝更好地凸顯現實境遇和激發改造世界的活力服務的。
這恰恰是對文藝評論之“政治想象力”的訴求:除非可以想象一個時代的基本社會圖景,否則就無法建構理解具體文本的問題;任何單個的文藝問題,都是想象整個時代和歷史的特定入口。這種政治想象力與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有內在的聯系:
個人只有通過置身于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經歷并把握自身的命運,他只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機遇。社會學的想象力可以讓我們理解歷史與個人的生活歷程,以及在社會中二者之間的聯系。它是這樣一種能力,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面,并觀察二者間的聯系。在應用社會想象力的背后,總有這樣的沖動:探究個人在社會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質的一定時代,他的社會與歷史意義何在。[1][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4頁。
當然,這種政治想象力不應該僅僅是“心智品質”,而是對于特定社會現實的基本狀況、核心矛盾、人生困境和價值沖突的深刻把握和理解,是建立在人類視野如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基礎上,以辯證性的方式,對個體經驗和知識進行解析和研究的途徑。王躍文的長篇小說《愛歷元年》(2014年)出版以后,引起了評論界的討論。大部分評論者將其定位為“情感危機”的作品,傾向于對其親情、愛情和友情的價值倫理問題的討論——這當然很好地闡述了這部作品的文化內涵。但值得反思的是,因為未能把這部小說所書寫的“愛情激情”與現實的總體性闡釋勾連在一起,就失去了以這部作品來窺探當下中國社會之“奧利給癥候”的契機。小說寫孫離和喜子從相識、相戀、相愛,到共同生活、各自出軌,最終又回到對方身邊;這看似是一個老套的認同愛情、回歸家庭的故事,卻隱含了另一種辯證性的驚顫:孫離和喜子從相愛的那一天起,就只能“陷入愛情”;不僅他們相識的那一天成為他們自己的“愛歷元年”,而且,他們分別成了學者和作家之后,也要繼續構建“愛歷元年”。小說顯示了這樣一種吊詭的生活:只要離開了“愛的激情”就仿佛沒法活下去。《愛歷元年》所寫出來的“情感危機”或“中年危機”并非那種衰朽不堪、昏沉待死的危機,而是刻板機械的生活和定時做愛的情感,讓人錯把愛情當作生活意義的危機——除了出軌,似乎就沒有什么可以燃燒自己的東西了。特定生活條件下同質化的人生、單調重復的歲月,讓我們的人生感覺不到掙扎和拼殺所帶來的激動。換句話說,《愛歷元年》是一個特定時代里面幾乎每個人內心中都有的悲悼:除了愛情仿佛沒有任何感情值得珍視,除了相戀再也點燃不了生命熱情;單調、重復的熱情搜尋的背后是情感荒漠寓言,而這則寓言的邏輯則是大家都擺出一副充滿意義的生存姿態,而生存本身則空空如也。在抖音短視頻中,一個光頭漢每天充滿力量地大喊“奧利給!”空洞無物卻充滿了神圣感。《愛歷元年》的深刻正在于它寫出了一種“假裝激動”的“意義匱乏癥”:活得無趣,并不無所事事或者百無聊賴,而是恰恰相反,活得動力十足、干勁十足和一往無前——瘋狂地做沒有意義的事情,掩蓋沒有意義本身。
于是,通過理解、闡述和把握現實生活中的“總體性意識”,一部被“誤讀”為情感救贖的小說,卻呈現出相反的意味:情感救贖本身就是情感無以為繼的癥候。顯然,看似瑣碎的婚姻情感的故事書寫,卻可以被辯證性解析為當前具有共同性的困境經驗;在這里,“發現”孫離和喜子的“愛情”的特異性乃至詭異性,遠遠比說明他們愛情生活的普適性內涵更有力量。那種嘗試建構一種普適性的文藝評論的理想是非常渺小的,因為這種批評只能在強調道德、信仰、靈魂和精神的層面上變成用“阿門”來結尾的說教。換句話說,文藝評論對于總體性意識的強調,旨在深入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和政治矛盾的內部,然后才能“發現”作品所書寫的經驗的獨特性,而不是把一個個不同版本的人生故事,都闡釋為同一種經驗。
要實現這一目的,文藝評論就總是要面對一個個單獨的事件,而也總是能夠透過每一個事件的不同細節,把一個文本置放在更加宏大的總體的歷史進程當中去,以此來凸現文本中原本被壓抑或隱藏的東西。簡言之,把文藝作品看作是多重意義內涵的文本,而不是簡單理解為單一聲音或主題的表達,致力于在文藝作品表達的意義之中,深挖其潛在的總體性內涵,辯證性地凸顯其內在意蘊,才是文藝評論政治想象力的主旨。格非2016年的作品《望春風》被看作是新時代的“鄉村”小說,截至2023年4月19日,在知網的搜索中,以“望春風”為主題詞進行搜索,得到221篇論文:其中,以“鄉村”為主題詞的是65篇,以“鄉土”為主題詞的是33篇。鄉土敘事、鄉村敘事、鄉村美學、鄉村烏托邦等概念,圍繞這部小說構成“概念的集合”。小說也被諸多評論家看作是故鄉消失敘事(森岡優紀)、鄉土中國的寫實力作(解志熙)、懷念故鄉(呂正惠),等等。[1]參見格非、王中忱、解志熙、曠新年、孟悅、李旭淵、呂正惠、森岡優紀、葉紋(Paola Iovene):《〈望春風〉與格非的寫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74-91頁。這些評論當然是對這部小說有力的闡釋和評價。但也同時讓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評論者對這部小說“貼得太近了”,人們更關注這部小說所寫出的故事、預示的含義和使用的形象或意象(包括鄉土、農民),卻很少從當前中國社會現實的總體性狀況展開評論的想象力,探討這部小說為何這樣書寫、作品所創生出來的作者連同讀者似乎都難以把握的“傷感”具有何種現實寓意,以及作品之“鄉村”所呈現出來的歷史性疑難(Aporia)是怎樣的諸問題。小說的結尾講述主人公“我”與“春琴”寄身于“便通庵”,開始他們所謂的“幸福生活”:
我們的幸福,在現實世界的鐵幕面前,是脆弱而虛妄的,簡直不堪一擊。有時候,春琴和我在外面散步,走著走著,她的臉上就會陡然掠過一陣陰云。只要看見路邊停著一輛橘黃色的挖土車,她就會疑心這輛車要去拆我們的房子。我們兩個人,我和她,就會立即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憂慮中。
危險是存在的。災難甚至一刻也未遠離我們。不用我說,你也應該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茍延殘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個弱不禁風的偶然性上——大規模轟轟烈烈的拆遷,僅僅是因為政府的財政出現了巨額負債,僅僅是因為我堂哥趙禮平的資金鏈出現了斷裂,才暫時停了下來。巨大的慣性運動,出現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停頓。就像一個人突然盹著了。我們所有的幸福和安寧,都拜這個停頓所賜。也許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將會在一夜之間化為齏粉,我和春琴將會再度面臨無家可歸的境地。[1]格非:《望春風》,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87頁。
“恐懼”成為這部小說的一個內在秘密:一個被時代或現實拋離在隨時坍塌的荒涼寺廟中的人,一種建立在資金鏈斷裂時刻的幸福生活,構成了這部小說的“疑難”(Aporia):幸福美滿的生活與支離破碎的寺廟,無法并存的兩種狀態,竟然在此現實性地融合在一起。作品對人作為“現實的殘余物”的書寫,超越了魯迅式的鄉土拯救或汪曾祺式的“抒情現實主義”,而指向了人的經驗無法被“歷史敘事”完整表達的尷尬。
顯然,《望春風》是這樣一種小說,它向人們呈現了個人命運與歷史命運的根本性疑難(Aporia)——只要用這種《望春風》的方式進行文學表達,我們就會遭遇這樣一種“命運真實”:那些無法被“故事”恰當安排的人生遭遇,卻是諸多“我”與“春琴”的刻骨經歷;同樣,在那些被故事化的人生中,我們看不到“我”與“春琴”的經驗。
從鄉村的故事中,發現“鄉村故事”對人的命運真實的剝奪,從而讓那些被快速發展所拋離的孤零零的“剩余人”的經驗,成為文學續寫的經驗,這正是對《望春風》作品進行辯證性批評的另一種內涵。格非這樣說:“這個不幸的人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僅僅在于有了這個回頭的一瞥,看到了這個堅固世界背后的東西,也就是虛無。但蒙塔萊詩歌中的這個人,在發現‘奇跡’之后,表現出了珍貴的謙遜。他沒有大喊大叫,沒有試圖否定常人看到的理性和堅固的世界,也沒有向人吐露他所看到的虛無。他一聲不吭,走在人群中,就像是什么事都沒有發生。”[2]格非、王中忱、解志熙、曠新年、孟悅、李旭淵、呂正惠、森岡優紀、葉紋(Paola Iovene):《〈望春風〉與格非的寫作》,《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第91頁。事實上,《望春風》的“真實”不僅僅是故事所依托的“鄉土空間”的真實,更是特定時期人們命運內在悖論的真實。只看到小說對“鄉村消失”的緬懷是遠遠不夠的,更要看到這種緬懷中所透露出來的冷徹骨髓的悲傷所依托的當代生活的歷史性疑難。如果沒有對當前社會人們生活之真正矛盾的領悟、對改變這種生活的欲望性表達,如何有這部小說的內在力量?不妨說,文藝評論想要建構和想象一個時代的“真實”,就必須首先確立基本的政治理想,即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理想;而只有具備了觀察世界的基本矛盾的欲望的時候,文藝評論的想象力才能被解放出來。
在筆者看來,文藝評論作為一種總體性意識的構建,它體現為,必須把任何單獨的文本鑲嵌到社會的總體性視野中才能凸顯其意義的文本。這事實上為文藝評論的政治品格和批判原則提供了基礎。毋寧說,在今天文化消費主義的時代,藝術的真實已經被現實意識形態的總體虛假生產體系暗中操控,不再成為有自我澄明能力的歷史敘事;而只有借助于特定的政治想象力,文藝評論家才能通過對藝術文本的意義重組,實現對現實真實處境的“重講”和“拯救”。
說到底,文藝評論的想象力乃是一種“批判的想象力”“辯證的解析力”和“經驗的溝通力”,即堅持用想象未來的烏托邦主義視野發現當下矛盾和困境,并通過堅守對當下矛盾和困境的開掘,致力于建構更好的未來的能力。簡言之,如果不能想象未來,也就無法發現現實的困境和內在的矛盾,從而也就無法建構真實,這正是文藝評論的宿命。[1]本文作者系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學創新團隊“文化轉型與現代中國”成員。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