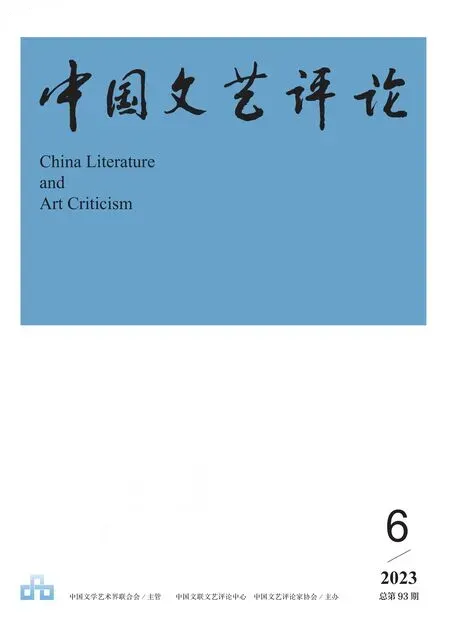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公約數
——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依據
■ 崔 柯
與社會總體發展格局相應,近十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格局明顯改觀,同時也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將此前的理論蓄力轉化為創新突破的動能,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今后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本文擬結合過去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態勢,以“中國式現代化”對理論研究提出的要求為依據,探析學科發展的關鍵問題。
一
自2013年起,筆者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年度發展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寫作[1]除2016年度“報告”刊發于《漢語言文學研究》2017年第3期外,其余諸篇皆刊發于次年《文藝理論與批評》第2期。,在寫作中,筆者和課題組同仁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十年來,研究水準明顯提高,學科格局逐漸改觀。
此前一段時間,學科研究較為沉寂,甚至一度被邊緣化。近十年來,雖然未提出著眼學科全局的新概念、新方法,但優秀文章數量增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時有出現。從整體格局看,此前相對薄弱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對當前重大現實議題的探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史論研究是新增生長點。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主要包括三個研究對象,相應地形成三個研究領域:經典、中國以及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在2013至2016年度報告的寫作中,課題組以這種三分法作為結構,對三個領域的發展狀況依次評述,從中發現該年度各領域的亮點力作。不過,課題組也意識到,這種區分較為簡單機械,不利于提煉共同議題、構建學科體系,自2017年起放棄了這種做法,轉而抓取當年的關鍵詞和發展態勢,總結、倡導值得肯定的新趨勢、新方法、新路徑。但是,這種三分是學科發展的客觀現實,而各個領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研究對象,呈現出各自的理論特點。
就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領域而言,研究重點體現為“細讀重釋”與“捍衛立場”。“細讀重釋”即通過文本細讀,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要命題、理論特質、批評方法進行總結、闡釋。“捍衛立場”即重申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科學性、真理性,批駁種種“誤讀”馬克思主義的做法,辨析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真精神”和內核。
就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而言,“歷史研究”與“當代形態研究”構成兩大研究領域。所謂“歷史研究”,即對理論發展史上的經典文本、理論家及命題的研究。其中,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直是研究熱點,此外有對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李大釗、魯迅、瞿秋白、胡風、馮雪峰、茅盾以及重要概念如“人民性”“文學反映論”等進行的專題研究。“當代形態研究”,即對構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藝批評的“當代形態”或“中國形態”的設想,這一議題自新時期伊始提出以來,相關探討始終未曾中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工作、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等系列講話,對文藝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如何深入理解這些講話的內在精神、更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成為理論熱點,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推進了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形態的闡釋。當然,“歷史研究”與“當代形態研究”的區分是相對的,“歷史研究”往往有著現實關注,力圖從中發現構建“當代形態”的啟示;“當代形態研究”有著歷史觀照,力圖通過爬梳歷史總結經驗。
就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而言,主要是以國外理論家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西馬”)理論家的個案研究為主,涉及面廣,西馬早期理論家盧卡奇、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馬爾庫塞,法國理論家阿爾都塞、朗西埃、巴迪歐,德國理論家布萊希特、本雅明,美國理論家杰姆遜,英國理論家伊格爾頓以及文化研究理論家雷蒙·威廉斯、斯圖亞特·霍爾、托尼·本尼特,等等,都不斷有專題研究出現。在此基礎上,也有學者嘗試對西馬進行整體研判,對中國研究西馬的路徑進行反思。此外,東歐、日本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以及中國理論對國外影響方面,也時有研究成果出現。
總體來看,十年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延續了新時期以來形成的三大研究領域并立的格局,在各個領域之內,有著較為一貫的研究對象及延續的問題意識。如果說,在2013年寫作之初,課題組對學科的基本判斷是“處于一個研究的平臺期,即更多的是量的積累”[1]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課題組:《2013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研究報告》,《文藝理論與批評》2014年第2期,第50頁。,在寫作的時候,盡管每年勉力尋找亮點,但時常為讀到平庸、瑣碎的成果而惋惜。相比相鄰學科自覺的學科問題意識及不斷引發集中探討的新議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進展更多體現為既有學科框架下局部、個別的突破。不過隨著寫作的持續,我們發現,這種現象有了一定改變,正如2019年的報告所指出的,該年度有一個變化,“那就是研究成果質量普遍較高,大多數論文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有的還有一定深度,前幾年常見的摻水式、應景式論文數量大幅降低”[2]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課題組:《2019年度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發展研究報告》,《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2期,第4頁。。
三個研究領域相比而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變化更為明顯,不僅數量增多、質量提升,而且得益于十年來學科努力回應黨和國家層面的方針、政策,逐步蓄力、積累,出現了一些值得稱道的研究。比如,對學科建設中長期存在的一些老問題進行了集中、深入的清理與探究,具體包括梳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學科歷史、調研當前馬克思主義文論教學教材狀況、分析馬克思主義文論邊緣化及理論與批評脫鉤等問題的根源、反思當下理論研究的不良傾向,等等;再比如,在教材建設方面,歷時12年完成、2021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3]參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編寫組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力圖解決經典、中國、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三分、彼此難以融合的問題,在體系建設上作了嘗試;此外還有對關涉體系建構的關鍵概念、命題所進行的深度學術史研究。這些都為今后的理論突破提供了條件。
二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發展的同時,問題和難題并存,其中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是研究缺少系統性、議題分散。不僅經典、中國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三者之間缺少共同的學科意識,鮮有對話溝通,而且在各個領域內部,不同學者往往也有各自獨立的研究對象和問題意識,彼此之間關聯少。
缺少系統性和對話性有著復雜的歷史根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未就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公約數達成共識,如有學者指出的,“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有其基本的問題框架的,但是后來這個問題框架不斷地被質疑乃至‘摒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根本性的差異”[1]張永清:《理論基石與問題框架》,《文藝理論與批評》2014年第5期,第27頁。。具體說來,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異議較少,分歧主要出現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馬文論之特點和關系的認識上。
中國學界一度將西馬文論視為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相異質的存在,認為中國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正統,而西馬則偏離了經典,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難以兼容。例如,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史論著作中,經典、俄蘇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構成三個主要發展階段,沒有西馬的位置。
在文藝理論的整體格局中,新時期之后,“審美”逐漸成為主導觀念,馬克思主義文論遭受冷遇,西馬文論研究也不例外。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多個西馬文論的選本出現,西馬文論作為一種重要理論資源出現在一些研究著作中,也出現一些專論,但總體發展不佳,其中原因是西馬文論一方面“受累于被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思潮”,另一方面“囿于政治制度不同,他們的文學批判往往缺乏類似的政治支撐而更多停留于文化層面,這種原罪就導致了它們難以進入國內馬克思主義者的法眼”。[2]陳學明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程與影響研究》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33頁。直到21世紀之后,西馬才蓬勃發展,快速增長,除了研究的深化,[3]參見陳學明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程與影響研究》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45頁。在文學與文化批評實踐、學位論文選題,乃至教學及教材撰寫方面,西馬都備受青睞。
同時,對西馬始終存在一種批評,即它抽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維度,較多停留于精神層面的分析與文化領域的批判。這一點,即便是一些研究西馬的學者也曾明確指出。因此有學者主張,在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系時,應辨析西馬遠離乃至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觀點,分離出其中與馬克思主義相“異質”的成分。[4]參見董學文:《文學理論研究“西馬化”模式的反思》,《天津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第87-100頁;趙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局限》,《湖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第156-158頁。需要說明的是,這一主張有時會被簡化為“西馬非馬”,實際上,持這一主張的一些學者并不否認吸收借鑒西馬文論的必要性,而是反對簡單化地把西馬文論觀點方法直接移植過來,甚至以西馬取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做法。
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馬文論存在沖突的觀點不只存在于中國學界,也受國外學界區分西馬和東方馬克思主義做法的影響。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在具有共同學術傳統的意義上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視為一個整體。不過,安德森在該書中對西馬的尖銳批評似乎常被忽略,在西方乃至中國,西馬一度以批判、超越東方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而當代意大利學者多米尼克·洛蘇爾多則試圖反轉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等級關系,提供了另一種聲音。
在2017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構:誕生、死亡與重生》一書中,洛蘇爾多梳理了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差異”到“對抗”關系的演變過程,在他看來,存在理論盲視的是西馬而不是東方馬克思主義,西馬忽視了東方包括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反殖民革命維度。反殖民革命不僅指爭取主權上的獨立,在當今,爭取經濟和技術獨立也是反殖民革命的一種表現。對反殖民維度視而不見,使得西馬既無法正確理解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意義,也導致自身失去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警惕和批判而陷入理論困境。根據洛蘇爾多的分析,西馬忽略了東方與西方國家在社會發展階段上的巨大差異,以及較多國家的經濟、政治仍受控于西方國家的現實。他不無諷刺地指出了西馬的傲慢與偏見:“讓東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所鼓舞的國家聽任命運的擺布,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許早就擺脫了那些束縛其翅膀并妨礙其高飛的東西。”[1][意大利]多米尼克·洛蘇爾多:《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構:誕生、死亡與重生》,李凱旋、李賽林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22年,第111頁。
可見,無論是中國還是國外學界,都認為東方/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馬之間存在差異與沖突。但在中國,新時期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與西馬文論都被共同放置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科名目之下。于是,一方面如前文所說的,各個研究領域更多是在獨立發展,彼此之間較少對話;另一方面,在具體研究中,不同學者不可避免地會傾向于選擇其中一個領域作為主要依據來理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因此,看似都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一名目下的探討,實際可能有很大理論差異甚至觀點沖突。這在具體研究中往往會帶來一些難題,比如,在學科關鍵詞、文本形態及功能等問題上存有分歧,對學科體系的構想缺少具體操作的路徑,等等。
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有別,是制約學科發展的一個瓶頸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多方面、長時間的努力。其中要做的一個工作,是尋求馬克思文藝理論的公約數,為經典、中國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提供對話的平臺。
三
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公約數,一方面,不言而喻,要立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源”與“流”,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近200年的發展歷史;另一方面,應從我們所處的現實語境、時代任務出發,根據現實需要,研讀原理,觀照歷史,進而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實踐中進行總結歸納。黨的二十大報告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概括現階段黨和國家的歷史使命與任務,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本質特征以及戰略安排、具體規劃,這為我們尋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公約數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依據。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頁。這些論述包含著深刻豐富的內涵,在筆者看來,“中國式現代化”涵蓋以下兩方面。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現代化”的普遍性,更具有立足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保持著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警惕與批判。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是在和西方發達國家競爭中開展的。中國對現代化的設想,始終強調“中國”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道路。西方現代化發展過程,伴隨著對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殖民,而中國通過艱苦的斗爭,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走的是另外一條不同的道路。在此過程中,中國不可避免要借鑒西方國家發展生產力的經驗,縮小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但同時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的規定性和根本要求,探索出既學習西方現代化國家的長處、又避免資本主義內在弊端的道路,從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2]習近平:《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埋頭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第9頁。。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立足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即提出建設“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現代化”最初主要指“工業化”,后來發展為“四個現代化”的完整表述。1954年,毛澤東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3]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建設現代化,是著眼“六億人口”的生活需求而提出的。新時期,出于對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力發展”的判斷,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對現代化的設想,從鄧小平的“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設想,到黨的十三大提出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都是始終著眼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的具體需求而提出的。
黨的十九大報告著眼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新成就、新問題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頁。,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緊緊圍繞這個社會主要矛盾推進各項工作,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頁。。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既繼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領導的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貫目標,又根據新的時代特點,闡明了新的歷史任務。“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表明人民的需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3]同上,第27頁。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核。而且,這里的人民,不僅指中國的“全體人民”,也具有世界的視野,即站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的立場進行現代化建設,不僅實現中國的發展,同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4]同上,第24頁。。
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警惕和批判,立足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兩點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點。就第一點而言,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就第二點而言,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視野是關注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境遇和未來發展,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5][德]馬克思、[德]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頁。這個“絕大多數人”,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工人階級”“無產者”,在列寧那里是“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是“工農兵及其干部”,是“人民群眾”,是“全體人民”。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內核界定為“為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贏得歷史上應有的文藝地位和美學權利”[6]董學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內核”是什么?》,《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5年“春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頁。,抓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據此出發,我們不妨以馬克思主義這兩個特點——批判資本主義、關注絕大多數人——來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公約數。說其是“公約數”,一方面是說,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不同理論形態都應具備這種特質;另一方面,公約數不是全部,在具備這一公約數的前提下,不同歷史階段的理論形態因時代語境、功能訴求以及理論主體不同,對公約數的顯現程度也是不同的,由此呈現出不同的理論面貌。以公約數的“同”和具體形態的“異”為依據,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與西馬文論各自的理論特質以及相互關系作一些闡釋。
四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德]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頁。馬克思主義是“解釋世界”的理論,更重視“改變世界”的一面。這道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一個特點,即不僅“解釋世界”,而且直接推動“改變世界”的具體實踐,或者說,本身就是“改變世界”實踐的組成部分。這里所說的“改變世界”,不僅指反帝反殖民、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實踐,而且也指在“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下,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打破了那種認為資本主義更優越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發展模式的論斷,在事實上形成了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始終和“改變世界”的現實實踐有著直接關系,比如,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李大釗、瞿秋白、郭沫若、馮雪峰等,同時也是革命運動、革命文藝的實踐者,其理論是服務于現實實踐的。到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直接推動、革新文藝實踐的行之有效的指導方針。理論主體和實踐主體同一,決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馬文論的一個重要差異,即是否具有通過介入文藝實踐進行思想動員、進而介入社會實踐的功能。對此,學界一度以“政治化”貶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不可否認,在特定歷史時期內,過度政治化帶來了理論的僵化,在實踐上造成了失誤。但理論要與現實結合,不可避免會介入政治,而且,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包括多數西馬理論家也從不諱言政治,不否認介入政治的必要性。
西馬文論的主體大都不直接從事訴諸現實變革的實踐,對他們來說,理論本身便是一種實踐,“實踐”更多在“解釋世界”層面。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現實實踐具有直接、密切的關系是優點,但也毋庸諱言,與西馬相比,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理論的沉淀、積累方面相對薄弱,未能像西方理論家一樣,不斷提出新的概念、范疇、方法,乃至構建體系、形成頗具特色的研究團體——這正是新時期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直試圖實現的目標。
對于西馬而言,縝密、系統的理論構建是其長處,其被引入中國后廣受歡迎,乃至一度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主流。[2]有學者指出,起初大學里只講經典馬克思主義,“但是后來,尤其是80年代中期后,‘西馬即馬’了。在有些高校,個別老師會覺得講‘馬’與現實有點距離,所以直接就從‘西馬’開講”。參見趙禹冰、張永清:《從現象學美學到馬克思主義文論——張永清教授訪談》,《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2頁。但如前文所述,對西馬一個常見的批評是其抽離了馬克思主義應有的政治經濟學維度。而且,如有學者指出的,西方對實踐的理解有另一條脈絡,即在精神領域內理解實踐,“往往把實踐歸結為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意志活動,這就把實踐主觀化、心理化、個人化、非理性化了,并在否定實踐首先是一種感性物質活動的同時,又把精神實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不恰當的強調和提高”[1]王元驤:《實踐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變革》,《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22年第1期,第57頁。。西馬亦受到這一理論傳統的影響。對此,我們一方面應加以警惕,另一方面,西馬重視理論批判、文化分析,強調人的精神層面的去蔽,忽視社會層面的變革,也并非全然出于主觀層面的輕視。根據佩里·安德森的描述,二戰后西馬從經濟、政治轉向哲學,有著深刻的歷史動因,即資本主義隨經濟的快速增長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打破了經典著作關于資本主義危機衰退或者危機即將來臨的預言,并提出新的問題,這促成了西馬的研究轉型。[2]參見[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铦、文貫中、魏章玲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63頁。因此可以說,西馬文論是具有批判意識的理論家面對其所處的現實語境與具體問題作出的研判,其理論短板是明顯的,“但是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即它們不僅都面向現實,反映著現代社會人們對文藝的內心需求,而且也是人們對文藝性質認識日趨深化的一種表現”[3]王元驤:《實踐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變革》,《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22年第1期,第56頁。,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和啟示意義。
因此,在批判資本主義這一維度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馬文論繼承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質,由各自語境和時代任務出發,作了各具特點的發展。不妨在堅持“批判資本主義”這一“公約數”的前提下,推動兩者進行對話、融合。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一方面堅持自身介入現實、助力實踐的品格,另一方面不妨借鑒西馬文論長于更新、創建概念、范疇、體系的長處。而且,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一些受資本邏輯主導的文藝現象、社會現象,有必要在理論上借鑒西馬文論較為成熟的理論思路,從他們對資本支配的現代性邏輯以及文化生產、人的精神狀況的批判性分析中獲取啟發。
在另一個公約數即“關注絕大多數人”而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因其與現實實踐有著直接關系,立足多數人的訴求以動員群眾、掌握群眾是題中應有之義,從左翼理論家對文藝大眾化的探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的強調,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都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絕大多數人”維度的堅持和重視。
而對于西馬來講,如果說早期西馬理論家盧卡奇、柯爾施與葛蘭西都曾直接從事革命運動實踐,那么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以自己的密碼式語言來說話了,它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愈來愈遠,但它對于工人階級的命運還是努力設法效勞并力求與之相聯系的”[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铦、文貫中、魏章玲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45頁。。時至今日,西馬在學院圍墻里的思考究竟有多廣泛的傳播面與影響力?精英主義立場、艱深的話語是否阻礙了理論的普適性與實踐效力?這些是西馬常遭到的質疑。而且,西馬文論更多是在理論層面推演,對實踐的復雜性估量不足,很多理論家對大眾的潛能缺乏認知,缺乏動員大眾的意愿和能力。
不過,就理論層面而言,“關注絕大多數人”也是西馬的潛在視野,即多數理論家都是將大眾的精神自由與主體解放視為理論工作的中心任務,比如,法蘭克福學派試圖將大眾從文化工業的欺騙與操控中拯救出來,本雅明賦予“機械復制”技術從傳統中解放藝術、為大眾所享有的動能,阿爾都塞力圖通過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揭秘拯救主體,還有霍加特對工人階級文化的描繪,拉扎拉托對當代西方“大眾智能”社會中“非物質勞動”的描述以及奈格里與哈特對“非物質勞動”之主體“諸眾”的革命潛能的分析,等等,發展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境遇的分析,試圖探求人的自由和感性解放的途徑。
讓我們回到馬克思的論述:“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2][德]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西馬固然缺少訴諸“物質力量”的路徑與能力,不過,其理論構想為擺脫資本主義社會“原子式”的個人視野的限制、打破資本宰制、重建大眾文化共同體等議題提供了啟迪。將其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野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武器的批判”的實踐效力相參照,發展其揭示西方現代性邏輯弊端的理論優長,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建構提供理論助力。
綜上所述,盡管表現形式和程度不同,但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馬文論皆繼承、發展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潛能,具有批判資本主義的視野與關注絕大多數人的維度,以此為公約數,經典、中國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之間具有深層對話的基礎和空間。當然,對話本身不是目的,在對話的基礎上,延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范疇,進而構建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效力的理論體系,才是關鍵所在。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頁。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同時,也將“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提上日程,并指出:“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要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頁。
“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道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旨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有機組成部分之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則應立足中國的文藝實踐,關注文藝新變,介入批評現場,帶著“中國的問題”回到經典、中國以及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武庫與土壤,進而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在問題及方法的碰撞中,在抽象和具體的往返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與當代品格的理論體系。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格局的改觀,也對下一步的理論更新提出了要求和挑戰。從中國的文藝實踐、社會實踐中發現問題,并通過解答、解決問題來充實、發展理論,應是今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