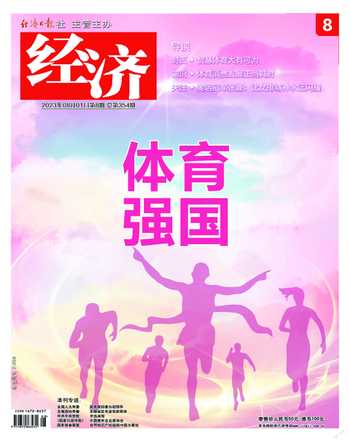專精特新:把性價比做到極致
馬明
1.2萬余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超9.8萬家專精特新中小企業、21.5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7月26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在2023全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大會上,公布了這組關于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的最新數據。
近年來,國家大力引導中小企業實現“專精特新”發展。《“十四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力爭到2025年,逐步構建起“百十萬千”的優質中小企業梯度培育體系。“按照此規劃,預計整個專精特新企業累計產出水平將達到10萬億元—20萬億元的規模,這對我國經濟穩定性將起到很好的基礎支撐作用。”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斌在接受《經濟》雜志記者專訪時如此表示。
數字化要“因企制宜”
作為增強我國經濟韌性與活力的重要支撐,專精特新企業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實施數字化轉型是必經之路。
在郭斌看來,對于數字化轉型的認知,目前普遍存在兩個誤區,需要厘清。一是很多數字化工廠和數字化企業的建設過于強調數字技術,認為引入大量的自動化生產線設備,再加上數據的應用,便做到了數字化,單純地把數字化看作是數字技術在制造上的應用。“它(數字化)只是一個工具和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要通過它來提升企業的整體運營水平和效率,增強市場競爭力,并帶來更多的業務增長。真正把數字化做好的話,要把信息技術融入到企業的業務運營和管理活動中。”他強調,數字化轉型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變革,還會對企業的文化、業務運營的基本方式,甚至商業模式產生影響。
二是很多中小企業擔心數字化轉型,因為不僅需要前期大量的投入,還要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郭斌表示,企業要了解,做數字化要與自身業務增長的需要結合在一起,不應該簡單地復制別人的數字化工廠到自己的工廠里。如果使用這種復制的邏輯,失敗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此外,如果企業自身的管理基礎能力太薄弱,盲目地進行數字化改造,也很有可能發揮不出數字化投資的效果。
對此,郭斌建議,企業不妨采取漸進的方式,找到自身業務運營中最主要的瓶頸環節,并以此為切入點開展數字化轉型,既能夠降低短期投入成本,還能夠通過市場回報來支撐進一步的擴展。另外,企業也可以使用Saas、低代碼等第三方提供的管理系統,將其與企業實施的管理策略相結合,在降低上云成本的同時,也能夠更好地進行數字化改造。
就管理能力而言,郭斌表示,這是企業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隨著野蠻增長時代的逝去,中國正進入新發展階段:增長速度變緩,并轉向結構性的增長。如何提升企業內部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基礎、優化企業的管理體系建設已成為當前一個重要的課題。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管理者和員工都要具備相應的對接能力。以管理者為例,首先,要具備從企業的戰略和業務增長開始的數字化規劃能力;其次,從實施的角度講,要具備變革管理的能力,因為數字化轉型是一場比較大的變革,涉及企業的方方面面;再次,要具備將IT技術和業務相融合的管理能力,既能夠理解IT技術,又能夠了解業務本身的狀況。
把性價比做到極致
受逆全球化抬頭、地緣政治沖突等因素的影響,當前全球制造業產業鏈正在加速重構。在此背景下,隨著勞動力成本上移,中國企業單純依靠人口紅利難以持續發展,未來發展的出路在哪里?
郭斌給出的答案是:充分發揮把性價比做到極致的優勢,并將這種能力復制到海外市場。
他認為,專精特新企業基于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定位,能夠很好地將市場響應的靈活性、高品質的要求和成本的優勢結合在一起。有些專精特新企業,雖然沒有品牌知名度,或者有品牌但沒有很強的國際影響力,但在參與全球產業鏈的競爭中,具備把性價比做到極致的優勢:在同等質量的情況下,做到產品價格最低;在同等價格的情況下,做到產品質量最優。
“把性價比做到極致,是中國企業獨有的一種優勢,西方的很多企業做不到,因為它們的定位邏輯是高質高價。”郭斌表示,我國企業能把性價比做到極致,是因為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具備完備的產業鏈。此外,我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單體市場,本土市場規模巨大,能夠為發展規模經濟奠定基礎,還是大型新興經濟體,擁有高度分割的市場。“拿手機來說,不管賣得多貴,或者賣得多便宜,在中國的每一個市場定位里都有大量的需求。這在西方的發達市場里是觀察不到的,它們往往很少有細分市場。這種獨特的市場情景是大型新興經濟體獨有的優勢,很難被復制。而且,中國企業還可以根據本土的需求進行市場化創新,比如,研發出雙卡雙待手機。”他進一步解釋道。
從發展的角度看,郭斌表示,未來有兩個復制經驗的機會。一個是復制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非洲、東南亞等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與中國相似,未來會走到與中國經濟發展類似的軌跡上。我國經歷過購買力不足的時代,無法承受高質高價的定位,非常了解這樣的區域市場的需求,因此要抓住擴展的機會,把中國這40多年來累積的制造能力和經驗復制過去。全球有70多億人口,有相當一部分人口并不處于發達市場,這部分的人口和市場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另一個是復制到歐美市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西方市場對價格開始敏感起來。歐美的一些企業開始關注性價比的產品,因為B端的企業有控制成本的需求,C端的用戶要把錢花在刀刃上,增強購買力。西方的跨國公司擅長做高質高價的產品,不擅長拼性價比,這就為中國企業發揮把性價比做到極致的非對稱優勢,擴張市場提供了機會。
增強創新策源能力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在創新能力方面,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共設立國家級、省級研發機構超1萬家,平均研發人員占比達28.7%,平均研發強度達8.9%,平均擁有有效發明專利15.7項。“相當一部分‘小巨人企業涉及的產品或業務領域往往與關鍵核心技術緊密相關。”郭斌說。
盡管我國涌現出一大批專精特新企業,從企業端彌補了某些關鍵領域的短板,但這遠遠不夠。整體上,我國在集成電路、光電顯示、精密儀器、工業軟件等領域仍然“卡脖子”,特別是從0到1的技術還掌握得太少,亟需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
郭斌表示,加快破解“卡脖子”技術難題,增強原始創新能力,首先要充分利用中國獨有的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以高鐵技術為例,從技術起點看,日本最早研發出高鐵技術,并于20世紀60年代建成世界上第一條高速鐵路——東海道新干線;從技術積累角度看,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龐巴迪等企業比我國企業擁有更好的技術積累。但如今,我國高鐵技術已經趕超其他國家。究其原因,一是其他國家缺乏廣闊的市場應用,而我國擁有海量的內部市場,能夠不斷提升內部的需求能力,客觀上為企業提供了試錯機會,不斷提升技術水平。二是高鐵技術具有長期價值,但短期內不太能夠獲得經濟回報。在這一點上,其他國家投資以短期目標為導向,純粹依靠市場機制運行,不利于發展高鐵技術。但我國則能夠發揮制度優勢,先后動員1萬多家企業和科研機構參與技術研發,后發趕超。
其次,中國的頂尖大學需要重回象牙塔,考慮如何推動科學前沿發展。在過去的40多年里,中國的頂尖大學做了大量圍繞企業需求的科學研究,離市場太近,離科學太遠。“科學的發展需要超脫短期的、純粹的市場需要。與技術發展的邏輯不同,科學的意義在于利用想象力,不應該有所限制,因為最有可能的那些答案往往在各個方向,甚至人們認為不可能的方向上,不斷試錯,才會出現。”郭斌強調,“以前因為發展環境比較好,我們可以從外部購買技術、引進技術。但接下來,沒有科學的支撐,我國技術想要上一個新的臺階幾乎不可能了。如何建立起發展科學、推動科學前沿的體系,是中國大學,尤其是頂尖大學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