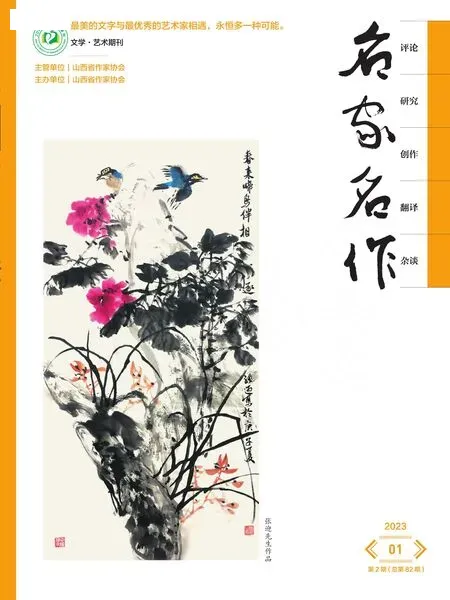基于笛卡爾、克拉里“暗箱技術”的觀察者形象視覺機制研究
張若曦 張 鵬
一、引言
在《觀察者的技術》一書中,喬納森·克拉里深入論述了笛卡爾和暗箱技術之間的密切關系。通過對笛卡爾的《屈光學》《第一哲學沉思錄》等相關文本的分析,克拉里把笛卡爾式的暗箱技術構建為17、18 世紀具有典范性的視覺認知模型,并指出這種視覺認知模型在19 世紀初遭到瓦解,從而被以多棱鏡和立體透鏡技術為典范的新視覺模式所取代。克拉里以視覺技術或觀察技術的變遷來描述藝術史的“范式轉型”問題,在當今視覺理論研究中獨樹一幟,但問題在于克拉里把暗箱技術知識框架與觀察者主體之間的斷裂歸因于其不能滿足日趨發展的新興經濟、文化和政治的需求,而忽視了笛卡爾視覺機制的局限性。因此,完全有必要重新考察笛卡爾和暗箱技術之間的關系,則有可能發現笛卡爾所隱含在暗箱視覺機制背后的科學排他主義態度,從而揭示19 世紀暗箱技術知識型被立體視鏡技術框架所取代的關鍵因素。
二、視覺主體的形成:笛卡爾與他的光學理論
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在1637 年撰寫的《屈光學》試圖通過機械粒子論的反射與折射原理,來完善阿爾哈曾(Alhazen)的光“入射理論”。在此前,中世紀的阿奎那—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體系卻認為我們能夠看見事物是因為物質潛在的可見形式,而這必須通過火焰與以太使觀察媒介變得透明方可實現。所以,如果沒有第三者的介入,人類的觀察必然是無能的,而這套主流論調也限制了中世紀視覺主體的形成。笛卡爾證明了在視覺方面人的廣延性也能把握實在本身,而這有助于視覺主體的形成。不過非常特別的是,笛卡爾是借助暗箱這種視覺技術裝置來闡述視覺機制,“暗室代表眼睛;小孔是瞳孔;鏡片是晶狀體,更確切地說所有眼睛的部分源自一些折射原理;白色的幕布是視網膜作為視神經末梢的組成部分”[1]。這表明笛卡爾把視覺當作機器去理解,這有助于我們去理解視覺的發生機制。事實上,笛卡爾不單把視覺當作一部機器去理解,更是把整個世界作為一部神創機器,以此來驅除教會神學對世俗的干涉。
在把暗箱和視覺機制進行類比的程序中實現視覺主體的形成,從中可以抽象出兩個前提:第一,我們需要一個觀察的本體論基礎。暗箱式的視覺主體形成伴隨著人文主義思想的興起,通過人類中心視角而不是通過神的無限去觀看世界,笛卡爾企圖建立起觀察的本體論基礎。“我要把我自己看成是本來就沒有手、沒有眼睛,沒有肉,什么感官都沒有,而且錯誤的相信我有這些東西。我要堅決地保持這種想法;如果用這種想法我還認識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斷。”[2]笛卡爾想要排除一切非廣延性的實體,從而通過理性的心靈把握實在本身。而在此之前,中世紀的經院神學拒絕以人類為中心的視覺認知方式,尤其是阿奎那把基督神學與亞里士多德主義結合起來強化了這種去主體的知識型,戴克斯特霍伊斯(Eduard Jan Dijksterhuis)指出:“幾乎任何領域都處于神學直接或間接的監管之下:純科學問題、天文學問題、落體和拋射體的運動問題、對氣壓現象的解釋問題……”[3]笛卡爾的本體論學說基礎在于對事物的質疑不能質疑其本身,這是一種思在的結果,在《第一哲學沉思錄》第二沉思這章中笛卡爾企圖塑造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純粹化視覺主體。第二,客觀性的視覺主體形成則需要科學性的描述方法,通過數學分析與力學的機械論模型試圖表達純粹化與客觀的認知方式。笛卡爾拒斥“感覺論”的干擾:“一個在戰場上激戰的士兵,在戰場上受到的傷感覺不到,不過當他退出戰場冷靜下來的時候,這個士兵感覺到疼痛……”[4]所以,如果物體可被看見,并不能說明物體本身能夠發光的感受是真實的,這無法成為視覺主體客觀認知的依據,笛卡爾依據粒子論的機械模型認為火焰與以太散發出來的粒子在物體上的反射和折射運動,使得物體的像在視網膜上呈現。通過折射與反射的數學幾何和粒子的力學機械論分析,排除了“感覺論”的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官能對它的混淆。
三、暗箱技術的隱喻:笛卡爾與克拉里的視覺考古學
笛卡爾試圖通過對“感覺論”的拒斥建立起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客觀世界,以反對自13 世紀以來的托馬斯主義神學體系對自然科學的控制和束縛。尤其在《屈光學》中,笛卡爾把人的視覺機制與暗箱技術進行對比,符合他把整個世界看作一部機器的機械論觀點,暗箱技術作為隱喻正是體現了這種機械論觀點,目的是為了建立客觀中立的視覺主體。而克拉里在《觀察者的技術》一書中對暗箱技術的知識型建構正是建立在笛卡爾的這個視覺隱喻之上,克拉里把笛卡爾式的暗箱作為技術主體構建為17、18 世紀的視覺模式。
第一,笛卡爾式的暗箱概念改變了視覺主體認知世界的方式,界定了內化的觀察者與外在世界的位置。具體而言,克拉里認為笛卡爾的暗箱隱喻指出:“暗箱的孔徑相應于一個可從數學角度加以界定的單一點,通過此點,世界可以借由符號的逐漸累積和組合……暗箱設計體現了人類在上帝和世界之間的位置。”[5]因此,這里的界定并不是任意妄為,而是通過數學角度加以把握。哈里斯(Karsten Harries)甚至認為:“笛卡爾贊成上帝用數學語言書寫了自然之書,人的思想和神的思想在這里協調一致。”[6]通過數學角度的界定,暗箱在笛卡爾這里被賦予了“上帝之眼”的形而上學稱謂,這使得視覺主體能夠借助暗箱去認知自然,而這種認知具有無與倫比的公正性價值。
第二,在《觀察者的技術》一書中,克拉里認為笛卡爾式的暗箱隱喻將觀察者從觀察者的身體之中分割出來,可以使視覺去身體化,而達到對視覺的客觀性認知:“對笛卡爾而言,在暗箱中觀察到的像就是透過去除身體的獨眼所形成,這只眼睛與觀察者脫離,可能連人眼都不是。”[7]戴克斯特霍伊斯也認為,13 世紀阿奎那—亞里士多德主義阻礙了對客觀世界的觀察認知。[8]笛卡爾在《屈光學》中表示如果我們想要通過視覺主體獲得一種純粹客觀的理性判斷,就必須避免靈魂受到大腦雜多感覺的蒙蔽。[9]因此,笛卡爾認為,這種蒙蔽方式的內在因素在于松果腺,作為共通感(common sense)的松果腺會接受外界其他不相干信息的干擾,而暗箱作為一種獨立的驅除肉體對其干擾的觀察設備獲得笛卡爾的青睞。所以,克拉里認為,“如果笛卡爾方法論的核心是要避開人類視覺的不確定性及感官的混淆,暗箱就正符合他的追求,將人類知識的基礎奠定在純粹客觀的世界觀”。
第三,笛卡爾式的觀察者借助暗箱技術形成一種“普遍知識”的關注。笛卡爾認為,世界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在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現在的狀態,這最終形成了笛卡爾的粒子論。笛卡爾對粒子論的闡述,使得普遍知識化具有了存在之球式的存在基礎。實質上,這里的普遍知識化,其實就是笛卡爾在《指導心靈的規則》中提出的“普遍數學”(mathesis universalis)。笛卡爾把自然科學與數學連接在一起,通過這種數學原理的演繹,形成普遍知識化的暗箱式觀察模型,從狹義上我們可以認為,人的心靈借助暗箱技術達到對世界普遍本質的關注與把握。
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克拉里試圖描述笛卡爾主義的暗箱隱喻如何把人的視覺機制喻為一種機械論的認知方式,以取代中世紀神學體系中上帝的觀察位置,從而使人作為觀察的主體達到從人至神的進步式提升。
四、無限與視角:笛卡爾與暗箱技術的局限
克拉里在《觀察者的技術》中指出三種暗箱與觀察者主體之間的隱喻,指出笛卡爾式的暗箱視覺模型在17—19 世紀之間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觀察模式,而暗箱技術隱喻在19 世紀的斷裂正是暗箱與觀察者之間關系的崩潰造成的,這預示著笛卡爾式的暗箱技術框架的破裂,但克拉里在本書中卻沒有指出這種斷裂所揭示的潛在性因素的內在機制。克拉里在《觀察者的技術》中認為暗箱知識型的瓦解是因為其無法滿足時代性的轉變需求,但為什么同樣是小孔成像原理的相機技術與當今時代能夠緊密關聯?
笛卡爾闡述光學原理的《屈光學》正是《談談方法》一書的附錄,該書是一本指導笛卡爾科學思想的方法論性質的書籍;換而言之,該書是《屈光學》一文的科學指導思想,在本書中笛卡爾以自傳的方式闡述了自己的方法論和科學觀。笛卡爾表明“真理”并不能由多數人完成,過去的傳統科學經驗(在這里笛卡爾主要指向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需要全部拋棄,并且指出除了自我構建驗證以外,任何哪怕有一絲可疑性的科學假設都應該予以拒絕。雖然笛卡爾與其他文藝復興以來的哲學家一樣都在力求拒斥中世紀阿奎那—亞里士多德主義科學體系,但是笛卡爾比其他哲學家更加強調對傳統科學的棄置,甚至認為唯有自我才能指導自己,除此以外都是不可靠的。
荷蘭科學史家科恩指出,“在笛卡爾看來,科學地完成既不在過去,也不在未來……或者更精確地說,交給了那位熱衷于獲得上帝允許人擁有的幾乎一切知識的思想家——笛卡爾本人”。笛卡爾不但徹底拒絕古代和中世紀的所有哲學以及科學的傳統,甚至認為自己就可以構建一個完美的世界圖景。笛卡爾對亞里士多德主義世界圖景的取代實際上固化了科學的發展,是與新科學(當代科學)的精神相左。對于觀察者而言,暗箱定義的單眼定點透視法所觀察的世界是一個單一固化并且具有排他性的觀察世界。可對于笛卡爾而言,這種固化的觀察方式正是構建一個透徹世界的必須方式,因為單一的觀察視角正如同他所塑造的世界圖景一樣具有極大的野心,那就是超越亞里士多德—托馬斯主義體系的局限性。而這種借助暗箱的隱喻試圖超越人類視角的野心導致了19 世紀科學理性的絕對化,這也就是克拉里所言的暗箱技術的“彈性”喪失了根本因素。這里我們可以得出,暗箱技術體系的瓦解是生理學進一步發展所造成的,這使得感覺經驗變得可控,其籠罩在感覺論上的神秘化得到祛魅。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暗箱技術所構建的認知機制崩潰以及被立體視鏡構建機制所取代的關鍵因素是與文藝復興時期對中世紀阿奎那—亞里士多德神學體系一樣,都是新型觀察方式對科學主體權威性的質疑,而這正是克拉里在《觀察者的技術》中所忽視的。雖然笛卡爾通過把心靈從外在物質之中排除出去從而為科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但是我們可以看出笛卡爾世界圖景體系仍然是一種全能的、不留余地的機械化世界圖景,企圖通過一己之力完成對整個世界的機械論構建。這表明,一方面笛卡爾嘗試通過自己機械論的世界構建調和歐洲宗教政治的互相傾軋,以恢復中世紀以來托馬斯主義所做到的那樣獲得權威性;另一方面笛卡爾試圖通過其科學體系的全能性以證明人性意志的無限。
因此,笛卡爾暗箱體系在19 世紀的崩潰與笛卡爾所構筑的科學圖景權威化之間存在必然性。笛卡爾希望借由暗箱技術去擺脫觀察者的固定視角所帶來的局限性,獲得一種超視角的觀察方式。因此,哈里斯又言,笛卡爾所認為的對人類視角的絕對超越實際上卻是固化的視角本身,因為其排斥了視角的多元性,笛卡爾式的暗箱技術實際上把觀察者囚禁在暗室之中,只能通過固定的觀看模型對世界進行觀察。
笛卡爾式視覺模型在19 世紀的崩潰,實質上就是混淆了實在與上帝存在之間的關系,把世界想象成一個已知的實體,而這正是造成笛卡爾世界體系固化的內在本質。因此,19 世紀暗箱技術所構建的視覺主體的崩潰在于其視覺模型拒絕對其他科學發現的兼容性,它試圖成為適應一切時代文化與社會的權力存在物,而這是不可能的。哈里斯在《無限與視角》的最后一頁指出:“如果求知是人類的本性,那么一次次地呼吁超越自己在世界中的偶然位置為其指定的觀點和視角,呼吁遠離曾被其稱為家的地方,也是人類的本性。”也就是說,面對人類的探索本性,即對視角的無限超越性,笛卡爾所構建的觀察體系終將被拋棄也是必然的,因為科學本身對權力的質疑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存在一種永恒的、歷史性的張力,而這正是笛卡爾所忽視的。
五、結語
本文試圖通過從視覺主體的形成、笛卡爾式暗箱機制的構建、笛卡爾式暗箱視覺模型的局限性三個方面漸進性分析笛卡爾與暗箱技術所構筑的視覺現代性問題,并認為克拉里在《觀察者的技術》中忽視了科學主體本身的權力模式。這導致了克拉里沒有從根本上對笛卡爾的觀察模型進行批判,而是表象地闡述19 世紀立體視鏡構建的知識體系對暗箱技術的取代過程。其內在原因是,笛卡爾所構筑的視覺機制研究,可以更好地發現科學主體公信力遭到質疑的主要矛盾。笛卡爾通過反對托馬斯主義的神學科學觀,實際上實現了對它的取代,而這實際已經違反了不斷進步的科學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