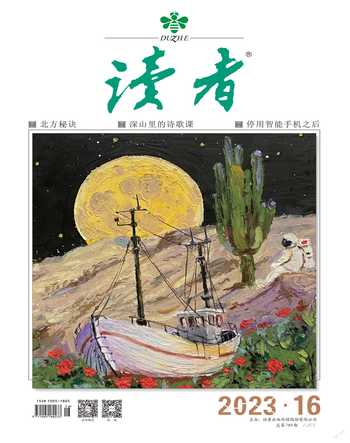物皆有情

“鴻雁長飛光不度”,鴻雁是一種候鳥:秋天時它們會往南飛,尋找比較溫暖的地方;春天來臨時,再往北飛。大概張若虛當時在長江邊,看到有大雁飛過。這剛好與“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形成呼應。
鴻雁已經飛過去了,可是它的光影留在河流當中沒有走。很難懂,對不對?
徐志摩的詩作《偶然》中有一句:“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講的也是這種意境,就是有一種東西經過了,好像不存在,但其實又存在。鴻雁飛走了,不記得自己留下了什么,可是河流記住了光、記住了影。張若虛非常巧妙地做了結構安排:前面是存在的東西,好像讓人感覺不到,也就相當于不存在;而不存在的東西,如果讓你有感覺、有深情,那它就像存在一樣。
不存在,卻成為永恒的存在,這其實是一種哲學層面的“對仗”關系。
宇宙之間存在的東西常常因為我們看不見,變得不存在;可是看似不存在的東西,如果你在意,也會變得存在。“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文”就是波紋。
張若虛在江邊,看到江面有很多波浪和水紋,是因為底下有魚和龍在翻騰,可是魚和龍并不知道波紋的存在。
沈尹默寫過一首詩——《三弦》。有一個人在土墻背后彈三弦,詩人走過,聽到了,感受到彈奏者的哀傷,就寫了這首很有名的詩。可是這個詩人并沒有看到彈三弦的人,彈三弦的人也不知道他影響了一個詩人。
宇宙之間有很多因果,我們常常覺得某個東西微不足道,可它的力量其實很大。每一個存在的個體,對別的生命都是有影響的;我們自己的生命狀態,常會使別的生命發生改變。
張若虛從“扁舟子”開始,帶出一座虛擬的“相思明月樓”,然后是一個虛擬的女性,虛擬的“愿逐月華流照君”。他說,如果你對生命有深情,一切看起來不存在的東西,都會變成你在意和珍惜的部分。
在這個世界上,當你對許多事物懷有深情時,一切看起來無情的東西,都會變得有情。鴻雁長飛,可光影會被記憶、被留住。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對于其他的生命可能不重要,可是對這天晚上的張若虛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有意義。他看到了鴻雁,看到了魚在翻騰,看到了水面上的波紋,然后留下了一首詩。
一千多年以后,我們在一個好像跟詩人毫無關系的環境中讀這首詩,感受到了張若虛當時感受到的生命狀態。
這首長詩非常像一曲交響樂,春天、江水、月亮、夜晚在詩中對話,組成好幾個樂章。
(林右右摘自湖南美術出版社《蔣勛說唐詩》一書,趙希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