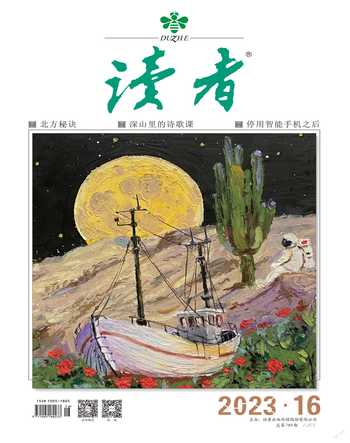外婆是美人
薛舒

外婆是美人,從對她有記憶起,我就這樣認為。尤其是我小時候,更是覺得世上沒有比外婆更美的女人了。
放學回家,剛進樓道,我就發現外婆來了。她站在走廊里的煤球爐邊,爐子上坐著一口鋼精鍋,鍋正冒熱氣。我大喊:“外婆!”她扭過頭,大眼睛笑盈盈,鵝蛋臉,墨綠色棉襖罩衫正合身。“要吃肉湯團,還是黑洋酥湯團?”肉湯團自然好,可黑洋酥湯團也是好的,我糾結起來。她不等我回答,已替我決定:兩只肉的,一只黑洋酥的。她的決定總是合我心意,她還總是那么好看。好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來,我就能享用各種美食,這一天,我便可擁有充沛的快樂。給孩子帶來快樂的人,就是美的吧!
我的學齡前生活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外婆生養了七個子女,我的母親是老大。那是我備受寵愛的黃金歲月,阿姨、阿舅們都圍著我轉。我騎在小舅肩膀上去鎮上的大禮堂看新上映的電影,下雨天被小姨背著送去幼兒園,外公每天下班回家給我帶一個面包或者一卷山楂片……
某日,外婆做的午飯是雪菜肉絲面,我不愛吃面,噘嘴生氣,纏著外婆要吃別的。外婆捧著一大碗湯面看著我,大眼睛一亮,笑盈盈地說:“不要吃面?那,要不要吃糕?”
“要啊!”我大喜,“什么糕?”
外婆不知從哪里摸出一把量衣尺,臉上依然掛著盈盈的笑意:“竹板糕,拿手來。”
我縮手逃竄。她竟然還笑,笑出了哈哈聲,惹得阿姨、阿舅們也哄然大笑。伴隨著七八張嘴吸溜面條的聲音,一家人倒吃出了一屋子層出不窮的喝彩。
教訓小孩時也要笑著,這樣的人總是美的。
上幼兒園大班時,我開始臭美了。二姨給我織的巧克力色小毛褲剛完工,藏在外婆的衣櫥里,天氣還不夠冷,她們不讓我穿。外婆開櫥門的時候,一不小心露出了櫥底的一片絢麗。“那是什么?”我問。外婆干脆把它們拿出來,一件件抖開,緞子旗袍、織錦夾襖、對襟綢布短衫……她念叨著,略顯粗糙的手里,那些漂亮衣服閃爍著絲織品細膩柔軟的光芒。我從未想到那些只在老電影里見過的漂亮衣服,會在外婆的衣櫥里出現,這讓我頗為吃驚。外婆帶著一臉神秘的笑:“猜猜這是誰的?”
我脫口而出:“我的。”
外婆又笑:“才不是你的,是我的。等你長大,要出嫁時,讓你選一件。”
我跳起來,撲向一條水紅色繡花香云紗裙。外婆一把摟起所有衣服:“不是現在,是以后,等你長大。”
好吧,等我長大,就可以選擇其中的一件穿上,也做一回美人。可是,擁有這么多漂亮衣服的人,才是最美的那一個人吧!
我愈發認定了外婆的美人屬性,雖然,我從未聽到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說她美。
那一年,大舅從云南回上海。大舅要結婚了,婚房就是外公外婆那間寬敞的臥房。打掃婚房的那一天,外婆把大衣櫥里的舊東西一樣樣搬出來:日常衣物、被面枕套,以及壓箱底的緞子旗袍、織錦夾襖、對襟綢布短衫,還有我看上的那條水紅色繡花香云紗裙……
整理完衣櫥,又整理紅木鏡臺——那張有著十多個抽屜和一面大鏡子的桌子。外婆打開中間最大的抽屜,一本厚重的相冊赫然躺在其中。外婆搬出相冊,翻開。第一頁,一張黑白照片,大約六寸,穿白色婚紗的新娘,頂著一頭鬈發,鵝蛋臉光滑白嫩,卻沒有笑容,只一副平靜得有些刻意的表情。她身邊站著的新郎,是一位儒雅俊朗、西裝革履的青年男子,有著挺直的鼻梁、細長的眼睛,瘦削、白凈。我驚叫起來:“外婆,這個新娘是你嗎?可是你身邊的新郎是誰?外公嗎?”
我一邊確認這個儒雅俊朗的白面書生是外公,一邊比對著那個雙眉間鑲嵌著憂慮的中年男子。對,那時候外公頂多只是個中年男子,可他總是駝著背,儼然一個“老頭”。這個少見笑臉的“老頭”,在照片里居然帥得那么干凈、純真、無瑕。
外公竟是個美男子。這讓我有些意想不到。那么帥氣的他,什么樣的女子能被他愛上呢?我第一次懷疑起外婆的美來,在我眼里一向擁有無敵之美的美人,似乎也難以做到與他般配了。我捧著相冊,甚至有些憂愁。
外婆不停地收拾著東西,嘴里還不忘講故事:“那時候,我19歲,我姆媽講,妹妹長得最難看了,不過也要嫁人的。你外公來提親時第一次到我家,媒人領著他那邊廂進了宅子,我嫂嫂這邊廂就喊:‘來了來了,妹妹快躲起來。他坐在客堂里與我爹爹講話,我躲在廂房里,拉開一條門縫看他,只看到一個側臉,高鼻梁、白面孔……后來,他就常來我家了。”
外婆捏著抹布擦著鏡臺抽屜里積淀的塵埃,不自覺地哼起當年的老歌老調,眼皮一抬,目光像陷入熱戀的年輕女孩。19歲的姑娘對未來的憧憬,除了美好,還會有別的嗎?
可是,生活似乎并不僅僅是美好的。很多年過去了,跌宕起伏的生活早早把外公磨成了一個愁容滿面的小老頭,卻并沒有把憂愁種植到外婆的臉上。外婆臉上依然掛著盈盈的笑意,眼睛依舊大,只是眼角布滿魚尾紋,鵝蛋臉也已松弛。湊近了,隱隱可聞到雪花膏的香氣,剛燙過的短鬈發里夾雜著幾絲霜白,這讓她的美,竟帶了些許克制與深沉。
大約就是從那時起,我便確信了外婆之于我有特殊的“美”的感覺。長大后,每遇需要送外婆禮物的日子,我都會挑選粉底、口紅、面霜之類,她亦總是歡喜地接納。在家族聚會的日子里,外婆常略施粉黛、淺笑清悅。偶爾,在我的鼓動下,她還會哼起那些老歌老調,聲音自是已難婉轉,臉上的表情卻還是真摯與歡喜的——眼睛不再是玲瓏的大,眼皮有些耷拉,目光卻是醺然的,一副美人陶醉的樣子。
外婆于92歲高齡去世,我們舉家回老宅參加葬禮。母親、姨母和舅母們唱著有歌詞的哭喪調,內容卻不全是痛楚與悲苦。她們哭唱著困難時期外婆自制的美味“月餅”,哭唱著外婆曾經打開神秘的錦盒讓她們在琳瑯滿目的物件中挑選一樣傳家寶,還有,外婆講過的數不清的笑話和故事……我在送葬隊伍里,聽著她們婉轉而又悠揚的“歌哭”,忽然覺得那不是哭喪調,而是一首首詩,明亮的、清越的、歡愉的詩。詩中的外婆,就是一個樂觀、豁達、通透、溫柔的美人,就像在我小時候,她對著我笑盈盈地說:“不要吃面?那,要不要吃糕?”
一場葬禮,就這么變得祥和起來。果然是美人,因為美,離別也變得不再凄厲。
可她到底長得美不美?我從未向任何人求證過,我知道,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把美留在了我的心里。
(十 三摘自《解放日報》2023年4月6日,曾 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