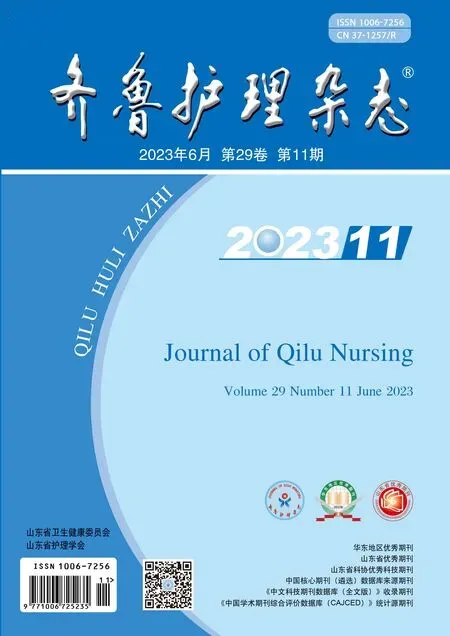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老年人生命質量研究進展
王 寧,季 紅,宋菲菲,孫康明,徐真真,張文忠,李 靜
(1.山東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 山東濟南250355;2.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山東省千佛山醫院;3.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
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我國人口轉變也在發生,而人口老齡化則被認為是其首要特征。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8.7%,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3.5%,與2010年相比增長5.4個百分比[1]。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老年撫養負擔將持續加重,成為我國在新時代所面臨的重大挑戰[2]。在此情況下,機構養老作為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關鍵支撐,被賦予了滿足老年人多層次和個性化需求的重要使命,成為很多家庭的選擇[3]。老年人群生命質量狀況是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社會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標志[4]。WHO將生命質量定義為:是針對個體所處的文化、價值觀的背景下,憑借一定的標準對自我及周圍環境的認知評價[5]。但實際情況來看,相比較家庭、社區,養老機構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處于最低水平,且還在持續下降中[6]。因此十九大報告指出,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作為國家戰略目標,進一步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醫養結合模式應運而生,其強調醫療與養老并重,能夠一定程度上提升養老的服務品質。政策和模式的調整實為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做出努力,滿足健康老齡化的戰略發展要求。因此,本文綜述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入住老年人的生命質量現狀及影響因素,為進一步提高養老機構服務水平,推廣醫養結合模式,提升機構入住老年人生命質量,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目標做出努力。現綜述如下。
1 基本概念
1.1 生命質量 也稱生活質量、生存質量,沒有統一的定義。WHO將其定義為:是針對個體所處的文化、價值觀的背景下,憑借一定的標準對自我及周圍環境的認知評價[5]。Lawton[7]則認為生活質量是一個多維概念,應從結構和內容兩方面進行衡量,結構上包括評價、個人標準、社會規范、人與環境等客觀標準;內容上包括行為能力、感知、心理等方面。鄔滄萍[8]認為生命質量是指身心健康,是生活質量的延伸定義。總結來說是涵蓋社會、醫學、心理等一定的標準來評估個體生命素質的一種健康測量手段,本文沿用鄔滄萍教授的定義,即反映人們的身心健康狀況。
1.2 醫養結合 王黎等[9]學者認為醫養結合是通過健康管理、專業護理及個體生活照料為老人提供連續性照顧的服務體系。佘瑞芳等[10]學者對醫養結合的概念進行分析后得出醫養結合是由政府統籌規劃,整合社會資源,對老年弱勢群體提供醫療、康復、生活、心理、臨終關懷方面的服務。另外,醫養結合并不單純強調醫院和養老院的結合,更多的是一種養老思維的轉變,不僅重視醫對養的關鍵作用,也不忽視養對醫的積極作用,最終滿足所有老年群體的養老服務需求,這才是醫養結合真正的內涵所在[4]。主要包含三種形式:公立醫院設立老年養護病房(內設式)、養老機構內提供醫療服務或與醫院簽訂合作協議(合作式)、家庭醫生進駐社區。
2 生命質量評估工具
2.1 歐洲五維健康量表 歐洲五維健康量表(EQ-5D)因其簡明、方便,是目前世界上應用范圍較為廣泛的一種生存質量測量方法,包括行動力、自理能力、日常活動能力、身體健康、心理健康5個維度,沒有困難、有些困難、極度困難3種水平[11]。但使用時需結合效用值換算表,Liu等[12]開發出適用的效用值積分體系,總分為0~1分,得分越高表明生命質量越高。
2.2 生命質量健康自評 生命質量健康自評(EQ-VAS)是EQ-5D的其中一部分,其代表是20 cm的刻度尺,末尾到頂端總值100分[11],受訪者通過打分反映健康狀況,分數越低代表健康狀況越差[13]。有學者表明,EQ-5D和VAS連用可從多個視角反映測量群體的生命質量[13]。
2.3 健康調查簡表 健康調查簡表(SF-36)共36個條目,包含生理和心理健康兩部分,共8個維度,較為全面地詮釋了生命質量的內容定義。SF-36的測量范圍廣泛,簡便易懂,信效度較高,可廣泛應用于一般人群的健康狀況和老年人群生命質量的評估中[14]。
2.4 連續性記錄與評估工具 連續性記錄與評估工具(CARE)是美國聯邦政府開發的統一標準化的綜合評估工具,能夠客觀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和照護需求,主要包含醫療狀態、功能狀態、認知情況和社會支持4個方面[15]。姜彩霞等[16]將其應用于醫院和養老機構的老年人,均顯示其良好的信效度。
3 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入住老年人生命質量研究現狀
3.1 醫養模式下,生命質量得到明顯提升 根據現有文獻總結,多數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入住的老年人生命質量普遍較高。胡秀香等[17]學者促成養老機構與社區醫院簽訂合作協議,制訂并實施醫養結合方案后結果顯示,入住老年人在生存質量、健康、心理、社會關系等領域都有明顯的改善,醫養結合效果顯著。唐怡[4]進行醫養與非醫養養老機構老年人生命質量的對比研究發現,除生理領域差距不明顯,心理、社會關系、環境領域都高于非醫養結合養老機構老年人的生命質量。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逐漸退化,漸漸感覺到力不從心,進而產生依賴感。另外印度學者調查發現,居住在醫養院的老年人心理幸福感高,其總體生命質量更高[18]。
3.2 不同形式的醫養機構存在顯著差異 基于醫養結合不同的表現形式,其老年人生命質量狀況卻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汪小杰等[19]調查發現,合作式機構老年人生命質量普遍低于內設式機構。分析原因可能與合作式機構提供公共資源少、服務供給層次低,加之處于經濟地位劣勢的老年人,往往被迫入住醫療服務等級低的傳統機構,衛生需求得不到滿足有關,進而造成生命質量的下降。
3.3 國外醫養機構生命質量呈現較低水平 與國內情況不同的是,從國外研究來看,受多種因素影響,入住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處于中等以下水平,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挪威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罹患癡呆、中風、心衰、癌癥等慢性病的老年人數量多,且將近半數居住在提供醫療和護理服務的養老院內,受養老院服務等級的限制、護理人員知識素養等原因導致該部分老年人群體身體殘疾和社會需求得不到滿足;煩躁、抑郁等心理問題頻發,其生命質量往往得不到提高[20]。巴基斯坦學者Siddiqui等[21]將居家養老與機構養老中老年人的生命質量進行對比發現,醫養院中老年人不僅總體生命質量偏低,細化到各個領域上其生命質量也呈下降狀態。這提示要重點關注老年弱勢群體,從不同角度、不同領域探索解決方案,以促進總體生命質量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地域文化、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越南學者Dung等[22]報道,居住在養老院的老年人其生命質量處于中等水平,與國家受集體主義文化影響有關,他們認為居住在養老院代表著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獨立自主性,并加重了孤獨感。未來隨著長期護理服務政策的開展執行,保持較高的生活質量將逐漸成為促進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主要目標。
3.4 醫養機構入住老年人生命質量的影響因素 根據機構間的對比發現,除去年齡、性別、社會支持、家庭和睦情況、子女負擔水平等共同影響因素后,仍顯現出影響入住醫養機構老年人生命質量水平的維度,總結如下。
3.4.1 生理健康 多項研究發現,慢性病患病情況是導致老年人生命質量各領域評分下降的重要影響因素,其患病的種數、類型、嚴重程度、是否存有后遺癥,都有可能造成生活自理能力的降低或喪失[23-24]。這也間接證明了生活自理能力對生命質量的影響,王萍等[25]研究發現,生活自理能力差的老人,其生命質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與李卓航[26]研究結果一致。徐東麗等[24]則發現,身體活動能力評分低的老年人,其反映生存質量的生理和心理維度得分均較低,而對身體活動能力差的老年人進行針對性、個體化的醫療護理干預,將會大大提高入住老年人的生存質量。其實不論是醫養或非醫養機構,健康狀況差的老年人生命質量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這類人群會更傾向于醫養機構的選擇,這也提示機構要重點關注入住老年人的健康狀況,盡早開展積極有效的慢性病預防管理措施,提供高水平的醫療護理服務,延緩疾病的進展,維持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從而提高其生命質量。
3.4.2 心理健康 多數研究來看,機構提供的精神慰藉服務對老年人心理健康有顯著差異,尤其表現在精神健康方面,也間接論證了醫養結合的服務模式便于滿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改善入住老年人的生命質量[27]。與韓磊[28]調查結果一致,入住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較高,且平均居住時間遠長于普通養老院,都體現了醫養結合模式的漸進效益對提高老年人生命質量的長遠影響。而老年人作為慢性病的高危人群,其對生命質量的影響逐漸受到重視,這一部分人群也是選擇醫養院的主力軍,體現了醫療護理服務水平在機構養老中的重要地位[23]。另外有研究發現,心理健康水平良好的老年人生命質量評分優于心理狀態一般的老年人,而心理健康維度是衡量生命質量較為客觀的一項指標,這也很好地體現了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在提供精神、心理健康服務上效果顯著,也提示我們更要關注老年人的情感訴求,配備專業的心理團隊,使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28]。幸福感是一種積極樂觀的情緒,它與生命質量息息相關,與有關研究結果一致,認為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對其生活質量有正向引導作用。但還未有醫養結合養老機構入住老年人的幸福感體驗研究,未來可納入評價體系中,有利于促進養老機構服務水平的提升。
3.4.3 社會學因素 多項研究表明,社會支持在保障老年人生命質量中產生了深遠影響,除國家政策、家庭的影響,老年人入住后由于環境的改變,產生心理依賴性的對象變更為機構中的醫務人員,他們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則與老年人的生命質量有著顯著的相關性[28]。唐怡[4]學者對居住在南京市醫養結合機構中的老年人進行調查發現,教育水平高、退休前有固定職業的老年人,其生命質量得分較高,他們大多能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健康生活,有著較強烈的健康促進意愿及實施自我保健的行動力。因此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還要多維度、全方面地分析老年人的生活背景,給予老年人一定的身心慰藉。有調查發現,宗教信仰對醫養院入住老年人的生命質量有重要影響,每個人都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宗教信仰在緩解老年人負性情緒、改善人際關系、增加社會參與等方面有積極意義,這要求老年人若有宗教信仰方面的訴求,機構應給予相應的尊重,但要進行引導與管理,不可產生盲目信教、違逆自然觀念的行為。有學者將醫養融合服務滿意度作為自變量納入老年人生命質量影響因素中,發現老年人對服務越滿意,生命質量則越高。進入老年的一大特征便表現為養老與醫療問題的融合,老年人又是醫養結合模式下的最大利益者及直接感受者,而這一指標包含助餐、助潔、助醫、轉診等服務評價標準,通過該指標進行評價更能體現出機構的服務水平與能力。
3.4.4 經濟學因素 醫療保險作為老年人生命安全的保護因素,在提高老年人生命質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4]。全民保險的價值將會在未來長期照護性護理模式政策的推動下逐漸體現,人民始終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另外,月收入水平也是老年人生命質量的影響因素之一。有研究指出,開展的多數與醫療服務和康復相關的項目都是需要另外單獨支付的,不作為醫保項目的報銷范疇,導致月收入水平較低的老年人將會在選擇機構服務方面受到很多的局限性,進而影響生命質量[28]。隨著老齡化形勢的嚴峻,醫養結合之于老年人便體現出其重要性,而這都離不開國家、政府政策的開展、推進、實施,并為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清除障礙,打破阻力,以保障老年人的生命質量。
4 提高老年人生命質量的對策建議
4.1 政策引導 在健康中國的大背景下,國家及政府層面應大力完善和推動醫養結合相關政策的提出與完善;在疫情當下更要重視智慧醫養的作用,構建智慧醫養平臺,便于調整養老政策,推動機構間信息共享;醫保方面制訂針對老年人群的慢性病、大病保險補貼政策,另外可鼓勵商業醫療保險的加持,全方位保障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4.2 機構內調 結構框架方面,考慮在社區、機構養老的基礎上增加醫養結合服務即合作式機構,拓展衛生社區服務中心的工作內容,但要加強公共資源的供給,建立起合適的醫養服務方案,提高醫療服務水平,滿足老年人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機構服務人員方面則更應關注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幫助其做好慢性病管理,指導體育鍛煉,延緩疾病進程;并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定時開展一對一訪談,及時察覺到老年人是否存在焦慮、抑郁情緒,并進行調整干預。
4.3 社會參與 本研究人員曾經調查過基層醫養院,為了看護方便,大多限定老年人活動范圍,使較多自理能力高的老年人產生抵觸情緒,甚至誘發心理問題。因此應增加社會工作者團隊干預的機會,讓老年人不再覺得自己是被禁錮在養老院的、孤單的個體,還可收集老年人的興趣愛好并舉辦相應的比賽,給予相應的獎勵,提高積極性、成就感和幸福感,不固步自封,努力實現健康老齡、成功老齡的目標。
5 小結及展望
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醫療與養老需求的激增,醫養結合作為一種新興養老模式方案,將逐漸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生命質量能夠反映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水平,是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生活的評價標準之一。關注醫養結合機構老年人生命質量狀況,對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目標具有積極影響。從現狀來看,普遍入住醫養結合機構的老年人其生命質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機構能較好地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的健康支持和綜合性的社會支持;但從發展狀況來看,醫養結合模式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因此國家在推行醫養結合政策時,應出臺相應配套制度,如利用稅務優惠政策和制度擴大醫保報銷范圍、結合我國老齡化的社會特點,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等,維護老年人晚年權益,滿足老年人多方位的健康需求;政府應簡政放權,下放一定權利到相關部門,縮短層層申報的時間,真正、快速地解決實際問題;還可以尋求與市場相結合的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源力量的加入,以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機構負責人應努力提升養老機構服務水平,明確養老服務項目的開展方式,根據省市級情況、收治對象的實際需求,制定收費標準。未來,可對醫養結合機構關于入住老年人生命質量評價監督機制的建立進行研究,為能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