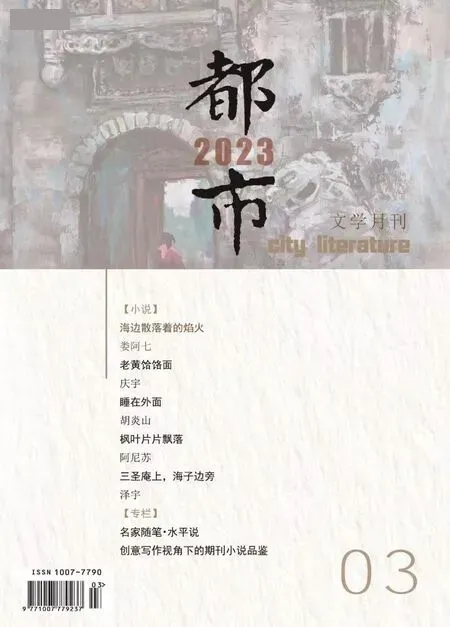走過時間
文 葛水平
壹:記憶是從氣味開始的
文字斑駁地記錄著老時光。北方的麻頭紙,再生環保。我還記得童年,植物的纖維,每次被平篩托起,即成一張紙。紙,有厚、有薄、有疏散、有凝聚。碼放在窯洞里的炕箱上,墻皮一樣的紙,粗糙里蘊含細膩,細膩里潛藏豁達,和風麗日中晾干,既浴著明媚干凈的陽光,又把光照消減在了蔭涼之外。
鄉人叫它黃草紙。
冬天的黃草紙糊在窗戶上,整個村莊都很懷舊,鐮刀似的月亮挑在樹梢,猜不透,窗外雪地上一長串狐貍腳窩,它的三寸金蓮盛滿了各種故事,與生活有關,與風霜有關,與情感有關。
糊窗紙沒有捅破之前,我聽一個女人喊:
“雪啊,涼啊,屁股蛋子掛了霜啊。”
空空蕩蕩的,站在千年文化的凝結點上,只要生活語言仍然沉浸在泥水里,這種一脈相傳的生活,總是牽掣人既溫馨又心動。山風不時撲打著窗格子“噗、噗、噗”,一股歲月沉淀的氣味冉冉飄起,驚異之外,我感到迷醉。風攜帶著雨水,那雨滴是那么的清亮和圓潤。
“雨來了。”
雨把屋子里想開腔說話的念頭壓了下去。雨讓暑氣消減下來。天光在窗戶前放下心事,屋檐下的雞狗們團成蛋,空氣里是泥巴被雨水濡濕的、清冽的味道。有一滴雨打在黃草紙窗格上,彈走了一只蒼蠅,雨聲隱去了蒼蠅的拍翅。赤腳就著石板桌凳寫作業的少年干號著跑回窯,黃草紙裝訂的作業本被雨淋得濕漉漉的。一個性躁又頑皮的孩子,聽不得大人的罵,吸著清鼻涕,惱上心來,跑進雨中。大人說:“叫他去害吧,驢脾氣,躲著,不招他。”
雨水滲漏在窗戶紙上顯出斑斑點點的漏痕,甚至漏在窗欞上,如果說一個人不需要所謂的遠大理想,守著舊屋,生命最天然的進程,也許最符合自然的生息、吐納、藏露,醒著,又糊涂著,不在乎那山外的世界,多好。
從前的黃草紙在窗格上,透過陽光能夠照見那些浮動的麻皮或者桑皮經絡,親切得讓你覺得如體內的血液流動。
我似乎總是想起從前,從前的心愛之物,陽光裹起密集的塵土,慢慢涌動著,親人們穿梭在中間,有一點兒生存的荒涼味道,風吹動他們的衣襟,而籠罩在這一切之上的是一股擴散開來的牲畜味兒,那一瞬間被惶惑了,最好的命運被篡改了,是什么樣的魔術手破壞了原有的秩序?
奇怪的是,事隔多年我站在故鄉山神凹的山脊上,村莊里的一些人和事如在昨天,或是由各種關系將我的從前與之聯系在一起的理由,或許出于不曾有過任何生活的記憶,或許因為不曾記得的矛盾,甚至一場單純的口角,那么多年過去了,依舊記得他們在黃草紙張滿窗格的天光下扭腰吊胯時妖嬈的身姿。
這些記憶是扎了根的,在心里,有時候做什么事情,也不知為什么就感覺從前非常熟悉地來了。
貳:歲月輕得像逝去日子的旁白
那些清新的人間柴煙味道的生活,讓我再一次回到尚不算遙遠的青春時代,回到那些已經在無數次的記憶中經過過濾留存下來的明月當空的日子,那些日子里有我們共同的卑微。
蟬鳴柳梢,一條清溪映月,時間似乎抹去了我的現在。站在山神凹河邊,河里沒有了漚麻的清溪,蜿蜒的河流用溫柔的力量引導著山脈朝不同的方向奔涌。我問河柳,你在守望什么?時間令你頑固地留守在這里,你的葉片如竹,我一直認為你是北方的竹子,北方的,有秋的意緒、夏的紛亂。蟬在許多年前落在柳樹枝梢,可知覺,蟬鳴時夏已經深了。
那時的土地并不荒涼。在灰色的秋光里,在漸漸強勁的北風中,因柳樹失去水分,柳葉將變得枯黃腐朽,風一吹如零零散散的日子紛自落下。很多年前,我和活在人世間的父親去河道里看過漚麻,漚麻上浮著綠茸茸的綠藻。故鄉人叫“蛤蟆咦”,麻如細蛇,中氣十足的蛙鳴在漚麻中搖搖曳曳鳴唱。
在曖昧的黃昏與白晝的邊緣,在迷蒙的晚夕的幻覺中,時光異常短暫,河流如同針線一樣串起了我的從前。
二十多年前,小爺葛起富從山神凹進城來,背了一蛇皮袋子雞糞,卷了兩刀黃草紙。小爺進門的影子給陽光蒙上了一層憂傷的情緒,屋子一下陷入一種迷蒙的絳黃中,讓人惋惜所有的失去是從看見時就開始了。
那一袋子雞糞隨小爺進得屋子時,臭也擠進來。小爺進門第一句話說:山神凹河細了,細得河道里長出了狗尿苔。
嚇我一跳。幾輩人指望喝河水活命,河斷了。小爺說,凹里人陸陸續續搬走了,河水斷流,人脈也就斷了。這兩刀黃草紙是要等我和你爸爸百年后用來剪“門頭才”,黃草紙比粉連紙耐風刮。
故鄉人去世,都要擇白紙剪成條狀,條數與死者年齡相同,砍斫一鮮柳木棍,將其縛于棍上,懸于大門外,男懸于門左,女懸于門右,出日,與棺木同葬。有些地方稱之為“紙骨朵”“歲數紙”,有些地方則稱之為“靈幡”。
幾年后,小爺和父親相繼去世,兩刀黃草紙派上了用場。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情緒攫住了我,那是憂憤和傷感,更是神秘。“門頭才”昭示著土地上生長的一些簡單的想法:黃草紙比粉連紙耐風刮。人生,痛苦似乎輕而易舉,實際上卻萬分艱難。歲數也許是一個人活著時化解痛苦的勝利,生死攸關的事縮減為一“骨朵”紙的存在,下葬時,亡者帶走了自己的歲數,帶走了人世間最后一串被遺忘了的樂天知命的數字。
窗戶上的窗花褪去了紅色,桃花在窗外粉白成一團,一只壁虎爬在窗欞上機警著眼睛,因為沒有見過屋子里有太多的人出入,它像一個充滿好奇的孩童,認真打量著躺在炕上陌生的熟悉人。
一場雨過后,我看到院子里用了祖輩的破水缸,聚集了雨水,風過時泛起一輪一輪的漣漪,我的心一下就起了難過。“個人即便來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
張愛玲的話,總是觸動我內心的哀婉,盡管一切都會成為過去。
惶惑之間又想起和小爺、小奶面對面坐在炕上說話,灶臺上鐵壺里的水冒著白氣。
小爺講當年制作麻頭紙的記憶:“工序有十八道。”
二尺半長、一尺二寬的黃草紙,“水中銀花現,簾上白云升”,可知,“古時候,朝中重臣向皇上進諫的奏折、民間向官府申訴冤情的狀紙,或制作鞋底、糊窗、裱房屋、訂賬簿等,都用的是黃草紙。”為你遮過風擋過雨收留過浪跡心情的住處,一年一年糊窗時總是把那些紛至沓來的人與事牽引到眼前。
叁:時間帶走了一切
山神凹后來只剩下一戶,我喊他叔。叔的一只眼睛害病,核桃大的包塊,臉上表情憂郁,落落寡合。我坐在叔對面的炕上,天光映照得人臉有點煞白,叔難以消弭內心巨大的悲涼,定定地看著我,彌漫在空氣中看不見的氣息,似乎被我捕捉到了,它喚醒了我對眼前人一再走失的惆悵。
叔說,一輩子沒有求過你啥事,我這眼睛,去年秋天收罷糧,眼疼,以為是秋蟲招了一下,生疼,慢慢就腫了核桃大,生膿,膿把眼睛糊了。娃領我去大醫院看病,大夫說是眼癌。癌就是絕癥啊。
我輕描淡寫說:叔,世上的癌,數眼癌好,剜了它,有一只眼,山神凹的地盤不大,夠你照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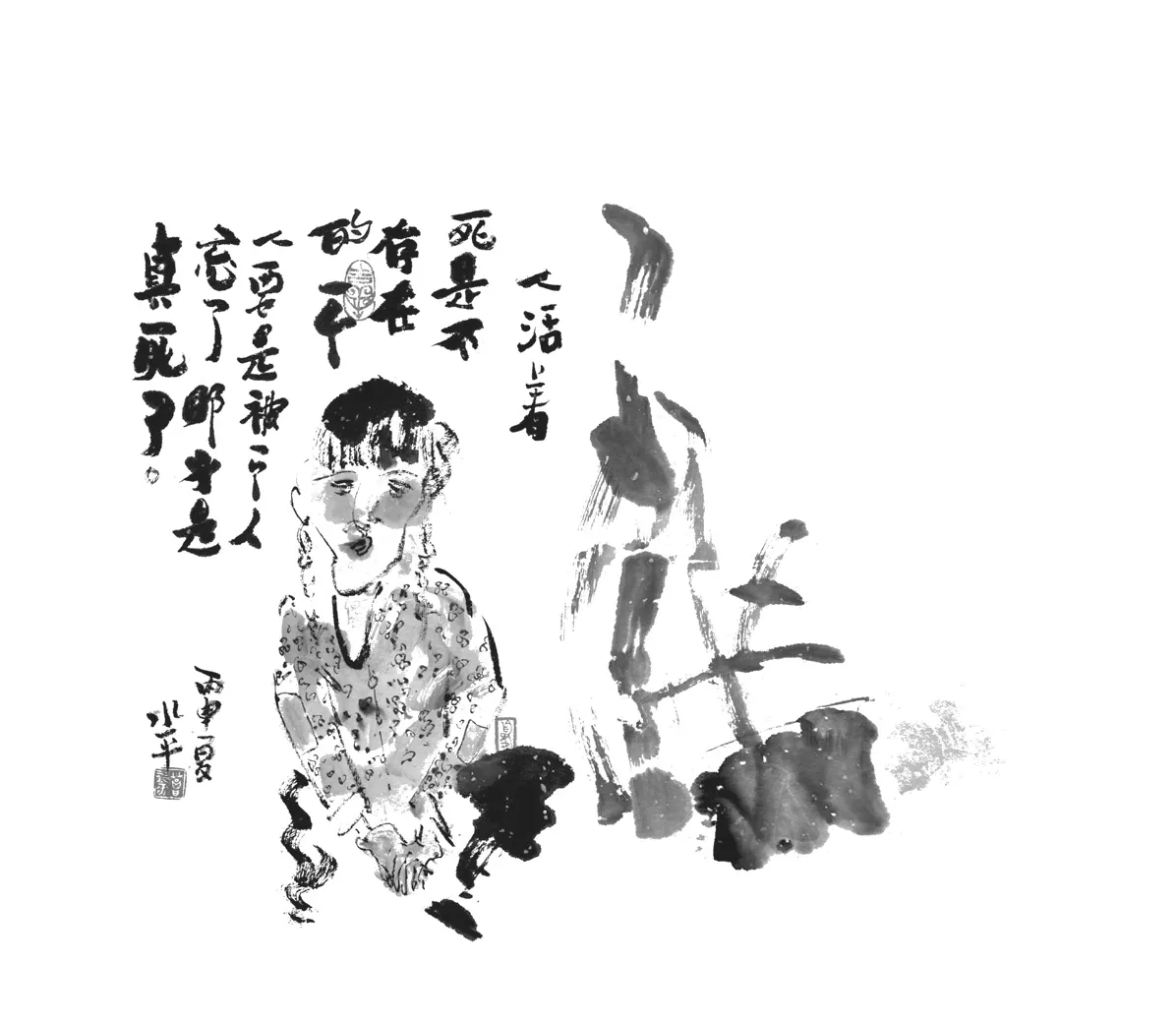
葛水平 畫
叔說,你在外真是長了見識,我就是想求你保住我的眼,一只眼看路,挑水都磕磕絆絆,一桶水灑了半坡。
一只眼肯定會影響生活,會對正常日子中整個視力和方向、動作產生很大的影響,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失去了雙眼單一視力,看東西沒有立體感,那種痛苦時時會提醒曾經有過的昨天,有過的從前。
叔說,都說眼病是雙眼病,一只眼睛得病了,另一只眼早晚也會得。
我說,叔,人到了一定年齡就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睜一只眼謀生活,閉一只眼保平安啊。
叔的一只眼睛里流露出幾分戲謔的神色,在我的臉上停留了一會兒,然后佯裝咳嗽。我的臉一下紅了。
一輩子沒有離開故鄉的人,也會得癌?真是累了青山綠水的好名聲。
那一天終于到來了。“門頭才”在院子里的棗樹上,粉連紙剪出叔的歲數,風“沙、沙、沙”地穿過粉連紙的縫隙,把“門頭才”一律壓向一邊。一個人不再活著,他的名字留在了墓碑上。我看見風撕走了一條“門頭才”,減去了叔一年的歲數。一條一條的“門頭才”被風撕走,歲數里布滿了痛、溝壑、貧窮、豐收、四季,還有埋入深土中的深度和厚實。無可名狀,飽含辛酸的淚水,我的親人們黑衣黑褲坐在碾道旁,沒有誰能讓時間回去,風同樣撕走了他們的歲數,他們隱去時,我突然理解了“黃草紙比粉連紙耐風刮”,那是一種寓意啊,是亡者在活人面前露出的自卑之相。
我在冬日稍嫌和煦的陽光里,走進空了的窯洞,黃草紙,石板地,泥墻和灶臺,梁椽清晰地發出活動筋骨的聲音。多么好的村莊,沉靜細碎的陽光灑滿了每一眼窯洞,多么不尋常啊,那熱鬧,那生,那死,那再也拽不回來的從前。時間悄然流逝,倏忽間,窯洞成了村莊的遺容。
時間帶走了一切。
如同日與夜交替形成力量關系。記得換窗戶紙時,小奶臉上皺紋成片爬著,像揉皺了的一團黃草紙。
小奶說,皺紋上了臉的人離死亡就近了。
生命與我更像是一種無法言語的距離,我對生命的所知,便是我仍然對它有所不知。曾經的山神凹,氣力和心勁讓凹里人歡馬叫。曾經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一個朝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朝代的誕生,是祖父的死亡,孫兒的成長嗎?積灰的老窗在暮色中合攏,我邁不動步,深遠的回憶在我的腦海里涌現,當河水斷流,黃草紙被風刮漏,老窯塌落,我突然覺得生活的意義再次變得恍惚。
還記得我穿著棗紅格格布衣裳,就只回了一下頭,已找不到我的親人們了。
沒有比河流的消失更動人心魄的了。它的消失沒有掙扎,沒有難過。正如彭斯用詩的語言描述的那樣:“我從未看到過野生的東西自怨自艾/小鳥凍死了,從樹上掉下來/也沒有自憐。”
河流在人的眼皮底下,誰也記不得它的消失,只知道長流水變成了季節河,當雨水再一次從天空降落時,河流的季節沒有了。
黃草紙之后是粉連紙糊窗,再后來有了玻璃,明亮讓單調的生活減少了想象。冰涼的內質和細膩、光亮的肌理,如同望著一段遙遠的時光,我看見明亮與天、與地、與風合而為一。不知為什么我懼怕清晰,它闊大了人間的距離、憂傷、悲歡和離合。我希望黃草紙蒙住我蘇醒的眼睛,讓每一種生命都能獲得動情的想象。書上說:人世間的物事在它消失的地方必定會重現。會嗎?親愛的文字,你一再欺騙這個世界!
許多物事已經消失。記憶潛入時,山神凹的土路上有膠皮兩輪大車的車轍,山梁上有我親愛的村民穿大襠褲戴草帽荷鋤下地的背影,河溝里漚麻上有蛙鳴,七八個星,兩三點雨,如今,蛙鳴永遠響在不朽的辭章里了。
肆:在半生半熟的黃草紙上行走
紋理粗獷但行筆卻不澀不滯,綻開來,仿佛頹敗的美好越來越大地澒洞開去,我把從前框在黃草紙上。
感覺行筆實在舒服流暢,黃草紙吃墨快,墨汁浸入紙張纖維迅速,因為墨汁加了水,紙張有少許的陰潤感,但不是很強烈,應該是因為半生半熟吧。
半生半熟是人世間最好的情愛,最好的水墨。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語),用什么樣的“意”才能表達心中的“言”?一切事物安靜到虛無的表象里,與土地一樣呈現于眼前的總是植物的麻和桑,斑駁翹落的窗格前,我的心中不由得就衍生出一個倘若能將歲月捕獲的假設,就是這個轉瞬即逝的臆想。
窗格子如年輪一樣開裂了,暈染的水墨如同黃昏的道理和法則。明亮的電燈,單調,蒼白,一味缺少表現力,再清楚不過的結果:生長的生長,敗落的敗落。
這實在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啊,夜的曠野覆蓋了一切,我多么喜歡在月輝朦朧如銀霧的窗格前,聽低語悅耳,浪蕩與冒失泛濫的言語。無窮的深淵般的尖聲浪氣,還有撲打窗欞的露水,全都是夜的內容和表情、夜的呼吸和生命,還有夜的親愛。
每個人都有自己靈魂的行走,時間意義上的行走可能千差萬別,而行走意義上的精神依托卻是最為重要。
行走在黃草紙上,面對河流,我停下來,我從它的水波流紋里讀出了精神行走中的麗日天光。走過群峰,遙想造山運動時,巖漿奔涌,地殼急劇強勁的自我搏斗之后,地質史終于迎來了一段珍貴的平靜的時光,自然過渡到了它運動的沒有目的的合理目的性,找到了秩序。秩序具有了更強的生命力和無限的可能性,更讓我,一粒細小的微塵,可以在浩渺的天地間自由舞蹈。
成長和人生閱歷、審美經驗甚至生命態度因水墨留下痕跡時,宛如回應了我平庸生命中的貴族氣質。潛在的目標,沒有功利,沒有矯飾。地理的奇妙組合為我的命運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并賦予我強勁的身骨。
時間迅疾而過。有多少生命骨殖深埋于時間中,親情、友情、愛情,終于待在了一個安全的地方,那個去處直叫人呼吸到了月的清香,水的沁骨。生命的決絕在所產生的文字和畫作中獲得回歸,當這些已逝的生命從我的生命中劃過時,我體悟到了溫情與哀絕,惆悵和眷念。“但使親情千里近,須信,無情對面是山河。”我不知這是誰的詩句,卻與我內心的感觸對接了。
時間如中國畫縹緲的境界,明知道一切不可能出現,卻還愿意在疲倦的時候沉溺其中。逝去的以另一種方式活在現實中。當我把逝去的還原成一幅畫作時,我就更深刻地了解了那段時間。我看到了時間塵埃掩蓋下的一些濃厚背景,無論輕賤卑微的生命,還是輝煌偉人的喧囂,一切都在時間的行走中驗證了一條真理:在已逝的歷史,在別人的轉述中,歌哭笑罵,述不完的無奈與辛酸,有我無法窮盡的多樣人生。
淺拙的寫作和作畫是對生活質量的尊重,并讓我在精神上獲得了慰藉。每當夕陽西下,在門前一條老路上躑躅時,我常常會想起出生地——窯洞。院中的棗樹,窯內的毛驢,向晚的炊煙和歸來的羊群,一切的一切讓我結想成疾。
還記得去冬的一領葦席,來年的夏日在院中央一鋪,就等于給夢的窗格找了一個憩身之地。不遠處的玉米地里,蛙鳴聲彈著青玉米的葉子,明麗的月影朗照一切,我不敢大聲喊叫,怕一不留神碰落了玉米的香氣,青草的香氣。老窯花紋繁復的窗欄板上的黃草紙,一棵樹寬的門扇,紫銅的門環,鐵葫蘆鎖,還有那年節時的甩鞭,我的先祖們進進出出的背影,在我的生命中顯影。從前的人對生活絕不是敷衍的,他們的尋常日子具備了音樂的韻律,他們過著世界上最平淡本分的光景,無羈無束,他們也滋生一些死去活來的故事,但他們不屑與人表訴。星光下那旱煙鍋粗大明滅的情懷,成為我作品中最豐滿的細節。
當我再一次回到村莊時,我看到了時間消釋的光芒,我和我先祖的腳印重疊著,在荒涼、蕭瑟的坡道中走來走去。那棵棗樹早已在追逐時間中高過窯頂,然而坐在它的葉子下守望幸福和豐收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他們的墳墓在對面的山坡上。夕陽落了,晚霞退了,在一切都可以顛覆的時間中,懷戀被放置在多維的記憶上,時間同樣給了我精神的薪火傳承。
走過時間。
我把行走的味覺寫成文字,歷史、現實、存在或存在過的生命,一切都始于行走,也在行走中結束。我想生命的價值僅僅在于:是否向真、向善、向美,即使目的地并未走到,但是朝向這個目的行走。
致敬——那些走得認真,摒棄了種種誘惑,走得執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