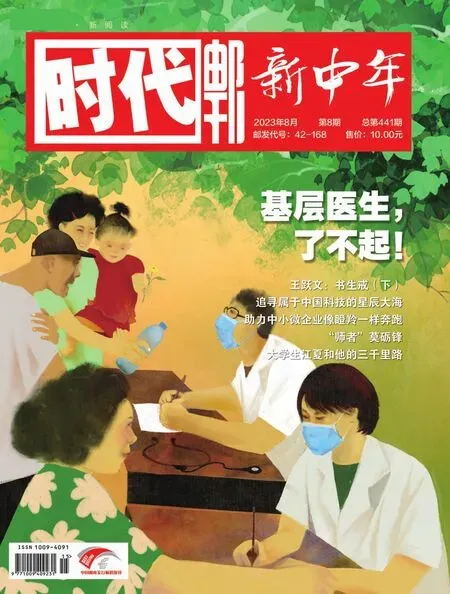書生戒(下)
王躍文
君王好諛,自古盡然。康熙皇帝卻是個例外,不太聽得進拍馬屁的話,曾說過:“人間譽言,如服補藥,無益身心。”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平定,朝廷要祭告天地、社稷、祖宗,并詔告天下。大臣們起草文告,說平亂摧枯拉朽,全賴皇帝一人之功德。康熙皇帝看了,立馬指出:此非朕一人能成之功德,亦非容易成功之事,文告重新起草!
康熙皇帝不邀功、不喜諛的事,可見于史料者極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皇帝為教育太子之事,曉諭大學士們:“朕觀古昔賢君,訓儲不得其道,以致顛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甚少。”“爾等宜體朕意,但毋使皇太子為不孝之子,朕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
道學家湯斌時任工部尚書,又在詹事府當差。他聽了皇上諭示,立馬奏對:“皇上豫教元良,曠古所無,即堯舜莫之及。”詹事府,即培養皇儲的機構;元良,指的是皇太子。
康熙皇帝聽了湯斌這話,很是生氣,斥責道:“大凡奏對貴乎誠實,爾此言皆讒諂面諛之語。今實非堯舜之世,朕亦非堯舜之君,爾遂云遠過堯舜,其果中心之誠然耶?”又說:“大凡人之言行,務期表里合一,若內外不符,實非人類。”康熙皇帝并不認為自己治理出了堯舜盛世。
且說一件后來發生的事情。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皇帝為著修明史的事作文曉諭諸臣,說道:“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歸罪于朕,未曾一時不自責也。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
但憑公論之,康熙皇帝治國是很有成就的,惟其虔敬謙恭而已。往日的少年天子,此時親理朝政已四十年,其間平定“三藩之亂”,收復臺灣,征剿噶爾丹,四十年間還在治理黃河。正是這一年,河工告竣,黃患暫息,黎民稱頌。
康熙朝,當面諛今,會被治罪。湯斌面諛皇帝沒多久,詹事尹泰入奏:“湯斌學問平常,年又衰邁,恐不堪此任。”皇帝說:“俟再過數日裁之。”沒過多久,康熙皇帝就把湯斌打發回老家了。
時隔多年,康熙皇帝說起湯斌,頗為譏誚:“昔江蘇巡撫湯斌,好輯書刊刻,其書朕俱見之。當其任巡撫時,未嘗能行一事,止奏毀五圣祠,乃彼風采耳。此外,竟不能踐其書中之言也。”
歷史真相是唯一的,但歷史演繹則如萬花筒。時人眼里,湯斌頗多堂皇之言,儼然是狷介之士;又經后人重重描畫,湯斌雍正朝入賢良祠,道光朝從祀孔子廟。到了近代,劉師培卻說湯斌“觍顏仕虜,官至一品,貽儒學之羞”,鄒容則責其為“馴靜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