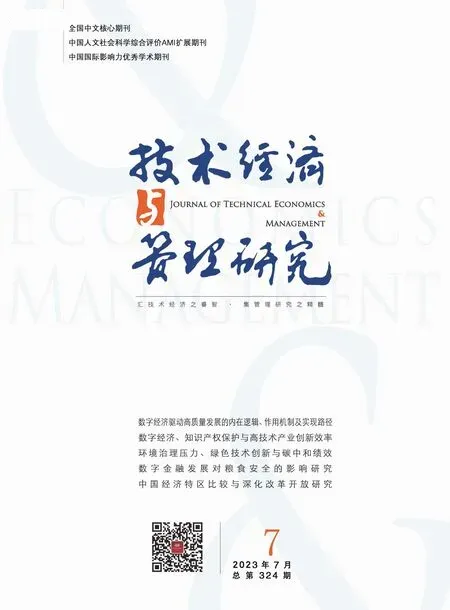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研究
吳冰彬,王林萍
(福建農林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一、引言
“貧困”是一個社會性、歷史性的概念,其內涵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遷而不同。貧困可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絕對貧困又稱生存貧困、赤貧,強調個人或家庭缺少最基本的資源以維持最低的生活需求。相對貧困主要體現為多維度的發展性貧困,強調個人或家庭雖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但不足以達到社會平均水平,存在相對“經濟差距”。中國在2020 年底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但貧困的多維性、動態性要求減貧目標仍將繼續。首先,消除的僅是“特定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絕對貧困線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逐步提高,如果處在貧困線邊緣的群體不能利用現有資源提高生活水平,則會產生返貧及新增貧困問題。因此,僅是消除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并不代表永久消除絕對貧困。其次,相對貧困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綜合而復雜的發展性貧困問題。其注重的維度更多,處理起來也相對更難。再次,貧困的本質是動態的,貧困的路徑是非線性的。經濟、社會等環境的未知變化促使個體資源(就業收入、非金融資產等) 產生向上向下的非對稱性流動,當向下流動的比例超過向上流動的比例時,個體將陷入絕對貧困。最后,貧困群體自身發展能力不足將影響脫貧可持續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主要依賴于政府的救濟政策,對于擺脫貧困后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面對瞬息萬變的經濟、社會等環境帶來的各類風險沖擊,農戶家庭自身發展能力是否足以應對,對脫貧的可持續性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外學者提及的“Resilience”一詞,國內相關文獻一般譯為“彈性”“恢復力”“韌性”“復原力”等詞,表明能夠衡量農戶應對各類風險沖擊的能力。雖然“Resilience”的具體內涵隨研究者的視角不同有所差異,但均強調某一系統或組織受到風險沖擊后恢復到原有或達到一個更好狀態的能力。文章借鑒Barrett Christopher B&Constas Mark A(2014)提出的“Development Resilience”,基于農戶家庭研究視角將其譯為“農戶家庭發展韌性”,指某一農戶家庭在面對各種壓力源和無數沖擊后避免陷入貧困的自身發展能力,當且僅當該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保持在較高水平上,則判定該農戶家庭具有發展韌性[1]。農戶家庭發展韌性越強,其應對各類風險沖擊的能力越高,陷入貧困的概率也就越低。
理論上,數字普惠金融集合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的優勢,有助于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及增強金融包容性,實現金融資源向農村、貧困地區下沉,能增強家庭在應對負面沖擊時的韌性,助推貧困人口家庭韌性戰略的實施,成為改善家庭發展韌性進行反貧困治理的關鍵途徑[2]。然而,當前國內關于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相關文獻很少,僅能從少量的國外文獻,獲知金融產品對韌性的作用。如,Felsenstein 等(2018)認為,技術保險產品是提高家庭韌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要發揮作用需取決于家庭對保險的偏好程度[3]。Vighneswara Swamy(2019)認為小額信貸產品的包容性優勢可以增強貧困人口的韌性[2]。因此,數字普惠金融最終能否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降低其陷入貧困的概率猶未可知。
有鑒于此,文章嘗試在評估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基礎上,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及其機制。文章的可能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在測算韌性方法上,嵌入估計非線性路徑動力學中的高階中心矩,將動態演進的發展韌性與傳統的韌性概念有所區分,更好體現貧困的多維復雜演變特征,豐富已有的韌性概念、測量方法及分析檢驗。第二,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戶發展韌性的作用機制,體現金融干預在農戶家庭遭遇沖擊前后全過程的影響,在考慮貧困動態性基礎上,填補傳統金融反貧困研究中只考察金融干預對貧困群體靜態結果影響的局限,對今后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發展韌性關聯問題起到探索與借鑒作用。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普惠金融自身的優勢能增強農戶使用金融產品應對風險沖擊及自身發展的能力。首先,數字普惠金融以數字技術為依托,有效降低了以大數據為基礎的征信體系等的交易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助于精準識別客戶,降低資金回流不善的風險,增強金融機構為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的意愿,提高農戶金融獲得性。其次,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山區由于獲取的資源有限,對金融的認知和接受能力程度較低。依托數字普惠金融的跨時空數字技術優勢,使農戶能夠通過如微信支付、支付寶支付、在線發紅包、轉賬等多項業務,在潛移默化中增強農戶的金融認知能力,知曉使用數字金融的快速性、便利性,增強農戶使用金融產品的意愿、需求與行為。最后,數字普惠金融依托數字化技術創新出多樣化符合農戶需求的金融產品,為農戶抵御風險提供風險響應工具。同時,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間接效應可為農戶提供外部發展機會,增強自身發展能力。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1:
假設H1:數字普惠金融正向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發揮作用存在一定的機制,結合以往數字普惠金融減貧相關文獻經驗,文章從人力資本投資和社會資本兩個作用機制進行分析。
1.人力資本投資機制
提高農戶的勞動技巧、對未來形勢的判斷、決策和防范風險等認知能力,使其充分利用資源、抓住機會改善自身的內生發展能力,是增強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引導部分金融資源流向貧困地區或弱勢群體,增加農村地區的教育資金投入,緩解一部分農戶因教育資金約束而產生的輟學、受教育水平低、勞動技能弱而無法實現自主就業或創業來增加收入的問題。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增加了農戶對金融市場的參與度,使農戶在潛移默化中接收有關金融產品收益、風險等方面的金融知識,既可以提升農戶使用金融產品的意愿與能力,最大限度發揮金融資源的效用,又可以提升農戶對未知風險的防范意識、判斷能力及決策能力,從而增強自身發展能力。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2:
假設H2: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投資,增強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2.社會資本機制
中國農村是一個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傳統社會,“社會資本”以社會資源為載體,以社會網絡為運行基礎,依靠成員在頻繁的交流、接觸和互動中形成內部的信任、聲望和制約關系,給成員帶來如就業信息、貸款支持等一定的資源和利益,有助于增加成員的收入和福利水平[4]。隨著數字技術的興起和互聯網的推廣普及,讓個體間“面對面”的交流方式延展到“互聯網多元化”的社交方式,有利于拓寬農戶原有的社會網絡,通過強化脫域型社會資本的積累,獲取更多的資源促進自身能力的發展。具體體現在:當農戶遭遇諸如生病、災禍等突發狀況時,可通過社會資本網絡成員轉賬、發紅包等方式籌集資金,或通過“水滴籌”等平臺,依靠網絡成員的轉移性支出及轉發獲得救急資金,緩解一部分的資金約束以應對風險沖擊。另一方面,農戶社會資本積累越豐富,獲取的就業信息、技術指導、原始創業資金等資源越多,越有利于農戶獲得就業崗位或通過創業實現收入的增加。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3:
假設H3: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社會資本積累,增強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三、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
文章的數據共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數字普惠金融的數據來源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集團聯合課題組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5]。其二,農戶微觀層面使用的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組織管理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CHFS)[6]。
文章采用兩個數據庫中的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四期的數據,將數字普惠金融的宏觀數據與農戶家庭的微觀數據進行匹配形成面板數據。在保留持續追蹤農戶家庭樣本、刪除異常值、對部分缺失值進行插值填補以及統一相關變量的觀測值后,最終得到有效樣本數據4826 個。
2.變量選取與測算
(1) 被解釋變量:農戶家庭發展韌性(DRijt)。
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測量應至少包括如下三點:第一,強調風險與貧困之間的關系。人們對風險將如何變化缺乏確定性,未知的風險可能會改變人們的生活狀態,產生返貧或新增貧困問題。第二,農戶抵御風險的能力、風險路徑及生活條件具有非線性動態性,在測量模型中應加入體現非線性動態的高階中心條件矩。第三,發展韌性有明確的規范基礎,即越多越好。它代表農戶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能力越大說明農戶防止陷入貧困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在測量過程中需選定一個規范標準值進行比較。
有鑒于此,文章借鑒Cissé J D&Barrett C B(2018)[7]、李晗和陸遷(2021)[8]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高階中心條件矩測算方法,將農戶家庭的隨機福祉(Wijt)作為衡量農戶家庭避免陷入貧困的能力,并規定一個特定標準閾值(1.9 美元貧困線) 以判斷農戶家庭避免陷入貧困能力的高低;當農戶家庭的隨機福祉大于或等于這個閾值時,就認為該農戶家庭具有發展韌性。即農戶家庭發展韌性(DRijt)是第i 個家庭在某個時期t 超過某個特定標準閾值(人均日消費額1.9 美元) 的可能性。具體測算步驟如下:
第一,對農戶家庭的隨機福祉均值進行建模,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Wijt為農戶家庭i 在t 時期的隨機福祉的均值,建模為包含一個滯后隨機福祉Wi,j,t-1的多項式函數gM一組個人、家庭、地區的特征變量Xit、農戶家庭i 受到的沖擊或暴露的風險參數βM以及隨機擾動項μMijt的函數。下標M 代表期望方程,k代表高階中心矩的矩數,W 為農戶家庭人均年消費支出總額的自然對數。其中,為了保證測算結果的可靠性,經過顯著性檢驗,將k 取值為5。
第二,基于隨機擾動項μMijt的零均值假設(E[μMijt]=0),估計農戶家庭i 在t 時期的條件期望μ1ijt的預測值如下:
第三,用模型(1)中的一階方程計算出來的殘差來估計條件方差V。同樣,在零均值假設下(E[μVijt]=0),估計農戶家庭i 在t時期的條件期望μ2ijt的預測值:
最后,假設分布的函數形式和估計的矩可以聯合估計特定家庭和特定時期的條件福祉概率密度函數和相關互補累積密度函數,估計農戶家庭i 在t 時期達到的某種規范的最低福祉標準W的概率,即文章的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如下:
(2) 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FIjt)。文章核心解釋變量DFIjt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中的總指數。
(3) 控制變量
選取能夠體現影響家庭生產與生活活動主要因素的指標:農戶的性別、年齡、家庭規模、受教育水平;選取體現農戶家庭抵御風險沖擊的主要指標:農戶是否從事工商業項目、務農以及家庭的總資產和總收入;選取能夠說明農戶家庭對數字普惠金融的關注度和參與度,體現農戶知曉防范金融風險的水平的指標:金融關注度和風險偏好。
3.描述性統計
表1 報告了文章的主要變量數據特征,結果顯示: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均值為0.120,標準差為0.0583,說明農戶家庭發展韌性較低,不同家庭之間的發展韌性存在一些差距。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均值為2.271,標準差為0.720,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總體上較好,但仍存在較大改善空間。從控制變量上看,農戶家庭的男性人數較多,但年齡偏大,且本科以上學歷的人口較少;另外,務農變量均值為0.594,工商業經營項目變量均值為0.109,說明農戶家庭從事務農較多,從事工商業經營項目較少;金融關注度的均值為4.008、風險偏好的均值為4.200,說明大多數農戶家庭對金融知識的關注度低,對風險比較厭惡,不偏好嘗試有風險的活動。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4.模型設定
(1) 數字普惠金融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檢驗
文章以農戶家庭發展韌性(DRijt)為被解釋變量,以相對應年份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FIjt)為核心解釋變量,選擇面板固定效應模型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影響:
其中,Xijt為一系列戶主、家庭特征變量,σi為家庭固定效應,μijt為隨機擾動項。
(2)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機制檢驗
為了進一步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機制,文章借鑒溫忠麟、葉寶娟(2014)[9]的方法,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以上三個模型中,Mijt為中介變量,包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兩種變量,其余變量與模型(1)變量相同。
如果解釋變量DFIjt通過影響中介變量Mijt來影響被解釋變量DRijt,則中介變量Mijt發揮了中介效應。對中介效應的檢驗思路如下:
首先,檢驗模型(6)回歸系數α1的顯著性,即解釋變量DFIjt對被解釋變量DRijt的總效應。如系數α1是顯著的,則進行下一步的檢驗;如果不顯著則終止檢驗。
其次,檢驗模型(7)的回歸系數β1的顯著性,以判斷解釋變量DFIjt對中介變量Mijt的效應。
再次,檢驗模型(8)的回歸系數γ2的顯著性,以在控制解釋變量DFIjt后,判斷中介變量Mijt對被解釋變量DRijt的效應。
最后,當回歸系數β1、γ2都顯著時,則檢驗模型(6)的回歸系數γ1,以判斷在控制中介變量Mijt后,解釋變量DFIjt對被解釋變量DRijt的直接效應。當該系數顯著時,說明中介效應顯著,即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中介變量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若該系數不顯著,則反之。
當回歸系數β1、γ2至少有一個不顯著時,則可通過Sobel工具檢驗顯著性。如果顯著,說明中介效應顯著;反之,則中介效應不顯著。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1.基準回歸結果
表2 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列(1)和列(2)分別為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首先,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估計系數均為0.013,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每增加1 個單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提高了0.013。原因可能是: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高了農戶資金的可得性,緩解了農戶家庭的資金約束,有助于農戶更好地生活和進行生產活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推動農戶利用數字化普惠金融平臺進行風險規避和實現多渠道增收,提升整個家庭發展韌性。

表2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其次,控制變量中,家庭規模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農戶的家庭總人口數越多,農戶家庭發展韌性越低。可能是家庭的總人口數越多,尤其是年輕勞動力越少的家庭,農戶需承擔的責任就越重,抵御各類風險的能力就越弱。受教育水平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可能是大多數高學歷的勞動力流出,導致參與農村建設的新興力量不足,從而不利于提高家庭發展韌性。風險偏好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可能是農戶認為自身現有資源不足以進行任何有風險的行動,不愿意或者缺乏能力嘗試通過諸如金融產品等方式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
2.穩健性檢驗
為了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穩健性,文章分別以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方式進行檢驗。首先,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覆蓋廣度”指標。表3 列(1)報告了覆蓋廣度的估計系數為0.011,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顯著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可能是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讓農戶接觸、享受到的金融服務更豐富,讓農戶越能借助數字普惠金融渠道提高家庭發展韌性。其次,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閾值替換為中國2015 年的相應脫貧標準,重新測算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并更換為被解釋變量。回歸結果如表3 列(2)所示,估計系數為0.007,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基于上述兩個回歸結果與上文中的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數字普惠金融能正向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數字普惠金融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機制檢驗
1.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文章以農戶家庭的教育培訓支出總額加1 的自然對數作為人力資本投資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表4 列(1)、列(2)分別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對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回歸結果,兩個回歸結果均不顯著。根據中介效應檢驗思路,選擇Sobel 工具進行進一步檢驗。表5 報告了Sobel中介檢驗結果,P>|z| 為0.033,中介效應通過。其中,數字普惠金融對人力資本投資的估計系數為-0.229,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估計系數為-0.001,說明數字普惠金融會減少家庭教育培訓支出,但不利于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可能的原因是,數字普惠金融能給農戶家庭帶來人力資本投資機會,如為農戶提供助學貸款等,擴大農戶家庭的教育培訓支出的資金來源渠道;但是,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可能會給農戶帶來較大的還款壓力及負擔,尤其是家庭條件不足以如期償付這部分款項時,反而會降低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表4 人力資本投資機制

表5 Sobel 中介檢驗
2.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社會資本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文章以農戶家庭交通通訊工具費用和人情支出費用金額的總額加1 后的自然對數作為社會資本變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表6 列(1)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向影響社會資本,估計系數為0.147,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每增加1個單位,社會資本提高了0.147;列(2)報告了社會資本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估計系數為0.003,說明社會資本每增加1個單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提高了0.003。綜合兩個回歸結果,表明社會資本中介效應成立。可能的原因是,數字普惠金融嵌入的互聯網數字化技術,便捷了農戶間的交流,擴大農戶的社會資本積累,有利于農戶獲取更多的就業信息、技術指導、暫時性或轉移性資金援助,提高農戶應對風險的能力,從而增強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表6 社會資本機制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農戶家庭發展韌性是衡量其應對各類風險沖擊的能力。農戶家庭發展韌性越大,反貧困能力越強。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治理貧困的活水之源,能否成為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有效途徑,以實現減貧、脫貧的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文章在測算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基礎上,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家庭發展韌性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一是農戶家庭發展韌性較低。其中,農戶家庭整體年齡偏大,受教育水平較低,尤其是家庭人口中,非勞動力越多可能會給家庭帶來更重的負擔,不利于提高農戶家庭發展韌性。二是各個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總體上較高,但大多數農戶家庭對金融知識的關注度偏低,對風險厭惡,可能會影響農戶使用數字普惠金融產品。三是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及覆蓋廣度均能正向影響農戶家庭發展韌性。四是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提高農戶社會資本積累,提升農戶家庭發展韌性。五是數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農戶在教育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但也可能帶來負擔,降低農戶家庭發展韌性。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和研究結論,文章提出如下對策建議:首先,繼續推行數字普惠金融政策,改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環境,完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體系,使數字普惠金融的可觸達性在合理、有效、精準的前提下進一步增強。其次,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金融機構可通過村干部帶頭入村入戶宣傳金融知識、實施相關金融知識、技能培訓,引導、提升農戶正確使用金融服務降低農戶家庭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支出及負擔。最后,在社會資本方面,倡導社區等相關主體通過農村合作社等經濟組織引入各方社會力量參與農村產業建設,豐富社會資本積累,讓農戶廣泛地參與或自主經營產業項目,提高收入水平和資產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