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癥患者與照顧者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對家庭韌性影響的主客體互倚模型分析
林 丹,王 睿,陳 培,戴正香,廖子婷,吳雨蓉
1.南京中醫(yī)藥大學護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2.南京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醫(yī)院,江蘇南京 210004
癌癥已成為全球性的公共衛(wèi)生挑戰(zhàn)。世界衛(wèi)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fā)布的最新數(shù)據(jù)顯示,2020年全球約有1 929萬癌癥新發(fā)病例,其中中國約有457萬,居全球第一[1]。在家庭視角下,癌癥患者及照顧者互相依賴,以成對形式共同經(jīng)歷疾病帶來的影響,但同樣包含著恢復和成長的機會。基于家庭壓力和家庭力量的研究,McCubbin等[2]提出家庭韌性的概念,即能夠幫助家庭抵抗變故帶來的破壞,適應危機環(huán)境,甚至從逆境和危機中獲得成長的能力。在癌癥患者康復過程中,家庭需要增強韌性,積極應對疾病管理的挑戰(zhàn),從而得以適應新環(huán)境。應對方式是家庭韌性個體微系統(tǒng)中的重要預測因子,而社會支持是家庭韌性外系統(tǒng)層面的主要影響因素[3],但兩者對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家庭韌性的交互作用未知。主客體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是一種分析成對關系的方法,常用于測定成對關系中的兩個成員所產(chǎn)生的交互效應[4]。本研究擬以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為成對整體,旨在分析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對家庭韌性影響的APIM效應,為提高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家庭韌性提供新視角與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經(jīng)醫(yī)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同意,編號:2021NL-KS100。采用便利抽樣法,于2021年7-8月在南京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醫(yī)院選取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作為成對研究對象。納入標準:患者明確診斷為癌癥,處于康復期,并且病情穩(wěn)定;照顧者是家庭中無償承擔癌癥患者主要照護工作的人,照顧時間不少于12個月;患者及照顧者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承諾書。癌癥患者或照顧者存在以下任一情況,均予以成對排除:認知功能障礙;嚴重的精神疾病;語言溝通障礙。
1.2 調查工具
1.2.1一般資料問卷
由研究者自行設計,采集癌癥患者的年齡、性別及疾病類型等,照顧者的年齡、性別、照顧年限、每日照顧時長、與患者的關系。
1.2.2家庭韌性量表
該量表由劉洋等[5]翻譯并檢驗信效度,共20個條目,分為責任(9個條目)、挑戰(zhàn)(5個條目)、控制(6個條目)3個維度。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1~4分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數(shù)越高,說明家庭韌性越強。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03,折半信度系數(shù)為0.738。
1.2.3簡易應對方式量表
該量表由解亞寧[6]編制,用于反映受到外界刺激時可能出現(xiàn)的應對傾向。量表共20個條目,包括積極應對(12個條目)、消極應對(8個條目)2個維度。量表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0~3分分別表示“不采用”至“經(jīng)常采用”,維度得分越高表明該應對方式的傾向性越強。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90,重測相關系數(shù)是0.89,內部一致性較好[7]。
1.2.4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該量表由肖水源[8]編制,共10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3個條目)、主觀支持(4個條目)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3個條目)3個維度。總分為66分,得分越高表明得到的支持越多。量表Cronbach’s α系數(shù)為0.896,3個維度與總量表的相關系數(shù)為0.724~0.835[9]。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現(xiàn)場問卷調查,研究者向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解釋研究目的和意義后發(fā)放問卷,研究對象自行填寫,對于因視力差或文化程度低而無法獨立完成調查的研究對象,研究者按照統(tǒng)一方式復述問卷內容并根據(jù)研究對象回答情況代為填寫。為確保問卷合格,研究者當場進行檢查、核對后收回。問卷收集結束后,2名研究者對數(shù)據(jù)進行篩查,剔除答案明顯規(guī)律性錯誤或邏輯混亂的問卷。本研究共發(fā)放問卷31份,回收有效問卷31份,有效回收率100%。
1.4 統(tǒng)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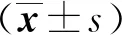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癌癥患者:年齡(69.58±18.29)歲;性別,男13例、女18例;疾病類型,肺癌8例、乳腺癌7例、胃癌5例、宮頸癌5例、食管癌5例、膽管癌1例;患病年限10年(1~20年)。照顧者:年齡(56.00±12.91)歲;性別,男16人、女15人;照顧年限3年(1~15年);每日照顧時長4 h(1~16 h);與患者關系,父子8人、母子9人、夫妻13人、其他1人。
2.2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應對方式及社會支持和家庭韌性情況
癌癥患者及家庭照顧者的應對方式與感知到的家庭韌性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均>0.05),社會支持總分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4),其中,照顧者感知到的客觀支持與主觀支持水平高于癌癥患者,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應對方式及社會支持和家庭韌性得分情況
2.3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與家庭韌性的相關性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消極應對與對方家庭韌性的相關性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積極應對、社會支持與對方家庭韌性的相關性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應對方式和社會支持與家庭韌性的相關性(r)
2.4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消極應對與家庭韌性的APIM分析結果
以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消極應對為預測變量,以兩者的家庭韌性為結果變量進行主客體效應分析,見表3;將回歸系數(shù)標準化后構建APIM模型,見圖1。在主體效應方面,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消極應對與自身家庭韌性之間的交互作用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在客體效應方面,照顧者消極應對方式對癌癥患者家庭韌性具有負向影響,照顧者的消極應對水平越高,癌癥患者感知到的家庭韌性水平越低(P<0.001),而癌癥患者消極應對對照顧者家庭韌性的影響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注:1)P<0.001。

表3 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消極應對與家庭韌性交互作用的主客體效應
3 討論
3.1 癌癥患者與照顧者家庭韌性現(xiàn)況
癌癥患者及照顧者的家庭韌性是家庭及家庭成員所具備的良好品質、親密的家庭關系、高水平的家庭支持以及與外界的互動[10]。本研究結果顯示,癌癥患者與照顧者家庭韌性總分分別為(56.52±1.39)分、(58.55±1.01)分,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的家庭韌性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癌癥康復過程中,患者與照顧者需要共同面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并協(xié)同采取反應和做出決策,以一個單元的形式整體進行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管理,在應對疾病過程中的行為反應相互關聯(lián)并相互影響,因此,所感知到的家庭韌性同步變化。
3.2 應對方式對癌癥患者及照顧者家庭韌性的交互作用
應對方式是個體為減輕或避免壓力而有意識、有目的地調節(jié)自己認知和行為的策略,是影響個體心理應激的重要因素。研究[11]顯示,癌癥患者的積極應對與家庭韌性呈正相關,消極應對與家庭韌性呈負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癌癥患者與照顧者的積極應對、消極應對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間接反映了兩者作為一個整體的二元應對關系,同時,癌癥患者感知到的家庭韌性受照顧者消極應對的負向影響。消極應對方式容易使照顧者的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行為控制能力變差,產(chǎn)生負性情緒,造成家庭照顧角色紊亂、照顧質量下降,影響癌癥患者感知到的家庭韌性水平。但本研究亦發(fā)現(xiàn),癌癥患者及照顧者的積極應對與家庭韌性的相關性無統(tǒng)計學意義。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的患者處于癌癥康復期,病程及受照顧時間均較長,積極應對方式對自身及照顧者家庭韌性的影響逐漸弱化,內心的負性情緒得不到釋放。此外,癌癥患者在康復過程中,主要依靠照顧者的幫助來維持內心感知的平衡,因此,照顧者消極應對方式對癌癥患者家庭韌性產(chǎn)生影響。這提示對癌癥患者進行康復干預時,不能僅限于關注主體,也應該關注客體的影響,制定相應的干預措施來引導家庭照顧者改變消極應對方式,幫助患者提高家庭韌性水平。
3.3 癌癥患者及照顧者社會支持對家庭韌性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
社會支持是個體從社會人際網(wǎng)絡中得到的物質以及精神支持,可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社會關系,進而促進疾病的恢復。本研究發(fā)現(xiàn),癌癥患者與照顧者的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表明兩者所感知到家庭以及家庭外系統(tǒng)的支持有所差別,但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社會支持與家庭韌性的相關性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從二元角度分析,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可能通過其他的調節(jié)或中介因素作用于家庭韌性,而并非直接的作用關系。社會支持在癌癥患者家庭韌性與生命意義感或心理社會適應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12-13],進而影響家庭韌性水平。此外,社會支持的不同來源,如家人、朋友、同事、社會團體等,對患者及其照顧者個體心理韌性、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均存在復雜的二元交互作用[14]。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不同,可能與本研究納入的樣本量較小有關,后續(xù)還將擴大樣本量,并引入其他變量,進一步探究癌癥患者及其照顧者社會支持對家庭韌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