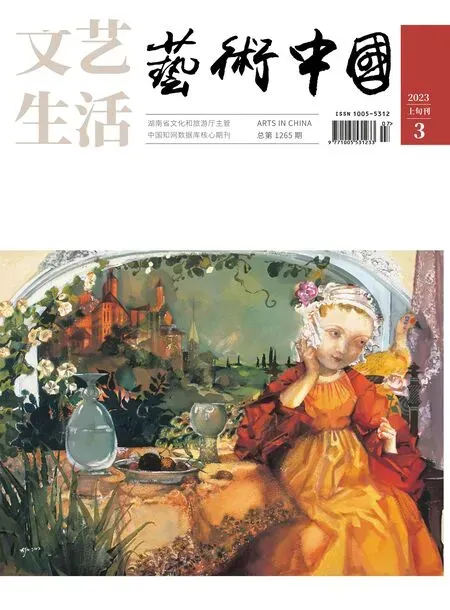論書寫內容對書法創作、欣賞的作用
◆ 阮天倫(中國美術學院)
當代書法創作語境歷經了由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繁體到簡體、豎式到橫式、無句讀到句讀、毛筆到硬筆的轉變,以及此后電子輸入的興起又快速占領了實用性書寫領域。書法曾作為文人書齋式的雅玩以及日常實用性書寫的功能消逝,個性解放思潮的出現、展廳文化的渲染更是突出了書法的視覺性功能,書寫內容則成了“視覺性”的形式載體。雖然視覺層面的審美感受也能夠形成一定的作品意蘊,但一些觀者進一步將注意力轉移至書寫內容時,會發現書寫內容與作品意蘊的脫節,這不免造成一種遺憾,造成了對書法的欣賞很難走向更廣闊的層面。書法何為?作為由視覺形式與書寫內容共同構成的書法,其書寫內容是否僅僅只能淪為形式的“載體”?書寫內容又是否能夠影響書法作品的意蘊表現?
一、書寫內容與書法作品的關聯
漢字是構成書法視覺層面的基本要素,它的豐富性與神秘感使其具有足夠的藝術表現力,這使得書法較之于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書寫藝術而言具有先天的優越。正是這樣的優越性,使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漢字本身及其結構性的變化中,以尋找書法的可能。無可否認,在客觀上一件書法作品首先由點畫構成漢字的結構,再由漢字構成完整的章法。然而,對于書法作品意蘊的表現而言,真正構成書法視覺層面的是由漢字組織而成且具有一定內涵的文字內容,而非僅僅是漢字獨立的結構形式。張懷瓘《書斷》云:“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征,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書、文向來有著“自然而然”的聯結。先秦時期,甲骨刻字的內容以“卜辭”與“記事刻辭”為主。商代末期的青銅器到秦漢時期的刻石、竹帛所鐫刻書寫的內容亦然。直至漢末魏晉時期,受道、玄思想影響,書法完成了審美性的“自覺”,書寫內容也從原先的實用性文字開始擴寬至具有文學性的內容,開始圍繞著書寫者的精神世界展開。或自撰內容,或借他人之言欲抒己見,其所選用的書寫內容與“人”的關聯變得愈加密切。
近代以來,受西方現當代藝術的影響,書法創作中書寫內容的擇用邊界被進一步拓寬。雖然仍以多字數、完整的書寫內容為主,一些特殊的單字,甚至是無序的內容在一定的氛圍中被賦予了某種特定的觀念及內涵,如井上有一《貧》《愚徹》等作品。如此能夠表現某種內涵的單字以及無序的漢字組合也屬于本文所指的書寫內容。
二、書寫內容在書法作品中的意義與價值
從《書譜》“達其性情,形其哀樂”到《藝概·書概》的“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也”再到井上有一提出的“將書法從‘書法家的書法’中解放出來,變成‘人的書法’”①,書法作品的內涵逐漸形成了寬泛的表現機制,大抵上包含視覺層面與意蘊層面。視覺層面指作品中點畫、結構、章法的視覺構成以及所傳遞的審美感受;意蘊層面指作品所傳遞的情感、反映的創作者的學養及修為、時代特征以及藝術觀念等。書寫內容對于上述二者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且從創作者與欣賞者兩個角度來說明。
1.從創作者的立場
對于創作書法作品的客觀進程而言,絕大多數的創作是由選擇書寫內容開始,再到點畫、結構、章法逐步完成。井上有一曾說:“我腦海中出現了‘愚徹’一詞,我認為這個詞好,便寫了下來。的確,自己發現的詞使你能在創作文字時傾注全部心血。反之,動機不充分時,則一事無成。所以,書道,最關鍵的是,寫什么。”此話關鍵為“動機”二字。在井上有一看來,創作者存在某種情緒與表現意圖時,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創作動機,而這樣的動機往往直接體現在“寫什么”即書寫內容的選用上。“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②我們由外部接收到某種信息,再轉化為動念,或是由此直抒胸臆,在書法創作時自撰書寫內容;或在古往今來的經典文賦中尋找最符合自身創作動機者,如此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完成創作者動機與作品意蘊層面的連接,形成這件作品獨立的“神氣”。
在充分動機下撰寫或選用的內容為作品定下一個基調,這是書法創作的先決條件,同樣影響著創作者的創作狀態。元代陳繹云:“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郁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基調既定,才能夠自然而然地使用合適的點畫形質、結構方式以及章法來構成作品的視覺層面,再與書寫內容的意蘊共同構成作品的意蘊層面,如此在最大限度上完成書法作品意蘊的表達。
對于創作者的創作狀態而言,孫過庭曾有“五乖五合”之說: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③
此說指出心境、氣候、材料是影響創作者創作狀態的因素。孫過庭認為當時書法作為文人雅玩其背后所暗示的是普遍的對于閑適生活狀態的追求。當然,書法史中有一部分創作者在特殊時期創作的作品,如《喪亂帖》《祭侄文稿》等。雖不符合“五合”之說,其邏輯卻是一致的——即創作者的創作狀態與作品意蘊相符時有助于創作出得“神氣”的作品。
“院僧有少師(楊凝式)未留題詠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④這一段關于楊凝式“偶然欲書”的例子雖然無法看出楊凝式具體的動機為何,但也能說明創作狀態對于創作而言的重要性。“且吟且書”這幾字亦恰恰說明在楊凝式創作時,對于書寫內容有著深刻的體悟。我們很難想象當他在“似若發狂”的狀態下,書寫他所不熟悉、不理解的書寫內容,還能夠達到“筆與神會”的狀態。
2.從欣賞者的視角
一件作品意蘊的呈現,除了有創作者精熟的藝術表現手段、充分的動機、合宜的創作狀態之外,還存在著欣賞者基于自身對作品意蘊的解讀。書寫內容在書法作品中的意義從欣賞者的視角看,首先在于對審美感受的引導與制約。類似標題音樂中的標題⑤,如古琴曲《高山流水》,這一標題往往使欣賞者在欣賞音樂時能夠想象出意境悠遠的山水景色。而書法作品中的書寫內容比音樂的標題所起的作用更為徹底,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貫徹于作品的始末。觀者可以通過書寫內容更準確地接近于創作者的自身表達。當然,前提是它如實反映了創作者的欲念。
例如弘一法師的絕筆《悲欣交集》(圖1)。“九月初一日,書‘悲欣交集’四字,與侍者妙蓮,是為最后之絕筆。”⑥此四字點畫縱橫錯落,結構脫去往昔的精嚴,墨色由濃到淡,過渡自如,章法亦不復往日。弘一法師在選擇“悲欣交集”四字作為絕筆的書寫內容時,有著完整的動機。
在視覺層面,此作蒼潤的點畫、疏瘦的結構自然也能夠將我們引向一種“無執”、恬淡的感受。然而,簡單的“悲欣交集”四字卻在此基礎上使得觀者能夠試圖去共情弘一法師臨終前的感受,進一步聯想至弘一法師韻極風流再遁入空門的一生。此時此刻,關于歷史、哲學等層面的感受與視覺形象共同構成作品飽滿的意蘊。此后,由于欣賞者對書法、歷史、社會、哲學等知識儲備的相異,對此作會產生不盡相同的理解。學者葉圣陶先生解釋“欣”字,一輩子“好好地活”了,到如今“好好地死”了,歡喜滿足,了無缺憾。上海音樂學院錢仁康教授認為“‘悲’是悲憫眾生的苦惱,‘欣’是欣幸自身得到解脫”。⑦書寫內容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意蘊的廣度,甚至于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生命體驗的改變,對于作品意蘊的感受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以此賦予書法作品以鮮活的生命感。
三、經典之作中的書寫內容
在古往今來的經典之作中還存在許多書寫內容與作品的視覺層面相匹配、與作品所傳達的意蘊相得益彰的作品。
《蘭亭序》(圖2)便是一例。它書于最混亂、最痛苦又最自由的魏晉時期。可將前十一行作為一段,此段記錄了日期、環境與心情等實用性內容。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王羲之與友人相聚,左右環抱著“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在側,欣欣然嘆宇宙之大、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信可樂也。”⑧故第一段正是在這樣閑適的心境中,以清雅的內容、舒朗的章法、偏行楷化的結構、不激不厲的筆調來共同表現出人生當下所享受的歡愉。然而,“王羲之雖然深受黃老虛靜曠達思想的影響,具有飄逸優游,超脫寧靜的道家色彩,但又受到當時因‘世積亂離’而得到強化的悲劇意識的熏陶,形成了以悲為美的審美心理。”⑨在歡愉之中,他忽覺“俯仰一世”,所有的歡愉不過“暫得于己”,而壽命長短亦“終期于盡”。隨著“悲夫”之嘆,感慨“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⑩正是隨著王羲之對于人生、時間、命運的復雜思緒之涌現并付諸毫端,從十二行開始,《蘭亭序》的章法逐漸緊密,行列之間的穿插挪移變得更為激烈,結構的傾斜度也變得更為夸張。

圖2
顏真卿《祭侄文稿》中內容與作品意蘊的緊密關聯同樣典型。
與《蘭亭序》中微妙的情緒表現不同,《祭侄文稿》所表現的情感通過回憶中美好的迅速破碎,強化悲劇的氛圍。再念及當時的情境,將對逆賊與賊臣的痛恨、對顏杲卿和顏季明的追憶與痛心表現而出,直至推向最終的高潮,發出“嗚呼哀哉”之嘆。
全篇用筆沉著雄渾,延綿處一氣呵成,殺筆處風檣陣馬,沉著痛快。在開頭交代時期、官職等日用性內容時,整體節奏偏慢,以偏行楷化的結字為主。隨著書寫內容中出現的情緒激烈變化與悲情的不斷疊加,字法逐漸向行草過渡,最后的“嗚呼哀哉”四字更有一瀉千里之勢。如王澎《虛舟題跋》中所稱:“《祭季明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其書頓挫郁屈,不可控勒。……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情事不同,書法亦隨以異,應感之理也。”?書寫內容中所內蘊的悲慨之情與作品視覺層面的變化交相輝映。其二者各自開辟的意蘊空間同聲相應,共同構建起一個完整的審美場域,推動作品整體意蘊的表現。
“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書譜》此句同樣反映出對書寫內容意蘊層面的深入把握,能夠使我們維持在一定的創作狀態中來完成作品,以期作品意蘊層面的立體、豐滿。
還有諸多古代、近代的經典之作中,書寫內容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陸維釗書毛澤東詩詞集成之聯《抽寶劍 縛蒼龍》(見圖3)、沙孟海書毛澤東詞《清平樂·六盤山》(圖4),似岌岌蛟龍相纏,攝人心魄,豈未得書寫內容之助乎?

圖3

圖4
又如弘一法師書《世間虛妄樂》(圖5)煙火盡褪、纖塵不染,反觀徐生翁書《普賢觀經句》(圖6)幾近狂狷。皆言佛理,相去甚遠,是以書文相注,盡得“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卻是莊子注郭象”之趣。

圖5

圖6
再如良寬禪師為孩童借風而書的《天上大風》四字(見圖7),或許“好事者”又會聯想至“忙趁東風放紙鳶”了。而四字表現出的對書寫慣性毫不理會的灑脫,結構幾近支離而又純乎天然的靈妙,似又能與風產生某種關聯……
當然,在歷史上并非所有作品的書寫內容與作品意蘊之間都具有某種關聯。如王鐸的諸多作品,我們很難從這個角度對它做如是分析,這也并不妨礙其作品重要而獨特的價值。然而,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即書寫內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存在著發揮作用以期豐富作品內涵的可能。

圖7
結語
綜上所述,于創作者而言,書寫內容的選擇作為創作者創作的第一步,蘊含著創作者完整的動機。如此,書寫內容為作品奠定底色,建立起創作者自身與作品之間的關聯。同時,由于書法作品時間性的存在,使得書寫內容有著影響創作者創作狀態之用。當然,對于創作者動機的形成而言,書寫內容對創作者的觸動并非唯一的路徑。對于傳遞某種觀念的渴求、對于表現萬物之情狀的欲望等也足以構成完整的創作動機。
于欣賞者而言,首先,書寫內容會對作品意蘊的傳遞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引導作用,通過書寫內容所蘊含的意蘊使得欣賞者更容易接近創作者真實的動念。其次,書寫內容也在很大程度上擴寬了書法審美群體的邊界,使得更多不同領域、有著相異知識背景的人群能夠進入書法的鑒賞領域,進而對書法作品意蘊呈現多層面、多視角的解讀。
當然,關于書寫內容與書法作品創作與欣賞之關聯的探討容易產生牽強附會之嫌,容易走入主觀臆造的誤區。客觀上而言,對于任何一件作品的解讀都無法求證其最終呈現是否與創作者的動機相符,作者本身對于作品意蘊也不具備絕對的解釋權。然而,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在二十世紀提出的“作者已死”的著名論斷給予這個難處一個突破口。他認為作品一經完成就擁有了獨立的生命。將“作者已死”論與孟子“知人論世”的觀點相結合,一件作品的意蘊便是由創作者與欣賞者共同建構而成。對于書法作品而言,其書寫內容與作品意蘊的相映成趣——或“有意為之”或“不謀而合”——都給予了作品意蘊層面的表達更為廣闊的空間。
注釋:
①[日]海上雅臣:《井上有一——書法是萬人的藝術》,楊晶、李建華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88頁。
②[唐]孫過庭:《書譜》,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45頁。
③[唐]孫過庭:《書譜》,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91-93頁。
④李劍國 輯校:《宋代傳奇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0頁。
⑤邱振中:《書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頁。
⑥鄭逸梅:《清末民初文壇軼事》,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⑦方愛龍主編:《弘一大師新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頁。
⑧[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十,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99頁。
⑨何來勝:《蘭亭序及其書法文化意義》,[畢業論文],中國美術學院,第20-21頁。
⑩[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十,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99頁。
?[清]王澍:《虛舟題跋》,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頁。
?[唐]孫過庭:《書譜》,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