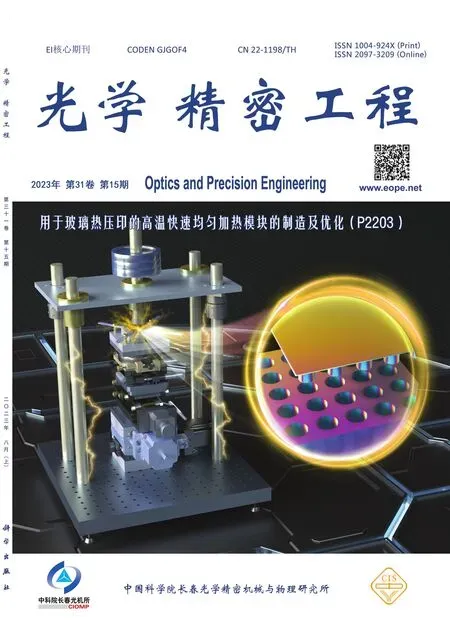液相下激光燒蝕快速制備圖案化銅微納結構
于苗苗, 翁占坤,2*, 王冠群, 郭川川, 胡俊廷, 王作斌
(1.長春理工大學 國家納米操縱與制造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 130022;2.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機電工程與自動化學院,廣東 佛山 528225)
1 引 言
金屬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導電性、導熱性和抗摩擦性等特性,廣泛應用于生產生活中,如半導體器件、基礎設施和工業設備等[1]。金屬表面微納結構化產生諸多優于體材料的特性并展現出新的性能,如浸潤性[2]、熱輻射[3]、耐腐蝕[4]和結構色[5]等,因此成為科學界和工業界關注的熱點,是當前金屬表面技術中重要的研究方向。
過去的二十年里,金屬表面微納結構制造技術得到了大量的研究,如光刻[6-7]、電化學[8-9]、氣相沉積[10-11]和激光加工技術[12-17]等。其中,激光加工技術具有高效、精密、靈活和無污染等優點,廣泛地應用在金屬微納結構的制備中[18-20]。Lloyd等[12]基于納秒脈沖激光器(Nd∶YVO4)于大氣環境下在不銹鋼表面制造了平均周期為30~50 μm的微錐結構。Li等[13]通過優化激光加工參數,采用納秒激光在鈦合金表面制備了具備減反射功能的無序微結構。Rajab等[14]利用皮秒和納秒激光在不銹鋼表面制備了24種超疏水結構,并研究了不同超疏水表面在室溫、高溫和冰水環境下的穩定性。Samanta等[15]在空氣中利用納秒脈沖激光表面織構技術在鋁合金表面制備微尺度溝槽,隨后通過化學修飾實現了疏水、疏甘油和疏乙二醇等特性。然而,大多數研究集中在氣相條件下制備金屬微納結構,相比之下,液相環境具有一定優勢。液相下激光燒蝕金屬表面,液體可通過汽化和形成等離子體的方式將部分光能轉化為機械脈沖,從而運輸材料并誘導形成結構[21]。在某些情況下,液體或其解離產物可以與材料發生化學反應,有助于目標產物和微納結構的形成[22]。此外,液相環境不僅能夠冷卻金屬表面,還能避免激光燒蝕金屬過程中產生納米顆粒,從而導致氣溶膠污染環境[22-24]。
在眾多金屬材料中,銅金屬不僅在自然界中儲量豐富,而且還具有高導電性、熱穩定性和優良的催化活性等性能。本文采用激光燒蝕技術在液相下快速制備了大面積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研究了激光功率、掃描速度和掃描次數等參數對銅微納結構的影響,分析了激光加工過程中微納結構的形成機制。此外,還研究了圖案化銅微納結構對純凈水和食用油的浸潤性。
2 實 驗
2.1 Cu2O微米粒子制備實驗
本實驗采用水熱還原法制備氧化亞銅微米顆粒(Cu2O microparticles,Cu2O-MPs)。首先,在磁力攪拌下,將0.88 g硝酸銅和1.36 g聚乙烯吡咯烷酮分別加入30 mL和60 mL乙二醇溶液中。攪拌至完全溶解(約30 min)后,將上述溶液充分混合并轉入聚四氟乙烯內襯的不銹鋼高壓反應釜中,在160 ℃下加熱6 h。最后,通過離心清洗(7 000 r/min)獲得Cu2O-MPs,室溫下分散在乙醇溶液中備用。
2.2 激光燒蝕制備圖案化銅微納結構實驗
本實驗以Prime級單晶硅(尺寸為1 cm×1 cm,厚度為50 μm,晶面為(100)晶面,單面拋光)作為襯底材料,采用光纖激光加工系統(型號為FB20-1,長春新產業光電技術有限公司)在液相條件下制備圖案化銅微納結構。該激光器波長為1 064 nm,脈寬約為100 ns,激光光斑直徑約為50 μm,頻率為20 kHz。
圖1為激光燒蝕制備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示意圖。首先,使用超聲波依次在丙酮、乙醇和去離子水中清洗硅襯底,以去除表面有機物和其他雜質。隨后,將清洗后的硅襯底放置在加工池中,并注入含有Cu2O-MPs的乙醇分散液。設置不同組合激光參數的納秒激光進行加工,從而制備圖案化銅微納結構。本實驗中,在50 μm的結構周期下,研究激光功率(1,2,3,4和5 W)、掃描速度(125,100,75,50和25 mm/s)和掃描次數(1~10)等參數對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影響。
2.3 測量與表征
通過掃描電子顯微鏡(SEM,FEI Quanta 250)對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形貌進行表征和分析。利用能量色散X射線光譜儀(EDS,Aztec 3.3)和X射線衍射儀(XRD,Y-2000)分析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元素組成和晶體結構,采用共聚焦顯微鏡(CSM 700)研究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平均粗糙度。使用接觸角測量儀(DSA100)測定了樣品對水和食用油的浸潤性(水為娃哈哈純凈水,食用油為金龍魚玉米胚芽油)。
3 結果與討論
3.1 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形貌結構表征
圖2(a)~2(e)顯示了在相同掃描速度(100 mm/s)和掃描次數(4次)時,不同激光功率(分別為1~5 W)下銅微納結構的SEM圖像和局部放大圖。如圖2(a)所示,激光功率為1 W時,由于激光光斑中心區域的能量和溫度大于光斑邊緣位置,中心區域的銅顆粒部分氣化,從而形成納米級銅顆粒[22,24]。從圖2(a)的光斑邊緣放大圖可以觀察到,銅顆粒僅有輕微燒蝕痕跡,這是因為高斯光斑邊緣位置激光能量較低[25]。對SEM圖進行快速傅里葉變換(Fast Fourier Transform, FFT)后生成頻譜圖(插圖),從明暗頻率分布可以看出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為周期性結構。當結構分布存在多個對稱軸時,在FFT頻譜圖中則存在多對中心對稱的頻率分量。通過選取第一級頻率分量(距離中心零頻率分量最近的一對呈中心對稱的頻率分量),根據其頻率分布進行計算,可以得到制備的圖案化銅微納結構周期約為52.3 μm。制備結構周期與設計值相差2.3 μm。當激光功率升至2 W時,如圖2(b)所示,光斑中心區域依然只有少量的銅納米顆粒,但是光斑邊緣位置形成的微米級顆粒明顯增多,并且微米級顆粒分布在光斑交界處形成微島結構。圖2(b)的光斑邊緣放大圖還顯示出此條件下顆粒的熔融程度加劇,顆粒之間的聚集現象更加明顯。由頻譜圖可以看出,結構輪廓邊緣越清晰,頻譜圖中明暗對比越強烈,與結構的周期性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根據頻率分布計算得出制備的結構周期約為51.2 μm,與設計值的誤差減小至1.2 μm。激光功率增加至3 W時,如圖2(c)所示,由于激光能量的增加,光斑中心位置形成的納米顆粒粒徑明顯增加,光斑交界處的微米級顆粒進一步熔融聚集。FFT頻譜圖中顯示,明暗對比減弱,對應于圖2(c)中有序度降低的現象。經計算,結構周期約為51.6 μm,誤差為1.6 μm。隨著激光功率繼續增加到4 W和5 W時,銅微納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圖2(d)和2(e)所示,硅片表面大部分激光掃描區域發生熔融現象,結構輪廓邊緣的清晰度明顯下降。光斑中心位置因高激光功率作用會產生飛濺物,這些飛濺物與熔融金屬顆粒混合后會迅速冷卻并凝固在光斑交界處[13]。根據FFT的頻譜圖計算得到結構周期分別約為52.5 μm和52.4 μm,與設計值的誤差進一步增大。以上結果表明,隨著激光功率的增加,結構的周期與設計值的誤差呈現先減小后增加的趨勢,在激光功率為2 W時,誤差最小。此外,在激光加工過程中,樣品表面會發生熔融現象,且該現象隨激光功率的增加而加劇。當激光能量適宜時,在光斑中心高能量區域形成納米顆粒,而邊緣低能量區域金屬顆粒因熔融而聚集成微島結構,由此形成圖案化銅微納結構。

圖2 掃描速度為100 mm/s時不同激光功率下制備的銅微納結構SEM圖像(插圖為傅里葉變換后頻譜圖)Fig.2 SEM images of Cu micro-nano structure prepared at scanning speed of 100 mm/s with different laser powers(Illustration is Fast Fourier Transform spectrum)
除激光功率外,掃描速度也是影響銅微納結構的關鍵因素之一。圖3(a)~3(e)展示了掃描4次,激光功率為2 W時,不同掃描速度(125,100,75,50和25 mm/s)對銅微納結構形成的影響。當掃描速度較快(見圖3(a)和3(b))時,激光燒蝕在同一點持續的時間較短,光斑交界位置形成的微米級銅顆粒的熔融程度較輕,顆粒之間的聚集程度較低。通過FFT頻譜圖計算得到結構周期分別約為52.8 μm和51.2 μm,導致誤差明顯不同的主要原因是銅顆粒的尺寸差異。當掃描速度降低至75 mm/s和50 mm/s時,每個燒蝕位置都受到連續脈沖的影響且隨著Cu2O-MPs分散液的不斷補充,在光斑邊緣位置聚集了更多的熔融銅微納顆粒。這些熔融銅微結構在液相下快速冷卻和凝固,在光斑交界處形成新的微點陣結構,如圖3(c)和3(d)所示。從光斑邊緣放大圖可以發現,形成的微島結構的致密性也有所增加。與此同時,在光斑中心區域形成了更多的納米顆粒。FFT頻譜圖顯示,當掃描速度為50 mm/s時,中心對稱的多級頻率分量明暗對比更加強烈,結構的周期性較好,計算得到的周期約為50.9 μm,與設計值更加接近。隨著掃描速度的繼續降低(見圖3(e)),激光在同一點燒蝕時間過長[26],會使熔融聚集的金屬顆粒再次發生熔融現象,顆粒的粒徑明顯增大,由FFT頻譜計算周期約為55.6 μm,與設計值的誤差較大。

圖3 激光功率為2 W時不同掃描速度下制備的銅微納結構SEM圖像(插圖為傅里葉變換后頻譜圖)Fig.3 SEM images of Cu micro-nano structure prepared at laser power of 2 W with different scanning speeds (Illustration is a Fast Fourier Transform spectrum)
掃描次數也是影響樣品表面形貌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27]。圖4(a)~4(j)為相同掃描速度(50 mm/s)和激光功率(2 W)時,不同掃描次數(1~10次)下形成的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SEM圖像和FFT頻譜(插圖)。如圖4(a)所示,當掃描次數僅為1次時,光斑交界處的非輻照區域形成的微米顆粒分布較為分散,且光斑中心處形成的納米顆粒較小,對約1 000個納米顆粒的粒徑進行統計,如表1所示,97.3%以上的納米顆粒小于200 nm。經過FFT頻譜計算制備微納結構的周期約為54.4 μm,與設計值相差4.4 μm。當掃描次數增加時(見圖4(b)和4(c)),光斑中心和邊緣位置形成的顆粒數量均明顯增加,中心區域小于200 nm的納米顆粒比例逐漸減少,較大尺寸的納米顆粒比例逐漸增多。另外,位于光斑邊緣處的顆粒存在熔融再聚集成更大金屬顆粒的趨勢。制備的結構周期與設計值誤差從3.3 μm減小到1.7 μm。如圖4(d)~4(h)所示,當掃描次數進一步增加時,微島結構更加規律地分布在光斑之間未輻照的區域,而光斑中心位置亞微米級的納米顆粒的比例隨之增大。當掃描次數達到5次以上時,中心位置粒徑大于500 nm的顆粒數量明顯增加。通過FFT頻譜計算得到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周期分別約為50.9,50.7,50.3,50.5和51.0 μm,制備的結構與設計值誤差呈現先減小后增大的趨勢。當掃描次數為6次時,頻譜中存在較多中心對稱的多級頻率分量對,且明暗對比較強烈,制備的結構周期與設計值的誤差最小。當掃描次數增長至9次和10次時(見圖4(i)和4(j)),顆粒的熔融現象更加明顯,光斑中心位置顆粒的尺寸明顯增大且無序度增加。制備的微納結構周期誤差也隨之增大,由1.5 μm增至2.1 μm。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如下:隨著掃描次數的增加,光斑中心位置會吸收更多的激光能量[28],產生大量的熔融納米顆粒,這些納米顆粒之間相互融合從而在中心位置形成尺寸更大的顆粒。此外,在激光照射區域會產生一定的等離子體,這些等離子體向兩側飛濺,聚集在激光非輻照區域并冷卻沉積,從而形成復合的微納混合結構。

表1 掃描次數對光斑中心顆粒粒徑的影響Tab.1 Effect of scanning times on particle size in center of laser spot

圖4 激光功率為2 W,掃描速度為50 mm/s時不同掃描次數下制備的銅微納結構SEM圖像(插圖為傅里葉變換后頻譜)Fig.4 SEM images of Cu micro-nano structure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scanning times at laser power of 2 W and scanning speed of 50 mm/s(illustration is Fast Fourier Transform spectrum)
3.2 EDS和XRD分析
為了確定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元素組成,采用EDS進行表征。圖5(a)為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EDS能譜,經過分析可知該結構含有Cu,Si,O和C元素。然后,隨機選取一個區域對圖案化銅微納結構進行元素面掃描測試。相應的元素映射圖像如圖5(b)~5(f))所示,Cu元素分布在整個樣品表面,含量大約為17.69%,主要對應于圖5(c)中較亮的區域。其中,光斑中心區域Cu元素信號較弱,光斑交界微點陣處Cu元素信號更強,這是由于光斑中心區域Cu含量較少,而光斑交界處Cu含量較高。此外,EDS結果顯示Si元素信號最強,占比約為65.27%,其原因是襯底為硅片。從圖5(e)中觀察到Si元素含量幾乎不會分布在微點陣區域,進一步證明此處存在更多的銅金屬顆粒。O元素(見圖5(f))含量最少,可能源自硅基底表面的氧化膜和Cu2O-MPs中含有的O。以上分析表明,液相激光燒蝕技術成功地在硅片表面沉積了銅金屬,并且形成微納復合結構。

圖5 掃描4次的銅微納結構的EDS能譜及元素映射圖Fig.5 EDS and element mapping images of Cu micro-nano structure prepared by scanning 4 times
對圖案化銅微納結構進行了XRD測試,如圖6所示,位于36.4°,61.3°和69.3°處的衍射峰分別與Cu2O的(111)和(220)晶面相對應;位于43.3°和74.1°處的衍射峰與銅的(111)和(220)晶面相對應,由此證明Cu2O和Cu同時存在于圖案化銅微納結構中,說明部分Cu2O顆粒經激光誘導還原生成Cu。

圖6 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XRD譜Fig.6 XRD spectra of patterned Cu micro-nano structure
3.3 激光燒蝕演變過程分析
基于激光加工參數對微納結構的影響規律,分析了溶液中納秒激光燒蝕形成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機理。通過比較不同激光參數下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形貌差異,并進行EDS和XRD分析,初步推斷微納結構是由激光誘導金屬熔融再凝固積累而形成的[13]。納秒激光加工金屬的主要作用是熱效應,由于納秒激光具有較大的峰值功率,材料表面發生熔融。在激光加工過程中,Cu2O-MPs中的電子吸收大量光子[29]。隨后,電子在短時間內轉移到晶格中,引起熱擴散,使金屬顆粒的溫度迅速升高,導致金屬顆粒的熔化和蒸發,從固態轉變為液態或氣態,甚至形成等離子體。由于輻射區域和附近未輻射區域之間存在明顯的溫差,從而產生馬蘭戈尼效應,這一效應驅使熔融金屬向激光照射位置邊緣移動。
當掃描次數為1次時,單位面積接收的激光能量較少,因此只有少量銅顆粒聚集在硅片表面,其周期性分布不明顯,如圖7(a)所示。然而,隨著掃描次數增加到4次,單位面積接收的激光能量增加,可以觀察到光斑邊緣位置聚集的銅顆粒增多,如圖7(b)所示。此外,EDS分析也證實這些位置Cu元素相對含量較多(見圖5(d)),且周期性分布更加明顯。隨著掃描次數的進一步增加和Cu2O-MPs分散液的補充,熔融金屬不斷聚集形成微島狀結構,如圖7(c)所示。在激光加工過程中,激光誘導等離子體形成的納米團簇會不斷地沉積到已加工區域和微島結構表面[30-31]。通過圖7(c)中的SEM插圖可以觀察到微島結構表面隨機分布大量納米顆粒。

圖7 液相下激光燒蝕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演變過程Fig.7 Evolution of patterned Cu micro-nano structure by laser ablation in liquid
由實驗結果可知,在激光加工過程中,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形貌特征與掃描次數是有一定相關性和規律性的,即當掃描次數增加時,光斑交界處的非燒蝕區域聚集的銅顆粒增多,形成微島結構,并且微島結構表面分布著大量納米顆粒。
3.4 浸潤特性
由于激光加工參數不同,硅片表面形成不同的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相應地,表面粗糙度也不盡相同。表2為不同掃描次數下樣品表面的平均粗糙度統計結果。隨著掃描次數從1增長至7后,樣品的表面粗糙度呈現增加趨勢。而當掃描次數達到7次以上時,粗糙度開始減小。樣品表面粗糙度是影響其浸潤特性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隨后針對樣品表面粗糙度開展浸潤特性的研究。

表2 掃描次數對圖案化銅微納結構表面粗糙度的影響Tab.2 Effect of roughness of patterned Cu micro-nano structure on different scanning times(μm)
一般來說,靜態接觸角(Contact Angle, CA)大于150°的表面被定義為超疏水表面。在自然界中,荷葉具有明顯的超疏水自清潔性能,人們稱這種自清潔過程為“荷葉效應”[32]。隨后,人們也在玫瑰花瓣上發現了類似的效應,稱為“花瓣效應”[33]。不同之處在于該表面除了超疏水性能外,還對水有很強的附著力,即使將花瓣倒置,水滴也不會滾落[33]。由此可見,“花瓣效應”與“荷葉效應”相似,但仍有區別。超疏水有兩種可能的模型:(1)一部分液體完全浸入固體表面結構(Wenzel model)[34];(2)液體與固體表面結構之間留有空氣(Cassie-Baxter model)[35]。Wenzel model 可以用以下方程來描述浸潤性:
式中:θw和θy分別為Wenzel接觸角和Young接觸角,r為粗糙度因子,表示粗糙表面的實際面積與其投影面積之比。
Cassie-Baxter模型用來描述非均質浸潤,即:
式中:θc和θy分別為Cassie-Baxter接觸角和Young接觸角,r為固體表面被液體浸潤的實際面積與投影面積之比,f為投影浸潤面積的面積分數。
在Cassie-Baxter體系中,液體只停留在凸出結構的表面,故此液滴下表面會與微觀結構構建相對穩定的空間,形成所謂的“氣穴”。另一方面,針對“花瓣效應”,基于Cassie模型發展的Cassie-impregnating模型[36]進行解釋更為合理,Cassie-impregnating模型認為液滴完全滲透到微米結構之間,但只能部分滲透到納米結構之間。因此,Cassie-impregnating被認為是一種中間狀態,液體浸潤表面的比例低于Wenzel狀態,但卻高于Cassie-Baxter狀態。
圖8為低黏附(Cassie-Baxter狀態)和高黏附(Cassie-impregnating狀態)超疏水表面液滴示意圖。在Cassie-Baxter體系中,由于液滴僅停留在納米結構頂端,在微觀結構之間部分下垂形成氣穴,因此液滴具有非常低的接觸角遲滯(CAH)和黏附力。針對Cassie-impregnating狀態,存在于納米結構間隙的氣穴使得微觀結構完全滲透和納米結構部分滲透,導致該結構存在高CA和高CAH狀態[37]。

圖8 低黏附(Cassie-Baxter狀態)和高黏附(Cassie-impregnating狀態)超疏水表面液滴示意圖Fig.8 Schematic of droplets on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ith low adhesion (Cassie-Baxter state) and high adhesion (Cassie-impregnating state)
本文分別測量了不同掃描次數下制備樣品的食用油和純凈水接觸角,以研究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疏油疏水能力。圖9顯示了不同樣品的油接觸角,整體呈現高斯分布。當掃描次數為1和2時,結構表面表現出顯著的親油性。隨著掃描次數增加至6和7時,樣品表面的油接觸角逐漸增大,分別達到(100.0±1.3)°和(101.0±2.0)°,呈現疏油性。當掃描次數為8及以上時,油接觸角開始減小。可見,樣品對油的浸潤性能與粗糙度變化規律有密切的關系,均呈現先增加后緩慢下降的趨勢。

圖9 不同掃描次數下制備的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水接觸角和油接觸角Fig.9 Water contact angle and oil contact angle of patterned Cu micro-nano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scanning times
從圖9可以看出,樣品對水的浸潤性與食用油的浸潤性變化趨勢相似,掃描1~10次后,接觸角變化亦呈現高斯分布。掃描1~3次后,水接觸角之間的差值變化較大,達到29.6°;而掃描4~6次后,疏水角變化趨于平緩,差值為7.1°。當掃描次數為6時,圖案化銅微納結構水接觸角達到(155.2±1.5)°,表現出超疏水性,優于同類銅基材料[38-42],且明顯高于硅片表面水接觸角[43]。當掃描次數為7~10后,接觸角開始下降,并呈現線性遞減的趨勢。這與樣品表面粗糙度的變化趨勢一致。
由許多獨立的微島和納米顆粒組成的圖案化銅微納結構表面具有“花瓣效應”,且每個微島表面均覆蓋少量納米顆粒構成微納跨尺度的二元結構[36]。顯然這些二元結構對表面粗糙度具有重要貢獻。當樣品表面垂直或上下翻轉時,微結構之間形成的氣穴就會產生負壓,對水滴產生吸引力,從而貢獻為水滴與表面的黏附力,如圖10所示。即使當樣品垂直或倒置時,水滴依然保持近球形狀態或球形狀態。

圖10 圖案化銅微納結構垂直和倒置時水滴的形狀Fig.10 Shape of droplets when patterned Cu micro-nano structure were vertical and inverted
4 結 論
本文討論了激光功率、掃描速度和掃描次數對液相下激光燒蝕制備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影響,分析了激光燒蝕過程中圖案化銅微納結構的形成機制,并驗證了該結構在疏水疏油表面材料方面的潛在應用。實驗結果表明:在激光功率為2 W,掃描速度為50 mm/s的條件下,隨著掃描次數的增加,銅微納結構呈光斑中心為納米顆粒,邊緣為微米顆粒的銅微納復合結構,并且結構表面的粗糙度與水/食用油接觸角的變化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呈現高斯分布。當掃描次數為6時,樣品表面水接觸角可以達到(155.2±1.5)°,油接觸角為(100.0±1.3)°,呈現超疏水和疏油特性。本工作提供了一種簡單、廉價、便捷和無粉塵污染的圖案化銅微納復合功能表面的制備方法,這種既具有疏水性又具有黏附性的表面在集水凈水系統、微流控和污水處理中有良好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