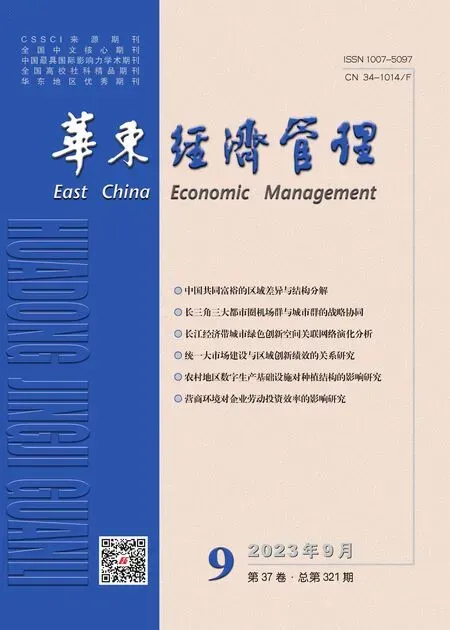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研究
王仁祥,郭曉媛
(武漢理工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0)
一、引言及文獻(xiàn)綜述
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進(jìn)入新常態(tài),如何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成為國(guó)家的重要目標(biāo)(陶鋒等,2017)[1]。金融與科技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兩大引擎,深析金融與科技系統(tǒng)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促進(jìn)兩者有效耦合,對(duì)走穩(wěn)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道路具有重要意義。“十四五”規(guī)劃明確指出,“加快建設(shè)科技強(qiáng)國(guó)”“完善金融支持創(chuàng)新體系”應(yīng)成為新時(shí)代的主要任務(wù)(1);《金融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2022—2025年)》再次強(qiáng)調(diào),要促進(jìn)金融與科技的深層次融合(2)。因此,加快現(xiàn)代金融體系建設(shè)步伐,推動(dòng)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緩解“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是建設(shè)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新時(shí)代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支點(diǎn)。
近年來,我國(guó)金融系統(tǒng)與科技系統(tǒng)的耦合發(fā)展緩慢,隨之產(chǎn)生的耦合脆弱性問題也一直存在。以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云計(jì)算、人工智能、區(qū)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shù)逐漸與傳統(tǒng)金融全方位融合,在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帶來了因部分資源無法自由流動(dòng)、有效匹配而產(chǎn)生的脆弱性問題[2],主要表現(xiàn)在當(dāng)系統(tǒng)遭受內(nèi)、外部擾動(dòng)時(shí),耦合系統(tǒng)內(nèi)部原有序列狀態(tài)會(huì)被破壞,若這種受損積累過多,可能引發(fā)區(qū)域性耦合系統(tǒng)危機(jī)[3]。同時(shí),在我國(guó)許多區(qū)域興起的“金融中心熱”,使金融資源加速向某些城市集聚。中國(guó)(深圳)綜合開發(fā)研究院發(fā)布的《中國(guó)金融中心指數(shù)》第十三期指出,以直轄市和省會(huì)城市為主體的31 個(gè)金融中心城市貢獻(xiàn)全國(guó)金融業(yè)增加值的60.2%,其金融機(jī)構(gòu)總資產(chǎn)規(guī)模占全國(guó)比重超過3/4,擁有全國(guó)商業(yè)銀行總資產(chǎn)的74%、證券公司總資產(chǎn)的96%、保險(xiǎn)公司總資產(chǎn)的90%(3)。金融資源在地理空間上呈現(xiàn)的集聚特征對(duì)金融與科技耦合系統(tǒng)脆弱性有什么影響,發(fā)揮何種作用,各區(qū)域金融產(chǎn)業(yè)集聚的作用如何?對(duì)此,本文以2005—2020年我國(guó)各省份的面板數(shù)據(jù)為研究對(duì)象,采用空間計(jì)量方法分析兩者的空間效應(yīng)及區(qū)域性差異,探析金融資源集聚能否降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為促進(jìn)金融發(fā)展與科技創(chuàng)新的有效耦合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參考。
在金融集聚發(fā)展過程中,韋伯最早在空間分析體系中提出了“集聚經(jīng)濟(jì)”的概念。1980 年,馬歇爾利用空間集聚外在性理論解釋金融集聚現(xiàn)象,金融集聚的研究逐步得到學(xué)者們的重視。早期學(xué)者對(duì)集聚效應(yīng)的研究并未充分考慮空間效應(yīng)的影響,20 世 紀(jì)90 年 代,Krugman(1991)[4]、Krugman 和Venables(1995)[5]和Fujita 等(1999)[6]在新經(jīng)濟(jì)地理學(xué)的研究中成功分析了金融集聚的空間效應(yīng)產(chǎn)生的影響。此后,學(xué)者們從不同角度開展了對(duì)金融集聚理論和實(shí)證方面的研究。目前,金融集聚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關(guān)注對(duì)技術(shù)進(jìn)步、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影響。陳林心和何宜慶(2016)[7]、劉繼和馬琳琳(2019)[8]對(duì)經(jīng)濟(jì)、地理因素綜合研究后,認(rèn)為金融集聚具有空間同質(zhì)性,能夠促進(jìn)本地生態(tài)效率提升;孫建國(guó)和高巖(2019)[9]、李海艦(2019)[10]研究發(fā)現(xiàn),金融集聚為城市整體層面的技術(shù)進(jìn)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張秀艷(2019)[11]借助工業(yè)行業(yè)的大中型企業(yè)數(shù)據(jù),分析了金融集聚對(duì)工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負(fù)向影響效應(yīng);張鐘元等(2020)[12]認(rèn)為,金融集聚可以通過規(guī)模經(jīng)濟(jì)、網(wǎng)絡(luò)協(xié)作及擴(kuò)散效應(yīng)促進(jìn)綠色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同時(shí)金融集聚還存在非線性效應(yīng)。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xué)者們開始關(guān)注金融與科技間的密切互動(dòng)和深度耦合,并將物理學(xué)的“耦合”“脆弱性”等概念引入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深入研究“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耦合效率及其脆弱性。徐玉蓮等(2011)[13]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guó)各省份科技金融與科技創(chuàng)新的耦合協(xié)調(diào)度偏低,多數(shù)省份科技金融發(fā)展較為滯后,地區(qū)間耦合協(xié)調(diào)度差距明顯;隨著科技創(chuàng)新與金融創(chuàng)新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因其涉及系統(tǒng)廣、需協(xié)調(diào)因素多、環(huán)節(jié)相對(duì)長(zhǎng)等特點(diǎn)而逐漸凸顯[14];王仁祥等(2016)[15]從耦合系統(tǒng)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廣義虛擬環(huán)境基礎(chǔ)、耦合系統(tǒng)功能效率三個(gè)維度構(gòu)建科技創(chuàng)新與金融創(chuàng)新耦合系統(tǒng)脆弱性指數(shù),分析了34 個(gè)樣本國(guó)的耦合系統(tǒng)脆弱性演進(jìn)趨勢(shì)及差異性表現(xiàn),研究表明,樣本國(guó)的耦合系統(tǒng)脆弱性大多處于中等水平,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耦合系統(tǒng)脆弱性整體低于發(fā)展中國(guó)家;基于網(wǎng)絡(luò)DEA 方法,王仁祥和楊曼(2018)[16]對(duì)中國(guó)1996—2014 年省域科技與金融的耦合效率進(jìn)行了科學(xué)測(cè)算;張芷若和谷國(guó)鋒(2019)[17]從空間角度分析我國(guó)科技金融與科技創(chuàng)新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結(jié)果顯示兩者的空間集聚特征顯著,并呈現(xiàn)東部強(qiáng)、中西部弱的分布趨勢(shì)。
目前,學(xué)界在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影響方面還未深入研究。王仁祥等(2020)[18]認(rèn)為,金融資本要素集聚會(huì)增強(qiáng)“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但效應(yīng)并不顯著;進(jìn)一步分區(qū)域探討發(fā)現(xiàn),東部地區(qū)金融資本集聚與脆弱性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中西部地區(qū)金融資本集聚與脆弱性呈顯著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本文擬在現(xiàn)有研究的基礎(chǔ)上,深入探究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以期豐富“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研究?jī)?nèi)容。
二、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空間影響的理論機(jī)理
“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是科技子系統(tǒng)與金融子系統(tǒng)相互作用、不斷交融產(chǎn)生的復(fù)合體。各子系統(tǒng)與外界環(huán)境間進(jìn)行物質(zhì)、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在復(fù)雜的要素交換過程中,耦合系統(tǒng)難免會(huì)受到內(nèi)、外部的干擾,一個(gè)或多個(gè)子系統(tǒng)在某些干擾下會(huì)面臨崩潰的風(fēng)險(xiǎn),而這些面臨崩潰的子系統(tǒng)會(huì)進(jìn)一步間接影響其他子系統(tǒng),最終導(dǎo)致系統(tǒng)局部或全部癱瘓。隨著復(fù)雜系統(tǒng)的部分或整體功能喪失,整個(gè)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也表現(xiàn)出來。與此同時(shí),金融部門、機(jī)構(gòu)、公司等在地域上向特定區(qū)域集聚,形成一個(gè)大型動(dòng)態(tài)網(wǎng)絡(luò)圈。在網(wǎng)絡(luò)圈中,各要素金融資源相對(duì)自由流動(dòng),各機(jī)構(gòu)、企業(yè)間近距離溝通交流,信息流動(dòng)性大大提升,同時(shí)競(jìng)爭(zhēng)也更加激烈。由此,本文認(rèn)為金融集聚主要通過本地效應(yīng)和空間溢出效應(yīng)對(duì)耦合系統(tǒng)的干擾度、敏感性、恢復(fù)力產(chǎn)生影響,并進(jìn)一步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產(chǎn)生影響。具體影響機(jī)制如圖1所示。

圖1 金融集聚影響“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作用機(jī)制過程
(一)金融集聚影響“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本地效應(yīng)
金融集聚是以政府和市場(chǎng)為主導(dǎo)的、從無序到有序的金融發(fā)展過程,其最大的特點(diǎn)便是金融產(chǎn)業(yè)、人才、技術(shù)、信息等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性的空間地域集聚,逐漸發(fā)展成具有互動(dòng)性、層次性、多樣性的金融網(wǎng)絡(luò)。金融網(wǎng)絡(luò)的復(fù)雜結(jié)構(gòu)使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時(shí)空、方向、金融結(jié)構(gòu)間的復(fù)雜差異。金融資源的集聚通過要素遷移以及強(qiáng)化區(qū)域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的方式發(fā)揮本地效應(yīng),進(jìn)而影響“金融—科技”的耦合脆弱性。
一方面,金融資源的本地效應(yīng),通過優(yōu)化資源配置、強(qiáng)化市場(chǎng)監(jiān)管、推動(dòng)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有效集聚方式影響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從資源配置角度來看,金融資源的有效集聚能夠打破區(qū)域間資源互動(dòng)的壁壘、加快區(qū)域間金融資源流動(dòng),進(jìn)而優(yōu)化區(qū)域資源配置;從市場(chǎng)監(jiān)管角度來看,區(qū)域經(jīng)濟(jì)規(guī)模集中能夠提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網(wǎng)絡(luò)主體的溝通效率和風(fēng)險(xiǎn)防范能力,使區(qū)域成為一個(gè)高效的經(jīng)濟(jì)資源共享有機(jī)體,降低監(jiān)督管理成本的同時(shí)強(qiáng)化市場(chǎng)監(jiān)管;從技術(shù)創(chuàng)新角度來看,人才、資金與技術(shù)的集聚,給區(qū)域的創(chuàng)新帶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和信息資源,推動(dòng)區(qū)域技術(shù)創(chuàng)新。有效集聚的最終結(jié)果,是可以降低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另一方面,金融資源的本地效應(yīng),通過剝削區(qū)域資源、引發(fā)區(qū)域過度競(jìng)爭(zhēng)、打破區(qū)域?qū)哟谓Y(jié)構(gòu)的擁擠集聚方式影響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從區(qū)域資源角度來看,中心城市的虹吸作用使周邊資源向其集中,而過度集中將導(dǎo)致區(qū)域資源擁擠,極化金融網(wǎng)絡(luò)節(jié)點(diǎn)間的資源配置,降低金融網(wǎng)絡(luò)節(jié)點(diǎn)間的互動(dòng)效率、減小互動(dòng)規(guī)模;從區(qū)域競(jìng)爭(zhēng)角度來看,金融要素的高度集中使地區(qū)金融機(jī)構(gòu)密度過高,引發(fā)行業(yè)內(nèi)過度競(jìng)爭(zhēng),破壞行業(yè)內(nèi)的多樣性,造成行業(yè)內(nèi)壟斷,不利于區(qū)域金融與科技網(wǎng)絡(luò)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從層次結(jié)構(gòu)角度來看,擁擠集聚使要素在空間上產(chǎn)生斷層現(xiàn)象,加深各個(gè)要素主體間的互動(dòng)鴻溝,導(dǎo)致金融網(wǎng)絡(luò)運(yùn)行紊亂。擁擠集聚的最終結(jié)果,是可能增強(qiáng)了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
因此,金融集聚通過資源集中改變區(qū)域金融與科技間的要素交流,為“金融—科技”的耦合提供內(nèi)部及外部環(huán)境,以金融集聚的互動(dòng)性、層次性、多樣性影響著“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干擾度、敏感性及恢復(fù)力。
(二)金融集聚影響“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溢出效應(yīng)
金融集聚是一個(gè)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利益最大化的發(fā)展過程,包含時(shí)間、空間上的靜態(tài)和動(dòng)態(tài)變化。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并反哺周邊地區(qū),在地理空間上影響“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一方面,金融集聚能夠提高金融服務(wù)業(yè)的效率,帶動(dòng)周邊地區(qū)金融服務(wù)業(yè)發(fā)展,提高區(qū)域“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抗干擾性,同時(shí)加速信息技術(shù)進(jìn)步,改善周邊地區(qū)信息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提高區(qū)域“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恢復(fù)力;此外,金融集聚能夠加速金融與科技的融合,優(yōu)化資源配置,使周邊地區(qū)共享金融與科技深度耦合的成果,有效降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另一方面,資源、技術(shù)與人才長(zhǎng)時(shí)間的過度集中,導(dǎo)致周邊地區(qū)的資源配置等基礎(chǔ)設(shè)施難以吸收中心地區(qū)的反哺,技術(shù)與人才的匱乏降低科技創(chuàng)新的活力,加劇區(qū)域發(fā)展的不平衡,降低了區(qū)域“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抗干擾性;加上區(qū)域資源消化能力有限,過度的資源集中使得人才和金融機(jī)構(gòu)難以回流,降低區(qū)域“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恢復(fù)力;此外,周邊地區(qū)對(duì)中心城市的依賴性過高,缺乏風(fēng)險(xiǎn)防范能力,導(dǎo)致“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不穩(wěn)定,加深了“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
由此看來,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技術(shù)創(chuàng)新等內(nèi)生動(dòng)力推動(dòng)區(qū)域金融集聚,并通過行業(yè)溢出、技術(shù)溢出、知識(shí)溢出回饋周邊地區(qū);經(jīng)濟(jì)規(guī)模、市場(chǎng)機(jī)制、區(qū)域因素、人力資本、政策環(huán)境五方面的外生動(dòng)力加速區(qū)域金融集聚,促進(jìn)了周邊地區(qū)的發(fā)展。在此過程中,金融集聚帶來的本地效應(yīng)及溢出效應(yīng)影響著“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復(fù)雜性以及區(qū)位因素也給中心城市對(duì)周圍地區(qū)的“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帶來不確定性。
三、研究設(shè)計(jì)
(一)計(jì)量模型
本文首先構(gòu)建基準(zhǔn)回歸模型(OLS)如下:
其中:ε符合正態(tài)分布;Frag、Fa分別表示“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金融集聚;X表示控制變量,包括信息化水平(Inf)、市場(chǎng)化水平(Mar)和經(jīng)濟(jì)水平(Fin)。
考慮金融集聚與“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空間效應(yīng)、動(dòng)態(tài)效應(yīng)及內(nèi)生性問題帶來的影響(Elhorst,2014)[19],本文采用空間動(dòng)態(tài)面板模型進(jìn)行分析,即在公式(1)的基礎(chǔ)上增加時(shí)間和空間因素的影響。構(gòu)建的動(dòng)態(tài)空間面板模型如下:
其中:Fragit、Fait分別表示i省份在t時(shí)間的“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金融集聚;αi、υt、εit分別為地區(qū)效應(yīng)、時(shí)間效應(yīng)和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θ為滯后一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反應(yīng)系數(shù);ρ、λ分別為空間自回歸系數(shù)和空間誤差系數(shù),衡量“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空間關(guān)聯(lián)程度,反映“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空間溢出效應(yīng);wit為空間權(quán)重矩陣,采用地理距離的倒數(shù)作為權(quán)重;ln Fait表示本地金融集聚表示鄰地金融集聚。
(二)變量說明
1.“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
本文基于實(shí)證經(jīng)驗(yàn),構(gòu)建“干擾—敏感—恢復(fù)”的評(píng)價(jià)框架,從干擾度、敏感性和恢復(fù)力三個(gè)維度建立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標(biāo)體系,見表1所列。

表1 “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標(biāo)體系
干擾度反映耦合系統(tǒng)受系統(tǒng)內(nèi)部和外部擾動(dòng)的程度,干擾度越大,潛在耦合脆弱性越高,本文主要考慮金融和科技系統(tǒng)規(guī)模、外部系統(tǒng)刺激情況;敏感性反映“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受到外界干擾的難易程度,敏感性較高的區(qū)域,受破壞的可能性較大,耦合脆弱性較高,主要考慮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和社會(huì)系統(tǒng)狀態(tài);恢復(fù)力反映耦合系統(tǒng)適應(yīng)外界干擾和從破壞中恢復(fù)的能力,恢復(fù)能力越強(qiáng),耦合脆弱性越低,主要考慮金融系統(tǒng)恢復(fù)力和科技系統(tǒng)恢復(fù)力。綜合考慮指標(biāo)的科學(xué)性、代表性、可獲得性和可比性,結(jié)合“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評(píng)估需求和實(shí)際情況,參考學(xué)者研究成果[20],本文構(gòu)建“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評(píng)估指標(biāo)體系,選取的指標(biāo)均為負(fù)向指標(biāo)。為消除指標(biāo)量綱差異,采用極差變換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運(yùn)用熵值法計(jì)算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測(cè)度“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
2.金融集聚
金融業(yè)主要包括銀行業(yè)、證券業(yè)和保險(xiǎn)業(yè)三大行業(yè),這三大行業(yè)能很好地反映金融行業(yè)空間集聚情況。受地區(qū)規(guī)模差異因素的影響,為較好反映地區(qū)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現(xiàn)有研究通常使用區(qū)位熵指數(shù)計(jì)算金融集聚指數(shù)。本文參考周炯等(2014)[21]的方法,計(jì)算公式如下:
其中:下標(biāo)Hi、m、n分別表示不同行業(yè)、年份和地區(qū);qn為地區(qū)n的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q為全國(guó)各地生產(chǎn)總值之和;在銀行業(yè)中,F(xiàn)H1amn為地區(qū)n金融業(yè)的區(qū)位熵,qmn為地區(qū)n金融機(jī)構(gòu)人民幣在m年的存款之和,qm為全國(guó)金融機(jī)構(gòu)在m年的人民幣存款之和;在證券業(yè)中,F(xiàn)H2amn為地區(qū)n證券業(yè)的區(qū)位熵,qmn為地區(qū)n在m年股票市價(jià)總值,qm為全國(guó)股票在m年的市價(jià)總值;在保險(xiǎn)業(yè)中,F(xiàn)H3amn為地區(qū)n保險(xiǎn)業(yè)的區(qū)位熵,qmn為地區(qū)n在m年的保費(fèi)收入,qm為m年全國(guó)保費(fèi)收入。根據(jù)(3)式計(jì)算出三個(gè)行業(yè)的集聚水平并進(jìn)行因子分析,得到最終的金融集聚水平。
3.控制變量
為控制省域異質(zhì)性的影響,本文納入一些其他變量:①信息化水平(Inf)。根據(jù)前文理論分析,信息化水平是影響金融集聚、“金融—科技”耦合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水平測(cè)度方面,限于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借鑒劉生龍和胡鞍鋼(2010)[22]的做法,本文采用人均服務(wù)郵電量予以代理。②經(jīng)濟(jì)水平(Fin)。地區(qū)經(jīng)濟(jì)水平會(huì)影響地區(qū)的金融集聚水平,本文采用地區(qū)財(cái)政收入占GDP比重表示。③市場(chǎng)化水平(Mar)。本文采用樊綱等構(gòu)造的《中國(guó)市場(chǎng)化指數(shù)》表征市場(chǎng)化水平,該指數(shù)目前只公布了2019年前的數(shù)據(jù),故2020年該數(shù)據(jù)通過采用市場(chǎng)化測(cè)算公式得到。
(三)數(shù)據(jù)說明與統(tǒng)計(jì)描述
本文選取2005—2020 年我國(guó)30 個(gè)省份(不包括西藏及港澳臺(tái)地區(qū))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jìn)行分析,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guó)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guó)金融年鑒》等。相關(guān)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jì)結(jié)果見表2所列。

表2 主要變量的基本統(tǒng)計(jì)特征
四、實(shí)證分析
(一)“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分布特征
對(duì)2005—2020年我國(guó)30個(gè)省份“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進(jìn)行測(cè)算,如圖2 所示。可以發(fā)現(xiàn),脆弱性指數(shù)整體位于區(qū)間[0.49,0.80],處于中高水平,近年略微下降;同時(shí),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具有顯著的空間差異,東部地區(qū)脆弱性指數(shù)低于中西部和全國(guó)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區(qū)脆弱性指數(shù)高于全國(guó)平均水平。

圖2 2005—2020年“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
(二)金融集聚時(shí)間演變特征
本文運(yùn)用Origin 軟件繪制2005—2020 年我國(guó)金融集聚的空間梯度分布圖,如圖3 所示。在研究期內(nèi),我國(guó)金融集聚呈現(xiàn)顯著空間差異,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高的地區(qū)金融集聚水平也高(如北京、上海等),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低的地區(qū)金融集聚水平同樣較低(如貴州、甘肅等)。從空間分布特征來看,金融集聚的分布為明顯的梯度結(jié)構(gòu),2005—2020 年,金融集聚均呈現(xiàn)自東南向西北地區(qū)逐漸遞減的空間分布格局。東部沿海地區(qū)金融集聚水平普遍較高,而中西部地區(qū)的金融集聚水平大部分偏低。截至2020 年,我國(guó)金融集聚水平整體明顯提高,金融集聚水平低的省份明顯減少。

圖3 2005—2020年我國(guó)各地區(qū)金融集聚水平
(三)空間面板回歸
1.空間相關(guān)性檢驗(yàn)
使用Moran'sI指數(shù)對(duì)中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進(jìn)行空間相關(guān)性檢驗(yàn)。定義地理距離空間權(quán)重矩陣W,wij構(gòu)造原則為:
其中:下標(biāo)i、j分別表示相應(yīng)省份;d表示兩地區(qū)中心位置之間的距離。
Moran'sI指數(shù)的計(jì)算公式如下:
Moran'sI指數(shù)及其統(tǒng)計(jì)檢驗(yàn)結(jié)果見表3所列,可以看出,研究期內(nèi),我國(guó)地區(qū)間“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存在正向空間依賴性。2018 年、2020 年Moran'sI指數(shù)分別為-0.022 和-0.001,均不顯著,說明這兩年“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在省份間呈現(xiàn)弱負(fù)空間自相關(guān)性;其他年份的Moran'sI指數(shù)皆顯著為正,說明省份間“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整體呈現(xiàn)空間聚集性。在考察期內(nèi),Moran'sI指數(shù)呈“鋸齒形”變化趨勢(shì),在2010 年和2014 年均達(dá)到了極大值0.066。

表3 2005—2020年中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Moran's /指數(shù)及其檢驗(yàn)
為進(jìn)一步揭示耦合脆弱性的空間異質(zhì)性,本文繪制出2005 年、2010 年、2015 年和2020 年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的Moran'sI散點(diǎn)圖,如圖4 所示(4)。除廣東、安徽、河北、江西和內(nèi)蒙古等,其他省份多位于第一、三象限,說明我國(guó)地區(qū)“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之間的依賴特征是正向的。位于第三象限的地區(qū),如上海、江蘇、山東和浙江等東部省份,表現(xiàn)出“低—低”集聚現(xiàn)象;位于第一象限的地區(qū),如甘肅、青海、云南和黑龍江等中西部省份,表現(xiàn)出“高—高”集聚現(xiàn)象。同時(shí),從Moran'sI散點(diǎn)的時(shí)序變化可以看出,各地區(qū)所處的象限沒有太大變化,說明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存在的空間相關(guān)性較為穩(wěn)定。還需說明的是,2020 年的Moran'sI指數(shù)散點(diǎn)圖表明各區(qū)域耦合脆弱性并未表現(xiàn)強(qiáng)相關(guān)性。

圖4 “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的Moran's I散點(diǎn)圖
2.估計(jì)結(jié)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穩(wěn)健Lagrange 乘數(shù)對(duì)空間面板模型進(jìn)行選擇,檢驗(yàn)發(fā)現(xiàn),空間自回歸模型(SAR)與空間誤差模型(SEM)的穩(wěn)健Lagrange 乘數(shù)在10%的水平上均通過了檢驗(yàn),考慮“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滯后影響,以SAR 模型為基礎(chǔ)構(gòu)建空間動(dòng)態(tài)SAR 模型進(jìn)行檢驗(yàn),結(jié)果見表4 所列,模型估計(jì)結(jié)果見表5所列。

表4 SAR與SEM模型的穩(wěn)健Lagrange乘數(shù)檢驗(yàn)
由表5 可知,在模型(1)中,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是負(fù)向的,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yàn),即金融集聚每增加1%,“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平均減少0.195%,說明我國(guó)金融行業(yè)處于有效集聚狀態(tài),能夠降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此外,信息化水平、經(jīng)濟(jì)水平、市場(chǎng)化水平也能降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進(jìn)一步分析發(fā)現(xiàn),模型(2)—(6)的估計(jì)系數(shù)符號(hào)及顯著性與模型(1)沒有太大差異,本地金融集聚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鄰地金融集聚系數(shù)顯著為正且遠(yuǎn)大于本地金融集聚系數(shù),說明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空間溢出作用遠(yuǎn)大于本地效應(yīng),金融集聚每提升1%,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平均降低約0.08%,而金融集聚每提升1%,鄰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平均增加約0.33%。空間動(dòng)態(tài)SAR 面板模型的估計(jì)結(jié)果與靜態(tài)SAR 面板模型的系數(shù)及符號(hào)基本類似,說明考慮地理距離和空間溢出效應(yīng)來分析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效應(yīng)是合適的。但靜態(tài)空間面板模型低估了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本地效應(yīng)并夸大了空間溢出效應(yīng),原因在于模型(6)中的金融集聚度系數(shù)(-0.065)顯著大于模型(5)中的金融集聚度系數(shù)(-0.072)、模型(6)鄰地金融集聚系數(shù)(0.415)大于模型(5)中的鄰地金融集聚度系數(shù)(0.369)。更重要的是,動(dòng)態(tài)空間面板模型中“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一階滯后項(xiàng)都為正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yàn),說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的一階滯后項(xiàng)能將影響耦合系統(tǒng)的潛在因素(如經(jīng)濟(jì)及政策環(huán)境等)從空間結(jié)構(gòu)因素的影響中分離出來,從而使靜態(tài)空間面板模型的偏差得以糾正,也反映了中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具有動(dòng)態(tài)性、連續(xù)性的特征。
由模型(5)的估計(jì)結(jié)果可知,金融集聚的空間滯后項(xiàng)系數(shù)顯著為正,表明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具有正向溢出效應(yīng),金融集聚可以提高鄰地的“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由于金融行業(yè)較少受到區(qū)域運(yùn)輸成本的限制,因此,金融集聚甚至可以跨區(qū)域影響“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可見,金融集聚對(duì)地理距離的弱敏感性,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地理距離的束縛,使金融集聚可以通過優(yōu)化資源配置、強(qiáng)化市場(chǎng)監(jiān)管、推動(dòng)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方式遠(yuǎn)距離作用于相關(guān)地區(qū)的“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在控制變量方面,經(jīng)濟(j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存在明顯降低作用,且都通過了10%和1%的顯著性檢驗(yàn);市場(chǎng)化水平系數(shù)為正,說明市場(chǎng)化水平會(huì)提高耦合脆弱性,但不顯著。可見,外界環(huán)境因素是“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從低級(jí)形態(tài)向高級(jí)形態(tài)不斷演化的關(guān)鍵要素。
3.行業(yè)層面的差異性
考慮我國(guó)金融行業(yè)在各區(qū)域的分布密度不同,“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在不同金融行業(yè)中可能存在差異性。本文進(jìn)一步檢驗(yàn)三大行業(yè)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估計(jì)結(jié)果見表6所列。

表6 不同行業(yè)的動(dòng)態(tài)空間面板模型估計(jì)結(jié)果
在我國(guó)金融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由于地區(qū)資源錯(cuò)配,三大行業(yè)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有較大差異。由表6可知,銀行業(yè)和保險(xiǎn)業(yè)的集聚顯著降低了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而證券業(yè)的集聚會(huì)提高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但系數(shù)未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此外,三大金融行業(yè)的集聚都具有顯著空間溢出效應(yīng),從估計(jì)系數(shù)來看,溢出效應(yīng)遠(yuǎn)大于本地效應(yīng),銀行業(yè)的集聚對(duì)耦合脆弱性的降低作用與空間溢出效應(yīng)都最大,銀行業(yè)集聚水平每增加1%,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平均降低0.07%,鄰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平均增加0.40%。在我國(guó)三大金融行業(yè)中,證券業(yè)區(qū)域發(fā)展最不平衡,上海和北京等中心城市證券業(yè)高度集中,減弱了本地區(qū)證券業(yè)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負(fù)向影響。在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背景下,協(xié)調(diào)三大金融行業(yè)區(qū)域平衡有助于降低“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
4.區(qū)域?qū)用娴漠愘|(zhì)性
我國(guó)幅員遼闊,地區(qū)間的金融集聚水平各異。根據(jù)我國(guó)的行政區(qū)域,將30 個(gè)省份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qū),分別研究三個(gè)區(qū)域的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影響,結(jié)果見表7所列。

表7 三大區(qū)域動(dòng)態(tài)空間面板模型估計(jì)結(jié)果
表7的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在本地效應(yīng)中,東部地區(qū)的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有顯著降低作用,中西部地區(qū)的金融集聚則會(huì)提高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且系數(shù)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在溢出效應(yīng)中,只有西部地區(qū)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檢驗(yàn)。東部地區(qū)是我國(guó)金融要素高度集中的地區(qū),金融集聚通過優(yōu)化資源配置、完善市場(chǎng)監(jiān)管和加速技術(shù)創(chuàng)新顯著降低了本地耦合脆弱性,處于有效集聚狀態(tài),符合本文理論預(yù)期;中西部地區(qū)因?yàn)橘Y源的不合理配置、發(fā)展的不均衡,對(duì)耦合脆弱性并未表現(xiàn)出與東部地區(qū)相同的作用。從三個(gè)區(qū)域的結(jié)果來看,金融集聚水平需要在一定范圍內(nèi)才能降低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金融集聚對(duì)本地耦合脆弱性的影響是非線性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重點(diǎn)發(fā)展東部地區(qū),導(dǎo)致金融資源大量流向東部地區(qū),區(qū)域內(nèi)發(fā)展較為均衡,從而減弱了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空間溢出效應(yīng)。中部地區(qū)在“中部崛起戰(zhàn)略”的支撐下,資源配置效率逐漸提高,但由于“技術(shù)勢(shì)差”,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沒有對(duì)脆弱性產(chǎn)生顯著的降低作用和空間溢出效應(yīng)。此外,中部地區(qū)的技術(shù)回流仍處于低水平狀態(tài),科技系統(tǒng)與金融系統(tǒng)的快速融合所需的技術(shù)轉(zhuǎn)化未達(dá)到期望標(biāo)準(zhǔn),金融資源在不完善的信息技術(shù)下轉(zhuǎn)化難免出現(xiàn)資源不匹配的情況,這使得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效率的促進(jìn)達(dá)不到理想效果。西部地區(qū)資源配置相對(duì)落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基礎(chǔ)設(shè)施薄弱、科技發(fā)展緩慢等因素,導(dǎo)致中心地區(qū)的金融集聚增加了其他地區(qū)的“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脆弱性。
(四)穩(wěn)健性檢驗(yàn)
前文構(gòu)建的空間動(dòng)態(tài)面板模型是一種從低級(jí)演化到高級(jí)的動(dòng)態(tài)過程,而GMM 方法不需要滿足經(jīng)典計(jì)量假設(shè),為保證模型擾動(dòng)項(xiàng)的隨機(jī)性和解釋變量的有效性,采用GMM進(jìn)行檢驗(yàn),檢驗(yàn)結(jié)果見表8所列。其中,檢驗(yàn)一為以本文研究數(shù)據(jù)進(jìn)行的GMM檢驗(yàn)實(shí)證結(jié)果;為使檢驗(yàn)更加科學(xué)可靠,檢驗(yàn)二更換金融集聚的測(cè)度數(shù)據(jù),采用區(qū)位熵直接測(cè)算金融集聚水平。具體公式如下:

表8 穩(wěn)健性檢驗(yàn)
其中:fit、pit分別為i省第t年末金融業(yè)增加值和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F(xiàn)t、Pt分別表示全國(guó)第t年末金融業(yè)增加值和全國(guó)生產(chǎn)總值。
檢驗(yàn)結(jié)果表明,無論是檢驗(yàn)一、還是檢驗(yàn)二,GMM回歸的系數(shù)與模型(4)、模型(5)的系數(shù)符號(hào)均相同,說明本文模型結(jié)果是穩(wěn)健的。Arellano-Bond檢驗(yàn)中檢驗(yàn)一、檢驗(yàn)二AR(2)的P值分別為0.401、0.564,均大于0.05,故擾動(dòng)項(xiàng)為隨機(jī)項(xiàng);Sargan檢驗(yàn)中檢驗(yàn)一、檢驗(yàn)二的P值分別為0.852、0.827,均大于0.05,故模型的工具變量是外生的。
五、研究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jié)論
如何促進(jìn)科技與金融的有效融合一直是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的重要課題。通過實(shí)證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結(jié)論:
第一,整體上我國(guó)“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中等偏高,近些年隨著金融和科技發(fā)展有逐步降低的趨勢(shì),存在明顯的空間聚集效應(yīng)。地區(qū)間差異較大,中西部地區(qū)“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高于東部地區(qū),東部地區(qū)“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遠(yuǎn)低于全國(guó)平均水平,中西部“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數(shù)則略高于全國(guó)平均水平之上。
第二,從全國(guó)數(shù)據(jù)估計(jì)結(jié)果來看,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存在明顯空間溢出效應(yīng)與本地效應(yīng)。金融集聚能夠顯著降低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并提高鄰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提高幅度遠(yuǎn)大于降低幅度。在其他控制變量中,經(jīng)濟(jì)水平和信息化水平能夠顯著降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
第三,從分地區(qū)、分行業(yè)的估計(jì)結(jié)果來看,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本地效應(yīng)和空間溢出效應(yīng)在不同地區(qū)、不同行業(yè)間存在明顯差異。一方面,東部地區(qū)的金融集聚能夠顯著降低本地區(qū)“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西部地區(qū)的金融集聚會(huì)顯著增加鄰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中部地區(qū)具有負(fù)向溢出效應(yīng),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另一方面,銀行業(yè)和保險(xiǎn)業(yè)的集聚對(duì)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存在顯著降低作用,但顯著提高了鄰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證券業(yè)集聚對(duì)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具有正向作用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金融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影響效應(yīng)受限于各地區(qū)“金融—科技”耦合發(fā)展階段,不同金融行業(yè)的集聚對(duì)“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表現(xiàn)出不同大小、不同方向的影響。
(二)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結(jié)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應(yīng)當(dāng)使區(qū)域金融中心的資源有序回流到其他金融個(gè)體中,在缺乏中心城市的區(qū)域,使該區(qū)域內(nèi)的資源有序集聚到多個(gè)中心城市,形成“多點(diǎn)帶面”的局勢(shì),空間上建立具有結(jié)構(gòu)層次的金融網(wǎng)絡(luò),促進(jìn)金融要素的有效集聚,預(yù)防金融要素的擁擠集聚,使本地與鄰地的“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都能得到持續(xù)降低。
第二,在不同區(qū)域與行業(yè)中,一方面,需要控制東部地區(qū)的金融集聚對(duì)其他地區(qū)進(jìn)一步的資源虹吸,預(yù)防擁擠集聚,在穩(wěn)定東部地區(qū)金融結(jié)構(gòu)的同時(shí)讓金融資源逐步回流至周邊地區(qū),推動(dòng)本地區(qū)金融要素的有效集聚,使金融資源在更大區(qū)域范圍內(nèi)自由流動(dòng)。發(fā)揮中心地區(qū)積累的資源優(yōu)勢(shì),輻射周圍地區(qū),帶動(dòng)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降低本地區(qū)“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減弱西部地區(qū)的“鍋底效應(yīng)”,堅(jiān)持推進(jìn)“西部大開發(fā)”政策,優(yōu)化西部地區(qū)金融資源配置,從人力、物力上提高金融活力,為金融技術(shù)創(chuàng)新提供動(dòng)力,使金融集聚能夠緩解西部地區(qū)的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并降低鄰地“金融—科技”耦合系統(tǒng)的脆弱性。穩(wěn)定中部地區(qū)的資源回流速度,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加大金融業(yè)投入,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豐富地區(qū)產(chǎn)業(yè)多樣性,使中部地區(qū)能夠高效接納東西部的要素流入,成為全國(guó)互動(dòng)的重要橋梁,從而緩解本地“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另一方面,使三大行業(yè)在空間上形成具有層次結(jié)構(gòu)的集聚,讓整個(gè)金融網(wǎng)絡(luò)體系的資源流動(dòng)更加充分。銀行業(yè)與保險(xiǎn)業(yè)需要細(xì)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擴(kuò)大服務(wù)覆蓋面,提高服務(wù)效率,進(jìn)一步縮小區(qū)域差異;對(duì)于證券業(yè),集聚中心在高效發(fā)揮市場(chǎng)交易職能的同時(shí),要使相對(duì)集中的資源分散到其他地區(qū),防范擁擠集聚風(fēng)險(xiǎn)。第三,無論是不同行業(yè)還是不同區(qū)域,穩(wěn)固的“金融—科技”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是降低“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的關(guān)鍵。應(yīng)當(dāng)以金融結(jié)構(gòu)的多樣性、互動(dòng)性和層次性為基礎(chǔ),通過要素自由流動(dòng)優(yōu)化資源配置,預(yù)防結(jié)構(gòu)斷層;另外應(yīng)注重科學(xué)技術(shù)人才的培養(yǎng)、科學(xué)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提高地區(qū)信息化水平和經(jīng)濟(jì)水平,為“金融—科技”的深度耦合奠定牢靠的基礎(chǔ),讓金融科技服務(wù)切實(shí)有效地服務(wù)于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
注 釋:
(1)資料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第十四個(gè)五年規(guī)劃和2035 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綱要》(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資料源自《金融科技發(fā)展規(guī)劃(2022-2025 年)》(http://www.gov.cn/zhengce/2022-01/07/content_5666817.htm)。
(3)資料源自《中國(guó)金融中心指數(shù)(CFCI)報(bào)告(第十三期)(http://www.cfci.org.cn/html/2022/06/20/202206200349 017310001520.html)。
(4)圖中序號(hào)1—30分別對(duì)應(yīng)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甘肅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qū)、貴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龍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蘇省、江西省、遼寧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青海省、山東省、山西省、陜西省、上海市、四川省、天津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云南省、浙江省、重慶市。
- 華東經(jīng)濟(jì)管理的其它文章
- 資本市場(chǎng)國(guó)際化與審計(jì)師風(fēng)險(xiǎn)應(yīng)對(duì)行為
——基于企業(yè)生命周期視角 - 營(yíng)商環(huán)境對(duì)企業(yè)勞動(dòng)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
- 人口老齡化對(duì)家庭數(shù)字金融參與的影響研究
——基于中國(guó)家庭金融調(diào)查數(shù)據(jù) - 農(nóng)村地區(qū)數(shù)字生產(chǎn)基礎(chǔ)設(shè)施對(duì)種植結(jié)構(gòu)的影響研究
- 數(shù)字化發(fā)展對(duì)環(huán)境治理效率的影響及其內(nèi)在機(jī)理
——兼論制度環(huán)境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 - 數(shù)字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與城市創(chuàng)新質(zhì)量
——基于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110個(gè)地級(jí)市的實(shí)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