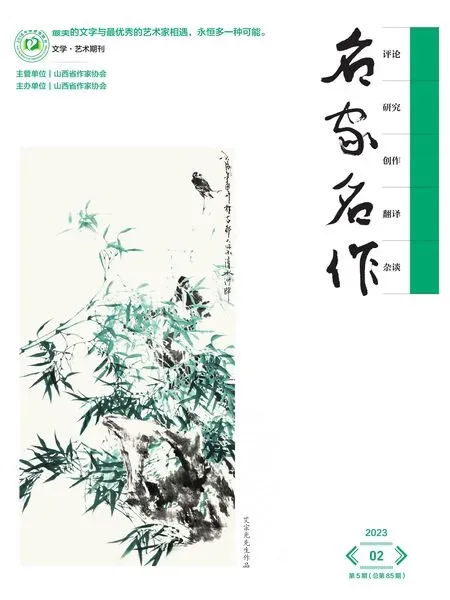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交織
——周梅森改革小說三部曲研究
白英杰
周梅森的改革小說在 20 世紀 90 年代誕生,其中很多作品已被改編成了影視劇,收視率頗高。其改革小說多次獲得國家級獎項,如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獎等大獎,這一切使得周梅森被譽為“中國政治小說第一人” 。隨著小說的爆紅,周梅森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 目前學界對周梅森改革小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責任感、小說內容藝術特色、 影視劇改編歷程等方面,但是很少有人從人文關懷和歷史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其藝術價值和文學地位。
童慶炳先生 1998 年在《文藝評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缺失——“新現實主義”小說再評價》中指出:“現實主義并不是單純復制現實,現實主義的核心是在對現實的客觀描寫的條件下,對現實做出判斷, 而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就是他們判斷社會轉型現實的兩個尺度。”①童慶炳、陶東風:《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缺失——“新現實主義小說”再評價》,《文學評論》 1998 年第4 期,第43-53 頁。同時,童慶炳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20 世紀 90 年代興起的國企改革題材小說的嚴重不足之處在于,“對轉型期的現實生活中的丑惡現象采取某種認同態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人文關懷在他們心中沒有地位”②童慶炳、陶東風:《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缺失——“新現實主義小說”再評價》,《文學評論》 1998 年第4 期,第43-53 頁。。童慶炳先生在此文中還提出一個深刻的問題: 真正寫得好的現實主義小說“更值得描寫的是轉型時期人們的情感生活,是人性的變化,是社會轉型在人的心理層面造成的隱秘而又深刻的震撼,是人的命運的悲喜劇” ,只有這樣,才是“具有藝術震撼力的文學杰作”。
作為新時期現實主義小說的杰出代表,周梅森改革三部曲《我主沉浮》《我本英雄》《我的太陽》,深刻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真實展示了當代中國官場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種種矛盾沖突。周梅森的改革三部曲緊抓社會熱點與痛點,直擊歷史中理性的真相,將官場浮沉的故事擺在讀者面前。 按照童慶炳先生所提出的“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就是他們判斷社會轉型現實的兩個尺度”的觀點,周梅森改革三部曲在人文關懷和歷史理性方面的具體體現是怎樣的呢?相較于20 世紀90 年代的國企改革題材小說,周梅森小說有沒有體現出更強烈的現實主義批判力度?按照童慶炳先生衡量新現實主義小說的標準,周梅森改革三部曲是否屬于“具有藝術震撼力的文學杰作”?對以上問題的探究,對于認識和評判周梅森小說在新時期現實主義小說中的藝術價值和文學地位有重要意義。
一、以人性的復雜性顯示官場“真實”
周梅森的改革小說擁有強烈的戲劇張力,這使得其小說的沖突與對立格外顯眼卻不突兀。周梅森將文學藝術立于現實卻高于現實。正如周梅森所認為的,要把社會問題講透,就必須多方面尋找光明的力量。③丁薇、史雅萍:《于創作中尋找光明的力量、正義的氛圍——專訪電視劇〈突圍〉編劇周梅森》,《中國藝術報》2021 年11月15 日,第4 版。在小說《我主沉浮》中,錢惠人面對前來審問的老領導趙安邦,以滴水不漏的嘶吼表達著自己的不滿,一時間難分正邪明暗。錢惠人為自己的套現、挪用經費等行為辯解,認為趙安邦等領導干部同樣存在這些問題。
錢惠人也激動了:“趙省長,這全是誤會,天大的誤會!你被套住了,我也被套住了,而且套得更深!不錯,一九九八年我是違規操作,從四個機動賬戶調動過三億資金,可那是為了挽救一家已被ST 的上市公司,不存在你所說的以權謀私問題!這種違規操作既不是由此開始,也不是由此結束的,長期以來,是得到你和天明書記支持鼓勵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最早這么干的不是我,是你、是白天明同志!剛到寧川當市長時,你們就挪用過省交通廳的道路建設資金償還集資款!”①周梅森:《我主沉浮》,群眾出版社,2001。
面對趙安邦對“違規動用建設資金”的質疑,錢惠人拿出寧川市發展過程中白天明、趙安邦等人同樣違規的事件回擊。事實上,這也是錢惠人仕途的悲哀之處。年輕時期的他打破程序,挪用經費,只是為更好地發展經濟。面對他人賄賂的價值三十萬的手表時,他毅然決然地拒絕了這種行為。但之后紀委組織特別是以于華北為首的派系對他進行了長期的調查控制,使得其內心不斷走向扭曲。在傳統觀念里,對于貪污犯的描寫往往是扁平的、片面的,這些對立面角色往往是狡詐的、貪婪的,這種狡詐與貪婪甚至是與生俱來的,而非在人生某個歷程中發展而來的。周梅森筆下的錢惠人則一反常態,滿腔熱血的人民公仆因為不堪受辱轉向黑暗,原本紀委制度的設立是為了維持公平正義,在這里卻促成了錢惠人走向貪污腐敗的黑暗極端。對于錢惠人的遭遇,周梅森從極強的人文關懷視角表達了同情。然而,貪污犯罪已成事實,也許過程多有曲折,但錢惠人終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經歷官場摸爬滾打的趙安邦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現得那么無懈可擊甚至冷血,但在想起老領導白天明之時內心卻會涌起暖流,因為白天明在照顧其妻子與兒子時曾違反一些原則。 官場之內的斗爭冷酷無情,一句不經意的話便可招來禍害,這一切逼迫著從來不被看好的趙安邦用冰冷的面具保護自己。而在官場之外,亦有屬于趙安邦的人性。面對白天明之子白小亮挪用公款、貪污腐敗的案件時,雖在內心想要保護一手提拔上來的錢惠人,但仍舊選擇堅持原則與黨性,保持著強大的冷靜,與省委書記裴一弘共同處理問題。最后,在發現錢惠人確實有腐敗問題時,趙安邦堅持原則,選擇了正義,而非個人私情。周梅森改革小說的主題在揭示社會矛盾的同時,還帶有對人性的關注。因為社會矛盾的形成與人性有關。錢惠人因人性中的貪戀而步入歧途,邁向貪污腐敗的無底深淵。趙安邦因人性中的喜好而在初期力保錢惠人,一定程度上違背了黨紀黨規。他們是相似的,但他們又各不相同。錢惠人在人性的惡念中一去不復返,而趙安邦卻在人性的軟肋中站穩了腳跟,堅持了原則,選擇了正義。在趙安邦與錢惠人的身上,便展現了人性在矛盾中的決定性的作用,前者在矛盾中堅持原則,后者在矛盾中放棄原則。
《我主沉浮》中以一句“常回家看看”作結,盡管錢惠人最后遭到逮捕,但至少彌補了情感上的遺憾,讓女兒擁有了真正的家。《我本英雄》以石亞楠勇擔責任作結,盡管石亞楠和方正剛的班子對文山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失,但他們最終并沒有逃避責任,而是盡自己所有的能力挽回局面。在種種歷史理性之下,仍然處處包含人文關懷。
二、直面重大社會矛盾以顯示文學的使命擔當
周梅森認為,總是需要一部分作家去關注社會的現實問題,而不能閉上雙眼,視而不見,關注現實社會的問題是屬于改革開放時代作家的一個責任。②沈杰群:《周梅森:作家不能在社會矛盾前閉上眼睛》,《中國青年報》2021 年11 月2 日,第11 版。周梅森的改革小說與此前的國企改革文學相比,最大的特點在于飽含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批判,對于其中大多數問題,其思想核心是批判它并解決它,并非情緒發泄式的消極批判,也非毫無理論依據的盲目指揮,而是帶有積極社會責任的理性的批判與整改。深入探究其中的歷史理性內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周梅森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學者楊立元也認為,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在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出現的重大矛盾和社會問題,歌頌了奮力前行的改革者和人民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力,顯示了崇高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品格和開拓人間正道的獻身精神,表現了他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憂患意識和為人民的至高利益而寫作的使命感。③楊立元、孫瑞新:《為了人民的至高利益——周梅森小說論》,《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04 年第2 期,第7-13、39 頁。
(一)領導層貪功冒進而貽誤城市發展
在《我本英雄》中,方正剛和石亞楠貪功冒進,不顧省長趙安邦的勸阻,強行在文山經營七百萬噸鋼,最終釀成大禍。
她和方正剛這屆班子苦心經營的七百萬噸鋼竟成了一顆巨型定時炸彈,隨時有可能把他們和剛剛啟動的新區經濟一起炸翻。方正剛對此和她一樣清楚,在落實中央和省委精神的市委常委擴大會上警告說,別以為這只是新區管委會和吳亞洲的事,這實際上是我們整個文山的事。不客氣地說,我們政府和被查處的亞洲鋼鐵聯合公司都坐到了已爆發的火山口上。如果不能挽狂瀾于既倒,抓住省委聯合調查組調查期間最后這點寶貴時間提前做好善后,損失將極為慘重,文山經濟總體水平可能將倒退三至五年。新區管委會主任龍達飛發牢騷說,即使如此,這個責任也不在我們,都是上面鬧的。這七百萬噸鋼本來熱火朝天上著,銀行金融機構搶著貸款,不存在任何問題。石亞楠當時就火了,責問龍達飛:怎么不存在問題?根據省委目前掌握的情況,問題已經不少了,大家都不要有僥幸心理,這顆定時炸彈一定會炸的!①周梅森:《我主沉浮》,群眾出版社,2001。
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座看似穩定的大廈劇烈晃動起來,文山發展來到了懸崖邊。經濟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別是以資源為導向型的發展,尤其受到政策風口影響。對此,周梅森借趙安邦之口表達了對此類貪功冒進、不計后果的官員的諷刺:
為了烏紗帽,什么牛都敢吹,什么事都敢做!只要能爬上去,哪怕踩斷老百姓的脊梁,踩碎老百姓的腦袋也在所不惜!一官功成萬骨枯嘛,老百姓在你們眼里,就是些無關緊要的數字!
(二)政治斗爭掩蓋事實
錢惠人早期一心為公,從未接受過任何賄賂。盡管如此,也因為三十萬手表事件而屢被調查,甚至失去了職位晉升的機會。這個結果主要是以于華北為首的勢力造成的,于華北與白天明、趙安邦的激烈斗爭,造成了錢惠人的仕途不順,甚至使錢惠人產生了墮落的想法。“既然都說我腐敗,那我便真腐敗給他們看”是錢惠人決定腐敗時的想法,這在其與白原崴的溝通中可以看出:
白原崴幾乎要哭了,一把拉住錢惠人的手:“錢市長,您怎么變成這樣了?當年你敢分地賣地,敢和我一起炒恒生期指,一個紙條、一個電話就敢把億萬資金調出國門!我這一生中佩服的人沒幾個,可您是其中之一!走到哪里我都說,沒有您和白天明、趙省長這幫敢闖能拼的改革派干部,就沒有我們改革開放的今天啊!”錢惠人激動了。“可是,結果呢?是讓人家查,我錢惠人落了一身不是!”②周梅森:《我主沉浮》,群眾出版社,2001。
政治人物之間的斗爭,使得原來具有正義性的紀委監察工作被于華北等人利用,用以加害錢惠人。
周梅森在《我主沉浮》《我本英雄》中,均是描述了一個“失敗的故事”。《我主沉浮》用盡千方百計證明錢惠人并沒有貪污腐敗,最終錢惠人卻真相大白而落馬。《我本英雄》則描述了一場失敗的經濟改革運動。故事的結局都不是美好的,歷史理性之下的政治斗爭通常走向兩敗俱傷,但往往有最后一絲人性的光芒將事件拉回。
三、不足之處
(一)部分人物形象有扁平化之嫌
在《我主沉浮》《我本英雄》《我的太陽》中,周梅森選擇塑造扁平主人公趙安邦這一偉光正的形象,他精通經濟學,為人正直,敢闖敢拼。學者楊經建認為,周梅森改革小說在從對歷史的審美體驗轉向對當下社會政治問題的寫實性表述的過程中,非但沒有使其小說內容與深度達到進化,反而陷入庸常的困境。③楊經建、唐孕蓮:《離棄佳境 陷入庸常——致周梅森》,《中國文學研究》2003 年第4 期,第87-90 頁。趙安邦這一扁平化形象在三部曲中的存在感甚至不如立體化的錢惠人、石亞楠、方正剛等。這也是政治小說中難以避免的一個弊病。
(二)故事情節稍顯單一化
周梅森的改革小說雖具有較高藝術成就,且相對此前的國企改革文學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但仍舊在一些方面具有不足,甚至造成其作品有“樣板戲”之嫌。例如其大部分小說中,難以跳脫“高干文”的范疇,主人公為干部子弟,天生就具有高眼界、敢打拼的精神,一絲不茍、潔白無瑕的扁平化主角使得小說劇情逐步走向單一化。總體脈絡為貪腐分子造成了損失,而主人公則代表正義解決了問題。當然,我們也不能單一地去評判作家的創作風格,因為在評價一部作品時,應當結合時代特征去考量,脫離時代特征的文學批評只是空中樓閣。
四、結語
周梅森改革小說三部曲《我主沉浮》《我本英雄》《我的太陽》以人文關懷的視角深入歷史理性的內容之中,將一幕幕生動的官場現狀展現出來,提出了他對現行社會制度的殷切反思與希望。周梅森以人性的復雜揭示官場的真實,將官場中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呈現出來。同時,他也將挖掘社會矛盾作為其創作改革小說的任務之一。
周梅森的改革小說三部曲并不力求揭示政治社會運行的全部規律,但注重表現政治官員內心的探尋,以此探究人性,并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社會問題。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特別是官場文學,重在提出對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在力度上有所收斂,這與時代趨勢直接相關。周梅森通過描寫現實的、歷史的、具體的人性來挖掘腐敗的深層次成因,讓文學的認識作用發揮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