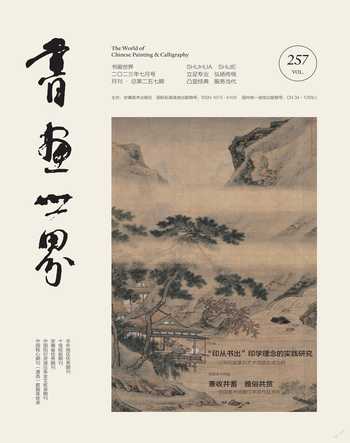賴少其扇面藝術的審美取向淺析
方磊



賴少其
賴少其(1915—2000),當代著名的版畫家、國畫家、書法家、篆刻家和作家、詩人。全國第一、六、七屆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歷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處長、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文聯主席、華東局文委委員、華東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上海文聯副主席和華東、上海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及黨組書記,1956年兼任上海中國畫院籌委會主任。195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安徽省書法家協會第一任主席,長期兼任安徽省美術家協會主席。1983年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曾擔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版畫家協會副主席等。
關鍵詞:賴少其;扇面;藝術;審美取向
東漢鄭玄在注解《禮記》時,曾說:“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由此可知,在先秦時人們就開始在扇子上進行裝飾。六朝以后,書法盛行,在扇面上作詩題字逐漸流行。宋元以降,扇子更是被文人士大夫賦予了濃厚的藝術氣息。在方寸之間的扇面上題詩、作畫、鈐印,于精致細微處或仰觀宇宙之大,或俯察品類之盛,均代表了文人士大夫對審美趣味的身份認同,即審美取向。近現代以來,扇面藝術深入民間,并非文人士大夫專享。廣大藝術家在繼承傳統扇面藝術的基礎上不斷創新,不僅內容取材廣泛,而且意境清新且形式多樣,既飽含個人特質,又富有時代氣息,或爽朗雅致、自然清新,或含蓄雋永、平中寓奇,或散淡飄逸、氣韻貫通,無一不是他們內在審美取向的外在反映。
作為一位高產的藝術家,賴少其一生創作的作品不僅種類齊全,有版畫、國畫、書法、篆刻等,藝術形式也豐富多彩,有中堂、立軸、斗方、條幅、小品、鏡心、冊頁、手卷、信札、扇面等。其中,現存可見的扇面作品數量不過數十件,卻精彩紛呈。在題材上有書法、花鳥、山水,在創作時間上有早期、中期、晚期,在形制上有折扇、團扇,在材質上有紙本、絹本,在用途上有自用、饋贈。通過梳理發現,這些扇面作品歷史脈絡清晰,風格特點顯著,審美取向彰顯,凝聚著賴少其對周遭事物的切身思考。畫家將情感、技藝、理念、胸臆、學養,甚至性格綜合作用于扇面這一載體之上,讀者由此可以一探賴少其扇面藝術的審美取向。
一、扇面書法的韻味雋永和拙樸淳厚
縱觀賴少其不同時期的作品,其顯著特征就是關注時代熱點,能反映時代特質,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扇面《憶秦娥·婁山關》(圖1)繪制于1965年,是目前可見的賴少其最早繪制的扇面。正面以行書書寫毛主席詞《憶秦娥·婁山關》:“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另寫“毛主席詞婁山關,一九六五年夏為曾菲同志書于肥濱,老賴”。書法布局采用了“隔行長短錯落法”,即每一行所寫的長短不一,隔行錯落,形成上寬下窄之勢。反面(圖2)用隸書書寫毛主席詞《十六字令·山》:“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另落款“一九六五年夏日為曾菲同志書,老賴”。書法布局采用了“頂端法”,即沿著扇面的頂端自右往左書寫,每行一個字或兩個字,下方留白。
賴少其的書法藝術博采眾長又重點取舍,他在1980年的《點滴體會》一文中總結道:“一定要臨帖,幾年、十幾年臨一個帖。我臨《蘭亭序》臨了二十多年,我學過鄭板橋,后來學伊秉綬,最后才學金冬心。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到:金冬心的漆書,結體是學《蘭亭序》的,用筆是學晉碑,如果學歐陽詢,便有些像金冬心的漆書了。歐陽詢便是用碑寫《蘭亭序》的。顏真卿也是從《蘭亭序》變化而出,不過顏字直粗橫細,結體端莊,落落大方;金農漆書反其道而行之,橫粗直細,結體長方,凝重如鐵,但道理卻是一樣的。”[1]200觀此扇面,其時,賴少其的書法風格尚在探索階段,尤其是隸書風格并未完全成熟,但不難看出其書法藝術的審美取向,即從王羲之、鄭板橋、伊秉綬、金冬心等格調高古的書法正統入手,練就扎實的基本功,繼而推陳出新。
至于《蘭亭序》為何符合賴少其對行書的審美取向,傅愛國認為:“在書法上他選擇臨習的對象是王羲之的《蘭亭序》,我想,五十年代他崇尚王羲之,首先,可能受到當時的海派書風的感染,取法乎上,起點即高;其次,是《蘭亭》用筆遒麗、結構多變、章法天成的藝術韻味感動了他;再次,因為不激不厲、不亢不卑的中性平和書風好使審美心理得到一劑調節的良藥。”[2]賴少其對《蘭亭序》二十多年的追慕,形成了自己行書的審美取向,即韻味雋永,我們在其眾多的手札上也可以目鑒。觀扇面《孟浩然詩》(圖3)上題孟浩然詩句“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畫家借詩抒情,用雋永的行書寫就,淡而有味,含而不露。不難發現,其行書的取法也不僅僅是賴少其自己常說的《蘭亭序》,我們從其收藏情況和書寫痕跡中亦可看到孫過庭《書譜》、宋拓《十七帖》、董其昌《書品冊》及鄭板橋的影響。又如扇面《松濤風吼》(圖4),書法布局采用“頂端法”,下方留白,雋永的行書與精巧的扇面相結合,書法張力自然流出,風韻天成。
除了行書,賴少其在扇面上書寫最多的是隸書,扇面《嶺上臘梅》(圖5)以隸書寫就“嶺上臘梅已結子,二月春風似剪刀”。其隸書取自金冬心、鄧石如、伊秉綬,旁涉“二爨”,晚年兼學泰山榜書之祖《泰山經石峪》,逐漸形成其拙樸淳厚的書風。此外,賴少其在幼年時期便喜歡觀看老師臨摹康有為的“康體”,稍長便喜歡臨習鄭板橋那種隸楷相融、獨具個性的“六分半書”。賴少其所秉持的書法觀點是兼容并收,他說“碑與帖各有優點,可以互相補充”,無須刻意地把“碑”與“帖”劃出界限。又如扇面《泠泠瘦骨寒》(圖6),用隸書寫就“泠泠瘦骨寒,扣之響當當。月下橫斜影,風送十里香”,隸楷相融給人巧拙相生、淳厚盎然之感,獨具匠心。
其創作于1999年的扇面《一陣風》(圖7),具有強烈的隸楷兼容特點。其時,賴少其因病已難以控筆,但其筆墨仍力透紙背,扇面布局渾然天成。在吳雪看來,“賴老的行書有金石氣,而他的‘漆書也深深地打上‘蘭亭的印記,那就是雄渾中見靈性,開張中顯文雅。所以,我認為,賴少其的書法是以碑為骨、以帖為韻的。他把兩種風格有機地統一在‘賴體的作品當中了”[3]。可見,站在王羲之、金冬心、鄭板橋、鄧石如、伊秉綬等古人的肩膀上,賴少其的書法已有較大變化和升華,融入新意,這便是賴少其書法的審美取向。趙樸初對其理解為“其書法遍臨名碑法帖,兼收并蓄,吸收消化。拙樸淳厚,形成獨特書風,韻味雋永”[4]。
二、扇面花鳥畫的鐵骨錚錚和深情溫婉
賴少其的花鳥畫題材眾多,尤以寫梅見長。賴少其對梅的喜愛程度非同一般,他在詩中常寫“寒梅香徹骨,月下橫斜影”“疏影橫斜月有跡,幽香處處沁羅襪”[1]14,還有自書詩云“自古畫梅多高士,鶴子梅妻林處士。王冕畫梅稱高標,金農水邊數畫須。吾愛梅花骨如鐵,吾畫梅花發畫癡”[1]26。
關于其習梅的對象,賴少其在一幅梅花作品上題“梅學王冕、王謙二家,字學冬心先生”。可知賴少其明確地指出王冕、王謙的梅花畫法與金冬心的“金農體”題款相結合符合其寫梅的審美取向,即其自評“我畫梅花白如雪,我畫枝干曲如鐵”。關于梅花的創作心得,賴少其也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審美觀點,“我在此(20世紀50年代)時學習書法,也同時學習國畫,才認識到‘書畫同源的道理。更直接的理由,我學習書法,首先是為了‘題畫,特別是當我學習金冬心的梅時,更感到有學習金冬心‘漆書的必要了”[1]266。可見,賴少其學書不僅為題款所用,更是要以書入畫,其飽含金石韻味的書法更加強化了墨梅的鐵骨錚錚,從而使賴少其的扇面梅花作品更加筆墨淋漓,氣韻生動。
扇面《墨梅》(圖8)上題“以金農法畫墨梅一枝”,梅花枝干遒勁,斜勢伸發,各展其姿,淡墨點花,筆觸古拙,富有色彩感,在輕盈瀟灑的風姿中含有沉厚穩健的意趣,構思布局與筆墨意趣的形成獨有特色。此扇面以簡單的折枝經營構圖,以少勝多,以微見宏,別出心裁,小巧別致。所寫梅花,枝多花繁,生機勃發,古雅拙樸。賴少其在扇面上喜寫墨梅,這也與扇面在形制上具有小巧玲瓏、形狀各異的特點有關,畫家將花草枝干適當裁剪截取,得到以小觀大、一斑窺豹、由表及里的視覺效果,使花鳥畫的創作更加清新活潑,形式多樣,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又如扇面《畫金農墨梅一枝》(圖見扉頁),不僅具有較多的想象空間,還以漆書入畫,獲得如木刻般的厚重感。畫面與書法融為一體,題字和梅花之間又有著微妙的對應關系。
其寫梅的動因,與其所處的時代特征及其人格品性也有著莫大的關系。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賴少其花鳥畫的主要描繪對象是梅花。在特定的年代,賴少其將毛主席詞《七律·冬云》《卜算子·詠梅》大量地題寫在梅花作品上,幾乎有梅痕處必有毛主席詞。“梅花歡喜漫天雪”(圖見扉頁)、“猶有花枝俏”等詞句足見其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鮮明地表明了他不向世俗獻媚的堅貞,以及鐵骨錚錚的操守,彰顯出崇尚高雅、淡泊名利的精神風范。這正是他對人生感悟的體現。
賴少其將這種帶有強烈人格特征的審美取向大量地反映在扇面梅花的創作上。扇面《潘天壽詩意》(圖11),寫一老梅,枝干上新枝茁壯,花蕊繁密,璀璨異常。畫家用順逆有勢的散鋒在質地堅韌的黃皮紙上皴擦枝干,筆力雄勁,有蒼龍出岫之勢。枝梢線條勁如彎矢,吸收了王冕的寫梅遺法。梅花勾瓣點蕊,冷艷綺麗,與粗壯的枝干相映,蒼勁中見清氣,冷峻中見風姿。上題潘天壽《詠梅花》中的詩句“氣結殷周雪,天成鐵石身”。在扇面《夢梅》(圖12)上,賴少其更是直抒胸臆,上題自作詩“看長江滾滾東流急,千古英雄多磨折。斥佞臣,一尊頑鐵我遲來。梅花已謝,北望中原,漫天大雪”。賴少其借梅抒發個人豐富的思想感情,將主觀感受的表達與客觀物象的描繪進行了高度的結合。
畫家的藝術語言從來不是只有一面,賴少其扇面梅花的審美取向除鐵骨錚錚外,還有著一層溫婉深情,這與賴少其溫潤的性格息息相關,所謂“鐵骨柔情”。扇面《宋之問詩意》(圖13)中,白梅造型嚴謹,枝干虬曲,大片的金農體題跋強化了深沉之力,漆黑的書法與淡淡梅花形成對比呼應,逸趣橫生。作品繪于1977年,此時寫梅可以沒有顧忌地題上古人詩詞了,上題唐代詩人宋之問詩《題大庾嶺北驛》:“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扇面整體呈現的是一種平靜、淡雅的意境,畫家借景托物,借詩抒情,寫心寫意,表達思鄉之憂傷與行程之艱難,也體現了畫家對前途命運的思考。
扇面《韋應物詩意》(圖14)是賴少其為女兒賴小虹所畫,是賴少其扇面花鳥畫作品中少有的非梅作品,上題韋應物詩句“獨憐幽草澗邊生”。圖中幽草、頑石幾乎布滿整個畫面,這種飽滿的構圖在賴少其的扇面花鳥畫中實為罕見。端莊大氣的設色布局將幽草的嬌嫩柔美表現得栩栩如生,使我們更加直觀地感受到幽草的清純高潔。此外,賴少其還常在扇面上題“夏為曾菲同志書”“為曾菲驅(祛)暑”“為女兒小虹畫”“為在海書”“為在海寫”“研吾同志正書”“偉智同志屬(囑)”“小林小弟囑”等詞語,體現了賴少其對妻女、好友的深情,這也是其扇面花鳥畫重要的審美取向之一。
三、扇面山水畫的蒼茫沉郁和渾厚華滋
早在北宋時期,扇面山水畫藝術成就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在藝術形式上以工整寫實繪畫為主,也有寫意扇面山水畫。元代以后,扇面山水畫在形式上以寫意為主,更加注重文學詩詞的修養與筆墨意趣的表達。無論哪種形式,都與時代和畫家共同審美取向息息相關。賴少其的山水作品常見于中堂、立軸、斗方,少量見于手卷,在扇面上繪制山水更為少見。如何在小巧的扇面上體現山水畫的筆墨、構圖、立意等元素,無疑更能精準和集中地反映賴少其山水畫藝術的審美取向。
在筆墨的審美取向上,賴少其喜用枯筆焦墨。扇面《夢筆生花》(圖15),用側鋒淡墨皴擦山體,用中鋒濃墨點染礬頭,用黑線勾勒房屋,前景后景呼應,虛實相生,在精致玲瓏的扇面上營造出平遠幽深、蒼茫沉郁之感。無疑,其扇面山水畫的審美取向源自新安畫派,其核心是枯筆焦墨。賴少其分別于1962年和1974年,兩次臨摹程邃《山水冊》八幀,并題跋“邃畫用枯筆干皴,余喜其粗筆蒼茫渾厚,落墨不多,氣象萬千,此大手筆也。余習之經年,苦未能入室,惜晚生三百余年,未能拜其門下也”[5]。賴少其一生中臨摹程邃、漸江、汪之瑞和戴本孝等新安畫家的作品數十件,他也借鑒了石濤筆法之流暢凝重,松柔秀拙,尤習其點苔之法,密密麻麻,劈頭蓋面。賴少其取新安畫派之枯筆焦墨,去其冷峻靜逸。他也反復臨摹黃賓虹,往往“愈似愈遠”,遂悟“不似之似”。
1986年賴少其回歸故里廣州,開啟了藝術變法并臻高度成熟的時期,這一年為丙寅年,他自謂“丙寅變法”。“此期明顯增添了畫面設色用水的比例,拉開了水色層與干筆焦墨層的色差,畫面也因方形石塊的簡化既使畫面結構緊密,也增添了畫面的抽象意味。”[6]扇面《山水》(圖16)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在枯筆焦墨鋪底的基礎上,反復施以赭黃,以求畫面色彩的渾厚華滋。筆、墨、色縱橫交融而又靈動有致,在枯筆焦墨中以濕墨襯托出蒼潤清脆,筆墨略為收斂、含而不露。其重要特征是進一步把西畫的審美取向直接融合入畫,畫面更趨向于意象,將客觀事物與主觀表現融為一體,主觀表現更強烈,更重情境意境,突破傳統筆墨的束縛,畫面構成和形式更具當代感,也更符合當代人的審美體驗。
在構圖的審美取向上,賴少其吸收了“荊關”的北派畫法來描繪南方山水雄偉的一面。賴少其曾反復臨摹唐寅的《匡廬三峽圖》,也曾臨摹《山居招月圖》《千巖競秀圖》等多幅“黑龔”作品,取二者山水構圖之雄奇。賴少其對此解釋為:“我的筆法是學程邃和戴本孝的,但它清麗而不雄偉;因此,我在結構上學習唐寅和龔半千。我在黃山時,每每找尋便于發揮雄渾的大山為背景,當我臨摹龔半千的作品之后,以西畫寫生之法畫黃山,不僅可以如實地反映黃山,還有自己的特點。”[1]235扇面《黃山紫云樓》(圖見扉頁)對丘壑的經營,便借鑒了龔賢“愈奇愈安”之法,在奇中求安,安中求奇,構圖的視野更廣,氣象更大。
在立意的審美取向上,賴少其注重扇面山水畫的“意境”,“畫的好壞,主要看‘意境,景物能否吸引人,有沒有寄托,能否畫外有畫”[1]200。宋元以來,扇面山水畫在形式上已十分成熟,難以出新出奇,所以其內在的“意境”顯得尤為重要。真正要把扇面畫出“味道”,不單在于形而下的技巧,還在于作者的氣質稟賦、文化素養乃至胸襟器識。扇面畫不但要耐“看”,即形式動人;更要耐“讀”,即意境豐富。觀扇面《蘇東坡夜游赤壁》(圖見扉頁),在畫面處理上,前景筆墨較重,中遠景表現得最為生動,若隱若現,山色空蒙景亦奇。筆墨嚴謹,虛實相生,氣韻生動。賴少其特別注重詩情畫意的表達,上題“此蘇東坡夜游赤壁乎”,在意境上追求靜謐之美、詩意之美。尺幅雖小,但意境宏大,表現了畫家對虛靜、淡泊、幽深之境的追求。
四、文化啟示
1988年7月2日,賴少其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演講時說:“每個畫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道路,不可能所有的畫家都走一條相同的道路。”演講中,賴少其詳細地介紹了自己的創作道路:少年學習西畫,青年創作木刻版畫,中年研習傳統國畫,晚年變法。不難發現,其每一步的選擇都取決于自己對藝術的審美取向。扇面藝術是賴少其藝術創作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梳理可知,賴少其對大量格調高古的傳統書畫的認真研習,以及其西畫的根基,使其在扇面藝術的創作過程中既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又善于結合時代特征和自我個性,有選擇、有側重地對研習對象做出有價值的審美判斷,從而形成自己的審美取向。這需要畫家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寬廣的胸懷,以及獨到的審美眼光。這無疑也是賴少其扇面藝術留給后人的重要文化啟示。
參考文獻
[1]洪楚平,賴曉峰,于在海. 賴少其詩文集[M]. 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
[2]傅愛國. 孤獨生命體驗中的藝術升華:賴少其先生藝術人生及書法漫議[M]//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安徽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文藝百家.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46.
[3]吳雪. 魏晉風度 金石氣概:賴少其書法藝術源流初探[M]//于在海. 賴少其書法篆刻集.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6:11.
[4]趙樸初. 《賴少其書畫集》序[M]//杜滋齡.賴少其書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10.
[5]賴少其.《明程邃山水臨本冊》題跋,1986年作[M]//于在海. 賴少其山水畫集. 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15.
[6]尚輝. 鐵筆爛漫寫蒼茫:賴少其對20世紀山水畫現代性的深度探索[J]. 中華書畫家,2006(9):6.
約稿、責編: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