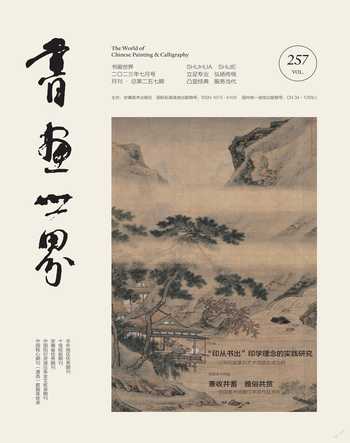體育精神在藝術創作中的表現
仲思潤


關鍵詞:體育精神;藝術創作;繪畫;審美表現
一、體育內涵及其精神流變
進入奴隸社會后,人類擯棄了原始時期茹毛飲血的生活習慣,也逐漸失去為了生存而與野獸搏殺的斗爭精神。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為維護主權、保衛疆土所展開的不斷征伐,依舊是建立于求生需求之上的斗爭精神的延續。以尋求群體與自身安全為主導因素的歷次戰斗,造就了人們自強不息的尚武精神。而以生存為第一要務的原始體育在尚武精神的影響與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演變為以養生為主、帶有娛樂意味與社交性質的傳統體育(如蹴鞠、馬球、投壺等),以其承載的文化屬性與情感價值成為社會文明的表現之一。
到了近代,中國國力衰微,列強的侵略與壓迫愈演愈烈。戰爭一再失利,主權淪喪,民生凋敝。社會上下暮氣沉沉,久經戰火,人們的精神早已頹弱不振,體質更是羸弱不堪,被列強公然蔑稱為“東亞病夫”。人們迫切希望通過個體力量的強大帶動民族實力的提升,以此贏得尊重,扭轉國家在國際交涉中的頹勢。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撰寫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便以敏銳的政治眼光將體育建設與國家發展相聯系,指出發展體育的目的在于以充沛的體力與強健的體魄作為知識武裝的載體,通過運動調節情感,使精神始終保持清明、平和以助思辨、析理;同時運動過程對身體素質的考驗亦是對意志力的磨煉,如此動心忍性方可增益其所不能;在野蠻其體魄的基礎上文明其精神,重振武風,以此推動國力的強盛與民族的振興。文中關于體育、德育、智育三者全面發展的論述也成為我國體育事業的指導思想,為新中國的體育建設奠定了基礎,對體育發展亦有著深遠的影響。[1]
二、體育與藝術的融合發展
力量的絕對壓制在原始時期代表著至高的權威。原始人將體育活動中的肢體表現以舞蹈等形式進行展現,配合著樂曲吟唱,以娛天神。可見在原始時期,體育與藝術便是密不可分的。
藝術創作將技術視作個人情感的間接體現,體育活動則將其作為個人力量的直觀展現。情感與力量借由技術這一載體相互轉化,將生命的律動節奏以體育的形式為觀者帶來流動的視覺體驗,同時以藝術的手法將其進行具象表現,成為審美意識的集中反映。
及至現代,體育與藝術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在觀賞娛樂的社會功用基礎上更多地發揮著教育功能[2]。同時人們對體質健康的重視使得體育活動中的群體性特征在全民推廣的進程中得到了加強,更加強了其在社會建設中的教育作用。此外,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蓬勃發展也為競技體育注入了新的精神動力,成為體育助力文明建設的一大導向。
但將運動者作為審美對象始終無法擺脫時空局限,無論高難度動作還是驚人力量,都只向處于同一時空的觀者展現,以稍縱即逝的感官體驗給人帶來情感沖擊,具有瞬時性的表現特征。而藝術記錄功用的恒久性恰好彌補了體育之美不可長存的遺憾。同時,藝術有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特征,能將體育活動中精彩刺激、奪人眼球的瞬時性表現所蘊含的現實美進行集中概括,并融入藝術創作者的主觀情感與審美情趣,形成兼具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特征的有意味的形式。而在體育活動與藝術活動不同形式美感碰撞下所產生的審美意識及審美取向的集中反映,也體現著兩者之間審美內涵的趨同性與協和性。
三、體育精神的藝術化表現——以繪畫為例
體育的創作主體與表現主體都圍繞著人的本質進行探尋,對人類力量、速度、技巧等方面的不懈追求反映著從古至今人們對人體的認知與崇拜。原始時期,先民還未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建立起完備認識,人體在探索自然的社會實踐中展現出的特質便令人們驚嘆不已。力量與速度代表的爆發力與敏捷度在捕獵等維持生存的必要活動中成為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體育的重要性得到充分體現。人們將圍獵場景中的肢體行為演變為舞蹈動作,以娛天神,并予以記錄,借此實現神人溝通。
由繪于內蒙古陰山巖石上的《圍獵圖》(圖1)可見原始時期人類對圍獵場景的直觀表現。盡管此時人類受限于工具等條件,僅能以平面形式極度抽象、概括地描繪人類圍獵場景,但我們仍能從畫面上人類追逐獵物所產生的強烈動勢感受到圍獵時刻的緊張氣氛。云南滄源地區原始時期巖畫《舞蹈牧放戰爭圖》和廣西寧明縣明江岸邊戰國至東漢時期巖畫《祭神舞蹈圖》則在單純描繪圍獵活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人類勞動生活與祭祀祝禱的場景作為描繪主體。通過觀察兩幅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們可以看出其身體動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祭神舞蹈圖》中人物體態比《舞蹈牧放戰爭圖》中的更加舒展、規范,并以整齊的形式排布于畫面之上,舞姿中蘊含熱烈奔放的形式美,反映出體育精神與藝術表現的初步結合。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進入封建時代后,人類不必再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費神,原始體育逐漸轉化為帶有娛樂與社交屬性的傳統體育,其精神也由近于野蠻的斗爭精神轉變為尚武精神。后來,儒學思想與政治因素等影響削弱了武力崇拜的成分,令體育活動逐步發展出競賽娛樂和健美養生的表現形式,向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表現形式靠攏。[3]
漢代帛畫《導引圖》作為以道家保健運動為表現對象的作品,其內容展現了由動物形態變形而來的運動姿勢。繪圖記之以供長存的形式,則體現著藝術在體育活動中發揮的記錄與教育功用。而南宋張擇端所繪的《金明池爭標圖》表現的是體育活動所體現的競賽及娛樂屬性。畫面中龍舟在人們奮力劃動之下左沖右突,上下翻飛的旗幟與船槳激起的水浪所營造出的緊張激烈的爭標氛圍,體現著健兒們你追我趕、不甘落后的運動精神。創作者以藝術的手法將競賽中極具感官刺激的典型場景展現出來,將流動的視覺體驗凝于靜態作品之上,令觀者在畫面所營造的審美空間中感受生機的勃發與生命的律動。體育和藝術在此實現了情感與動感、主觀與客觀的高度統一。
及至現代,在社會對體育事業的持續關注之下,體育中的教育作用越發明顯,成為增強人民體質、培養運動精神的絕佳助力。同時,體育作為一種非口語化的形式語言,有著跨越種族、連接國際的精神力量,也是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的重要標志,體現著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與綜合國力。因此,在國際交流頻繁、全球一體化趨勢日益增強的今天,體育更是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于我國而言,從近代積貧積弱、飽受欺凌的局面中一路走來,人們迫切希望通過參與體育競賽的方式扭轉西方對我們持有的“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以舉辦體育盛會的形式向各國宣告國家的強大與民族的崛起。體育大會的召開不僅旨在增強國人體質,也蘊含著“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興”的中國夢。
體育的塑造及引領作用也促進了藝術創作的發展,如中國體育美展便是以體育運動精神為表現主題的國家級展覽。其中曾慶榮的《激流勇士》展現了皮劃艇運動員面對自然挑戰迎難而上,奮力劃槳對抗激流的場景。畫家用寫意的手法描繪山石與浪花,為自然景觀賦予了粗獷豪放的粗糲質感,在山石與浪花的掩映之下更加凸顯出人物動勢所具備的力量感與形式美感。洪日的《越過云端伴鳥飛》相比前者則更多融入主觀情思,將跳高的運動場景擺脫現實設定,摒棄了對賽場的寫實描繪,轉而以天空作為全部背景,飛鳥騰空振翅的形態與人物躍桿而過的經典瞬間相呼應,同時也暗示著運動員起跳之高,以藝術加工的理想化表現體現著運動員超越自我的體育精神。
而奧林匹克運動會作為國際級的體育盛會更是吸引著國內外藝術工作者的關注。以第九屆中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為例,其中入展作品《融情冰雪 圓夢雙奧》(圖2)即是為迎接北京冬奧進行的主題性創作。該作品以運動員為表現主體,通過工筆形式描繪運動健兒在賽場競技拼搏的場景,以精致入微的神態刻畫與動勢表現將觀者引入超于現實的審美空間,沉浸式感受體育競技中緊張刺激的競賽氛圍。同時各國健兒同臺競技的場景也喻示著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各國人民齊聚一堂,以體育交流為契機,在奧林匹克這一國際盛會中向著勝利共同拼搏,象征著世界共同體的和諧發展,展現了和平、友誼、團結的奧林匹克體育精神。此外,創作者將北京作為觀照對象,把“鳥巢”“雪如意”等運動場館及中國高鐵等元素融入背景,也令觀者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我國建設發展的速度及日益強盛的國力,從而使國際友人更加了解我國的發展現狀。
結語
體育與藝術以不同形式的造型表現將個體生命的節奏韻律與社會文明的審美內涵予以展現,運動員將自身作為載體,以力量與技巧兼具的動態美感與永不言棄的意志力詮釋著體育精神。畫家被體育運動中健兒們昂揚積極的精神狀態感染,在畫卷上潑墨揮毫,營造出極具審美情態的視覺空間。將人文精神融入體育運動,以有溫度、有厚度、有深度的繪畫創作完成人文視角下體育精神的藝術化表現,成為藝術作用于體育的絕佳闡釋。體育精神在時代語境下的藝術化表現,以其大眾化、普及化等特性持續引領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參考文獻
[1]張德利.“野蠻其體魄”與“文明其精神”口號的歷史流變、價值斷裂與彌合[J]. 體育與科學,2020(5):81.
[2]胡小明. 論體育與藝術的關系[J]. 體育科學,2008(10):3-5.
[3]沈斌. 中國傳統美術中的體育形式與精神[J]. 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08(04):9-12.
約稿、責編:史春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