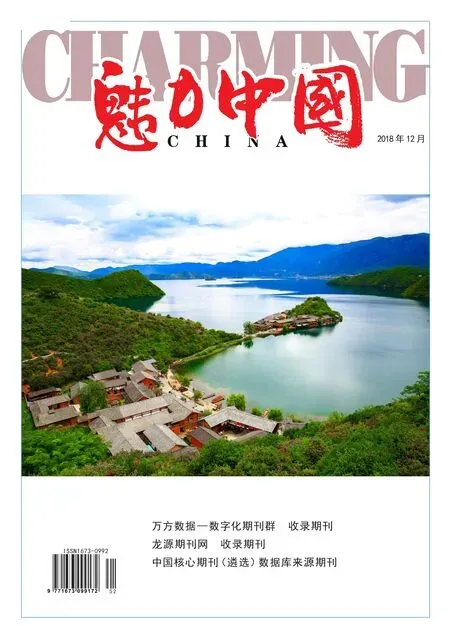芻議小學語文教師課堂教學的五重境界
王旭東
(福建省永泰縣同安中心小學,福建 永泰 350700)
一、借鑒名家授課模式
小學語文教學課堂的第一重境界,是指教師在借鑒名家講課,未能徹底消化其精華,模仿其授課的一種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是由于新晉教師教學時間較短,教學經(jīng)驗不足,未能完全吃透課程教學理論,未能具備獨自設計課堂內(nèi)容的能力。新晉教師為了快速提高自身教學水平,借鑒名家教授的經(jīng)驗,卻未能徹底消化吸收,故而其課堂教學處于第一境界。然而只借鑒名家的教授經(jīng)驗,具有較為成熟的教學模式的同時,卻不可忽視其生搬硬套的弊端。
二、開始建立自己獨立的體系
小學語文教學課堂的第二重境界,是指教師已經(jīng)意識到只借鑒名家授課模式的弊病,并且在教學過程中希望結(jié)合自己的教學體悟,構(gòu)建自己的授課模式,更好地實現(xiàn)教學目標,完成教學過程中的蛻變。在這一教學階段,教師往往已經(jīng)較為熟悉教材,他們對教材開始有自己獨立的體系,進一步結(jié)合自身經(jīng)驗編寫教案。然而,這一階段的教師理解教材未能深入,未能涉及語文教授過程中的核心問題,故而,此時教授重點較為瑣碎、偏頗。
例如:在《觀潮》一文的教案設計中,教師在帶領(lǐng)學生通讀全文后,提出問題,與學生互動:“我發(fā)現(xiàn)課文中許多語句寫得具體形象。例如:‘過了一會兒,響聲越來越大,只見東邊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現(xiàn)了一條白線,人群又沸騰起來。’這些語句描繪了怎樣的潮水景象呢?不妨用自己的話說一說自己見到過的壯麗景觀。”這樣的教學設計明顯偏離了語文課程教學的教學目標,更加重視語文與生活的聯(lián)系,而忽視了語文的功用,即語文是開拓學生眼界,積累詞句,培養(yǎng)閱讀習慣以及能力的一個有效工具。
三、重視語文的功用
小學語文教學課堂的第三重境界,是指教師已經(jīng)意識到語文的功用,并非僅僅局限在將語文與生活相聯(lián)系的這一范圍內(nèi),而是積極發(fā)揮語文的功用,重視語文的實用性。故而在此階段的教師,注重培養(yǎng)學生字詞讀寫、句子分析、篇章的章法的能力。教師更注重語文的實用性,為學生今后閱讀學習奠定基礎(chǔ),但單方面地注重語文的功用,必然產(chǎn)生一定的弊端。
四、語文陶冶情操的作用以及工具性皆備
小學語文教學的第四重境界,是指教師結(jié)合自身豐富的教學經(jīng)驗,借鑒了許多名家的教學經(jīng)驗,兼顧語文陶冶情操以及功用,建立了自己的教學體系,設計出切合學生實際的教學設計的教學階段。在此階段的教師,他們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jīng)驗,漸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理念以及教學特色,教師注重活躍課堂氣氛,在教學中不斷完善教學設計,實現(xiàn)教書育人的目標,讓學生掌握語文基礎(chǔ)知識以及方法技巧的同時,發(fā)揮語文潛移默化的作用,將語文與生活相聯(lián)系,為語文學習注入活力的同時,也為生活指明方向。例如:在《落花生》一文的教授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學習字詞,理解文章的結(jié)構(gòu),并且體悟作者筆下“花生”的獨特品質(zhì),將花生與人的一生相結(jié)合,引導學生對人精深品質(zhì)的思考。以此將語文的功用與其陶冶人心的作用相結(jié)合,完善小學課堂教學,為學生學習以及生活奠定基礎(chǔ)。
然而,此種境界的教學以其引導性太強,而失去了教學最本質(zhì)、自然的東西,故而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弊病。
五、發(fā)揮學生主觀能動性
小學語文教學的第五重境界,是對教師為主體課堂的一種改革,要求建立以學生為主體,重在發(fā)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發(fā)揮教師引導性作用的一種教學模式。這一模式旨在激發(fā)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改善因教師引導過多而將學生至于被動狀態(tài)的現(xiàn)象。例如:《桂林山水》一文的講授過程中,教師可以讓學生熟讀字詞,并且引導學生以教師的角色講授字詞,在此基礎(chǔ)上,教師引導學生交流課文閱讀中遇到的問題,交換意見,拓展思維,以此開拓眼界。這樣既發(fā)揮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又避免了學生盲目學習而效率低下的現(xiàn)象。
六、“閱讀”提供“寫作”技法
“閱讀”提供“寫作”技法,在我國古代的科舉中,文章取仕,大力推崇這類“讀寫結(jié)合”,這成為我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讀經(jīng)是為了寫文章,讀是寫的一種手段。“誦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古代崇尚詩歌寫作的格式和技法。現(xiàn)代教育家丁有寬明確提出“讀寫結(jié)合”的教育思想,一方面進行閱讀教學,一方面進行仿寫訓練。在實踐中,開創(chuàng)了“七條讀寫關(guān)系鏈”。例如,小學語文六年級上冊《小蟲的村落》的小練筆:“豐富的想象使課文中的小甲蟲有情有意,請你寫一寫自己觀察過的小蟲,注意展開想象,融入自己的感受。”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入課文中美好的想象,激發(fā)小學生豐富的想象力,使學生學會運用“想象”這一寫作技法描繪自己所觀察過的事物。
小學生的寫作借鑒運用得好不好,教師的教學形式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教師可以讓學生堅持仿寫,比如仿寫一句話、一段話或一篇文章,使學生熟練運用所學習的各種寫作方法。教師也可以通過讓學生帶著寫作任務去閱讀,在閱讀過程中,全面吸取所需要有利于寫作的各種寫作技法。
以小學語文五年級下冊《橋》為例,教師要指導學生從課文中體會“橋”的引申義和尋找“橋”的表現(xiàn)手法。比如,文中的橋不是生活中的本意“橋”,而是寫黨和群眾之間的連心橋,是生活中的引申“橋”。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寫作時如何擬定作文題目。再如,教師認真分析文中老漢的神情動作細節(jié),引導學生學會“細節(jié)描寫”這一寫作表現(xiàn)手法。
總之,小學語文教學過程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這里將其稱為小學語文教師課堂教學的五重境界,本文就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希望以此為小學語文教學改革提供借鑒。小學語文教學過程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這里將其稱為小學語文教師課堂教學的五重境界。小學語文教學的不斷改革有利于教師充分發(fā)揮其引導作用,學生發(fā)揮其主觀能動性,以此促進語文教學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