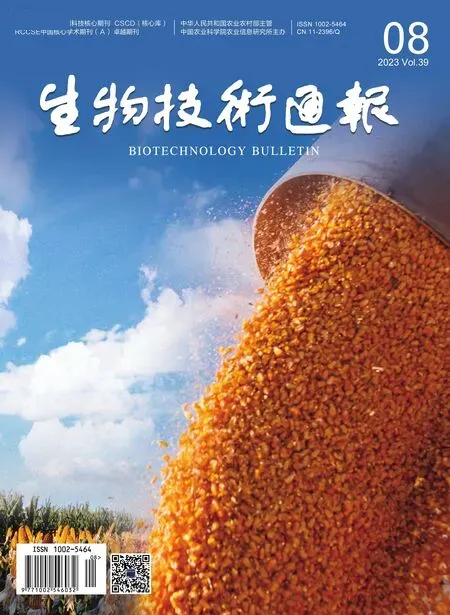微生物強化植物修復鉛污染土壤的機制研究進展
江潤海 姜冉冉 朱城強 侯秀麗
(昆明學院農學與生命科學學院 高原湖泊生態與環境健康云南省高校協同創新中心,昆明 650214)
土壤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當前全球大量土壤受重金屬污染嚴重。由于重金屬的不可降解性、毒性、持久性和在食物鏈中的生物累積性,一旦通過食物鏈進入機體的重金屬含量超出人體可接受的最大容納量時,會引發各種疾病,對肝、腎、神經組織等造成損傷,潛在危害極大。據估計,歐盟有350萬個地點可能受到污染,其中50萬個地點受到高度污染[1]。在美國,約有60萬hm2的土地(尤其是棕地)受到了重金屬污染[2]。2014 年 4 月 17公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3]表明,全國土壤重金屬總體超標率為16.1%,Cd、Hg、As、Cu、Pb、Cr、Zn和Li的超標分別達7.0%、1.6%、2.7%、2.1%、1.5%、1.1%、0.9%和4.8%,其中Pb是五大重點監控重金屬之一,其毒性極強[4-5]。土壤中過量的重金屬元素,對糧食生產和人類健康帶來了潛在威脅,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亟待解決[6-7]。
植物修復是一種綠色環保的重金屬修復技術,在利用植物修復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的同時,對生態環境具有無害和安全的優點。但是在使用植物修復的過程中,污染物容易在植物中儲存和積累,植物受到多種污染物的脅迫使修復效果不明顯[8-11]。因此,研究者提出改變植物根際微生態環境以提高植物修復效率,根際微生物分泌的有機酸可以降低土壤的pH,活化并促進植物對重金屬吸收,微生物分泌物還能與微量元素Cu、Zn、Mn、Co等絡合,提高根際環境中這些元素的生物有效性,同時微生物特殊的細胞結構可以通過吸附、沉淀、絡合等將重金屬固定,降低重金屬對植物的毒害作用。微生物協同植物修復重金屬污染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生物替代方法來修復土壤中的重金屬[12]。但微生物對重金屬的吸附機制和微生物與植物之間對重金屬的修復機理并不明確,本文以Pb為例綜述了微生物吸附重金屬的主要吸附機制和植物根系與微生物系統修復重金屬Pb的機理,旨在為我國修復土壤重金屬污染提供參考。
1 不同微生物對Pb的吸附作用
微生物特殊的細胞結構對重金屬具有吸附作用,微生物吸附重金屬的過程最初發生在與細胞壁表面的結合位點,隨后金屬離子被膜運輸至細胞質[13-15]。具有吸附重金屬能力的微生物主要包括細菌、真菌和藻類等,不同類型的微生物對各種重金屬都表現出良好的生物吸附能力[16-19](表1)。例如枯草芽孢桿菌(Bacillus subtilis)能夠在低溫下去除Pb,而且在弱酸性或近中性污染的土壤中輔助植物修復Pb。Tunali等[22]利用從土壤中分離出的芽孢桿菌(Bacillus sp.),在pH值為3.0、吸附溫度為25.0℃時對Pb2+具有最大吸附量。Kang等[20]從金屬礦山土壤分離出陰溝腸桿菌(Enterobacter cloacae),并利用陰溝腸桿菌的尿素酶活性的生物礦化去除Pb,結果表明,在30℃下培養48.0 h后,Pb的去除率約68.1%。

表1 不同微生物吸附劑對金屬Pb的生物吸附Table 1 Biosorption of metal lead by different microbial adsorbents
真菌對重金屬也具有較強的吸附作用。Akar等[23]研究發現Pb2+積累在灰霉病菌(Botrytis cinerea)表面,當pH值為4.5、接觸時間為1.5 h、接觸溫度為25℃時,Pb2+的含量從350.0 mg/dm3降低到107.1 mg/dm3。Iqbal等[24]用黃孢原毛平革菌(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測試了一種新的生物吸附系統,研究海綿固定化真菌(fungal biomass immobilized within a loofa sponge, FBILS)對重金屬的吸附性能,結果表明,當pH為6.0、吸附時間為60.0 min時,FBILS對Pb的吸收達到最大為135.3 mg/g。Dursun等[25]分析比較了Cu2+、Pb2+和Cr2+的生物富集性,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對3種金屬離子的積累量大小為:Pb2+>Cu2+>Cr6+,表明黑曲霉是一種有效的Pb2+生物吸附劑。
藻類微生物對重金屬的結合能力主要取決于細胞壁的性質[28],其細胞壁幾乎由磺化多糖的纖維素組成,存在大量的氨基、羧基、羥基和羰基等官能團,這些官能團作為金屬離子的結合部位,對金屬離子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15]。不同類型的海藻生物量對Pb2+的吸附量表現的吸附功能存在較大差別:褐藻(Phaeophyta)>綠藻(Chlorophyta)>紅藻(Rhodophyta)[29],褐藻含有豐富的基質、多糖和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因此對于Pb2+具有較強的吸附能力[28]。
2 微生物吸附重金屬Pb的機制
微生物對土壤中重金屬的修復和解毒具有重要作用,微生物修復重金屬Pb的機理和過程主要通過生物吸附進行[30-32]。生物吸附過程指細胞壁與金屬離子相互作用的總和,包括靜電相互作用、離子交換反應、絡合反應、氧化還原反應和沉淀作用[33-37]。
2.1 靜電相互作用
微生物的細胞壁結構成分是生物吸附重金屬的第一道防線,對重金屬吸附起著重要作用。生物吸附是細胞外隔離重金屬以限制其進入細胞而減少毒害的一種途徑。細胞壁表面存在帶負電荷的官能團,如羧基、羥基、氨基、巰基和磷酰基等[36,38-40],這些帶電官能團吸引金屬陽離子,并通過其他驅動力進一步鍵合重金屬。Maldonado等[41]從微生物群中分離出一株細菌菌株(DE2008),研究表明該細菌產生的EPS中含有帶負電荷的糖醛酸和硫酸基團,與重金屬離子發生靜電相互作用,從而有效地吸附Pb2+。官能團的結合還受到反應介質環境制約,環境pH值會對金屬物質和微生物細胞壁官能團的電荷性質產生影響。例如在生物吸附過程中,在較低pH值(1.0-3.0)下,由于-NH2等官能團在細胞表面被質子化,陰離子通常比陽離子更易被吸附,如Pt和Pd在pH值為1.6-1.8更易被吸附,而陽離子則在較高的pH值(3.0-7.0)下易被吸附,如Pb和Cu的最適pH值為5.0,Cd、Zn和Ni在pH值為5.5時最佳[40]。
2.2 離子交換反應
在重金屬脅迫下,微生物通過代謝活動改變代謝產物,增強對重金屬Pb的離子交換作用。由微生物分泌代謝并由細胞裂解產生的高分子量聚合物EPS,具有很高的生物絮凝活性并對微生物細胞具有重要作用[42-43]。EPS由多糖、蛋白質、核酸、腐殖質、脂類和其他低分子成分組成,通常含有5%-25%的糖醛酸殘基,酸性的EPS極易與金屬離子結合[44-47]。在低pH條件下,由于排斥力的作用,細胞壁上的配體被質子化,金屬陽離子不被EPS吸附,隨著pH值的升高,使得EPS中暴露出更多的配體,并攜帶負電荷,從而吸附更多的金屬離子[48-50]。微生物在吸附重金屬的同時伴隨著其他陽離子的釋放,發生離子間的相互交換作用[35-36,51-52]。陳志[53]分別對兩種芽孢桿菌(B. cereus12-2和B. thuringiensis016)細胞在有無Pb2+條件下釋放K+、Na+、Mg2+進行實驗,在無Pb2+條件下,B.cereus12-2和B. thuringiensis016細胞只釋放少量的K+(≤0.3 mmol/L)和Na+(≤0.1 mmol/L);在Pb2+存在條件下,隨著細胞對Pb2+的吸附,B. cereus12-2和B. thuringiensis016細胞釋放的K+逐漸增加,當Pb2+濃度降為0 mg/L時,細胞釋放的K+濃度趨于平衡,Mg2+濃度少量增加,而Na+濃度有所下降,表明兩種芽孢桿菌吸附Pb2+的過程中,K+、Mg2+和Na+可能參與對Pb2+的離子交換或轉運。Qiao等[54]以一株耐鉛細菌枯草芽孢桿菌X3為菌種,制備了一種用于固定化和去除Pb的生物吸附材料,使用EDS圖像分析細胞表面的化學成分,與對照組相比,P、Ca和Pb的百分比增加,而Na的百分比從3.16%下降到1.66%,結果表明Pb、Ca和Na之間存在離子交換,不僅形成了鉛-羥基磷灰石,還形成了Ca3(PO4)2,細胞壁表面的Na+和Ca2+在溶液中與Pb2+交換,證實了離子交換過程發生在礦化之前。
2.3 絡合反應
絡合反應是微生物胞外分泌物和微生物細胞壁上的官能團與金屬間形成絡合物的過程,是生物質表面金屬-配體相互作用吸附重金屬的重要現象。Pb2+通過與細胞表面的羥基、羰基、羧基、胺和磷酸基團等官能團之間的絡合反應,通過配位鍵形成穩定的絡合物[55]。在土壤微生物分泌的大量含羧基的化合物,例如酒石酸、草酸、檸檬酸、蘋果酸等,其在中性pH溶液中帶負電荷,通過靜電相互作用吸引帶正電荷的金屬陽離子形成有機金屬絡合物[51]。通過X射線衍射譜分析發現,蘇云金芽孢桿菌在吸附Pb2+的過程中,與細胞官能團通過絡合反應形成不溶物Pb5(PO4)3、Pb10(PO4)6(OH)2和Pb5(PO4)2Cl[54]。Xing等[56]在研究兩株菌株H13和H16對重金屬的吸附實驗中發現,兩個菌株都能產生胞外多糖,并在金屬脅迫下顯著增加,將有毒的可移動重金屬離子轉化為不可移動的絡合物,可以降低其對細菌的毒性,實現重金屬的固定化,兩株菌株產生的無機不穩定硫化物與二價陽離子重金屬具有極好的結合效率,可與Pb2+絡合形成PbS沉淀。
2.4 氧化還原反應
變價金屬離子被具有還原能力的微生物吸附后,可能發生氧化還原反應[57]。微生物通過氧化還原反應改變或轉化土壤中重金屬的價態,使其毒性降低,或將金屬離子還原或轉化成磷酸鹽、硫化物等形式[58-59]。據報道,微生物分泌代謝的EPS可以將重金屬從高價還原為低價,Pb2+到Pb0,U6+到U4+[60],Cr6+到Cr3+[61],并因其豐富的官能團而吸附在EPS上,重金屬被還原為低價后其毒性相對降低。硫酸鹽還原菌(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 SRB)可通過與游離金屬離子發生氧化反應生成不溶性金屬硫化物沉淀如PbS[62]。Govarthanan等[63]研究發現,從尾礦分離的芽孢桿菌KK1,可通過氧化還原將可溶性Pb轉化為硫化物和碳酸鹽或者硅酸鹽形式,該過程使Pb可交換態降低34.0%,可以對高含量土壤中的Pb起到礦化作用。
2.5 沉淀作用
在微生物修復重金屬過程中,微生物可以將有毒的金屬離子轉化為不溶性的沉淀物,如磷酸鹽、碳酸鹽和硫酸鹽。研究發現,真菌類微生物細胞壁可以充當結合金屬離子的配位體,并且通過主動吸收、胞外和胞內沉淀將重金屬吸附到菌絲體和孢子中從而將重金屬固定在細胞內[14]。海洋細菌哈氏弧菌(Vibrio harveyi)是一種有效的Pb沉淀轉運抑制劑,并且能夠和Pb結合生成Pb9(PO4)6化合物而沉淀Pb[64]。Park等[65]發現土壤微生物分泌物會促進金屬Pb與硫化物、氫氧化物和碳酸鹽形成復合物而有效固定Pb,從而降低了Pb2+的生物有效性。耐金屬Pb的銅綠假單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對Pb2+具有較強的吸附作用,使Pb在菌株中形成生物沉淀固定Pb[66]。金屬雷氏菌(Ralstonia metallidurans)CH34對Pb2+具有吸收、外排和積累的功能,當介質pH值為9.0時,金屬雷爾氏菌CH34與氫氧化物或碳酸鹽反應生成復合物沉淀固定Pb[67]。土壤解磷菌可將土壤中難溶的磷酸鹽轉化成可溶的磷酸根離子,而磷酸根離子又可與土壤中的可交換態Pb2+反應形成穩定的Pb3(PO4)2沉淀,有效降低土壤中可交換態Pb的質量分數,降低了其生物可利用性[68]。
3 植物修復Pb污染過程中微生物緩解Pb對植物毒害的作用
3.1 產生促生因子提高修復植物生物量
植物根系與微生物兩者之間相互協作,可以提高植物生物量和重金屬耐受性,以達到吸收、固定和降低重金屬在土壤中的濃度,減少其毒害作用[69-70]。微生物從植物根系分泌的初級代謝產物和次級代謝產物中獲取所需的營養物質,微生物在感知植物根系釋放的信號后會釋放相關物質并將其轉化成植物所需的營養物質從而對植物的生長和抗性產生影響[71-72]。Akiyama等[73]研究發現,銀杏(Ginkgo biloba)根系分泌的倍半萜內酯類化合物,可以促進叢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us, AMF)孢子萌發以及菌絲分枝的形成,同時使菌根定殖和促進植物根系對營養物質的吸收,提高植物的生長速率。
微生物分泌植物生長激素(吲哚乙酸、赤霉素、細胞分裂素等)促進植物生長,提高植物的生物量和抗性,增強植物對重金屬的富集作用。同時,微生物分泌的鐵載體可與土壤中的Fe3+等金屬離子螯合,促進植物對營養元素的吸收。乙烯可以加速植物的衰老與死亡,微生物分泌的ACC脫氨酶能夠分解乙烯合成前體ACC為α-丁酮酸和氨,從而有效緩解植物體內乙烯的積累,減輕逆境下乙烯對植物的傷害,促進植物的生長和產量的提高,并在促進植物抗鹽堿、干旱及重金屬脅迫等方面都有顯著作用[74-76]。Liu等[77]發現接種葉狀桿菌(Phyllobacterium myrsinacearum strai)RC6b能夠顯著提高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 L.)和東南景天(Sedum alfredii)的生物量,接種RC6b后紫花苜蓿生物量中Pb含量增加了13.8%-24.7%,東南景天生物量中Pb含量增加了18.6%-31.2%,表明接種RC6b顯著提高Pb的吸收和積累。在相同重金屬脅迫條件下,接種耐Pb根際細菌菌株不僅能夠顯著促進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葉片光合作用,還能提高Pb脅迫植株的生物量和對重金屬的抗性,減弱Pb對植株的毒害作用[78]。Shabaan等[79]在土壤Pb濃度分別為250、500和750 mg/kg時,豌豆(Pisum sativum L.)根際接種熒光假單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ce)后,與未接種菌株的對照處理相比,豌豆地上部鮮重增加了51%、45%和35%,根鮮重增加了56%、100%和139%,籽粒鮮重增加了96%、104%和142%,籽粒干重增加了91%、59% 和73%,每盆粒數也分別增加163%、200% 和329%。同時,在相同條件下,土壤中可提取態Pb含量比未接種對照組降低57%、56% 和50%,接種處理后豌豆籽粒中Pb的含量分別比未接種對照組降低57%、55%和 49%。結果表明,豌豆在不同濃度的土壤Pb中表現出了更好的生長和產量。同時,菌株還能夠有效地減少土壤中可提取態的Pb含量,并降低植物體內和籽粒的Pb含量。
3.2 改變土壤中Pb的化學形態降低植物毒害
微生物特殊的細胞結構及其胞外聚合物等,可以將重金屬吸附在細胞表面或積累在細胞中,降低重金屬對植物的毒害作用。一些解磷微生物還能釋放出磷酸酶,將土壤中的難溶性磷酸鹽溶解,溶解后的磷酸鹽與土壤中的Pb發生反應,形成磷酸鉛化合物沉淀,從而有效降低土壤中Pb的有效性[80]。Szuba等[81]在銀灰楊(Populus canescens)上接種適當的耐Pb真菌將Pb2+固定在真菌細胞中,并對寄主植物的生長和Pb的穩定性以及緩解Pb2+植物毒性都具有顯著的影響。李益斌[82]在研究解磷菌對Pb的鈍化效果中,解磷菌存在條件下可以生成Pb(PO3)4Cl沉淀,且該沉淀結構穩定,不再溶解,固定重金屬的同時不僅活化了土壤中的磷酸鹽,促進植物對磷素的吸收。植物根系和微生物分泌的有機酸可以酸化根際土壤環境,與重金屬形成絡合物,改變土壤中重金屬的存在形態,增加其有效性,從而促進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83]。施積炎等[84]研究了海州香薷(Elsholtzia splendens)和鴨跖草(Commelina communis)根分泌物,以及假單胞菌(P. aeruginosa ZD4-3)對污染土壤重金屬活性的影響發現,海州香薷和鴨跖草根分泌物對污染土壤中重金屬有一定的活化能力,假單胞菌對污染土壤中的Pb有很強的活化作用,促進了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量。姚潔等[85]將寡養單胞菌屬(Stenotrophomonas pavanii)分別與袖珍椰子(Chamaedorea elegans Mart)和鳳尾蕨(Pteris cretica L.var. nervosa)構建聯合修復體系發現,接種耐Pb微生物后與對照組相比,袖珍椰子地上部分在Pb2+濃度為2000 mg/L時Pb含量增加了112.61%,鳳尾蕨地下部分在Pb2+濃度為200 mg/L時體內Pb含量增加了113.01%,植物-耐Pb微生物聯合修復Pb污染土壤效果顯著。
3.3 誘導植物抗性系統(ISR)及調控基因表達降低毒害
植物根際促生菌能夠通過誘導植物抗性,上調脅迫響應相關基因表達,調節植物體內過氧化氫酶(CAT)、過氧化物酶(POD)、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多酚氧化酶(PPO)、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SH)和抗壞血酸過氧化物酶(PPO)的活性,使重金屬誘導的氧化壓力下脂質過氧化丙二醛(MDA)的產生減少,降低重金屬脅迫下對植物的毒害作用[86-87]。接種耐Pb微生物后,袖珍椰子的過氧化氫酶(CAT)活性在Pb2+濃度為200 mg/L時達到最大值,為對照組的1.33倍;鳳尾蕨過氧化物酶(POD)活性在Pb2+濃度為400 mg/L時是對照組的2.64倍;袖珍椰子在Pb2+濃度為400 mg/L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是對照組的1.53倍,植物-耐Pb微生物聯合修復增強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及對Pb2+的富集作用,提高了植物抗氧化酶系統的活性,增強了植物對Pb的耐受力。
同時已有研究表明接種植物促生菌能夠調控植物部分基因的表達。研究表明AMF在植物根際定植可以緩解重金屬誘導的壓力,并且對部分植物基因的表達有重大影響,這些基因編碼的蛋白質可能參與重金屬耐受和解毒,目前關于AMF耐重金屬機制分子基礎方面的信息十分有限[88-90]。Ouziad等[91]研究了重金屬脅迫下AMF侵染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的差異基因表達,無論是在重金屬含量特別高的自然土壤上還是添加Cd污染土壤上生長時,接種AMF的植株比未接種AMF的對照,能夠更好地適應環境并生長良好。該實驗被用來分析推測與重金屬耐受性有關的基因的轉錄本形成,通過Northern雜交分析表明,番茄基因Lemt2(編碼不同的金屬硫蛋白)和LeNramp1(編碼廣泛的重金屬轉運蛋白),在沒有AMF侵染植物的所有根組織中都有強烈的表達,而這些基因在AMF侵染的植株根中的薄壁細胞中只有少數被表達,侵染部位明顯降低了該基因的轉錄水平。AMF在根部定植可能將植物細胞中的重金屬濃度降低到不足以誘導這些基因的表達水平。在含有被認為與緩解重金屬脅迫有關的基因中,一些基因在接觸重金屬時強烈表達,并且通過與真菌共生而下調。例如在銅誘導下,共生菌絲體中金屬硫蛋白基因(BeG34)的表達上調,在短時間和長時間的鋅脅迫下,海藻菌絲體中可能存在陽離子擴散促進因子家族(CDF)的鋅轉運蛋白基因(GintZnT1)的轉錄水平增加,這表明該酶可能在保護鋅脅迫中發揮作用[92]。
3.4 根際微生物-植物根系共生系統在修復Pb污染土壤中的作用
微生物-植物根系共生系統是一種修復重金屬的有效手段。一些根際微生物如植物根際促生菌、固氮菌、根瘤菌等具有改善植物營養,促進植物生長、提高植株生物量和降低重金屬對植物的毒害的作用[93]。在重金屬污染的土壤中,微生物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促進植物的生長和土壤修復。豆科植物根瘤中的固氮菌可以增加Pb元素在植物體內的穩定性,從而減少其向地上部分轉移,同時也有助于提高植物發育[94]。AMF與植物形成共生關系后,能夠幫助寄主吸收更多養分,并限制有害金屬向地上部分轉移[95-96]。此外,在保護適當的土壤質地、防止淋溶以及將重金屬轉化為無毒性等方面也起到了積極作用[97]。豆類植物進行土壤修復時還可與根瘤菌形成共生關系來促進氮素經濟和提高土壤肥力以及作物產量[98]。中華根瘤菌(Sinorhizobium meliloti)顯著提高了紫花苜蓿的結瘤效率,并增加了其對重金屬的生物積累能力,從而促進了土地恢復和潛在農業產出[99]。Zhang等[100]在不同濃度Pb污染土壤中種植玉米(Zea mays L.)接種AMF后,通過透射電子顯微鏡觀察菌根后發現Pb主要積累在AMF的菌絲壁、菌絲內室、菌絲內室膜和液泡內室膜中。叢枝菌根固定Pb的能力可以減少Pb從土壤向根系的遷移,從而減輕Pb對玉米的毒性。
由上述可以看出,微生物-植物聯合修復技術對土壤重金屬污染的修復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主要機制作用如圖1所示。

圖1 微生物-植物聯合修復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機制Fig. 1 Mechanism of microbial-plant combined remediation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4 展望
重金屬Pb污染土壤是一種嚴重的環境問題,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危害。傳統的修復方法包括物理、化學和生物等多種手段,但這些方法存在著高昂的成本、副作用大以及效果不穩定等缺點。因此,微生物聯合植物修復Pb污染土壤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而未來微生物聯合植物修復重金屬污染土壤應當著重從以下4個方面開展:一是,深入研究微生物-植物互作機制。目前對于微生物-植物互作機制仍然存在很多未知之處,在深入探索這方面內容時需要綜合運用分子遺傳學、基因組學和代謝組學等現代技術手段。二是,優化菌株篩選。當前已經發現了許多具有降解或吸收能力的菌株,但這些菌株適應性差、活性低下等問題也比較突出。今后需要加強對于優質菌株篩選工作,并針對不同類型污染場地進行相應調整。三是,探索新型修復材料。除了常規使用天然植物外,還可以嘗試引入一些非天然材料如納米材料進行修復工作。同時結合其他治理技術如電動力法和超聲波處理法也值得進一步探討。四是,加強實踐應用。雖然該技術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 但要真正推廣起來仍需更多實踐驗證, 并建立完善評估體系。總之,微生物聯合植被治理重金屬污染具有可持續性、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安全環保等諸多優勢,在未來必將得到更廣泛的推廣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