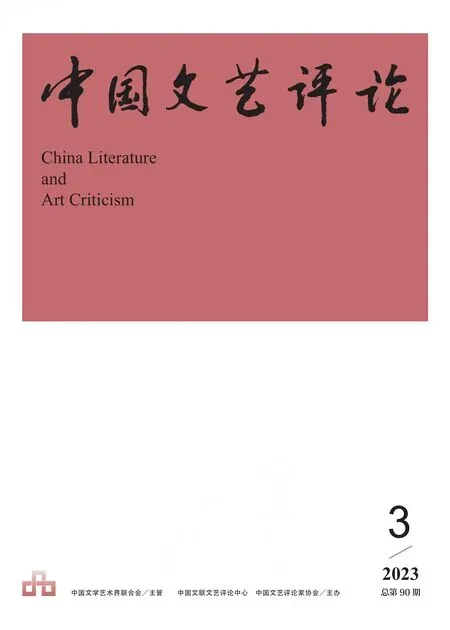音樂材料的非語義性特征研究
■ 許佩暉
音樂和語言,都以聲音為媒介,但音樂更擅長表達情感——豐富、細膩且深刻。法國作曲家、理論家、指揮家萊修埃爾認為:“作為音樂所固有的特點,乃是表達與人心聯系最緊密的感情,音樂能夠表達言語所不能說的。”[1]何乾三選編:《西方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論音樂》,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第116頁。但音樂表達更為開放,也更為抽象,不像語言的表達有明確、具體的含義,音樂本身有一套獨特的表達系統,音樂所能表達的維度比語言更為寬廣。音樂的民族性和歷史性特征又增加了音樂的情感表達的豐富性和分析過程的復雜性。與語言相比,音樂具有明顯的非語義性特征。王次炤教授的《音樂美學基本問題》中“音樂材料的基本屬性”一節從音樂與語言比較的角度論述了“音樂材料非語義性——表情性(與語言音調比較)”[2]參見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39-41頁。這一特征,闡釋了音樂表達的特點。德國音樂學家卡爾?達爾豪斯1979年發表的《音樂如同文本》[3]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2000, pp.388-404.也是在音樂與語言的比較中闡釋音樂文本的特性,進而延伸探討音樂特性及音樂意義。兩位學者涉及相同的問題域,都在音樂與語言的比較中闡釋音樂表達的特征,并提出了如何分析音樂文本的基本思路。二者的觀點,對于深入理解音樂作為文本的重要特性,無疑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梳理兩位學者關于音樂材料和音樂文本的論述,在比較的基礎上進行延伸思考,以聲音作為起點闡釋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以期在音樂實踐和音樂教學中更好地分析音樂文本,實現音樂表達。
一、音樂與語言的比較范式
關于“音樂的文本特性”這一內容,王次炤在《音樂美學基本問題》第三講的第一節提出“音樂的非語義性美學特征”這一論題。首先,文學語言與音樂都使用聲音來表達,但是二者對聲音的使用有重要區別。王次炤援引黑格爾在《美學》中的論證,“詩的聲音‘是含有精神世界的觀念和觀照的明確的內容,是這種內容意義的純外在的符號’;而音樂的聲音是‘直接與內心生活合而為一的’‘保持一種獨立的價值或效力’的媒介物”。[1][德]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出版社,1979年,第一卷第113頁,第三卷(上)第21、340、341頁,轉引自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39頁。簡言之,文學語言更注重表意,或者說表意更為直接有效。而音樂則在表“情”方面更為直擊人心,將人們許多復雜的、矛盾的、不可言說的豐富情感轉化為音樂的語匯表現出來。音樂的聲音成為直接表達感情的音調,不像文學語言成為傳達觀念的符號,而是一種具有獨立價值的材料。
音樂的聲音和語言的聲音在目的和功用方面雖然完全不同,但之所以將音樂與語言做比較研究,是因為兩者有共同的表達因素——表情音調。“語言中的表情音調往往能決定語言的總體含意,而這些音調的變化方式在音樂中也同樣存在”[2]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 40 頁。,這便是音樂與語言二者的相似之處。同樣的一句話,當我們用不同的語氣來傳達時所表達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這一點在漢語中尤為明顯。在一些特殊的場合,語言的聲調甚至可以表達較為復雜的意義,但語言表達主要的還是由詞義、句義來完成的,聲調表達是輔助的手段。而音樂的聲調則是基本的表達方式,而且衍化為音色、旋律、和聲等豐富的表達方式,自始至終都以聲調(聲音)作為直接的表達手段。聲音是作為語義的能指,從而傳達詞義,聲調的表意功能是輔助性的。音樂的聲音是非語義性的,音樂的聲音直接表達內容,無需指稱語義。
“音樂的聲音雖然是非語義性的,但這并不排斥音樂作為一種約定性音響存在的可能性。”[3]同上,第 41 頁。這也是音樂的特點之一。最容易感知的是模仿性的約定,人聲、樂器都可以近似地模仿其他聲音,例如嗩吶作品《百鳥朝鳳》,當人們一聽到作品中大段的、自由而極具表現力的嗩吶華彩時,無論民族、年齡,無論是否受過專業的音樂訓練,聽眾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這是用音樂來表達鳥鳴聲。但作為描繪景物的音樂,需要更多歷史形成的約定因素。當人們聽到捷克作曲家斯美塔納的《沃爾塔瓦河》前奏中旋律化的伴奏在木管組和弦樂組依次出現、交相輝映時,心中也仿佛有一條溪流在山間蜿蜒回轉,奔流不息。這種受民族、歷史、社會長期影響而潛移默化根植于人們心中的“約定俗成”,便是音樂作為一種約定性音響存在的最好體現。
由于音樂聲音表達的約定性關系,音樂材料可以通過模仿、象征、暗示等手法表達豐富的意義,但與語言比較,音樂表達還是非語義性的,所以王次炤在闡釋音樂材料具有非語義性特征的基礎上得出“音樂的聲音是一種表現性的聲音”的結論,并指出這種表現性中“占主導地位的應該是表情性”[1]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49頁。。這是他在《音樂美學基本問題》中指出的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之一。
卡爾?達爾豪斯的文章《音樂如同文本》的出發點是對當時音樂學界關于音樂文本的價值、樂譜文本本體論研究及音樂意義的實現等論題進行回應。文章可以分為五個部分,其核心觀點聚焦于分析音樂文本特性的重要概念,研究音樂的合理方法以及用歷史學、語言學等跨學科方法研究音樂的某些局限。
在前兩部分中,達爾豪斯從闡述、反駁格奧爾吉亞德斯[2]西布羅斯?格奧爾吉亞德斯,希臘裔德國音樂學家。的音樂文本概念入手,論證自己所認可的音樂的文本特性。格奧爾吉亞德斯認為,“樂譜文字并未構成與語言文字同等的現象形式,而僅是一種載體;樂譜未表達一種音樂以外的意義而僅是規定音樂的意義;它僅是音樂的外部客體。”[3]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p.389-390.而達爾豪斯指出,格奧爾吉亞德斯把音樂意義的“非對象性”與樂譜“只是規定而非文本”聯系起來,忽視了樂譜作為客體的“對象性”,并不恰當。隨后,達爾豪斯引用了海德格爾關于“現成在手的”工具與“使用上手的”工具的相關理念,承認樂譜的作用。也就是說“音樂文字是意義的表述,是強調意義的文本,是音樂的具象形式,而不只是演出規定”[4]同上, p.390.。音樂的意義是非對象性的,但是正是由于意義的非對象性,樂譜的對象性才具有開放的狀態,完成的樂譜只有通過鳴響,才能到達音樂的全部現實。而樂譜并非像語言文字一樣僅簡單地通過一種“能指”直達“所指”。在論證樂譜的文本特性的過程中,由于“什么是音樂的意義”這一爭論頗有探討的余地,達爾豪斯折中地提出了一種研究音樂要以音樂表現和音樂邏輯相互結合的方法,認為以此方法才能得出相對全面、真實的音樂意義。音樂表現的因素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是其鳴響著的主體性還是作為音樂形式存在的客體性,這種表現性的意義是必然的。然而,音樂邏輯研究也十分重要。達爾豪斯認為,音樂邏輯是指一種由音樂自身出發的,在作品內部被解讀的和聲—調性、主題—動機的合理性規律及規則。
對音樂邏輯的研究并不只是像研究語言一樣研究句法。語言學中關于語義學、語用學的結論在音樂上是不可行的。自約翰?尼古拉斯?福克爾[1]約翰?尼古拉斯?福克爾(Johann Nikolaus Forkel,1749-1818),德國音樂家、音樂學家與音樂理論家。創構“音樂邏輯”一詞以來,人們對它有著多角度的理解。胡戈?里曼[2]胡 戈?里 曼(Karl Julius Hugo Riemann,1849-1919),德國音樂理論家。認為的那種和聲邏輯研究僅停留在和聲本身,并不能得出調性、主題—動機在實質意義上的深刻結論;音樂邏輯也不僅是在動機關系里,以一種年代學順序展現。在達爾豪斯看來,音樂邏輯應該是二者相結合,從和聲—調性出發,與主題—動機相關聯的一整套作曲內在邏輯。
音樂的表現性是使用音樂的問題,達爾豪斯在文中以葬禮進行曲為例,說明該題材由其外部功能逐漸通過歷史進程而滲透進作品內部這一音樂特性,是完全用語義學、語用學無法得出的,一定要進行音樂邏輯研究。對音樂邏輯的分析引入音樂表現性的維度是十分重要的。在此樂譜中的音樂邏輯,不僅僅是和聲的解決、動機的發展,還要闡釋為什么要如此運用和聲—調性,主題—動機為什么要如此發展。這些都與具體的音樂表現情境相關,而且在不斷重復的表現情境中(歷史進程),某種音樂語匯、旋律、和聲產生了豐富的社會性內涵,各種思想意義和情感意義從而滲透入音樂之中。由此表達的象征意義雖然抽象,但卻比語言表達更豐富、深遠。
隨后達爾豪斯強調,對于音樂表現性的現象學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把現象學事實情況解釋為真實的現實,這在美學話語中完全是錯誤的。相反,顯現的東西在美學對象上才是事實本身”[3]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395.。因此,只有把音樂表現因素與音樂邏輯結合起來分析,才能得出音樂完整的意義。對音樂表現進行現象學研究,實際上就是要在音樂感受中放開感官,排除各種先入為主的觀念與情感偏向,無偏見地感受音樂聲響,讓音樂在聽者的意識中完整地呈現。達爾豪斯在提醒我們高度重視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
在第三部分,達爾豪斯引用了在20世紀60年代由音樂圖像學激起的爭論中所產生的行為文字和結果文字概念,即“行為文字只規定演奏者應做的事;結果文字還嘗試調解音樂本身、音樂客體的概念”[4]同上, p.396.的相關論述。首先,達爾豪斯認為音樂文本特性的條件體現在結果文字而不是行為文字中。其次,音樂不同于語言,語言無需發音即可直達所指。而音樂文字只是一種聲音樂譜而不是意義樂譜,只有介入音樂邏輯的規則,音樂文字的符號特性才能被解讀。這就是達爾豪斯所認為的“理解音樂”,即“僅從摹寫聲音的象征里,解讀出一種未記譜的意義”[1]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397.。
在第四部分,達爾豪斯繼續從“音樂是一種語言”這一廣泛的命題入手。語言作為一種系統的表達方式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索緒爾所分類的語言及言語概念深刻地區分了我們想要研究的事物的“真實性”。在音樂中,由于語言的局限性導致音樂主體構成了一種存在于語言中并受其束縛的特殊“語言”[2]參見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Laaber, 2000, p.399.,因此在談論、研究音樂時,也要注意其歷史上、語言上的雙重特性。達爾豪斯以“諧和音與非諧和音”概念為例討論了這兩點:其一,他指出音樂心理學由于其發展的歷史性逐漸產生了聽覺習慣,這種對理念的更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其二,音樂語言的這種語言學思維,會導致我們有一種音樂邏輯思維上的標準,兩者均為在研究中需要考慮到的,進而通過一種“交織著語言發現的歷史決斷”[3]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401.,構成了音樂事實。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達爾豪斯通過音樂史,及當時學界認為的多維度解讀“音樂作品”概念,詳盡地論述了音樂文本的外延性,開放地看待音樂文本。達爾豪斯對音樂文本特性的分析,正是根據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展開的。如他所說,開放地看待音樂文本,那么我們可以說在音樂表現環節,演唱、演奏者實際上創作了音樂的第二文本,這個文本將第一文本(樂譜)現實化。兩個音樂文本的創造,都根基于音樂材料,是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制約著兩個音樂文本的創作。
二、音樂的文本特性
王次炤的《音樂美學基本問題》第三講以“音樂材料的基本屬性”為題,論述了音樂材料的非自然性、非語義性、非對應性的特征,他提出的“音樂材料屬性”這個論題對理解音樂文本、音樂表現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音樂思考的起點和終點,所有問題我們都必須在音樂材料屬性的基礎上展開。但王次炤對這個論題的闡釋,在論述其非自然性之后,立即將音樂的聲音表達與語言的聲音表達相比較,從而得出音樂材料的非語義性、非對應性特征,將音樂的聲音界定為表現性聲音。[1]參見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48頁。
達爾豪斯同樣在音樂與語言比較的維度上闡釋音樂文本的特性。他并不否認語言文本和音樂文本均有類似的從能指到達所指的指向性。但正是由于音樂的意義“唯獨通過音樂實踐實現”[2]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388.,在媒介這一性質上,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他重點闡釋樂譜作為文本的特殊性,因為音樂的意義是“非對象性”的,作為其載體存在的樂譜文本在客體上又是“對象性”的,它只是一種聲音樂譜,而不是意義樂譜。[3]參見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Laaber, 2000, p.388&397.在這層關系上,兩者的媒介表達作用截然不同。在黑格爾的論證中,他以詩的聲音和音樂的聲音作比較;在達爾豪斯這里,他也認同“比較語言和音樂的美學理論必須由口語或學術語言轉入抒情語言中對比”[4]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388.。抒情語言的那種比喻性的內涵與所指音樂頗為相似,但音樂的歷史變化區別和本體論變化區別的復雜性仍會加深其意義的內涵程度[5]參見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Laaber, 2000, p.388.,以此區分音樂與語言的載體及意義。達爾豪斯強調的音樂文本是一種聲音樂譜而不是意義樂譜,這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引導我們的思路走向另一種音樂文本,即音樂表現過程呈現的聲音文本。樂譜的文字文本與音樂表現的聲音文本,應該是音樂文本兩種不可分割的文本形式。
整體的音樂文本,不管是樂譜還是聲音表現,都表達一定的內容,但音樂文本所表達的內容具有更寬泛、深遠、超越的意義。關于音樂表達內容的特點,王次炤歸納為表情性,但各種聲音所表現的情感并非固定的對應關系,而是約定性的寬泛表達。在闡釋音樂表現內容方面,達爾豪斯要求以音樂的語言性、歷史性綜合看待音樂,“通過一種交織著語言發現的歷史決斷”構成音樂事實。[6]同上, p.401.達爾豪斯的闡釋側重于歷史性視野,在歷史性的音樂表現過程中,社會性的內容進入音樂,從而讓后來的接受者一聽到某種調性、節奏、旋律、和聲就聯想到特定的內容。兩位學者殊途同歸地闡釋了音樂內容的建構與理解特點。
歷史地形成的音樂語匯具有一定的語言性,王次炤認為音樂的表情性與語言的表情音調有著一定程度的類似。“用小提琴柔美的音色來表現愛情的主題”“用沙啞的銅管樂器表現《波西米亞人》中魯道夫聲嘶力竭的呼喊”“用小提琴與大提琴的對答表現《梁山伯與祝英臺》中二人在樓臺相會時的情形”[1]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40-41頁。,這種音樂的表情性內容達到了與語言相似的表情效果。在闡釋音樂語匯方面,達爾豪斯側重于從歷史性中分析外部因素滲透入音樂而導致新音樂語匯的形成。“諧和音與非諧和音”,這個二元對立概念,是外部音樂心理學理論中形成的,隨著音樂活動,而成為音樂概念。而一個音樂概念正是通過類似“聽覺習慣”一樣的由外部考慮的特性而逐漸滲透進作品內部的。實際聲響的“諧和音與非諧和音”在音樂作品中合邏輯地得到應用,被接受者接受。例如,西方大小調體系的 I-IV-V-I 和聲進行,V7的解決帶來這種完滿的終止感,是伴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進入我們的習慣的。這種“語言性”的特征一方面可以說是音樂中的表情內容體現,另一方面也是我們感受音樂的一種局限。
音樂所表現的內容具有約定性的特點,當達爾豪斯引入歷史維度闡釋這個問題后,音樂所表現的內容顯得更為復雜、豐富。音樂作為約定性音響的特征正如達爾豪斯所說的音樂的歷史性因素。“葬禮進行曲的功能性通過歷史過程逐漸作為特性而移入了作品內部”[2]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 Laaber, 2000,p.392.,這種受歷史因素影響的特征作為約定俗成的音樂表現特征流傳了下來。王次炤則揭示了特定情景下的約定性表現,“我國西北地區的某些情歌,用唱不同的歌表達對情人說的不同的話”“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連長用笛聲指揮阿米爾的行動,不同的音樂代表不同的語言信號”[3]王次炤:《音樂美學基本問題》,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41頁。。用鼓傳遞信息,是非洲文明的一大創造。起源于西非部落土著民族的傳統樂器非洲鼓,鼓聲中復雜多變的節奏表達出各種不同的感情。盡管非洲的方言很復雜,但在某種情況下,鼓語卻可以為持不同方言的部落所理解。鼓語又有重音、輕音和聲調之分,重音和重擊的位置不同,其所強調的內容和語氣也不相同。因而,鼓語不僅能夠達意,而且還可以言情。這些例子表現了其約定性特征,其深層的約定性依據,也正是達爾豪斯所說的音樂的歷史性因素。
綜上所述,王次炤與達爾豪斯均在音樂與語言的比較范式中展開論述,王次炤闡釋音樂材料的非語義性與達爾豪斯闡釋音樂文本的特性,有許多相通之處,為我們理解、分析音樂文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與范式。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他們所闡釋的音樂材料、音樂文本特性,都與音樂材料本身的性質相關,但他們囿于音樂與語言比較的論述范式,尚未直接對音樂材料本身做進一步的探討。因此,本文試圖在這個基礎上,從音樂材料本身深入闡釋音樂材料特性,不能僅僅在與語言比較的外部關系中描述音樂材料的特性。
三、音樂的“聲音”本質
我們在音樂教學和音樂研究中體會到,深入理解音樂材料的功能與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對此,我們有必要回顧嵇康的《聲無哀樂論》中的論述,我們不是要加入“聲”是否有哀樂本性的爭論,而是要采取與嵇康相同的討論起點——“聲”。其實那些主張聲音具有哀樂性質的人,他們討論音樂材料的起點是音階、調性、旋律直到完整的樂曲、歌曲作品,而嵇康討論音樂材料的起點是“聲”。自然中某種器具發出的單獨聲響、某個頻率的聲音,在一個曲調中參與表達喜悅的情感,在另一個曲調中可以參與表達悲傷的情感。在中國古漢語中,“聲”指單獨的聲響,其按一定關系構成音調才是“音”,“宮商集比,聲音克諧”“聲比成音”[1][三國魏]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316頁。。也就是說,我們思考音樂材料的特性時,有必要區分單獨的“聲”與形成曲調的“音”,用現代漢語來表達,就是應當區分聲音與音調。
考察音樂材料從“聲”開始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對音樂材料做一個層次分析,應區分為聲與音,“聲”是獨立的聲響包括自然聲響、人聲、樂器聲,“音”包括音階、動機、旋律、和聲、曲式,所有的音樂美學問題都與“聲”的品質、特性有關。人類音樂,產生于從自然當中挑選出來的最和諧的聲音,最和諧的自然泛音成為各種音階的骨干音,從而演變出各種美妙的旋律。演奏家天天練琴,歌唱家天天練聲,為的就是呈現出最佳的聲音。作曲家譜曲,也要根據演奏、演唱者的聲音來創作。從最初的樂音選擇到最終的音樂呈現,都離不開“聲”的品質錘煉。如果說聲音的品質在音樂文本的構成中無關緊要,那么演奏家、歌唱家練基本功就沒有意義了。只有在音樂美學中高度重視“聲”本身的品質問題,我們在教學和創作中對聲音的嚴格要求、刻苦磨煉才具有合理性。
達爾豪斯將樂譜視為文本時,又將這個文本引向音樂表現,在音樂表現中的“聲音文本”概念就呼之欲出了。我們應該使用聲音文本這個概念,在分析音樂文本時引入聲音的維度。在音樂表現中,“聲”的品質對音樂內容的表達具有極大的影響。在中國當代音樂活動中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小澤征爾指揮中央樂團演奏《二泉映月》,這時的《二泉映月》就是一首普通的樂曲,第二天他去聽姜建華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卻被感動得流淚。同一個曲目,用不同的“聲”來呈現,就構成了不同的聲音文本,所表達的內容大不相同。二胡的《二泉映月》與管弦樂的《二泉映月》,由于聲音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聲音文本,體現了以聲音為基礎的音樂材料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在分析音樂文本時,應當高度重視音樂材料的特性,當然必須以聲音為起點思考音樂材料的功能。
達爾豪斯意味深長地指出,要重視音樂表現性的現象學研究,這里也提出關于音樂材料研究的重要問題。首先我們就應該排除各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力求無偏見地感受各種聲音,在聽者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挑選可以使用的聲響,將它們用于音樂創作。在當代音樂創作中,不諧和音(甚至噪音)、非調性、十二音體系等的使用,都基于對“聲”的探索與嘗試,從而在合適的歷史階段進入音樂創作與欣賞活動之中。我們只有突破各種先在概念的束縛,才可能引入新“聲”作為音樂材料,才可能推動音樂的發展。所以,研究音樂材料,必須從“聲”開始。
重視“聲”的品質特性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王次炤所述的音樂材料的非語義性特征,讓音樂材料表達更豐富的內容。音樂作品為了更有效地表達,就要研究聲音對人的影響。在當代社會,不能只憑作曲家想當然地做,可以借助現代科技手段更精細地挑選、組合各種聲音,還可以借助現代科學手段分析各種聲音對人的感受能力的影響,借助社會科學的理論分析歷史性的內容在聲音中的體現,等等。音樂分析也只有從聲音這個層面開始,才能更符合實際地闡釋音樂文本的內容價值。
對音樂文本的分析,也可以更具有實踐性。特別是音樂表現的聲音文本,要構成最美妙的聲音文本,對樂曲中每一個樂音的琢磨都是非常重要的,由盡善盡美的樂音構成的聲音文本,才可能是最感人的。從聲音層面開始的音樂分析,對音樂教學、創作、表現來說,才具有實踐意義,這也正是音樂美學最具特色的地方。音樂美學研究的對象,是最抽象又是最具體的音樂語言。它的抽象性主要體現為表情性、非語義性;音樂語匯的具體性,就在于以聲音為基礎的音樂材料特性。從樂音的選擇到最終作品的完成接受,都離不開聲音。聲無哀樂,卻能演繹出感人至深的音樂,這其中的奧秘令人贊嘆,引人探索。
音樂材料的特性是我們研究音樂無法忽視的一個重要對象,無論是作為聲音的鳴響著的形式,還是以樂譜作為載體的客觀形式,材料始終是探究音樂意義的難題。達爾豪斯把音樂意義的構成定義為音樂邏輯和表現因素相互交替而起的作用[1]參見Carl Dahlhaus.“Musik als Text ”,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10 B?nden, Bd.1, hrsg.von Hermann Danuser in Verbindung mit Hans-Joachim Hinrichsen und Tobias Plebuch, Redaktion: Burkhard Meischein,Laaber, 2000, p.390.,而材料便是構成表現因素的重要手段,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始終存在。在創作的過程中,組織音色、音高、節奏、力度等因素是作曲家的事,這可以還原為以各種方式對聲音及聲音流的設計與塑造。在音樂表現的環節,如何理解作曲家設計的聲音流的意義,從而準確呈現作品內容,是受到語言性與歷史性雙重支配的。樂器聲音、歌唱聲音如何與某種含義相聯系,既有語言的方式,更是歷史地形成的關系。外部的社會、宗教、科技、經濟因素,正是通過對聲音的影響而進入音樂,成為音樂的內容。巴赫的賦格不是憑空出現的,經歷了圣詠、經文歌、文藝復興、中世紀等多樣的音樂變化,才形成了巴赫的多聲部音樂作品。巴赫的音樂語言也是受其文化、習俗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的產物,其語言特性、宗教屬性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最終呈現。只有這樣的音樂分析,才能得出客觀、合理的音樂事實。
結語
音樂材料的特性研究是聚焦于一種研究視野下的產物,而對于其特性的審思,也具有一定的價值。但由于音樂歷史悠久,人們對聲音的感受早已習以為常,理論上思考音樂材料特性時,往往對聲音的重要性重視不夠。但人們在音樂創作和演奏中,卻自然而然地在聲音上面下功夫。所以,我們應該強調音樂材料重要特性的基礎在于聲音的特性,在理論研究中,以聲音為起點闡釋音樂材料的重要特性。或許隨著科技的發展,音樂進入電子技術與人工智能時代,可以合成各種奇特的聲音,可以用AI奏出自然人無法演奏的聲音,那么,以這種方式構成的音樂材料也許將形成不同的特性?這是我們面臨的新挑戰,也是我們應該努力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