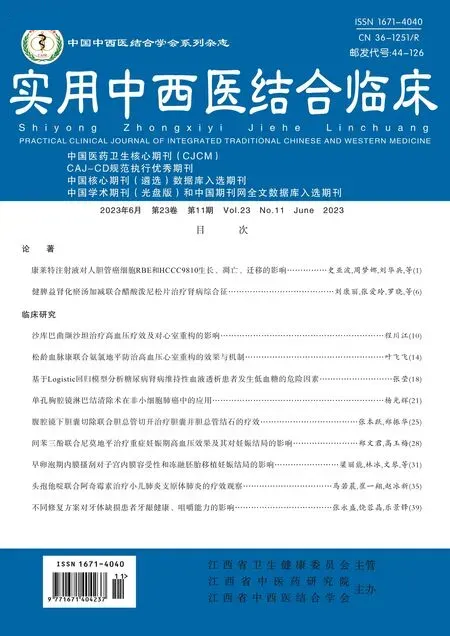加味黃芩湯對晚期乳腺癌患者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的預防效果
周莊 王建榮 王麗虹
(福建省福州市第二醫院設備科 福州 350009)
乳腺癌在我國女性惡性腫瘤中的發病率高居首位,是乳腺上皮細胞在多種致癌因子的作用下,發生增殖失控的現象。乳腺癌早期多無明顯臨床表現,可伴有乳頭溢液、乳房腫塊、乳頭或乳暈異常等局部癥狀,難以引起患者重視[1]。而病情發展至中晚期則會發生乳腺癌細胞遠處轉移,伴有多器官功能病變,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健康。目前,放化療治療是臨床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主要治療方式,其中伊立替康是臨床常用的化療藥物之一,在結直腸癌、乳腺癌、食管癌、肺癌等多種惡性腫瘤中應用廣泛,但該藥物呈劑量限制性毒性,用藥后遲發型腹瀉的發生風險較高,不僅降低患者生存質量,還會對治療的進程造成影響[2~3]。因此,選擇有效的藥物對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進行防治對改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加味黃芩湯是臨床中醫常用方劑,具有清熱止痢、和胃止瀉之效[4]。鑒于此,本探究探討加味黃芩湯對晚期乳腺癌患者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的預防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8 月至2021 年8 月福州市第二醫院收治的82 例晚期乳腺癌化療患者,按簡單隨機化法分為對照組與研究組,各41 例。對照組年齡45~65 歲,平均年齡(53.75±4.72)歲;體質量指數(BMI)20.8~26.5 kg/m2,平均(23.48±1.27)kg/m2;病程3~6 年,平均病程(4.28±0.65)年;病理TNM 分期:Ⅲ期12 例,Ⅳ期29 例。研究組年齡44~66 歲,平均年齡(53.83±1.72)歲;BMI 21.4~27.1 kg/m2,平均(23.60±1.53)kg/m2;病程3~6 年,平均病程(4.34±0.64)年;病理TNM 分期:Ⅲ期10 例,Ⅳ期31 例。兩組一般資料均衡性良好(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批號:福建省福州市第二醫院倫理字2019031 號)。
1.2 診斷標準 西醫符合《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治指南與規范(2019 年版)》[5]中的乳腺癌相關診斷標準,且經病理結果證實為晚期;中醫符合《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6]中的相關標準,證型為氣滯血瘀型,主癥為乳房腫塊疼痛,質地堅硬,經色黯黑,有血塊或痛經;次癥為面色晦暗,胸悶;舌脈癥為舌有瘀點瘀斑,苔微膩,脈澀或弦滑。
1.3 入組標準 (1)納入標準:均符合上述中西醫診斷標準;均簽署知情同意書。(2)排除標準:預計生存期<3 個月;合并其他惡性腫瘤;對本研究藥物過敏;伴有精神或認知功能障礙無法配合治療;近期接受過相關化療治療。
1.4 治療方法 對照組接受常規化療治療。FOLFIRI 化療方案如下:注射用鹽酸伊立替康(國藥準字H20020687)180 mg/m2靜脈滴注,30~90 min;亞葉酸鈣注射液(注冊證號X20000332)400 mg/m2靜脈滴注1 d;氟尿嘧啶注射液(國藥準字H12020959)400 mg/m2靜脈滴注1 d;氟尿嘧啶 2 400 mg/m2靜脈微量泵注持續46 h。14 d 為1 個周期,共治療2 個周期。研究組在上述基礎上給予加味黃芩湯治療。組方:黃芩、黨參、白芍各20 g,生麥芽15 g,姜半夏、炙甘草各10 g,加水煎制300 ml,分早晚兩次服用,1 劑/d,于化療周期后服用,每次服用1周。
1.5 觀察指標 (1)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發生率。參照相關文獻標準[7],評估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的發生情況,1 級表示排便次數與治療前相比增加<4次,排出物量輕度增加;2 級表示日排便量4~6 次,排出物量中度增加,但未對日常生活造成影響;3 級為日排便量≥7 次,或伴有腹部疼痛劇烈或大便失禁,需靜脈補液治療,排出物量重度增加;4 級表示危及生命安全;5 級為死亡。(2)免疫功能。于治療前及治療后收集兩組空腹靜脈血10 ml,以3 000 r/min離心處理(時間為10 min),分離血清置于冷凍環境中待檢。采用流式細胞儀檢測CD3+、CD4+、CD8+水平,并計算CD4+/CD8+。(3)炎癥因子。將剩余空腹靜脈血取出后采用酶聯免疫吸附(ELISA)法檢測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1β(IL-1β)水平,所有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完成。(4)功能狀態評分。于治療前后采用功能狀態評分(KPS)評估健康狀況,量表總分為0~100分,得分越高則表示健康狀況越好。(5)不良反應。統計兩組骨髓抑制、惡心嘔吐、食欲減退等不良反應發生率。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3.0 軟件處理數據。免疫功能、炎癥因子指標及KPS 評分等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及不良反應發生率等計數資料用%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發生率對比 研究組患者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發生率(21.95%)低于對照組(48.7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發生率對比[例(%)]
2.2 兩組免疫功能對比 治療后,研究組CD3+、CD4+、CD4+/CD8+水平均高于對照組,CD8+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前后免疫功能相關指標對比()

表2 兩組治療前后免疫功能相關指標對比()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
?
2.3 兩組炎癥因子對比 治療后,研究組TNF-α、IL-6、IL-1β 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炎癥因子水平對比(ng/L,)

表3 兩組治療前后炎癥因子水平對比(ng/L,)
注:與本組治療前相比,*P<0.05。
?
2.4 兩組功能狀態評分對比 治療后,研究組KPS評分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治療前后KPS 評分對比(分,)

表4 兩組治療前后KPS 評分對比(分,)
?
2.5 兩組不良反應對比 研究組不良反應發生率(4.88%)低于對照組(19.5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不良反應對比[例(%)]
3 討論
伊立替康是臨床治療多種癌癥的一線藥物,該藥物易引發遲發性腹瀉,發生率可高達90%,其原因被認為與腸黏膜功能損傷、基因多態性及酶代謝異常等因素密切相關[8]。目前,臨床針對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的治療主要以控制癥狀發展、加速腸黏膜修復等為主,但由于常規西醫治療多無法預防性給藥,且部分藥物長期使用會引起腹瀉、厭食、惡心等不良反應,臨床應用受限[9~10]。因此,選擇中醫藥辨證治療對減輕西藥毒性、預防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具有重要意義。
中醫學將遲發性腹瀉歸屬為“泄瀉”范疇,認為脾虛濕盛是引起該病的重要因素,故治療應以運脾化濕為主要原則[11]。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發生率(21.95%) 低于對照組(48.78%),不良反應發生率(4.88%)低于對照組(19.51%),提示加味黃芩湯對晚期乳腺癌患者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的預防效果明顯,且安全性較高。分析原因可能是加味黃芩湯是《證治準繩·幼科》中經典名方,由黃芩、黨參、白芍、生麥芽、姜半夏、炙甘草組成,其中黃芩性味苦寒,主行清熱燥濕、瀉火解毒之效;白芍性苦酸,主行養血調經、平抑肝陽之效,兩者共為君藥。姜半夏性辛溫,主行溫中化痰、降逆止嘔之效;黨參性平,可行健脾益肺,養血生津之效,兩者共為臣藥,增君藥之效。生麥芽性甘平,主行消食健胃、疏肝行氣之效;炙甘草味甘,主行補脾和胃、益氣復脈之效,兩者共為佐使,調和諸藥之效。諸藥合用共奏調腸胃、化水濕之功效。
相關文獻表明[12~13],化療藥物可對胃腸道黏膜造成損傷,可引起炎癥因子的異常表達,因此化療后炎癥因子水平均有異常上升,但研究組治療后的炎癥因子水平較對照組低。CD3+、CD4+、CD8+均是人體中重要的免疫細胞,其中CD3+為成熟T 淋巴細胞,可反映人體細胞免疫的功能狀態;CD4+為輔助性T 細胞,對人體免疫反應起到重要調節作用;CD8+為細胞毒性T 細胞,與CD4+起到相互制約作用,兩者比值高低可反映機體平衡狀態[4]。本研究結果亦顯示研究組治療后CD3+、CD4+、CD4+/CD8+水平均高于對照組,CD8+低于對照組,TNF-α、IL-6、IL-1β 水平均低于對照組,KPS 評分高于對照組。提示加味黃芩湯可降低晚期乳腺癌化療患者炎癥因子表達,改善免疫功能,提高健康狀態。分析原因,現代藥理學表明黃芩含有黃酮類化合物,具有抗菌與抗病毒作用,可促進細胞免疫與抗腫瘤。白芍主含單萜類、甾醇類成分,具有抗菌、調節免疫力作用;半夏含有生物堿、氨基酸類物質,能夠抑制胃液分泌、嘔吐中樞,且還有抗癌作用;黨參含甾醇類物質及多種氨基酸及無機元素,可調節胃腸道,增加抵抗力;生麥芽含淀粉酶、轉化糖酶等成分,可促進消化;炙甘草含有甘草苷、甘草酸等成分,可調節胃酸分泌,并對胃黏膜起到保護作用,增強免疫功能[14]。
綜上所述,加味黃芩湯對晚期乳腺癌患者化療所致遲發性腹瀉的預防效果明顯,可改善免疫功能,降低炎癥因子表達,且安全性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