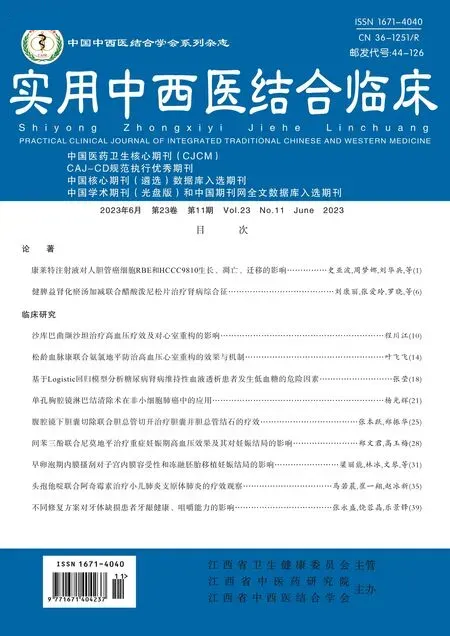局部麻藥注射壓力監測對手外傷患者神經阻滯效果與神經功能障礙的影響*
衣曉卓
(海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麻醉科 海口 570102)
外科手術是臨床治療手外傷的常用手段,而手術麻醉必不可少,其中局部麻醉較全身麻醉的優勢更多,比如圍術期鎮痛效果好、降低阿片類鎮痛藥物用量、縮短麻醉恢復室停留時間及降低術后惡心嘔吐發生率等[1~2]。近年來,隨著超聲可視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加速康復外科(ERAS)的要求,超聲引導下鎖骨上臂叢神經阻滯逐漸被應用于手外傷手術中,其可將局麻藥物精準地注射到目標部位,從而有效提高神經阻滯成功率,縮短麻醉起效時間,降低麻藥用量,神經阻滯效果得到臨床醫師與患者的廣泛認可[3~4]。臨床研究發現,神經阻滯屬于一種有創操作,存在神經損傷的風險,即便麻醉醫師已盡量規避了既往研究證實的與神經阻滯操作有關的神經損傷原因,但神經損傷仍有出現[5~6]。目前,諸多學者認為,超聲可視化技術應用并不能減少神經損傷的發生,而神經阻滯過程中局部麻藥的注射壓力與神經損傷間的關系日益被關注[7~8]。為進一步明確該關系,本研究選取150 例接受超聲引導下鎖骨上臂叢神經阻滯的手外傷手術患者,探討局部麻藥注射壓力監測對其神經阻滯效果、神經功能障礙等方面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1 年1~12 月在海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急診創傷科行手術治療的150 例手外傷患者,按密閉信封法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各75 例。對照組男45 例,女30 例;年齡18~65 歲,平均(43.10±9.55)歲;體質量指數(BMI)18~27 kg/m2,平均(23.10±2.75)kg/m2;受傷原因:機械設備傷35 例,刀具傷30 例,其他10 例;美國麻醉師協會(ASA)分級:Ⅰ級13 例,Ⅱ級37 例,Ⅲ級25 例;麻醉前心率(74.10±7.55)次/min;麻醉前收縮壓(123.28±8.10)mm Hg,舒張壓(83.45±6.07)mm Hg。觀察組男42 例,女33 例;年齡20~62 歲,平均(43.17±8.20)歲;BMI 19~27 kg/m2,平均(23.15±2.30)kg/m2;受傷原因:機械設備傷37 例,刀具傷32例,其他6 例;ASA 分級:Ⅰ級15 例,Ⅱ級36 例,Ⅲ級24 例;麻醉前心率(73.87±6.89)次/min;麻醉前收縮壓(124.75±7.78)mm Hg,舒張壓(83.90±7.25)mm Hg。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受傷原因、ASA 分級及麻醉前心率、血壓等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過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同意[倫理審批號:2021醫院倫審字(00012006)號]。
1.2 入組標準 (1)納入標準:年齡18~65 歲;ASA分級為Ⅰ~Ⅲ級;BMI<28 kg/m2;精神及意識狀態正常,可積極配合研究;心、腦、肝、腎等重要臟器功能正常;知情自愿參與研究。(2)排除標準:超聲下發現頸部結構異常者;合并糖尿病或周圍神經血管病變者;術前患側臂叢部位損傷者;神經阻滯期間出現神經癥狀者;手術或是止血原因造成的臂叢神經損傷者。
1.3 麻醉方法 對所有患者進行超聲引導下鎖骨上臂叢神經阻滯麻醉,對照組在非壓力監測下通過多點法注射0.375%鹽酸羅哌卡因注射液(國藥準字H20163207)20 ml;觀察組在壓力監測下注射0.375%鹽酸羅哌卡因注射液20 ml,即自注藥開始后便關注壓力監測儀表,全程保持注射壓力≤8 psi,直至注藥完畢。監測裝置是psi 單位電子壓力儀表與三通連接管及注射延長管制作而成的簡易壓力監測裝置,在使用前需借助雙儀表法確定三通各輸出口壓力相等,確保三通管和延長連接管腔無菌,在測量前通過三通管向儀表端連接管中注入少量液體,以便于觀察管腔液面的浮動情況。
1.4 觀察指標 (1)神經阻滯起效及完善時間:比較兩組腋神經、肌皮神經、正中神經、橈神經、尺神經阻滯起效時間、完善時間。(2)神經阻滯效果滿意情況:觀察兩組注藥完畢30 min 后腋神經、肌皮神經、正中神經、橈神經、尺神經感覺運動消失情況,據此對兩組神經阻滯效果進行滿意度評估,包括Ⅰ~Ⅳ級,如果神經阻滯范圍完善,且手術無任何痛感評為Ⅰ級;如果神經阻滯范圍欠完善,術中出現輕度疼痛感,但可耐受評為Ⅱ級;如果神經阻滯范圍不完善,術中出現明顯疼痛感,需輔以鎮靜鎮痛類藥物才可完成手術評為Ⅲ級;如果麻醉失敗,改為其他麻醉方式評為Ⅳ級。神經阻滯效果滿意率為Ⅰ級、Ⅱ級患者占比之和。(3)神經損傷癥狀發生情況:術后對兩組患者隨訪48 h,記錄其術后神經損傷癥狀發生情況,包括感覺過敏、感覺遲鈍、輕微疼痛及無力等,及時通過神經電生理檢查了解具體損傷部位和嚴重程度,然后盡早邀請神經內科醫生參與診治工作;對于出現神經損傷癥狀者,術后需每日隨訪,持續監測治療情況,直到癥狀完全消失為止。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 軟件分析處理數據。計量資料(神經阻滯起效及完善時間等)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神經阻滯效果滿意情況、神經損傷癥狀發生情況等)以%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神經阻滯起效及完善時間比較 兩組腋神經、肌皮神經、正中神經、橈神經、尺神經阻滯起效時間、完善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神經阻滯起效及完善時間比較(min,)

表1 兩組神經阻滯起效及完善時間比較(min,)
?
2.2 兩組神經阻滯效果滿意情況比較 兩組神經阻滯效果滿意率均為100.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神經阻滯效果滿意情況比較[例(%)]
2.3 兩組神經損傷癥狀發生情況比較 觀察組神經損傷癥狀發生率為1.33%,低于對照組的10.6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神經損傷癥狀發生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超聲技術的快速發展及超聲可視化技術的應用,外周神經阻滯成功率得到了顯著提升,再加之ERAS 要求的提出,讓外周神經阻滯于臨床麻醉領域中得以廣泛應用。但畢竟該阻滯技術是一種有創性操作,圍術期神經損傷的風險依然存在。臨床研究發現,大部分神經損傷均屬于短暫性且不會引起功能障礙的神經損傷,其發生與神經阻滯操作有著一定關系,通常可于神經阻滯后48 h 開始出現感覺過敏、感覺遲鈍、輕微疼痛及無力等神經損傷癥狀,也有小部分患者會出現延遲性神經損傷癥狀[9]。短暫性神經損傷可導致支配區域的感覺障礙或(和)運動障礙,一般會在2 周內恢復正常,但嚴重性神經軸索損傷或是神經離斷傷會造成無法逆轉的永久性損傷[10]。同時,臨床相關研究已證實,即便應用超聲可視化技術或神經刺激儀,也無法有效避免神經損傷的出現[11~12]。因此,尋找有效措施預防或減少神經損傷癥狀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
臨床研究發現,相比于近端外周神經而言,遠端外周神經中的結締組織含量更高,肌間溝臂叢神經橫截面的纖維結締組織含量僅為30%左右,而腘窩坐骨神經的纖維結締組織含量高達80%左右,可見近端外周神經對于外界刺激的敏感度較高[13]。所以,本研究選取近端外周神經-臂叢神經進行阻滯,該神經可于鎖骨部位形成“干”與“股”,在超聲引導下可清晰顯像,同時具有較為廣泛的神經支配范圍,因此鎖骨上臂叢神經阻滯通常為近年來上肢末端手術的首選麻醉方案。相關研究發現,在臂叢神經阻滯過程中測得局麻藥的注射壓力為8.0 psi 左右[14]。本研究在超聲引導下鎖骨上臂叢神經阻滯中應用恒定濃度與容積的局麻藥,并于注射過程中持續監測、控制注射壓力≤8 psi,結果顯示,兩組腋神經、肌皮神經、正中神經、橈神經、尺神經阻滯起效時間、完善時間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神經阻滯效果滿意率均為100%。這也有效證實了局部麻藥注射壓力監測與控制不會對手外傷患者術中神經阻滯起效及完善時間造成明顯影響,同時也可獲得滿意的神經阻滯效果。
既往研究指出,外周神經阻滯的起始注射壓力與神經損傷存在一定關系,當注射時感覺阻力較大,此時穿刺針可能已處于神經束內,一旦注射將會造成神經軸突損傷,即便穿刺針未接觸到神經,與其相距1 mm 左右,高壓(>25 psi)注射也會造成神經纖維出現機械分離現象,造成炎癥細胞浸潤,所以臨床推薦將注射壓力控制于15 psi 內[15~16]。雖然目前外周神經阻滯局麻藥注射壓力監測技術在臨床上已得到廣泛應用,但對于其壓力范圍的界定還未完全明確。近年來,很多經驗豐富的麻醉醫生常依賴手感來控制注射壓力,但易受主觀判斷的因素所影響,壓力控制效果不穩定,也有通過空氣壓縮原理進行注射壓力監測,但也會受空氣的可移動性所影響。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的注射壓力監測裝置,根據其優缺點制作了簡易壓力監測裝置,在注射過程中持續監測并控制注射壓力≤8 psi,結果顯示,觀察組神經損傷癥狀發生率為1.33%,低于對照組的10.67%,可見注射過程中監測注射壓力并進行低壓注射(≤8 psi)除可獲得滿意的神經阻滯效果外,還可降低神經損傷癥狀的發生率。這主要與穩定的低壓注射(≤8 psi)可有效避免對神經纖維造成機械分離等因素有關。但值得指出的一點是,雖注射壓力監測裝置的應用較為方便,但也會分散操作者的部分注意力,增加神經阻滯的操作難度。從此方面看,無須分散注意力的聽覺或限壓裝置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綜上所述,在手外傷患者術中進行局部麻藥注射壓力監測與控制不僅可確保神經阻滯效果滿意,還有助于減少神經損傷癥狀的發生,降低神經功能障礙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