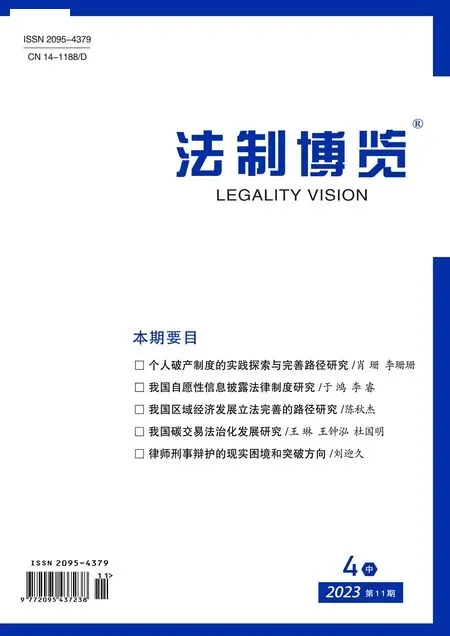刑事從業禁止“從其規定”的司法宣告
劉國平
北京科技大學天津學院,天津 301800
自2015 年8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發布以來,從業禁止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已然經過了“七年之癢”,學界對《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的研究熱情似乎已經消退。然而,實務部門圍繞從業禁止司法適用的困惑和分歧并未減少,尤其是在對從業禁止“從其規定”是否需要司法宣告問題上的理解分歧,造成了一系列“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感受,也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正確理解和依法適用從業禁止的規定,亦是公正司法的題中之義。
一、問題的提出:“從其規定”司法宣告的實務爭議
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刑法從業禁止的適用條件是行為人“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適用標準是“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適用內容是禁止“從事相關職業”,適用期限是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或者假釋之日起三年至五年。第二款規定的是違反從業禁止的法律責任,即由公安機關給予行政處罰或者依照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追究刑事責任。由于在我國法律體系內,還較為廣泛地存在由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從業禁止條款,《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三款特別明確“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其從事相關職業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規定的,從其規定”。該第三款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較大困惑:從業禁止“從其規定”的,是否還需要納入刑事判決進行司法宣告?
(一)刑事裁判立場的分歧
通過檢索裁判文書發現,一審法院對上述問題的理解存在較大分歧,其中部分判決引起了檢察機關的抗訴,而二審、再審法院對該問題所持的立場和理由也不盡相同。
1.將“從其規定”納入司法宣告的立場。在陳某某危險駕駛案中,一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判決禁止陳某某五年內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在劉某某銷售假藥案中,一審法院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判決劉某某終身禁止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在雷某、李某1、李某2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二審法院支持抗訴意見,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改判適用緩刑的李某1、李某2 終身禁止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工作,不得擔任食品安全管理人員。①相關判決的案號依次為:(2017)鄂1125 刑初179 號、(2022)遼0781 刑初154 號、(2020)川11 刑終67 號。
2.不將“從其規定”納入司法宣告的立場。在王某某、李某某、任某某等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從業禁止“應由相關部門作出處理”;在沙某某非法行醫案中,二審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已就醫生行業建立了較為嚴格的職業禁止制度,可滿足預防再犯罪的需要,不應判處從業禁止;在張某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再審法院認為“從其規定”應理解為“應遵循該法律法規中所規定的職業禁止的條件和期限等,不再受該法條中‘三至五年’期限的限制”;在宋某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再審法院以一審檢察院未對宋某某提出適用從業禁止措施的量刑建議,且根據案情沒有必要適用從業禁止為由,駁回抗訴。①相關判決的案號依次為:(2021)魯16 刑終49 號、(2022)遼02 刑終297 號、(2020)魯0811 刑再1-2 號、(2020)京02 刑抗4 號。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
關于“從其規定”是否需要司法宣告的問題,2021 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新修訂的《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時是有所考慮的。根據《〈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文的解讀,最高人民法院總體上傾向于認為刑法從業禁止的規定具有補充性,“由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作出從業禁止處罰即可,《解釋》無需再對從業禁止作出規定,人民法院也無需再作出從業禁止判決”。同時,該文章還表示:“該問題涉及刑法和行政法律的銜接,情況較為復雜,需要進一步總結實踐經驗,統一思想認識。”[1]
然而,在2022 年1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落實從業禁止制度的意見》中,最高人民法院卻采取了相反的態度,規定:“教職員工實施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犯罪的,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二條的規定,判決禁止其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這一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但根據相關部門的權威表態,之所以這么規定,主要是為了未成年人保護增加“隔離帶”和“防火墻”。[2]換言之,是為了切實體現對未成年人的優先、特殊保護。這就使得該意見所確立的司法宣告規則是否具有普適性,又變得模糊不明了。
二、規范理解:刑法從業禁止的雙重屬性
對刑法從業禁止“從其規定”是否需要司法宣告問題的妥善解決,應當回歸到對刑法從業禁止條款本質屬性的把握上來。筆者認為,在我國刑事法律的框架內,刑法從業禁止具有雙重屬性:一是實質上的保安處分屬性,二是形式上的裁判規范屬性。
(一)實質上的保安處分屬性
“保安性措施所指向的對象,就是那些具有較強人身危險性,且可能繼續實施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自然人。”[3]從刑法的條文表述來看,刑法從業禁止正是通過行為人既有的職業性或職務性犯罪事實來確證其具有較強的人身危險性,“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認為其可能繼續危害社會,并進而對其適用的、以禁止從事特定職業為內容的保安處分措施。
然而,保安處分并非刑法所專有的概念,還存在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張明楷教授認為,最廣義上的保安處分包含“對一切被認為有害的人或者物采取的刑事司法和行政處分”。[4]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也指出:“依行政機關所裁決或法院依據法律審判之不同,有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與刑法上保安處分之別。”[5]據此,區分刑法從業禁止和行政法從業禁止的關鍵,不在實質上是否具有保安處分性,而在形式上“依行政機關所裁決或法院依據法律審判之不同”。
(二)形式上的裁判規范屬性
《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并非為社會公眾提供行為指引的行為規范,而是為法官合理處理案件提供依據的裁判規范。刑法從業禁止條款的裁判規范屬性意味著對其適用要經過嚴格的司法審查程序,在適用過程中應盡可能保證各方參與主體的意見表達,并由法官進行最終的考量和擇用,而一旦形成生效判決,即受國家強制力保障落實。在我國刑事法律框架內,具體表現為:其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條,辦案機關可以就從業禁止的適用向司法機關提出意見或建議,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可以就是否宣告從業禁止進行辯護。另外,允許控辯雙方就從業禁止的適用問題提出抗訴或上訴、申訴;其二,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款,判決生效的從業禁止判項具有司法的既判力和權威性,違反從業禁止判項的,會招致進一步的法律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刑法從業禁止的裁判屬性,是其與行政法從業禁止相區分的關鍵。這一區分的核心意義在于:一是與行政法從業禁止適用的行政處罰程序相比,刑法從業禁止適用的是更為嚴格的司法審查程序,對當事人的權利保障更為到位,法官也采取裁量適用的立場,總體上呈現出較為慎重的態度;二是對違反刑法從業禁止裁判的行為,不但可能會承擔行政責任,還可能招致刑事責任,而對違反行政法從業禁止的行為,最多承擔行政責任,甚至是無責任。基于這種差別,那種認為刑法從業禁止僅具有補充性而主張優先適用行政法從業禁止的觀點[6],容易造成法律處置的輕重失衡,是不妥當的。
三、準確適用:“從其規定”的司法宣告及其規則
(一)“從其規定”司法宣告的證成
筆者認為《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三款中的“從其規定”,屬于具有裁判規范屬性的刑法從業禁止,原則上應納入刑事裁判予以宣告。理由如下:
1.基于文義解釋,“從其規定”屬于刑法從業禁止。《刑法》相關的條文表述是:“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對其從事相關職業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規定的,從其規定。”這里第二個“其”字,既指代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應當適用從業禁止的人,也指代第二款“被禁止從事相關職業的人”,三者具有同一性;“對其從事相關職業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規定”指的是對符合條件的人禁止或者限制從事相關職業的具體類型和期限另有規定,并適用主體、適用標準及法律責任都一律“從其規定”。
2.基于體系解釋,認為“從其規定”就只能適用行政法從業禁止的觀點明顯不合理。在行政法律、法規沒有規定的情況下,適用刑法從業禁止,而在行政法律、法規有規定的情況下,卻只能適用行政法從業禁止,會造成明顯的處置失衡。加之考慮,其他法律、行政法規之所以會“另有規定”,往往是因為特定當事人從事某些職業具有較為典型的危險性和禁止必要,這一觀點的不合理性就更加凸顯。
3.基于目的解釋,應對“從其規定”進行司法宣告。刑法從業禁止系基于既有的職業性或職務性犯罪事實,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實際需要而裁量適用的,行政法從業禁止往往是符合一定條件就一律適用,一般不會考慮犯罪預防的必要性,也不允許行政主體裁量適用。二者在適用條件和適用標準上存在較大區別,在適用效果上也存在明顯不同。在刑事案件中,對確有預防再犯必要的被告人采用更為嚴格的刑法從業禁止,給予司法宣告,并適用相對嚴厲的法律責任條款,更有利于對社會的警示教育和對被告人的特別預防。
(二)“從其規定”司法宣告的標準
從業禁止“從其規定”的前提是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即只有“根據犯罪情況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通過個案的具體判斷認為確有必要的,方可適用刑法從業禁止。據此,“從其規定”的司法宣告是屬于裁量宣告,而非必須宣告,對于沒有預防必要或者適用行政法從業禁止即可預防再犯的,不應納入刑事判項。
基于此,行政法中涉及特定職業消極條件的規定,可以不予司法宣告。特定職業消極條件的存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意味著被告人不可能再從事相關職業,也不能再進行相關的職業活動,沒有適用刑法從業禁止予以宣告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剝奪相關資質和禁止從事相關職業活動是不同的概念,通過剝奪相關資質不能杜絕被告人從事相關職業活動的,還是應當進行從業禁止的刑事宣告。如在教師性侵學生的案件中,單純通過行政法剝奪當事人的教師資格并不能杜絕其將來從事教育、培訓活動,有必要對此宣告刑法從業禁止。
(三)“從其規定”司法宣告的規則
1.判項依據。關于刑事判決能否援引“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的問題,學界和實務界都存在較大爭議。筆者認為,《刑法》中“從其規定”條款的存在,即為對法官必須在判決中援引“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授權和要求,否則無法形成依據充足的刑事判項。
2.禁止內容。基于法秩序統一原理,刑法和行政法對再犯危險和預防必要的判斷,原則上應保持一致,故“從其規定”宣告禁止的內容,一般應尊重行政法的表述。然而,刑法從業禁止的適用不能放棄具體判斷、個案裁量的標準,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如果認為行政法規定禁止從業的范圍不足以實現犯罪預防目的的,可以根據需要酌情疊加其他內容的從業禁止宣告。
3.禁止期限。刑法從業禁止“從其規定”司法宣告的禁止期限,原則上也應與行政法從業禁止的期限保持一致,但并不絕對。如果法官認為確實沒有必要按照行政法對被告人宣告終身禁止從業的,可以突破《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在五年以上確定合適的從業禁止期限。